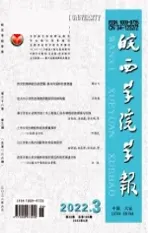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个人情感研究
2014-01-01盛亚军
盛亚军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河南 平顶山467000)
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记录历史时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要求历史学家如实记录,但这个过程仍是主观性的。这项主观性实践活动,表达了历史学家记录历史时的主观情感。考察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有助于分析历史学著作差异性的原因,发掘隐藏在客观史实背后的“记录者”的作用,为历史学的主观性研究提供论据与支持。
一、历史叙述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成果述评
历史叙述不同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可以包括文学、美术、影视等多种手法,历史叙述只是叙述历史时的一种手法。历史叙述专指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自己著述时秉承“实录”“秉笔直书”“求真”等写作原则,这是历史学严格按照历史记录的学科属性决定的。然而,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进行著述的主观实践活动。历史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则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且还带有爱憎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以著作为最终产物的一个主体实践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历史叙述过程图
从图1可知,历史叙述包括“历史学家主观选择史料”和“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2个步骤,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主动性实践过程。在这个模型中,中国古代的私家修史,以及西方史学叙事传统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学家个人感情主导主观选择”这个理论。而对于唐以后的史馆修史、集体修史,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计量史学等则不太适合。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个人撰写的叙事性历史著作。
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发表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研究。一是对历史叙事手法的研究,一般都在考察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如《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1]《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2]等。二是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比较研究,主要是谈区别。如《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3]《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4]等。三是有关历史叙述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5]《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6]等。
从以上成果来看,对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进行分析的较少,仅有陈新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7]一文,着重考察了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论述较少,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较欠缺。总体缺乏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过程前后的情感分析,以及由此构建的理论系统。历史叙述这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思想会不会影响历史的记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又会对历史叙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为何会有不同的情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二、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历史叙述这项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为历史著作。通过研读各种不同历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主体性活动隐藏着不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故从历史著作出发,溯源探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最为科学。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激发写作历史著作
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以客观历史为叙述内容,以读者为叙述对象。虽然历史学家一再强调“良史”,不“隐晦”,但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之前,都有着写作的动因,而这种动因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自己作《史记》的原因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8](P2068)此外,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9](P2490-2491)这种强烈的“意在斯乎”的个人责任意识激发了他写作的意志。
希罗多德称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10](P167)在史学最初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是从个人著史开始的,而历史学家对自己所述历史的个人强烈情感激发了其写作的动力。无论是记载历史的光辉,还是记载历史的阴暗,都是历史学家努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都表达了历史学家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个人情感。
(二)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
历史写作虽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对事实的记叙中,作者到底将史料加工整理成什么样子,与作者自身的史学积淀及个人情感关系密切。史料浩如烟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中,这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研究对象统统塞入他的叙述。无论他试图通观罗马失陷后的西欧,还是简述鲁比肯河渡口的变迁,情况都是如此。确实,在需要选择时,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认为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其中就蕴含着某种价值标准。”[11](P54)
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个人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分。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写道:“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12](P1)吉本想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展现给读者,他说:“我选择了一个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13]推演的目标就是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作者曾游历罗马,看到历史遗址后,难以抑制写作的冲动,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
历史学家选取一定的史料进行加工,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叙述,那么这些史料所推演的结论将是固定的答案。伯克霍福曾说:“如果我们可以询问谁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讲话,或者作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而说话,我们也就可以询问伟大故事是从哪种或谁的视角出发而被讲述的。历史学家必须同小说家一样,也选取一种与声音相伴随的视角。”[14](P256-257)历史学家选取哪些史料,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的叙述也是存在主观性的,即便所述符合客观史实,在叙述哪些内容时,历史学家仍然有着一定的主动性。
(三)历史叙述的主观性表现为对同一史实的不同态度
面对同样的史实,不同的作者在运用中可能表达不同,甚至出现相反的评价与态度。如图2所示。

图2 不同历史学家对同一史实的分析图
以对韩信的评价为例,《史记·淮阴侯列传》末尾对韩信的评价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9](P2038)《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末尾则强调韩信没有忠于刘邦:“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8](P1478)两书中对韩信的不同评价,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司马迁感叹韩信作为英雄的悲情结局,班固则指责韩信作为谋反之臣,应当受到惩罚。司马迁对韩信的态度是同情与惋惜,而班固则是对西汉帝国有着强烈的崇敬之心。
历史学的求真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如实地记录历史。但在记录过程中,历史学家也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会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述。金圣叹曾感叹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情感的表达:“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15](P526)在情感表达上,历史著作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这与文学著作有着一致性。历史著作中,史料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承载着作者要向世人展现的历史。
三、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表达个人情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历史分为客观和主观2个层面:“在我们德国语言文字里,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那个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16](P101)个人情感归属于历史学家的主观层面,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现实生活
除了官修史学之外,一直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个人写作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个人著史是一种顺应时代的现象。如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存在投降与抗战2种声音。范文澜感觉到现实缺乏抗战英雄,为了激励民众,写就了《大丈夫》一书,专门选取了从西汉到明代的25位古代“大丈夫”的英雄形象,“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17](P1)
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与现实隔绝。历史学是以过去为研究中心的学科,又只能如实记录,不能随意编造与杜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亲情、友情、爱情等现实情感与体悟。写作历史著作是个体参与的主体性实践活动,编史必然会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陈新曾提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实践的途径,主观性参与其中的运作,自然而然,在历史叙述的产物即历史文本中,就会映照出一行行主观性的足迹。”[18](P187)这种主观性的足迹,尤其是在现实社会出现大变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明史》的修撰、《清史稿》的编纂,都是在前朝灭亡后,一批文人(遗老)通过修史来寄托哀思、表达对前朝的依恋。如有外敌入侵时,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历史上抗击外敌的史实来鼓舞抗战斗志,如《大丈夫》的编纂。如政治清平时期,大臣往往通过编修史书来警示执政者。如吴兢的《贞观政要》、司马光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反映了其价值观念
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是其价值观的生动表现,无论是喜爱、憎恨,还是惋惜、崇拜之情。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前,已经有了“模式”:“史学家通过确认支配着一组事件的规律‘说明’历史领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作为一种基本上是悲剧含义的戏剧被情节化了。或者,反之亦然,在他找到支配着情节关联次序的‘规律’时,他也可以发现自己加以情节化的故事的悲剧含义。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特定历史论证的道德蕴含,它出自史学家假定的关系。”[19](P34)因此,在面对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时,历史学家大胆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推测历史的空白,直接将历史人物的对话生动地写了出来。
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与情感认定。毛曦认为,历史认识活动受“生理条件和认识环境的影响”,以及“情感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的影响。”[20](P71-73)应该说,在历史叙述中也存在客观和主观2个方面的要素,尤其是历史叙述更倾向于将个人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获得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那些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叙述的立场、对历史事件的感慨都属于主观层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事实是固定的,历史学家则存在个体差异。在历史事实向历史著作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起着核心作用,其个人情感认定往往让读者受到教育,读者与历史学家在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共鸣。
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来选取史料,进而通过史料来教育读者。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制》中曾谈到历史的作用:“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21](P303)无论是“自省”,还是“劝善惩恶”,都是历史学家价值观的体现。记叙“乱臣贼子”警示后人,必然记载其惨痛下场。记叙忠臣的光辉,无一例外地记载忠臣死后受到后人的敬重。记述朝代的更迭,都在有意识地对比前后朝代之间的差异;记述某朝代的强盛,无一例外地强调君主励精图治。
(三)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却是有情的
时间、空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历史事实的唯一性。后人在面对历史时,因为不是当事人,常常不断地追求真相,却只能越来越接近真相。历史都是远离现实的,人在回顾历史时,难以置身其中,只能靠着情感去接近真相。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却又常常心存历史的假设,这就是对历史事实无奈之情的明显表现。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一维性,让历史学家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于是在处理史料时,就有了文学与历史2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如图3所示。

图3 对客观史实的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方式图
对客观史实的不同表达方式造成了文学和历史2种学科不同的叙述原则。在此,本文不探讨2者之间的差异,而是着重强调历史著作也存在主观性。李大钊曾提出在情感方面历史和文学的作用有着相同之处:“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机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激动了,不由自主地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22](P166)
面对相同的历史,在文学叙述和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人们都是对客观历史表达无奈,发出叹息。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末尾感叹道:“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9](P239)司马迁对“霸王”的功绩由衷地赞叹,也对“霸王”的悲剧有着无限的感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司马迁认为项羽败于“以力征经营天下”,且“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这个总结可谓客观。后代文人在叙述项羽失败时,则不再受史实的约束,大胆地创作。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23](P129)以及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24](P289)2者截然相反的个人情感表达,均不再受史实的约束,主观大胆地假设结局。总之,无论哪种叙述手法,都是表达了对历史的无奈之情。
四、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作用
历史学家通过记述客观史实,而将思想与情感融入其中,最终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过程中受到教育,这就是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基本过程。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出发,逐步推演到读者接受,看看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
(一)会影响主体对史料的选择
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往往都是在内心先有想法,然后才开始搜集资料。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选题,选题往往有现实意义,并且还需要有写作的现实基础(资料丰富、时间宽裕、经济基础)。选题的现实意义,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就是时代背景。如范文澜曾在1944年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曾回忆说:“《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则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25](P4)为了更好地说明曾国藩的刽子手面目,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曾国藩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范文澜撰写这部书时的史料明显有所选择,侧重于其勾结洋人剿杀农民起义的内容。
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主要通过史实来表达。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历史学家会有意地精心选择史料,让读者看到的是史实,接受的却是历史学家的情感。米塞斯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不断变化的、不同的:“价值之一切判断系个人的及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外宣称我偏好、我较欢喜、我心愿。任何人亦无法否认,各人的感情、趣味,及偏好都大有差别,而甚至本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的事物,亦有不同的评价方式。”[26](P15-16)基于史实进行的价值判断,自然也随着主体、时间、角度的不同而迥异。如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存在着文革前后2种不同评价的现象,评价的不同正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政治背景有关。因此,不同的价值判断正是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历史学家置身于现实时代之中,自然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
(二)进一步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历史学从出现至今一直保持着实证的传统,即要求历史叙述严格遵循客观史实。通过寻找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工作追求、价值取向。然而,仅靠部分史料推断的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能否经历时间的考验?在此,笔者不论述真相的真伪度,主要是要分析历史学家所发现的“真相”已经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陈新提出:“历史叙述者不可能在他的叙述中避免做出历史评价,因为,即使他想拒绝自己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进入文本,这种拒绝本身也需要理由,它是建立在某个立场的基础之上的。”[18](P198)这种主观性是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因为历史学家所述对象往往距离自己较为久远,基于一部分资料之上的历史结论总会受到各种其他资料的冲击与质疑。即使是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也仅是从个体出发,并不能将事件参与者(他人)的状况完全说清楚,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历史疑案、历史反思与历史再现。
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呢?托波尔斯基曾分析道:“历史的(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是建立在历史学家进行科学地再现过去时对资料源和非资料源材料的运用的基础之上的。但那种再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那儿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学家即使仅仅就其非资料源知识而言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学家是通过构筑历史事实来再现过去的,但从某一种观点来看,他又是历史事实的‘创造者’。”[27](P222)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面对多种声音时必须要选择其一。如历史上关于曹操和魏延的评价一直没有结论。这主要是围绕着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魏延是否谋反展开的。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有“替魏武帝辩诬”和“替魏延辩诬”2章。但自《三国志》以来,历史学家大多沿用曹操是奸雄、魏延曾谋反的结论。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历史叙述中将疑问留给读者,只能是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并按照此说法填充史料。由此,许多历史学家沿用成说,最终进一步强化前人的结论,就出现了人云亦云的情形。
(三)最终影响读者对史实的接受
读者接受的史实大多来源于历史叙述。广大的读者在接受史实前,一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与判断能力。利科曾说:“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期待某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28](P4)读者与历史学家的交流是依靠历史叙述作为媒介的。情感在交流中属于传递的内容,也就是信息。如图4所示。

图4 历史学家、历史叙述、读者之间的情感传递图
历史学家依靠历史叙述与读者交流思想。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隐藏的情感凝聚到历史著作之中,间接地传递给读者,这是一个主体参与的传播过程。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后,逐渐分辨美丑、善恶,以反省自我、辨别是非。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9](P2493-2494)遭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将情感凝聚于《史记》之中,“思来者”正是为了将情感传递给后来人(读者)。再如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对宋文帝说:“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29](P1083)“鉴远”“贻诲来世”都是裴松之作注时个人情感的写照。
综上所述,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各种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是主观行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个人情感的载体,各种不同的历史叙述代表着历史学家不同的个人情感。读者通过阅读历史著作,最终领悟历史学家所要传达的个人情感。
[1]蔡宝玺.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4):35-38.
[2]姬春晖.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79-82.
[3]陈新,江睿杰.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J].江海学刊,2011(5):154-161.
[4]白春苏.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论海登怀特历史哲学之维度[J].西部学刊,2014(6):9-12,21.
[5]韩震.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J].山东社会科学,2001(6):57-60.
[6]易兰.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2):15-18.
[7]陈新.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J].史学理论研究,2001(2):24-35.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希罗多德.历史[M].王嘉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美)威廉·德雷.历史哲学[M].王炜,尚新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2](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8.
[13](英)爱德华·吉本.吉本自传[M].戴子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4](美)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M].邢立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5]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3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16]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17]范文澜.大丈夫·凡例[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18]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9](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0]毛曦.试论历史认识中的情感因素[J].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5(3):71-73.
[21]刘知幾.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2]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3]杜牧.杜牧诗文选译[M].吴鸥,译,注.成都:巴蜀书社,1991.
[24]王安石.王安石诗文选注[M].王安石诗文注释组,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
[25]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6](奥)米塞斯.理论与历史[M].淦克超,译.台北: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73.
[27](波)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M].张家哲,王寅,尤天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8](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M].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9]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