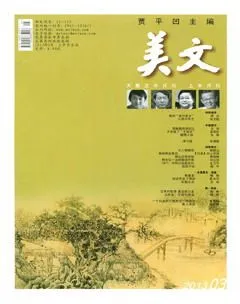1977,天际泛起鱼肚白
2013-12-29王力平
过了五十岁,对许多事情的理解变得越来越犹豫了。有人说早晨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历史从远古走来,遵循着发展规律义无反顾地奔向未来;也有人说早晨的太阳其实就是昨晚落下的那一个,日子就是年复一年的春秋寒暑,日复一日的昼夜更替。你相信哪一个?
但有一件事无需犹豫。1977年,在我的生命世界里,天际泛起了鱼肚白。
1976年春,我把行李搬上一辆卡车,在送行的锣鼓声中,一路颠簸着去插队了,目的地是河北赵县谢庄公社小东平大队。这一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渐近尾声,“扎根农村干革命”“消灭三大差别”的浪漫主义激情渐渐消退,代之以激情消退后的幻灭和茫然。
幻灭年代,人的现实和精神的困境是多重的。拿我自己来说,最直接的困境是待业。当年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记得课本上讲过“历史发展规律”,是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产业后备军。照这样说,应该是“不在乡下吃闲饭”才对。但流行观念所至,摧枯拉朽,不容置疑。我也真诚地认为,在城里待业是一件很丢人、很没面子的事情。不过,这种困境是浅层的、可以言说的,深层的困境是难以言说、不可告人的。那就是,“扎根农村”,非吾所愿。其实,虽然大家敲锣打鼓地插队去了,但尽早选调回城,差不多是每个人心里默默打着的小算盘。但这还不是最愁人的,更愁人的是,我从内心深处没把选调回城看作是从困境中解脱。在我看来,早晨带个饭盒上班,晚上拿着空饭盒回家,这和吃了饭扛着锄头下地,该吃饭了拖着锄头收工没什么差别。只是这种更深的困境,且不说可不可以告人,我甚至无法对自己说。
1977年暑热季节的一场暴雨中,我独自枯坐农舍,度过了我的19岁生日。那天凑成一首五言排律,结句是:“水深劈波苦,山高拓路难。涛头一叶舟,何处点篙竿?”
1977年10月2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考的通知。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儿。
多年以后回望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次转折是民心所向,国运所系,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但在1977年10月那个秋风飒飒的晚上,除去兴奋、憧憬和将信将疑,又有谁为这次转折做好了思想和物质准备呢?
1977年的高考,没有参考资料,没有辅导班,没有模拟考试。能够帮助复习的,只有几本卷角缺页的中学课本,像是我残缺的中学时代的象征;一份河北省普通高校1977年高考复习大纲,虽然只是一本简陋的骑马钉白皮小册子,却是第一次让那个飘忽的大学梦想变得可以触摸;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和我同在小东平插队的孙建新,一个是小东平的“土著”范瑞忠。
丑训叔是小队会计,知道我要参加高考,送给我两本书:上海科技出版社1957年10月出版的《自学几何的钥匙》,《自学三角的钥匙》。这两把“钥匙”并没有打开我脑子里那把生锈的“数学”锁,但这两本书至今藏在我的书柜里。小册子很薄、很轻,但情义很厚、很重。
考试定在12月15日、16日,复习时间不足两个月。好在秋收忙过了,大队、小队干部都是厚道人,我不再出工,把自己关在屋里“脱产”复习。
复习一开始就是冲刺,自然少不了夜以继日,点灯熬油。我的桌上(准确地说,是我的坐柜上)点着两盏油灯,两盏油灯烧的是柴油。说实话,柴油都是生产队的,大队电工俊、小队机手中华、小刚、甚至生产队长中友都给我弄过柴油。只是柴油点灯烟大,鼻孔总是熏得黢黑。
复习之道,无非是多读多写,这需要很多纸。我用的纸是从大队梨库“淘换”来的,是“天津鸭梨”包装纸。包装纸是正方形的,正面印着 “天津鸭梨”四个浅绿色的楷书字,还有两个淡黄色的鸭梨。背面不妨碍写字,只是稍嫌粗糙些。
12月15日,天还没亮就起床了,胡乱吃几口昨晚的剩饭,便和建新、瑞忠一起匆匆上路了。考场在范庄,离小东平村还有七八里的路要走。书包里揣了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下午还有一场考试,来不及回来吃午饭了。
赶到范庄学校,教室门还没开。看着考场门前熙熙攘攘的考生,我对建新兄说:“要想上大学,眼前这些都得灭掉。”建新兄笑了笑说:“横扫千军如卷席。”
经历了初选之后的漫长等待,我接到了河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建新和瑞忠则双双折戟于初选后的等待中。那一年,全国570万人参加高考,只有大约27.3万人走进了大学校门,录取率不足5%。
当我准备写这篇短文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把“鱼肚白”三个字写到文章标题里。因为在转弯处,历史的天空远远不是晴空万里,霞光万丈。
有两件事,至今想起依然是有趣的。
77级新生入学是在78年春天,入学几个月后,到了麦收季节。今天,也许农学院除外,莘莘学子的大学生活,不会和“麦收”有什么牵扯。但在1978年之前的十年间,按照“五七指示”的要求,学校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显然,在恢复高考,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978年,“学农”这件事变得有些尴尬了。我不知道当时的校系领导是觉得理当如此,还是颇费了一番斟酌,我经历的是,1978年麦收时,我们被安排去学校东邻的金庄参加麦收劳动。
“学农”通常会安排在“三夏”期间,因为这时农村劳动力相对紧缺。不过,学生成群结队地涌入麦田,收割工具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所谓“学农”,只能是拔麦子或者捡麦穗。捡麦穗通常是小学生的事,大学生应该拔麦子。但拔麦子是要做些准备的,须在前一两天将麦田洇湿,否则,旱地拔麦,事倍功半。在金庄,我们遇到的恰恰就是事倍功半的旱地拔麦,或者像小学生一样去捡麦穗。
其实,单就干农活儿而言,77级同学中间不乏全套的庄稼把式。我自己学艺不精,经历两年插队生活,割麦子这件事还是不憷头的。事实上,很多同学没有蹲在地上捡麦穗,而是接过了老乡手里的镰刀,跨开步子弯下腰,一看就知道是行家。
提起这件事情,不是要指责它劳民伤财,也不想借此讨论什么是大学精神,只是就事论事,这种在学校围墙外面捡捡麦穗的安排,与其说是“学农”,不如说是在糊弄自己捎带着糊弄别人。事实是,对“学农”这件事儿,一半是不想做,一半是不敢不做。后来读到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其中有“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很像是母校1978年的“学农”安排。
另一件事,异曲同工。
77级入学不久,交谊舞“风起青萍之末”,一时间,“嘭嚓嚓”成了青春的节奏和旋律。终于,素有“老夫子”之称的中文系也要筹办舞会了。
筹办舞会,要从学跳舞、教跳舞开始。要有场地,有音乐,有教跳舞的人,有学跳舞的人。为此事操心出力最多的是白贵。多年以后,白贵是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组织和教学能力的养成,当始于筹办中文系第一场舞会。
我自己完全没有乐感,身体协调能力很差,仅凭着年轻时缺乏自知之明,也曾跻身于学跳舞的行列。舞会如期举办,说“盛大”或许夸张,说“热烈”绝不过分。但在舞会之后,我听说系总支领导找白贵谈话了。详情无从得知,大概意思是说舞会办得不错,但下不为例。我不是班级活跃分子,我能听到的新闻,必是人人皆知的旧闻。诚如这位领导所言,这是河北大学中文系77级的第一场舞会。
在人们印象中,改革开放,除旧布新,必是摧枯拉朽,必是“日日新,又日新”。其实不然,破冰之初,举步维艰。思想的僵化,不只源于外力的禁锢,更多是因为内心的因循。还是那句话,转弯处,历史的天空远远不是晴空万里,霞光万丈。
77级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节点上,他们背负过去,面向未来;既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又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
因为站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节点上,因而“质疑”就成了77级最重要的精神品质。我保留着一本由河北大学教务处编选的《河北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选》,其中收录了白贵的毕业论文《司空图美学思想概观》,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以往的唐代诗歌研究中,一般都较多地肯定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创作,因而对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司空图等一批并未表现出许多积极社会思想意义的作家,却持较多的批判态度……一提唐代文学,便对前者推崇备至,无论对其创作还是理论都完全点头赞同,而对后者,至多肯定其创作中一些艺术性较高的,颇有影响的作品,而对理论则几乎是持完全的否定态度……这实际上反映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种并不少见的形而上学观念。”在今天,客观地看待文学史上不同的美学风格,无疑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在77级开始学习和研究文学史的时候,坚持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需要质疑僵化的思想观念,需要冲破极左思潮设置的学术禁区。
和同学俊彦相比,我是愚钝的,只是读了几本书之后,对文学理论发生了兴趣。兴之所至,就把当时不多的几本文学概论都找来一一读过,竟也读出些疑问。其中一个疑问是,所有的文学概论都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它们对“反映”的理解,却是无一例外地简单和粗暴。蔡仪是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他在自己主编的《文学概论》中说:“这些作品直接写的就是社会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解说虽然简捷通俗,但问题是“描写”等于“反映”吗?这在表面上是概念和逻辑问题,内里其实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思想被简单化的问题。后来,我把这个质疑写进了我的一篇论文,题为《反映论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
当然,并非只有质疑。对于未来,77级有坚定的信念和灿烂的梦想。我的书柜里有一本名为《苏醒》的油印诗集,诗集收录了河北大学中文系77级9位同学的32首诗,其中一首题为《我只有梦》:
@ 你知道吗
@ 我只有梦
@ 我飞奔在三千米跑道上
@ 起点——是梦
@ 终点——是梦
@ 我好像和梦竞赛
@ 眼前——是梦
@ 身后——也是梦
@ 我只有梦
@ 梦里有村头的柳笛吹起
@ 一只带风轮的风筝
@ 白鸽,衔着哨音
@ 飞走了,带去一天彩云
@ 我只有梦
@ 壮观的泥石流,后面跟着严冬
@ 封锁了池塘,一条小鱼
@ 嵌在贴着泥土的冰层
@ 太阳,带来春天
@ 晒化了梦和寒冰
@ 我只有梦
@ 梦中有浩瀚的海
@ 秋水一样的眼睛
@ 梦里有湛蓝的天
@ 彩虹搭成的凯旋门
@ 我把所有的笑和花束
@ 撒向林立的烟囱
@ 田野中绿色的田埂
@ 你知道吗
@ 我只有梦。
@ ……
诗作者是何振虎。多年以后,他已经是河北省广电局副局长。一路走来,当年的那些梦,圆了多少?碎了多少?又有多少新的梦想生长着,飞翔着……
王力平
1958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84年调河北省文联《文论报》编辑部任文学理论编辑,现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