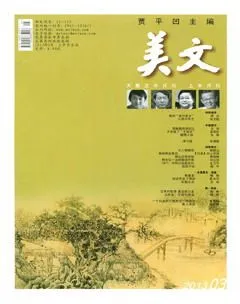大历史、个性与命运
2013-12-29杨辉
设若个人可以被视为类如词语一般的符号,其所置身的社会足可以成为此一符号意义得以生成的结构。结构有相对的稳定性,有大小、层次之分,有它自身的运作模式——由此而衍生出特定的赞成与反对,规约着一代人一时期的怕和爱。在这里,个人的才情发挥、生命舒展甚或彪炳史册垂范后世,总脱不掉结构的成就。当然,更多的时候,结构还呈现为一种限制,一种为了其自身运作的合理性而强行规训和压抑的力量。柏拉图深谙此道,他的理想国中并无诗人的容身之地。
所幸结构并非固步自封、始终如一,它会转换,会调适,会应时而动,会重新组织。与此同时,个人的命运遭际也会随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会出现“晓看红湿处”的绝妙胜景。
因此上,兴衰际遇、荣辱进退,于个人而言,自主的成分或许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若要看得清,须得放宽历史的视界。是为大历史观题中应有之意。
在去国二十多年间,本文作者对关渭城个人遭际的异乎寻常的关切,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的个性和命运的关系”的反思,恰可作为以上说法的注脚。
关渭城如果“早生20年,赶上毛泽东热烈赞扬的农民运动,能当威震四乡的农会主席……”如果解放后从政,以其过人的精力和野心,想必也会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如果他生在彼时的香港,崇尚个性,鼓励自由竞争的风气也断然不会使得他成为“不打白不打的落水狗”。如果他出洋谋生,或许也能成就一番功业……若非有刑满释放后精力、斗志与计谋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所成就的令众人艳羡不已的功业。关渭城的一生,不惟可以用来诠释“色空”,还要让人生出造物弄人的喟叹。至于那个让他沦为“落水狗”,从而身陷囹圄的作风事件,因办案过程漏洞甚多,且与其时的政治行为颇多勾连,原本就在许与不许之间。但个人生命本能释放方式的不合时宜,总难免遭人诟病,这一点,就不单是本能压抑的时代问题了。
但这个并不那么完美的人身上有着发自生命本能的无与伦比的精力,他的身先士卒、奖罚分明、干练明快和讲究实效,在那个虚浮的世风中独标清高,无一不在说明着未被知识分子的风花雪月的小资情怀驯顺的肉体蓬勃的生命力。他虽无法与作者心仪的英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比,但在那个世俗英雄缺席的时代,已足以成为众人崇敬的对象。这种崇敬的发生,除了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之外,或还有着对未被归化不曾驯顺葆有人的生命的鲜活力量的个人形象的精神期许。时代的精神结构原本应该为个人提供生命本能升华的可能性,惜乎其时,这还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
小到在乡村拔河比赛中以假情报取胜的花招,大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捞个盆满钵满,再加上生命的后半部分事业的兴旺发达。关渭城一生功业的成就还真应了作者的如下说法:“红尘万事,从政治到教学,毋论口号多冠冕,底下都不缺‘流氓特色’,流氓下海,胆子愈大,厚黑愈到家,愈能胜出。”
这不免让我们想到朱光潜先生对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形象之价值的体认与思考:“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和风车搏斗,以显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了。”这个曾让理想萦怀的我沉思良久且无由释怀的论断,或许可以说明关渭城命运转机的内在根由,至于本文作者是否有此想法,我是没有把握的。
杨辉
1979年生,陕西蓝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艺与文化传播学在读博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师。发表论文及小说多篇,著有《终南有仙真》《小说的智慧》《骊山释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