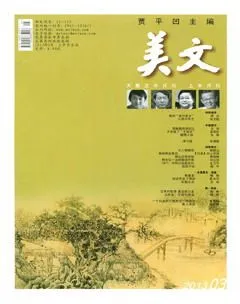转在弘一法师围墙外面
2013-12-29刘江滨
最早无意中走进弘一法师的精神世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城南旧事》有一首插曲《送别》,记忆深刻。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曲子舒缓婉转,歌词优美蕴藉,很有些宋代婉约词的味道。那时还不知道词作者是谁,也没听说过弘一法师的名字。后来读书多了,方知,这首著名的歌词竟出自一位大和尚之手——当然,那时弘一法师还未出家,他的名字还是李叔同。
弘一法师的一生极尽传奇色彩,他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反差之大完全判若两人,令人深思其中不尽的人生况味。胡宅梵云:“综观大师之生平,十龄全学圣贤;十二岁至二十,颇类放诞不羁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学风流儒雅之文人;三十以后,始渐复其初性焉。”此说不完全准确,但大体仿佛。
弘一法师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足的盐商之家。他的父亲李世珍是富翁,也是清朝进士,68岁生下他,过了4年就撇他而去。虽然缺少父爱,但他并不缺乏锦衣玉食的生活,家资巨厚足以维持他悠游卒岁的少爷公子哥的习性。少年的李叔同到上海后,同一干文人往来酬酢,走马章台,厮磨金粉,秦楼楚馆消遣,风尘场中寄情,还留下缠绵旖旎的风流诗词。到日本留学期间,花钱大方,衣着考究,“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即stick,手杖)、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丰子恺)为演话剧,他制一套戏服花一百多元,对一般普通留日学生来讲,一百元相当于半年的生活费用。在日本,他还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在天津老家有妻俞氏,育三子),在家中雇有保姆,过着上层有钱人的生活。
弘一法师艺术兴趣广泛,善书画,工诗词,喜金石,能篆刻,在中国现代戏剧、油画、音乐等多个方面,他都可谓开创者和先驱。晚弘一一岁的鲁迅很喜欢法师书法,从日本朋友内山完造那里间接获得“弘一上人”的一纸字,日记中用了一个“乞得”字样,其恭敬态度由此可见。在日本期间,李叔同与欧阳玉倩等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泪》等,在《茶花女》中,李叔同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盈盈细腰,手可掬握,令人惊叹莫名。回国之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他教授的主要是音乐钢琴课和美术课,这在当时都是开时代之先河的。著名文艺家丰子恺、曹聚仁、刘质平等都是他培养出来的高足。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对李叔同的艺术气息的熏染也非同小可,他经常在西湖中流连泛舟,在给一友的信中做了如此描述: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手,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态,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
李叔同年轻的时候,“异常的孤僻”,脾气很各。欧阳玉倩记述了留日时期的一件事。一次,李叔同与欧阳约好八点钟见面,欧阳住所距那里较远,赶电车耽搁了些时间,到了后,递上名片,不多时,李叔同开了楼窗,对欧阳说:“我们约的八点钟,你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工夫了,下次再约吧。”欧阳知道李叔同的脾气,只好掉头走去。浙江师范的同事、一生好友夏丏尊回忆了一件事,学生宿舍丢了东西,作为舍监,夏丏尊十分苦恼,李叔同出主意,劝其贴布告以自杀逼小偷自首,但如果小偷不为所动,那只好真自杀“以死殉教育”,夏丏尊认为这招太狠,没有接受。
李叔同年轻时候写过一些慷慨壮丽、雄奇豪放的诗词,如《满江红·民国肇造》:“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这首词填于1912年,距李叔同1918年出家仅有6年。
1918年,38岁的李叔同到杭州虎跑寺出家,一个月后在灵隐寺正式剃度。至1942年62岁圆寂,他的一生庶几被平分成僧俗两个世界,他也奇迹般创造了两个高峰:现代中国文艺先驱李叔同和律宗一代宗师弘一大师。这,的确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191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曾经的风流才子、曾经的公子少爷、曾经的豪放文人毅然断然决然皈依佛门?我试图在国内大背景和弘一法师的个人经历中寻得一点蛛丝马迹,但苦苦思索不可得,只好相信大师自己的自述,他有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讲述了出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渐变的,不是突变的。究其故,大抵有如下几个:1、深受马一浮的影响。马一浮,浙江绍兴人,曾留学美日,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同时又是佛学家,自号“马一佛”,他早年在上海与李叔同相识,在杭州交往频繁,李叔同视其为精神导师。在佛学上,“渐有所悟”,遂“世味日淡,职务多荒”。2、“断食”的因缘。1916年,李叔同在日本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耶稣都曾断过食。因李叔同身体一直不好,患神经衰弱,肺结核,还咯血,所以,在这年年底,他跑到清幽之地虎跑寺断食17天,虎跑寺后来成为他出家的地方,他自己也把此次断食视作他出家的近因。1917年下半年,李叔同开始吃素,房间里有了佛经、佛像,天天烧香,过年他也没回家,而是跑到虎跑寺过年。3、夏丏尊的“敦促”。夏丏尊与李叔同是一生的知交,友谊超乎寻常。1918年春节过后,李叔同皈依三宝,以演音为名,以弘一为号,原本打算以居士身份修行,寄住虎跑寺,暑假后辞去教职。夏丏尊见老友如此,心中寂寥,十分苦闷,有一天,对李叔同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这原本是心中难过的性情之言,却促使李叔同下了最后的决心。几年后,在一个场合,李叔同指着夏丏尊对大家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此恩永不能忘!”
俗世中的人们往往私心揣度,遁入空门的出家人,肯定是在现实中遭遇重大变故或打击,遂产生幻灭感,绝望感,看破红尘,剃度出家,著名如贾宝玉者即如是。这样的人确也所在多有,但不尽然,有些人完全是机缘巧合,一切随缘,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有人把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归于世事板荡,时局混乱,中国知识分子在苦闷中寻求不到出路,精神颓唐,于是,醉心于青灯黄卷;有人归于江南寺庙众多,佛教气息浓郁,儒家的修身与佛教的修行合二为一;……这些都是外在的情由,对于李叔同来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烟雨江南,歌榭楼台,红粉佳人,妻孥家人,都化作了“空”。当了和尚,对别人是“出家”,对他是“回家”,找到了最终的灵魂停泊地。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晚年信佛,曾撰一联:“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这话应在儿子李叔同身上,其间似有微妙的因缘。
我在想,作为一个文人,而且曾是一个放诞不羁的文人,李叔同为什么不选择禅宗,而选择律宗?一般来讲,禅宗讲究顿悟,更适合文人修行,饭来即食,觉来即眠,自由度高,而且参禅、谈禅也是件有趣的雅事。而李叔同选择了戒律非常严格的律宗,说白了,就是选择做苦行僧。律宗是佛教的一个派别,以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得名,对僧人生活要求持戒严谨,不得稍有违越,因而修习甚难。他之所以选择律宗,是因为,在他看来,近世所以佛门不昌,僧人不严格遵守戒律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僧人的道德品行,应该在一般人之上,如果仅与一般人相当,甚至不如俗家人等,社会就难免对佛教徒的鄙视。因此,弘一法师精心研习,持戒甚严。他一直保持过午不食的戒律,俗界朋友请他吃饭也非常尊重他这个习惯。穿不过三衣,即使严冬也是如此,所以冬天他的手上经常生有冻疮。
弘一法师有一张照片,穿着一身破旧的袈裟,头上戴着帽子,眼神悲悯、慈祥,给我心灵以强烈的撞击,有一种欲哭流泪的感觉,悲悯情怀油然而生。如果仔细看法师的照片,你会发现,他的衣服几乎都很破旧。一次,他在南普陀寺给青年佛教徒做演讲,第一条就是惜福,以他自己的衣着为例,一双僧鞋穿了十五年还要穿,一把雨伞用了十三年还要用,一条毛巾用了五年还舍不得扔。在他过五十寿辰时,他的学生刘质平在他的房间细细数过他蚊帐上布缝纸糊的洞共有200多个。夏丏尊曾约弘一到白马湖小住几日,期间弘一的生活境界,让这位老友慨叹不已,“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毛巾好,白菜好,菜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安泰、静默、谦和,随遇而安,构成了弘一一贯的生活态度。弘一不仅生活至简至朴,而且对声名地位更是淡如云烟,甚至视为累赘,对达官贵人避而远之。一次去青岛讲律,青岛市长晚间求见,弘一小声叮嘱他人说:“就说我已睡觉了。”第二天上午市长又来,弘一只写了一张纸条送出去,还是不见。但弘一却有一颗悲悯的菩萨心肠,他每次坐椅子都要将椅子颠一颠,唯恐上面有虫子,不小心将虫子压死。为了宣讲戒杀护生的教义,他与学生丰子恺合作——丰子恺绘画,弘一撰文——出版了《护生画集》,1929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他经常去开元慈儿院、温陵养老院、晋江平民救济院等这样的慈善机构,给他们说法,安慰他们孤苦的心灵。
弘一精研律宗,著述甚丰,代表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研习律宗,苦持苦修,使他成为一位纯粹的和尚,一位真正的僧人,一位德高道深僧俗两界均高山仰止的大师。他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现代女子奇才张爱玲,一向清高自许,目下无尘,却对弘一法师如此恭肃:“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1942年春天,郭沫若写信请求弘一法书,弘一写《寒山诗》相赠,诗云:“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上款题“沫若居士澄览”,郭沫若收到后复信致谢,称弘一法师为“澄览大师”。此诗写作距法师圆寂还有几个月时间,可以看做法师对自己一生的自我评价,明月皎洁,碧潭无尘,澄澈如许,光照后人。
1942年10月10日,弘一法师圆寂前三天,写下人生最后四个字:“悲欣交集”,留下偈语般的人生总结,令人玩味不尽。叶圣陶对此解释为:“悲见有情,欣证禅悦。”为众生苦海无边而悲,为修者回头有岸而悦,有大慈悲,有大欢喜,“悲欣交集”,一切的人生滋味尽在其中了。10月31日,夏丏尊收到弘一法师的一封挂号信,里面是弘一法师的遗书,是两则著名的偈语: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何意?不可说,说不得。叶圣陶说:“此境胜美,亦质亦玄。”善哉。此时,只觉得有春风拂过,淡云梳过,清水涤过,花香熏过,明月照过,内心澄澈如一泓碧潭,无痕无尘。
丰子恺在弘一法师圆寂几年后,在厦门佛学会做过一次《我与弘一法师》的讲演,他把人生比喻成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人中,没有谁比丰子恺更懂得他的老师了,他的这番话,是对弘一法师一生最好的诠释。
刘江滨
1964年生,供职于燕赵都市报,高级编辑。河北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散文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著有随笔集《书窗书影》,曾获河北省第八届文艺振兴奖、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散文《男人孟轲》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九年级语文教材,《理念的灯火》被编入中学语文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