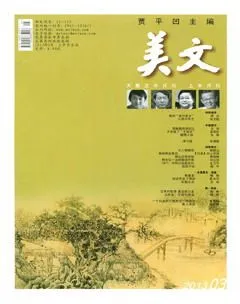顺从还是控制
2013-12-29费振钟
孟河镇在常州城西北,离扬子江南岸不远,因有孟河而成镇。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医学在南方的一个流派——孟河医派从这里产生。当日,小小孟河镇,名医云集,诸科咸备,据地方志上说,到孟河镇来求治疾病,“江船如织,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由于医学的带动,全镇各业繁荣,经济富裕,这种医学与社会经济的联动,几乎仅见于孟河一地。
清史稿对孟河医学亦有记载,史家从孟河医学中特选费伯雄作传,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最著。”作为孟河医派的领袖,费伯雄曾先后两次奉帝国的征召,前往北京,为当朝皇太后和皇帝治病。费伯雄的医学专长是治疗虚劳,而这时候帝国皇帝与他统治的国家似乎患了同样的疾病。
费伯雄从孟河港口过江,经苏北运河到达京城,行程艰难,而工作却闲庭信步似的,略一举手就治好了皇太后的肺痈和道光皇帝的失音症,荣耀地回到孟河镇,继续他名士兼名医的生活,精研医术,著书立说。没过几年,中国南方遭遇内乱,太平军攻占南京、苏州、常州一带,孟河镇也在战乱地区,医人费伯雄和江南的那些世家望族一样,不得不逃到江北避乱,而他先前已写成的医学著作《医醇》24卷,文稿与版刻都毁于战火,这一年咸丰十年,他60岁整。也许,家国不幸,社会危难之代,更能体现医学的价值与医人的理想。在江北泰兴一个叫五里圩的地方,费伯雄仍然坚持病弱之身,用三年时间,重新写作《医醇》精简本,取名叫《医醇剩义》,书成已到同治二年,又换了一个皇帝。费伯雄活到八十岁,在孟河镇由门人们举办的八十寿诞上,他向众人作了永别性的致辞后,于该年秋风乍起时平静逝世。他在江南的医学声望,由他的孙子费绳甫继承。由于费绳甫以及众门人的发扬光大,这个因医而兴的小镇,在风雨飘摇的末世,还能重建它昔日繁华。
却说《孟河费氏医案》,共两种:一为《孟河费伯雄先生医案》,一为《孟河费绳甫先生医案》,是费氏祖孙两代的医学实录,前者简易,后者翔实。伯雄先生生前可能只作记录,没有整理,亦未公开出版,这工作就由绳甫完成了;而绳甫自己的医案,则追写他四十多年的医学经验,选择其中“症之较重而出入较大者百数十条而存之”,于1914年他去世前与乃祖的医案一起付梓。而用不了多久,追求西学的激进学者已开始提出取消中医了。两种医案合读,可以看出孟河费氏医学的个性和整体面貌,也可校对人们对费氏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上的评价是否可信。
费伯雄理解的医学要义是“平稳醇正”,他在解释中国古代医学的两位前驱人物医和与医缓的名字时,领悟到医学与身体的一种“和缓”的关系与张力,这影响了他一生的医学思想与风格。尽管一般说来,费氏数代医人承传吴门医学一脉,但到费伯雄,之所以能够在吴门医学之外另开一派,当然离不开他对医学本质的理解有不同叶天士等人的地方,而非仅仅在医学技术上拓宽了“温病学”的医学场域。费伯雄说,“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方能神奇”,这其实是针对“温病学”医人们喜欢走奇峻轻巧的路数而言的。温病学的集大成者叶天士被称为“天机星”,与这种医学上的机巧相比,费伯雄宁取平淡无奇,所谓“平稳醇正”,并非技术和才能,而是一种医学原则和理想。
20世纪初,移居上海的费绳甫,正如他名叫承祖一样,对祖父的医学心领神会,“上承家学,恪遵祖训”,既发扬“平稳醇正”精神,亦有更多自己的心得。《孟河费绳甫先生医案》中,有一长案,记费绳甫诊治一位佚名的“湿温”病人,特别有代表性。该患者“阴液已虚,邪热内蕴,无从宣泄”,他担心“引动肝风”,导致“痉厥”,所以采用“甘平培阴”的方法,经过“七诊”,从肺经到胃经,缓慢地疏通,最后让病人从邪热的危险中解脱,彻底恢复身体正常的血分、气分。他的女婿兼医学传人徐相任在该案后称赞说,“胸有成竹,坚定不移”。
对这个案例的阐释,除让我们能够考察费氏医学“平稳醇正”原则的具体应用外,还可以让我们回到中国医学经典的身体观念上,认识费伯雄(包括费绳甫)坚持用“平淡之法”处理疾病与身体的关系时,所真正持有的知识立场。换言之,费伯雄怎样把对身体的理解,调整成对医学方法的译读呢?或者说,面对疾病的身体,何以是一种“平淡”对之的医学?这涉及中国医学对于身体的必要尊重与顺从。当疾病作为某种征候出现时,中国医学总是从身体整体上,将疾病视为身体的自然反应,通过对脉络和脏腑关系的清理,从而以一种顺应身体变化的方式,恢复身体的正常状态。“平淡之法”,即是对身体不刺激,不对立,不征服,在一种完全顺从身体的变化之下展开对疾病的治疗。可以想见,当费伯雄立意遵守“和”“缓”二人代表的医学古法时,他便将“平淡”的医学意义推向原点,从而达到醇正之境。平淡,在费伯雄那里,是对身体顺从的极致,而只有这种高度的顺从,所以才能产生化解疾病于无法之法中的神奇医学效果。
费绳甫将孟河费氏医学带到上海时,已是中医最后的荣光。20世纪初的中国医学,更加切近地感受到了西方现代医学的威胁。这个威胁来自于西方现代医学对身体解剖与分析技术的进步与成熟,它冲击和动摇着中国医学的身体观念,以及据此形成的信念。西方现代医学通过解剖学,将身体切割成各个组织分类,并进行病理分解,其医学目标在于通过对身体的控制,达到对疾病的控制与最终解决。不用说,这种控制性的医学,大大加强了处理疾病的即时性和有效性,与“和”、“缓”的中国医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毫不客气地将中国医学置于一种“失能”的境地。自然,中国医学其时没有主动应对这种冲击,尽管这一冲击在医学现代化的语境中,对中国医学传统是致命的打击,然而应对这种冲击的可能性仍然不存在。
我行我素的中国医学,过去没有今后仍然不需要依赖解剖与分析技术,难道知道“病变的位置与原因”对中国医人的疾病诊断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坚持中国医学精神的核心含义,就在于对疾病与身体有一个“顺从”的稳固立场,那么中国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的对立,实质上无从改变也无法通融。后发性的问题是,当西方现代医学越过20世纪,暴露出身体控制产生的医学危机时,顺从还是控制,有可能成为新的反思与选择,那么中国医学的古典之思,是不是又具有超前性的价值?孟河费氏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正当的回答。
费振钟
作家、历史文化学者。1958年出生,江苏兴化人。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主要著作有《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悬壶外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