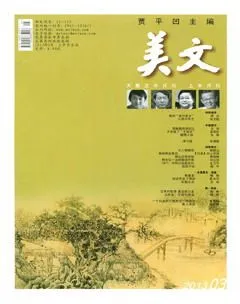不幸成了“王佳芝”
2013-12-29诸荣会
李安将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色·戒》于近年搬上银幕的意义之一,便是让人们又想起了那位70多年前为了民族大义而牺牲的民国名媛郑苹如。
然而,任凭原著作者张爱玲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大作家,李安又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大导演,电影中饰演主角的演员梁朝伟等又是多么耀眼的当红明星,都不能改变《色·戒》只是泼在郑苹如从头到脚的一盆污水的事实!
因此,实在有必要将历史上真实的郑苹如,与被张爱玲小说和李安电影解构和同构了的那个形象厘厘清楚,否则我们也太对不起烈士的在天之灵了!
一
郑苹如,1918年出生,原籍浙江兰溪。郑家在兰溪本是大户,父亲郑铖早年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回国在司法界担任要职。郑苹如丽质天成,聪明伶俐,又一路贵族学校读将过来,容貌气质自是非同一般,19岁就成了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画报《良友》的封面女郎,可谓大家闺秀,一代名媛。有着这样的“硬件”,如果郑苹如爱出风头,她自可以去傍大款,充大腕,当明星,在上海滩十里洋场上风头无限;如果她只想过低调的安稳日子,她自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事时或与太太小姐们打打麻将、逛逛商场,或与花花公子们谈谈恋爱、闹闹绯闻,一切都不会有太大问题。
虽说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度因落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而沦为了“孤岛”,但是,别忘了,郑苹如的母亲郑华君原名木村花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女人,郑苹如就凭着这中日混血的血统和从小跟母亲学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在上海滩左右逢源想来应该也不会是件难事。
总而言之,郑苹如如果想做闺秀,是有足够的条件将自己的闺秀人生进行到底的。
然而,郑苹如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郑苹如这条不归路的起点是“76号”。据说她走进“76号”属于偶然,这一点与另一位代表中共方面打入“76号”的女间谍关露十分相似。
据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后来回忆说,1939年3月的一天,一位腰别双枪、身材五短三粗,有点如“双枪老太婆”的女人,突然来到郑家,自报家门叫唐逸君,是在江南一带抗击日军的“忠义救国军别动总队松沪特遣支队”司令熊剑东的妻子,自己冒死进城找到郑府,自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熊剑东被捕,正关在“76号”,唐逸君通过疏通关系,“76号”头目丁默村已答应放人,但他开出的条件是要与沪上名媛郑苹如“认识”。唐逸君说,她也知道这丁某人是色场饿鬼,但是救夫心切,所以冒昧前来求郑小姐帮忙。
郑苹如听着来客说明来意,不知是真是假,自然无法作任何表态,只是一脸不以为然地看着唐逸君。唐逸君见此,又说,丁默村做过你的校长,他提出与你“认识”,原本也就是师生相认,即使说出去,也算不得太“出格”。
其实说丁默村与郑苹如有师生关系,只能算是强扯:虽说丁默村的确曾做过民光中学的校董(校长),郑苹如也的确在那中学读过书,但丁做校长是1934年这一年时间,而郑苹如在民光中学读书是1933年秋学期和1935年春学期,中间她因故休学了一年,所以她在民光中学读书的时间与丁默村出任校长的时间刚好错开了。但是这样的“师生关系”,若要硬扯,也能勉强扯上一点。
最后,唐逸君又晓以利害地对郑苹如说:“如果她能与丁默村‘认识’,对郑家至少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唐逸君这一句话,似乎一下子让郑苹如心有戚戚,因为郑苹如知道唐逸君所说的“坏处”是指什么。不久前,在她父亲手下任法庭庭长的大法官郁华,也就是作家郁达夫的哥哥,刚被人不明不白地暗杀了。
唐逸君离开后,郑苹如自然是第一时间将这一事情向组织汇报,没想到,“上峰”一听这事,竟然命令她将计就计,就此打入“76号”,设一道“美人计”。
众所周知,“76号”罪魁祸首有两个,一是其主任丁默村,二是其副主任李士群,皆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又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至此,算是都被国共两党的间谋“盯”上了。只是郑苹如与关露深入“76号”的具体任务却大不相同,关露的任务是从李士群身边设法窃取日伪情报,而郑苹如则是除掉丁默村。
看起来,郑苹如进入“76号”与关露一样,只是事出偶然,其实并非如此,背后是有着许多必然因素的。
郑苹如的父亲郑铖,虽早年留学日本,但是深明民族大义,即使面对日寇的白色恐怖也决不出任伪职,这自然已让日本人极为不满(直到后来郑苹如被捕,对方曾以他出任伪职为“保释”条件,他也坚决予以拒绝,并为此忧愤而死);母亲虽是日本人,但也难能可贵地深明大义,在平时的生活中,自称自己“嫁的是中国人,姓的是中国姓,自然也是中国人”,一直都站在反战的立场上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即使是日本的舅家亲戚,也多为进步的反战人士。
再看郑家其他成员后来的事实表现: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虽是在日本学会飞行的,但是“七七事变”后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于1944年1月19日,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战友,也于1944年8月7日,在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于湖南衡山。郑海澄和王汉勋的名字,至今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
因此,说郑家“一门忠义”,可谓当之无愧。郑苹如在这样家庭和人际环境中长大,因此,若说她走进“76号”,或许和关露一样,的确多多少少有点偶然因素,但是说她走上为国牺牲的道路,那却是一种必然。
还有人说,郑苹如进入“76号”,是背着她父母的,或父母是并不同意的,其实也不然。
同样据郑苹如的妹妹郑天如回忆的一件小事,我们大体上可以见出郑家的家教原本是很严的:有一次,郑家隔壁的一位邻居,从美国带回一把电吉他,邀请郑苹如晚上一起过去玩,没想到晚饭后郑苹如要过去时,父亲却不让。郑苹如一再说,一是就在隔壁,二是与人家都说好了,不去不好意思。但最终父亲还是不让,而郑苹如也只好作罢。生活琐事面前郑铖尚且如此严格,女儿要深入龙潭虎穴这样的事情,郑苹如又如何能瞒着父亲?据说郑苹如的行动事先是征求过父亲意见的,父亲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明确反对——根据父亲的性格,不反对实际上也就是同意甚至支持。当然,郑苹如之所以将“组织上”如此重大的事情征求父亲的意见,不怕泄密,里面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郑铖本人原本也是中统的人,郑苹如加入中统,介绍人也不是别人,正是她父亲郑铖。不仅如此,在此之前,郑苹如实际上已经与郑铖等多次合作,获取并传出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她曾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从日本人那里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并传给了重庆,只可惜并未引起重视,更没得到确信,这才使得重庆方面陷入了后来的一系列被动。不过,也正是因为此事,重庆方面这才开始对郑苹如重视起来,才对她的能力有所认识,也才将如此重要的“锄奸行动”交于她去实施。
与丁默村“认识”后,郑苹如一是设法获得丁默村的信任,诱使他放松警惕,二是寻找和创造机会,争取尽早除掉他。
机会终于来了!
1939年12月24日,那一天天气特别的冷,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街头行人似乎倒比平时多了不少,因为这一天是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这一天的夜晚就是所谓的“平安夜”。然而这是一个注定将不平安的夜晚,因为就是在这一天傍晚,中统特工郑苹如将与她的同伴将实施他们策划已久的“锄奸计划”。
那天中午,丁默村带着郑苹如在沪西的一个朋友家吃午饭,午后又一起坐车回虹口,半路郑苹如提出要去南京路,并说:“明天就是圣诞节了,今天是‘平安夜’,你不打算送一件圣诞礼物给我吗?”丁默村本来就确实说过几次要送一件礼物给郑苹如的,在这特殊时刻郑苹如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出来,作为特务头子的丁默村,虽然警惕性一直很高,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放松了警惕,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张无形的网这就开始向他套来,他爽快地命司机调转车头向南京路驶去,并问郑苹如想要个什么礼物,郑苹如说:“你看这天这么冷,你就送我一件皮大衣吧!”而此时,位于静安路与戈登路交叉口的“西伯利亚皮草行”周边,几名枪手早已潜伏停当、等待多时,就等着丁默村来送命了。
也就几句话的工夫,丁默村与郑苹如乘坐的汽车就开到了“西伯利亚皮草行”门前的马路上,丁默村让司机将车停在路边等着,他与郑苹如向店里走去,此后所发生的一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刚要进门的当口,丁默村似乎突然意识到有危险,转身就跑回了汽车;另一种说法是,他们走进了店内,正当郑苹如在挑拣皮大衣时,丁默村将一把钞票往柜上一扔,说了一声“我先走了”,就拔腿冲出店门,跑向汽车。究竟哪种说法是事实,今天已难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当丁默村突然拼命跑向汽车时,隐蔽在一旁的枪手有点措手不及,慌忙之间开枪射击,再加上其中的一个枪手的手枪竟然又正好在那节骨眼上出了问题,只一名枪手射出了子弹,但是只打在了丁默村的防弹汽车上,他算是拣回去了一条性命。
郑苹如自然是暴露了,但是为什么她没有逃跑和躲避,事后事实上还去自投罗网了呢?
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丁默村与李士群有矛盾,丁不想张扬出此事让李士群抓住把柄作为攻击自己的炮弹,他想低调处理,因此事发后他使出了欲擒故纵之计,装着并不怪罪的样子给郑苹如打电话,并一再说,只要她去自首,他会帮她“说清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郑苹如的一方,他们竟被丁默村的假象真的迷惑了,觉得既然这样,说不定真去“自首”后还能争取到除掉他的机会;再加上父母似乎也不反对她去“自首”,于是在事发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12月25日郑苹如就去“自首”了。
据说,那天下午,郑铖曾特定求人为此事算了一卦,卦象似乎很不好,他当场就曾自言自语了一声:“哎呀,从此我们再见不着了!”但是过了几天,郑铖竟又收到一张郑苹如从“76号”传出的纸条:“爸爸,我很好,请放心!苹。”然而事实上是,不久后,即1940年2月15日,郑苹如就被秘密处死了,其间虽多有一些传闻,但也只是传闻而已。而郑苹如的尸首郑家也一直没能领到,直至今日仍下落不明。
这便是历史上真实的郑苹如——一名特工的一生本事,一位巾帼的大义结局,一代名媛的薄命人生!
二
郑苹如被杀害四年后,抗战已进入尾声,此时的汪伪政权也早已风光不再,它台前幕后的主角也好,走卒也罢,都不由自主地捡点过去盘算未来了。大概正是这个时候,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不知出于什么契机,更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竟为他最新猎获的又一位妻子、有着海上花之称的著名作家张爱玲,讲述了这个在她当年似乎也有所耳闻的“美人计”的全部案情。
不久,张爱玲便以这个案情为素材,写下了一个短篇小说《色·戒》。正是这篇短短一万多字的小说,却几乎解构了真实的郑苹如。五十多年后,著名导演李安,又以张爱玲的小说为蓝本,拍摄了同名电影,对郑苹如又进行了一次解构与同构。就这样,明明是一位为民族大义而牺牲了的巾帼英雄,却成了迷恋汉奸的婚外情人;明明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战悲歌,却成了一场彰扬性欲的荒诞闹剧;明明是皇皇青史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却成了质疑信仰、嘲讽正义的一次言情娱乐。
或许有人会觉得此言失之过重,那么,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是如何对郑苹如进行解构和同构的。
这里有必要先将张爱玲小说的情节简单作一个复述:
故事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女特工王佳芝,以麦太太的名义,奉命用“美人计”刺杀投敌汉奸易先生,为了稳住那敏感而容易吃醋的易太太,她不得不与她及其一批汉奸夫人马太太、廖太太等人常打麻将,正是在麻将桌上,佳芝发现各位太太抓牌和洗牌的手上都有一只镶嵌着巨大钻石的戒指,而她没有,这让她觉得很丢人。刺杀的时机终于出现了,实施刺杀的地点定在一家珠宝店。王佳芝以要易先生为她买圣诞礼物为由头,将易先生诱至了店中,埋伏在店里的同伴正要开枪刺杀时,易先生竟然要为王佳芝买下一只很贵的钻戒。正是这只钻戒,让王佳芝一瞬间爱上了易先生,于是她轻轻说了一声“快跑”,周密的刺杀行为功亏一篑。然而,溜之大吉的易先生却并没有因此而放过王佳芝和她的同伴,当晚便将他们统统逮捕并屠杀了。
当然,小说还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补充交代了一些有关情节:王佳芝他们的这个“美人计”其实是早在几年前的香港就曾策划并开始实施了,当时的王佳芝还是岭南大学的学生,也是一位热血青年。她和她的同伴们为抗战上街游行、演剧。演剧的成功让他们一时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的抗战不能老停留在这地步,得来点“实的”,于是就策划了这个“美人计”,并由王佳芝扮成一个小开的妻子麦太太,让她通过接近易太太去色诱汉奸易先生。为了使佳芝积累性经验、色诱成功,“组织”还安排她与梁润生(唯有他嫖过娼有性经验)“一夜情”,尽管她有点喜欢的人并不是梁润生而是邝裕民,但是她也没有怨言地实施了。可是谁知道,易先生却突然间离开了香港,让他们的“美人计”最后落了空,当然这也让王佳芝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童贞。正在此时,由于战争,王佳芝华侨身份的父亲,竟然不负责任地带着儿子,撇下妻女去了英国,走投无路之际她只好来到上海投靠舅妈。就在王佳芝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里无所事事时,邝裕民竟然又出现了,他邀请王佳芝再次加入他们的“组织”,并继续当年的“美人计”。而这似乎又让那个热血青年的王佳芝复活了,她自然也就答应了。
这样两条线索加起来,便是张爱玲小说《色·戒》的全部情节。
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小说中最明显的改动,当然是将主人公郑苹如和丁默村的名字改成了王佳芝和易先生,小说情节与历史本身相比,改动的并不算太多,然而正是这很小的改变,却将郑苹如身上的原本闪闪发光的信仰、正义、勇敢等有意无意地全面遮蔽了,具体来看,她至少是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同构和解构:
一是其出生家庭。郑苹如出生和成长的郑家,原来是“一门忠义”;可是小说中的王佳芝,却几乎是一个“无家”的“问题少女”。虽然说父亲的离去有战争的因素,但是他为什么能将儿子带走就是不能将她这个女儿带走呵,这明明是在他眼里,女人是低一等的——事实上王佳芝被父亲遗弃了。既然父亲遗弃了她,她自然了也就没有孝顺父亲、维护家门荣誉的责任,甚至也没有了亲情值得留恋,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二是爱情生活。爱情是女人所看重的,也是张爱玲创作和生活中都看重的,她当然不会轻易放过。郑苹如的男友王汉勋是一位抗战英雄;可是小说中的王佳芝呢,却是在“革命”的名义下白白牺牲了童贞,而她喜欢的人邝裕民是完全不“懂”她的心的男人,更不在意她的爱,他在乎的只有“革命”,只是将她当作一把“革命”的枪在使,因此她也没有自己的爱情,也就没有爱的“忠诚”,甚至连爱的“拖累”也没有,她有的只是爱的无奈、失望和迷惘。张爱玲真不愧是小说高手,她在这里实际上为后来王佳芝不可理喻的表现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伏笔——后来她之所以会“爱”上易先生,并放了他一马,哪怕他是汉奸,是自己刺杀的对象,只因为那易先生“懂”她。然而,张爱玲在这儿解构的已不只是爱情了,而是连同人的信仰和正义,都是极大的反讽。在这儿,小说家的张爱玲真是既不懂得政治和革命,也不懂得爱情。因此,我们一点儿也不要奇怪,生活中的她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多为人们所不齿的汉奸胡兰成呢,只因为他能“懂得”张爱玲的小说的好处和妙处,并能说出其妙处是“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第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我们一点儿也不要奇怪,为什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么一句似是而非的话,会成为张爱玲一句常挂在嘴上的名言——而这话如果说白了,不就是“因为你懂得我,所以我对你慈悲”,不管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汉奸),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哪怕你已在我的枪口下)。
三是人生结局。小说中王佳芝们的刺杀行为与郑苹如们是一样的,都遭遇了失败,都做出了牺牲,但是郑苹如们的失败实际上只是一次偶然——如果丁默村跑得晚一点、慢一点,如果射出了子弹的那名枪手的枪法更准一点,如果另一名枪手的枪不出问题,结局就会相反,郑苹如再次接到丁默村的电话回到“76号”去“自首”的最后悲剧更是压根本就不会有了。但是在小说中,王佳芝们的失败,原因竟然是她“爱”上了刺杀对象,并主动放跑了他;而“爱”上的原因仅仅就是因为一只钻戒,即他能“懂得”她。虽然不能肯定人类在那种情况下是不是真的会患上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小说中,这一情节完全是张爱玲的凭空虚构——或许也不能说是“凭空”,她或许凭得恰恰就是自己在生活中爱上汉奸的事实。但是,一个爱上汉奸的女人张爱玲,就能证明天下所有的或多数的女人都会爱上汉奸吗?再看王佳芝最后的“自首”,在张爱玲的笔下竟然比史实更简单,几乎就是自作聪明、傻不拉叽地去送死。就这样,大义凛然成了自作多情,视死如归成了咎由自取,一次正义行动的失败成了活该;郑苹如身上原本的信仰、正义和勇敢,也便这样被张爱玲遮蔽和消解殆尽。
有人或许会说,《色·戒》只是一篇小说而已,小说创作自可对素材进行处理和加工,乃至虚构也属正常,干吗非得将小说中的王佳芝与真实的郑苹如对号入座地进行较真式批评呢?
此话当然说得有理,但是《色·戒》毕竟不是一篇普通的小说,如果它完全是一篇普通的以虚构为主的小说,我们大可不必与它如此较真;问题是它采取了与历史本身同构的方式来处理素材、设置情节和显示主题,从大处看,其人物角色、主要情节和最后结局等,都与历史本身基本相同,作家解构的只是细节,而这些细节的改变,会让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在小说与历史本身间迷惑;再加上作家在细节方面的解构,反使得小说比历史本身更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其人物形象的价值导向,也比历史本身更加集中、鲜明,其对于读者的影响也更大,无论是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所以,虽然张爱玲的《色·戒》说到底只是一篇张爱玲式的小说而已,但是我们不能不与它,也不能不与它的作者张爱玲较这个真。当然,更应该较真的还有李安及其电影,因为他的电影又在张爱玲之后——就在今天拍成的。
三
如果说张爱玲的《色·戒》本身就已经是对郑苹如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同构和解构,那么李安同名电影在此基础上又来了一次,虽然他事实上很忠实于张爱玲的小说,所作的改编看起来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只有“一点”;而就此“一点”,其同构和解构的恶劣程度比之张爱玲又走远了许多。
这里我们不妨将历史本身、小说和电影中的主要情节列出这样一个表格:
通过这个表格,我们首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其主体情节都是同构历史本身而来,其解构和虚构的只是其细节,这也再次证明,我们的较真并非不懂文学,更非无聊,而是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其次,我们也确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安的确很“忠实”于张爱玲的同名原著,改变的只“一处”,即,将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原因,由能通过一枚戒指表现出的“懂得”,改为了她由于从他那儿得到了太多的“性爱的愉悦”——电影通过多场“床戏”的反复渲染,至少给观众的实际感觉是如此,虽然电影中也有对钻戒的特写等。
——可以这样说,在这部电影中,李安的匠心、阴谋和挑战也全在此!
首先,他将历史本身中的庄重、神圣,连同张爱玲小说中的严肃、认真,来了一次大稀释。当然,张爱玲对历史本身已稀释在前,她的手段是将历史本身这样一个本来是有关信仰、正义和勇敢和主题,用所谓“真爱”稀释了,但是她至少还留下了爱的严肃和认真,尽管她严肃、认真得有点可笑;然而,李安却将爱情中的所有“情爱”,都归结为了“性爱”。这样一来,他的电影,就可以大演“床戏”吸引观众眼球,娱人身心,沉重的历史本事和严肃的文学作品,就有了言情片和娱乐片的功能。此或许可算作是李安的“匠心”吧!
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电影是有一个审查制的,一部电影如果不能通过审查是不能公映的。他如此一改,便可将审查者的眼光吸引到对于那些“床戏”的多少的纠缠上去了,反而会让审查者对于他要在影片中所做的挑战有所忽略,这无疑是有利于影片的审查通过的。事实上,李安的这一“阴谋”不能不说确实很高明,那些审查影片的老爷与专家们果然中招,于是影片胜利通过,公映全国。
再次,李安的挑战是什么呢?且看李安在电影中的这一改动,所呈现给观众的便是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逻辑:因为王佳芝从易先生那儿得到了“性爱的愉悦”,所以她爱上他便理所当然;因为她爱上了他,所以她关键时刻便放他一马,哪怕他是与民族为敌的罪人,便也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在李安这里,性爱成了人生的唯一,甚至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只要有了“性爱的愉悦”,什么都是都可以去做,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无所谓。这不是一种挑战吗,他挑战的对象与张爱玲相比并没变化,都是人的信仰、正义和勇敢,但是张爱玲是用所谓“真爱”,而李安干脆就用“性爱”,其对于前者反讽的意味、轻劣的程度和挑战的力度,无疑比之张爱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据说张爱玲这篇小说写成后迟迟没有拿出去发表,而是一改再改,改了多少次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从动笔写成到发表,前后经历了近十年。这很不符合张爱玲创作的固有习惯和“出名要趁早”的行事风格,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当然不能确知,但其中或许就有张爱玲对于自己在小说中的挑战,也十分犹豫、怀疑和不能把握的原因吧!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断,并不能确知。与张爱玲相比,李安似乎胆大多了,也幸运多了。他的电影不但顺利拍了出来,而且竟也顺利通过了审查,在全国城乡公映了好一阵。其中的原因,难道真是那些审查的专家老爷们,真中了李安的“美人计”,被其中的那些“床戏”看了血脉贲张,而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了吗?抑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们更不得而知。
其实“美人计”本身并不构成对于人们道德底线的挑战,不但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中多有使用,而且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对此也多有叙写和表现,中国人最为家喻户晓的莫过于西施及其种种传说了。
越国人将西施送给吴王夫差使其中美人计,最终灭了吴国。古往今来,人们之所以将西施尊为“中国四大美人”之首,并且还为她附会出与范蠡一起私奔而去,如同童话中的灰姑娘那样与心爱的白马王子“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人们对于西施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对于正义、信仰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的一种肯定。而《色·戒》呢,却对此作出了质疑,张爱玲用的武器是所谓的“真爱”,李安则是“性爱”。什么家国情怀,什么民族气节,什么人间正义,统统不如性的愉悦与快感有用、实在和有意义!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因为动物也有以“性”为前提与目的的快感,怎么说人总比一般动物要高级一点吧!事实上,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国家,还存在民族,还存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那么家国情怀、人间正义、民族气节、理想信仰等都是人所不可以放弃的,也不是轻易就可以去质疑的,哪怕是在所谓的“真爱”面前,更不用说只在动物层面上的“性爱”面前了;任何质疑,都是一种挑战,而这种挑战,其对象又是做人的底线和人类公德的底线。《色·戒》正是在作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的《色·戒》,其价值观导向是有极大问题的。遗憾的是,审查影片的老爷和专家们竟然对此没有看出,竟让一部本该封杀的电影蒙混过关(他们有没有将不该封杀的封杀,我不得而知,这里不敢乱说),且还让它打出“今年中秋,真爱无罪”的广告招揽观众。
不过,倒是影片公映后所发生的事很具有讽刺意味:一些普通观众,在看了影片后,竟看出了专家们没有看出的严重问题决不在它的几个情色镜头,于是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呼声,正是这自下层的声音让有关部门才如梦初醒,这才急急忙忙行动起来,一面收禁影片,一面封杀主演王佳芝的演员汤唯,以示亡羊补牢。这在中国影片禁映历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至少是极罕见的——多数都是自上而下的禁映,而这次竟然是自下而上的呼吁禁映。这真是又一次应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实属难能可贵!
不过这亡羊补牢做得也不算太漂亮:作为演员的汤唯,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当然是有责任的,但是相比之下她的责任比作为导演的李安们小多了,要封杀也该第一封杀李安们,不封杀李安们只封杀汤唯怎么看都有点“杀猪没杀着,砍板凳腿”的意思。
最近,听说被一度封杀的汤唯又复出了。李安更是不会因为《色·戒》而有损毫发,说不定反而会使他国际名导演的声名更大,使他在业界更牛。这当然没什么,甚至可以说,这正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今天的社会已变得十分宽容的一种表现;我也并不主张,一个艺术家有了一次或两次的失误,就将艺术家本人一棍子打死;但是,艺术家在创作中到底是创新还是失误,是质疑还是乱弹,是挑战还是胡闹?该较真的还是应该较真的,我以为!
四
说实话,促使我写作本文的直接动因是我一个朋友、作家耿立遇上的一宗官司:他的一篇写赵一曼烈士的文章,文中写到赵一曼烈士被捕后,任凭侵略者酷刑用尽,但始终坚贞不屈,其中他引用了一段军史上的资料,即侵略者曾将电极插进赵一曼的生殖器施以电刑。他之所以引用此史料,目的很清楚,一是为了具体揭露侵略者的惨绝人寰与惨无人道,二是为了歌颂烈士的坚贞不屈与视死如归。然而,这竟被一个自称是赵一曼后人的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作者赔偿包括她的“精神损失费”在内数十万元。
一样是叙写烈士的作品,明明是对烈士的歌颂,却成了被告;明明是往烈士身上泼污水,却能打着所谓“爱”的旗号大行其市、大赚其钱,甚至还能获得不少无聊的吹捧。这叫什么事呀!这叫什么世道呵!难道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当然不是!
郑苹如成了王佳芝, 成了一个执着于性愉悦的“问题少女;一段沉重的历史,成了一篇轻飘飘的小说,成了一部色情加娱乐的电影;一位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硬是被张爱玲和李安们,经过一番同构、解构、虚构,最后竟重构成了一件质疑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工具和一枚挑战人沦底线和人类公德的炮弹……呜呼!这真是作为烈士的郑苹如的大不幸,也是历史的大不幸!而这种不幸的造成,难道不是张爱玲们、李安们的无知、无聊和无耻吗?不也是我们今天的一种极大悲哀吗?
诸荣会
江苏溧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某出版社副编审。有作品发表并入选《中国散文60年》等选本。出版散文集等十数种。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