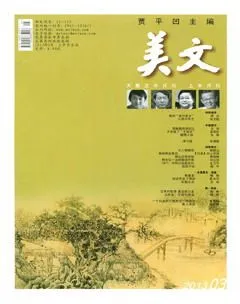心思与手艺
2013-12-29吴克敬
断臂玉兰
听闻这棵花树之王的古玉兰,已有一些年头了。今年春四月初六日,早起通过阳台上的玻璃窗,我看到小区绿化带里栽植的玉兰,或粉白,或紫红,开得正艳。但我知道,她们都太细嫩了,是不敢与秦岭深山中的玉兰王相媲美的。那棵大蟒沟里的玉兰树,在周至县的老志上即有记载,时在北宋初年的时候,如此算来,已逾千年的风霜雨雪。这让我不敢再想,觉得人真是不如物呢!一棵花树可以千年挺立绽放,而一个人百寿都属稀罕。我的心动了,以为她该是秦岭山里的树之神,花之仙了!
真得感谢四通八达的公路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老祖先步行三五日难见玉兰王的路程,我们驱车三五个小时不到,就顺顺利利地到达了。
连陇成片的茱萸林,开满了金黄色的小花,在茱萸花的簇拥里,隔着一条溪水潺湲的河沟,就是应该奉为仙妖的玉兰王了。正如我在家写的那两句话一样,是夜一场细雨,让含苞初绽的满树玉兰花,透出一股清亮的色彩来,她是紫红色的,吐露着高贵沉郁、大气自然的紫红啊!我猛地睁大眼睛,却不能尽揽她的美丽,我急喘的呼吸着,也无法尽收那铺天的幽香。同道而来的友人张龙,急忙取出他背囊里的相机,咔嚓、咔嚓……仿佛雷闪一样猛拍着。
哦!千岁、万岁,为人山呼着想要长生不老的人,通过摄影或许可以实现,但对这棵让人敬慕的玉兰王,却并不需要,她自己就已实现了千岁,而且还会进一步实现万岁。
人的渺小,让我站在这棵千年玉兰树下,感到从没有过的心伤。
这是因为,人天生着一副热心肠,但却常常无情。而玉兰王,我手抚她苍劲的躯体,虽感觉不到她的心跳,但我已知她的襟怀,是温情的,是恒久的……在她占地两亩六分的树荫下,横亘着数根从她身上折落的树股,粗者有碗口一般,细者也有人的胳膊那样。知性的长怀老友给我说,这些年,居住在玉兰王周边的山民,有一些搬出山外了。玉兰王眷念着他们,每搬离一户人家,玉兰王就要断去她的一根枝股!
啊!啊!
我蓦然抽回抚摸着玉兰王的手,心里天裂一般惊呼了两声。
断臂玉兰!
这四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字眼,倏忽映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要问,天下还有何物,能如此的与人同欢乐,共悲伤!
断臂悲人的玉兰王啊!她是还要发出新枝来的,与她断臂同工异曲的是,每有一根新枝生发出来,居住在她周遭的山民,就会有一家人,落草一个哇哇啼哭的光屁股新人呢!
让人恋恋不舍的玉兰王啊!我一步三回头地撤离着,幸运的觅见她的一截断臂。遭受到自然地风雕霜刻,这截断臂已然成为一件美轮美奂的艺术品,透、瘦、露,仿佛太湖石一般绝妙。我弯腰捡起她来,就不再丢手,一直地捧着,心想我捧着的该是玉兰王的灵魂呢!
我把这截玉兰王的断臂捧回家来,安顿在我的书房里,我面对着她,为她写下了这样两句话:
春风起时玉兰舞,细雨润后花自幽。
龟背竹
不是看到振川先生阳台上的那株龟背竹,我对这种植物是忽略了的。
我知道叫做龟背竹的植物,是热带气候里的植物骄子,四季常绿,极少开花,只是很孤立地从主干上蹿出一条须根,努力地生长着,这便有了一片嫩嫩的叶子,羞答答地蜷缩着,生长出来,由最初的黄绿色,渐渐地转变为墨绿色,然后舒展开来,成就了她的深厚、博大和挺拔。当然,她是不满足一条根须的发达,她有极大的耐心和能力,在以后的日子里,又要生出一条须根来,循序渐进地再生出叶子来。螺旋上升的轮生性叶序,确定了那极有特点的叶片,一片要高于一片,盘旋着向上而去,给人的感觉,也便十分的美妙,仿佛一个上进心极强的人,永远都不满足,永远都没有尽头。
龟背而竹,闻其名,再观其形,可以知道她的叶子,确有如龟背一样的形态,却一点也找不出竹子的样子来,这只能解释为人们对她的偏爱了,把自己认为美的东西,不合事实,却也要慷慨地送给她,使她也能具有“竹”的品质。
龟背竹仿佛通着人性,懂得了人的期许,在她生长的过程中,尽量的表现出这种让人感动的情怀来。而这正是我见识了振川先生画室阳台上的龟背竹后,所获得的感受。
是为画家的赵振川先生,秉承了其父赵望云先生的志趣,高举着长安画派的旗帜,在长安城里,已经度过了六十多年的笔墨生涯,他的成就,他的品格,像他父亲赵望云先生一样,已然成为这个城市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我敬仰先生,逮着空儿,就到他文艺路的画室去。一次去,先生在阳台上侍弄他的花草,见我来,也招呼我去了阳台,使我有幸发现,先生对于他侍弄着的花草,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一株花草就如他的一个儿女,有血有肉的儿女呢!他给我介绍着,这是牡丹,这是芍药,这是茉莉……每给我介绍出一株花草,他都小心地用手去抚摸一下那株花草,那个样子,惹得我差点儿要笑出声来。
这太有趣了,没有长相厮守的情感,是做不出他那亲昵的动作来的……轮到阳台东边角落里的龟背竹了,赵振川先生给我介绍得就更加情深意长,伸着手,把每一片叶子都摸了一遍,我看着他,突然有了一种别样的发现,发现茂盛的龟背竹的魂可是附着了赵振川的体,或者说是赵振川的魂可是附着了龟背竹的体,总而言之,龟背竹之于赵振川,赵振川之于龟背竹,相关之间,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两者的情感相连,命运相通,是一对须臾不可分割的生命体了。
龟虽寿……从赵振川先生的画室回到家里,我上网查了查,发现龟背竹,有着这样的一种习性,她一年只作一次梦,而她做梦的方式是用她生长叶子的过程实现的,也就是说,龟背竹一年只生一片叶子,但她却保持四季常绿的形态。为此,我要说,赵振川阳台上的龟背竹是长青的,赵振川的个体生命就是长青的,还有他的艺术生命就更是长青的!
礼乐陌上
天有道,风调雨顺;地有道,五谷丰登;国有道,忠臣良将;家有道,子孝妻贤。满头白发的杨先生,站在我的老友李少颇家的坟头前,声若洪钟,抑扬顿挫地主持着一场迁坟祭祖活动。为父亲的李少颇和他的长子李元,都是我的朋友。他们家为了国家的一项建设,自觉把祖坟从原来的地方,迁移到他们村北的新地方。地球人因为陈忠实先生一部《白鹿原》的小说,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一方风水宝地。端的是,父子两代为我朋友的他们老家,就在白鹿原的腹地孟村乡李家村里。白鹿原上关于白鹿的传说,世世代代,非常顽固地印记在这方土地上,以及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的心头。那只远古的白鹿,已被传说成了一个仙子。作为一个外乡人,我敬畏那只普降吉祥的白鹿,我幻想自己也能得到白鹿仙子的护佑。因为这样的幻想着,我看见白发飘飘的杨先生,在一个瞬间里,幻化成了那只传说里的白鹿。
传说里的白鹿,是特别的,它肩负着传播礼乐的责任,它希望它所传播的礼和乐,能够教化民众,使得千户百姓的民众,沐浴着礼乐文明的雨露,享受着礼乐文明的阳光。就在此刻,就在眼前,杨先生所持之礼,所润之乐,不正是仙子般白鹿所传播、而在今天渐渐淡薄了的礼乐吗!
在我意识里幻化成白鹿仙子的杨先生,如我于文头写的那样, 揭开了“赞碑”的程序后,依次就还不断“起乐”“乐至”,反反复复地调动着延请而来的乐人班子,进行着例如“揭碑”“祭酒”“上香”“吊表”“谢客”等等一连串的礼仪活动,让秋天的白鹿原,在那一个时段里,显得特别的肃穆,特别的庄重,也特别的五彩斑斓,仿佛悠游在蓝天之上的白云,也多了几分畅亮与超然。
我的故乡不在白鹿原上,而是在数百里之外的古周原上。
无论白鹿原,无论古周原,有关婚丧嫁娶的礼仪,似乎没有什么差异。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候见识过的一件事,我们老家的一户人家,老娘去世了,儿女守孝三年,到三周年祭日的时候,那家的儿女给自己的母亲,在坟前也立了碑,也请了乐人班子,应有的礼仪,也都在喧嚣的礼乐声里,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可是到了最后,问题出来了。
是个什么问题呢?现在的人有所不知,那时候,守孝三年的儿女,在三年祭日的祖宗坟前,依着应有礼规,一项一项进行着,到了最后,娘舅家的来人,要为孝子们卸孝的。戴在头上的孝帽,披在身上的孝服,作为孝子,自己是不能卸除的,这也是一项承传了许多年的礼规,自己卸除,便是不孝,其他人也不能卸,卸除了同样被认为不孝,非得娘舅家的人,来为孝子卸除孝帽、孝服,然后扔进纸火里烧掉,才能算作尽孝。
偏偏的,那户人家的孝子孝女,到了最后的关节眼上,看着他们的娘舅家人,而他们娘舅家人则旁若无人,根本不看戴了三年孝的他们。事情僵持了下来,使那家的孝子孝孙,没奈何地又守了三年孝。
礼乐陌上,无论白鹿原,无论古周原,无论别的什么地方,对我们人的道德和修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礼而乐之,白鹿原上的风在那一刻是清明。
伤心水
鱼是从哪儿来的?水生的?土长的?
提出这个问题,我知道会有被人耻笑,甚至被人唾骂的危险。我有这个思想准备,甘愿冒险,想与对此感兴趣的人做些讨论。我从不怀疑,鱼是生在水里的,没有水,鱼便会失去生命。这是一个常识,睁眼就能看见。但我怀疑,这不是唯一的解释,我有理由认为,鱼也是土里长的。
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人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眼见为实”,评判一件事情,难以得到定论时,说服人的话,就是这四个字,你“眼见”了吗?你没看见我看见了。这么说话,没理都成了理。然而,眼睛是会骗人的,就像耳朵一样,以为听进耳朵里的声音才是真实的。谁要这么认为,我就只能同情他,同情他的单纯和可爱。生活中,最常欺骗自己的,恰恰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魔术师的把戏,都是在观众的眼皮子底下完成的,就像今年春节晚会上,那位被动物保护者批评为“虐鱼”行为的魔术师,把画上的死鱼变进鱼缸成活鱼,又让那鱼在水箱里如仪仗队员列队而行,咱们真真切切地眼睁睁看见了,但咱们心里都明白,那不是真的,都是魔术师的障眼法。
所以,我是不敢过分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时更不敢太过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一种现象,童年起就塞进了我的记忆,让我至今疑惑不已。我生活的关中扶风原上,是非常缺水的,少见水里自由游动的鱼儿,可是一场雨水,在上不着天,下不接海的旱原上,突然地汪出一洼水来,三天不到,水洼里就有了青蛙,五天不出,水洼里就有了鱼儿,尽管那青蛙和鱼儿极小,小的只有指头肚儿一般,但它们什么都不缺,生的真是可爱。可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就这个问题,问了许多人,有人还是大学里有名的生命科学家,但他们不断假设,假设一切的可能,到后来又会被他们全部否定。
因此,我以为土里也是可以长出鱼儿的,只是长出来需要水的滋养。
想到这里,都是阳春三月溯黑河水而上,在黑河畔访问鱼水洞引发出来的。
神奇的鱼水洞,如一练银色的珠串,常年不绝地挂在黑河畔的那面峭崖上,向黑河河道倾注着她的清澈,使大堡子的西安城,有着取之不尽的甘甜用水。踏春进山,初听当地人抒说鱼水洞的故事,我即感到心的湿润,幽深不见来处的鱼水洞,经年流泻的白练,到了每年谷雨的日子,随着水流的不断泻出,会有肥美的鱼儿,荡跃在清冽的流水里,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银白的或是金黄的光亮,跌下涧来……一条两条,三条五条,七条九条,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摸透了鱼水洞这一规律的山民,头顶着太阳的光色,这一天提篮背篓,都要来鱼水洞下的黑河来捡鱼,赶天黑,捡鱼的人差不多都能捡得半篮半篓的鲜鱼归。
有人统计过,众人日捡鲜鱼会达数几万斤!
这些年,黑河作为西安市的水源地,山民们大多迁出山外,河水里不乏那些普通的常见的草鱼、鲫鱼等等,这一消息启示着鱼水洞,她在谷雨时节,就很少往黑河水里吐涌这些鱼儿了,她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开始大吐特吐娃娃鱼!当地人说,去年的时候,拇指大的娃娃鱼苗,一天时间吐得出三两万尾。
噫嘘唏!鱼水洞该是一处神秘的通灵之地,她知道秦岭的伤心,叫声嘤嘤,与儿童哭声无异的娃娃鱼,突然的成了饕餮者的口中美味,于是乎,就有胆大妄为的人,不断偷捕娃娃鱼,使这一国家特别保护的珍稀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鱼水洞不忍这一恶果的发生,她以她的情怀,为秦岭生物的存续,做着她的努力。
为此我泪水涟涟,在心里把鱼水洞叫了伤心洞,把洞里涌流不息的水叫了伤心水。
手和手
流行了很长一个时期的段子是:拉着小姐的手,激情澎湃来劲头;拉着情人的手,一股暖流涌心头;拉着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拉右手。
段子是否说了人之常情,我不敢妄加评论,初听时,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但我听了后,不像别的段子,随听随忘,全不当回事,倒是这一个,说黄不黄,说黑不黑的,却记了下来,甚至想,这手和手的接触,的确是很不同呢,便是形式上的不同,就有握手、牵手、拉手手等等区别,而且其所传达的内容,在本质上也是很不一样的。
怎么说,握手都是一种礼仪,是从西方舶来的东西。我们的老祖先,原来是没这个习惯的,见面了抱拳拱手,即是打招呼,也是对对方的致礼。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一场鸦片战争后,把我们的国门打开了,也把他们的握手礼塞进了我们中国。要说,这个礼节,其实不像西方的科学技术那么先进,更不如我们的拱手礼,隔空打招呼,可是多么健康啊!握手就没这么干净了,谁的手上都会带着病菌,如果只是一般的倒还罢了,如若是传染性的,手与手相握,给大家,或给自己带来健康问题,可就很不妙了。再者是,握手太少情感交流了,朋友相见握手,同事相见握手,便是敌对的双方,相见也是握手的。1993年的时候,香港还未回归祖国,末代港督彭定康要在香港推动政改,闹得大家势同水火。有一次,大屿山大佛开光,时任大陆驻港最高级别的官员周南,与彭定康不期而遇。这位末代督港大方伸手,欲与周南握手。双方当时虽处冷战状态,但外交场上的事情,周南不能拒人太过,那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失礼,甚至还会造成世界性的不良影响。怎么办呢?周南没有去和彭定康握手,他只对着末代港督,双手合十,作了一个佛家的礼仪手势,给予对方回应。
那种佛家的礼仪手势,与我们传统中的民间礼仪手势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核心在手,两个人的手和手,是不接触的。周南在国际外交场合,以此作为会见礼,真是太智慧,太有体面了。
在握手的事情上,发生的愉快事和不愉快的事,要说是很多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握手并没有那么了不起,那么不可少,倒是我们传统的拱手礼,在科学的今天,很有重新倡导和推广的必要。
牵手就更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还有拉手手。
牵手纯属一种惯性,家里人上街了,要过马路,或是爬台阶,你把手伸出来,她把手伸过去,自自然然地牵在一起,走过了马路,登上了台阶,又自自然然地松下来……因此说,牵手满含着怎样的亲情和关心啊!这就是恩爱夫妻,这就是骨肉儿女,因为熟悉,可能牵手在一起,仿佛自己左手拉着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却正好印证了一种当然,自然形成的关爱,自然形成的默契,绝不是什么感觉所可以比拟的。
女儿考上高中的那天,我和她上街散心,在东大街上,要从街南往街北去,过马路时,我走快了一步,女儿伸出手来,牵住了我的手。在此之前,可都是我主动去牵她手的,这一次被主动地、自然地地牵起来,我蓦然意识到,女儿长大了,知道关心我了。
亲人之间,也是最平淡、最动人的呢!
那么拉手手呢?那可是另一种情景了,陌生的一对男女,相互探索着对方,了解认识着对方,到各自的心里有了一点点对方,并情不自禁地侧身立着,偷偷地把两只手拉起来,没有点儿冲动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体会,倒是陕北信天游里的一支曲子,虽然直白了些,却也最能说明问题:
(女)你要拉我的手,
(男)我要亲你的口;
(合)拉手手呀亲口口,
(合)咱们二人疙崂崂里走……
说话与听话
还别说,人人都有一张嘴,除了吃喝,就是说话。在吃喝上,有人味重,有人味淡,有人好辣,有人好甜,是很不一样的,所谓“巧厨子难调众人口”,讲得就是这个道理。但这是不伤大雅的,而且也不会伤人,说话就不一样了,会说不会说,结果截然不同,不会说了,一言即出,撞得墙倒房塌,而会说了呢,阳光灿烂,皆大欢喜。
我就感动一些人,话说得真是绝。
不是我自夸,我的女儿就是个会说话的人,她和我的几次闲扯,把我说得就极服气。现在女儿在大学读书,寒假回来,朋友女儿出嫁,吃罢喜宴回来,我对女儿说:“你出嫁时,爸说不定会哭死呢!”我女儿笑了笑说:“别是我嫁不出去,你才要哭死呢!”如此一针见血,我还能怎么说?默默地去了书房,翻开一本杂志,随便地看着,女儿跟了进来,给我又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如果乐意作我的嫁妆,我出嫁时,你不会哭 ,我也不会哭。”
女儿人小鬼大,在我们家,活宝一个。一次回家坐到沙发上,我感觉到把女儿的脚压住了。她不等我抬屁股,自己已唉哟唉哟地叫上了,她说:“爸爸,你的屁股踩上我的脚了!”
一个“踩”字,被女儿用的真是叫绝。
女儿这种叫绝的话,写出来不知要消耗多少笔墨。那么,就此打住吧,因为我想写的是另一个人,这也是个很会说话的人。
这个人是我女儿敬重的叔叔穆涛,他们两个有过几次短暂的交往,其中就有一些非常使人难忘的对话。不过,我仍然不想在此用功夫,我只想说一说很会说话的穆涛。
我比穆涛年长十岁,但我发自内心的,把他视为我的老师。我所以二次走上文学的道路,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与他相熟,起先是我写的一些民间碑刻的随笔,受了他的唆使,我写了近一百通,后集书一册。书成之日,朋友们一起喝酒,他端了杯酒敬我,还说他有一句话相赠,他说了,老兄,你的故乡出土了那么多青铜器,你该写写它们了。这句话成了我们的下酒菜,我们仰起脖子,都很豪迈地灌进了肚子。他这一说,只是一杯酒的时间,而我为此,付出了一年半的光阴,在广州的《随笔》杂志开设专栏,写了三十来篇关于青铜器的随笔,2009年被紫禁城出版社结集为一本《青铜散》的书,出版后,很受市场青睐。
穆涛的话说到了要害上, 我乐意听他说话。
在我的枕边,放着他的新书《散文观察》,有他这本书伴我入眠,我睡得是很踏实的,当然也还有梦要做。有好多次,就梦到他书里的话,都是我入睡前,读得会心一笑的句子。
譬如:人格中怕的是虚伪。伪是容易看出来的,不需要讨论,人见人憎。但虚是需要认识的,散文写作里的虚,更需要认识。
还譬如:文学在实验室里,正如文而不化不是真的文化人一样。散文的手法要有突破和创新,更要有尘世感,一只脚可以云里雾里地摸索,另一只脚要踩到实地。
有此两段话可以了吧,我不能把穆涛的书全抄出来给大家读。仅此我们该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了。他说的都是人话!我在认真地听着,也在认真地实践着。
羞 耻
写过一部《羞涩》的中篇小说,后来又改编成了电影,虽然影响不是很大,其中的一些名词,还是有所流传。我借主人公的嘴说,现在的人啊!说假话是不会脸红了。大家把说假话视作了常态,偶然地说句真话,倒把他羞得要脸红呢!
近来看英国人斯幕夫·迈昆自编自导的电影《羞耻》,感觉很有意思。欧洲百万乐透奖主持人里奇。这位27岁的笑星,在看过《羞耻》后,还把自己的灵魂扒光了,通过BBC录制了一部专题片,向公众暴露了自己的痛苦隐私——性嗜癖。
里奇现身说法,讲叙自己“善于讨女人喜欢”,有时候,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能与10人以上女子发生性关系;而他平时也是,总把自己身边的每一位单身女性看成他可以从肉体上征服的目标。
身为公众人物,里奇以自身为例,提出“性嗜癖”的问题,该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里奇所以有此勇气,绝非一己的道德建立,而更包含着一种与羞耻有关的自省与自制。国内的情况我不好说,但从里奇的反省言论里得知,西方男人的性生活之开放和无度,几欲达到“滥”的程度。还有富豪和权贵们,也都有广泛的非正常性关系。他以为,这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品行问题,而是一种生理或者心理上的病态。活跃在欧美世俗生活中的心理医生,对此也作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性嗜癖”是人的一种精神疾病。
呜呼!我们国人闻听此话,可能会有一种被启蒙的惊讶。
其实,国人并非对此完全糊涂不知,譬如坐在帝王宝座上的人,就有权“后宫佳丽三千”,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一切的可能,都只为权贵者大开方便之间门,而平头百姓就不能了。
我说不好,但我想推荐一本书给大家,那就是章诒和出版的长篇小说《杨氏女》。
这部书作保持了章诒和一贯的文字风格,在文学性的叙述中又夹杂了十分浓厚的纪实性,让人读来,不知是她的虚构,还是她对史实的发掘。正如她自述的那样:“一次,我下山到劳改农场的场部领农具。一路上,先后迎面走来三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囚。一打听,都是通奸杀人罪犯,奸夫全枪毙了,她们徒刑20年。”
其中章诒和讲了个叫杨芬芳的女人,她是作品《杨氏女》的主角。与她搭伴儿的,还有刘氏女和邰氏女。章诒和说她在和她们的接触中,发现“女人除了吃饱穿暖和传宗接代外,她们也需要性快乐。”无独有偶,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一书,对此亦作了非常明晰的阐述,“西方的性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像外星人一样遥远。”这一点,成了杀夫女囚的杨氏女,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农村青年何无极不知道,激起妻子杨氏女举刀砍他的原因,就是他请求杨氏女给他“口交”。
“爱就是惩罚。”许地山天才的一句话,我过去无法理解,想来读到这句话的人,都有个滞后认识的过程。不过,人有病,又能怎么办呢?我想起一句俗话,“狗不要脸,一脚踢死;人不要脸,无法可办。”民间的态度,便是这样的无可奈何,但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些许人性的温暖,而庙堂之上的态度,就很冷酷了,祭出来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先教育之,教育不成法来办。
呜呼,杨氏女杨芬芳是被法办了,但是否治疗得了她的“羞耻”病。
隐 居
下雪天,读书天。不知有谁这么说过没有?说过了,不要骂我抄袭,因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去年冬天,古城的那场雪,给人的感觉,仿佛天是雪做的,天塌下来了,一猛子就把古城埋在了雪里。这个时候,不出门是明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于是,我从书架上随便地抽出一本书来,是顾随看似随意的涂抹,买回来随便翻了翻,就插进书架,这时候再读,便读出了不同的况味。我得承认,面孔古板,很有些老学究气派的顾随,其实是很吸引人的,我读了进去,顺着他的思路,这就发现了辛弃疾,发现了苏东坡,还有杜甫、李白,以及陶渊明,曹操等一干历史人物。
好像是,顾随对辛弃疾的喜爱胜过了苏东坡,他写辛弃疾时,一口一个“辛老子”,或者是“稼轩这老汉”,仿佛那个把酒临风的词人,就是他的亲老爷子一般亲切。有此兴致,他也就会这么看待杜甫的,他写杜甫,就同样的以为杜甫是胜过李白的,他说“老杜诗真是气象万千,不但伟大而且崇高。”而李白“才高惜其思想不深”,以至“诗豪华而缺乏应有之朴素。”对于顾随的观点,我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但也使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关于苏东坡、辛弃疾,关于李白、杜甫……窗外的雪没有停,在风的作用下,常常会有几片硕大的雪块,攥成一个拳头,擂向我的窗玻璃,砸得薄薄的窗玻璃发出惊人的声响,如此这般,倒显得家里安静,我没有抬头,也不换眼睛,深情地读着顾随,这就读到了他关于佛学的研究了。
佛学是个大学问,玄而又玄,年轻时候,我是躲着而行的,上了些年纪,对这方面的著述,很自然地有了一些兴趣,迷住了,就想往深里去翻一翻,譬如南怀谨,譬如李叔同,我后悔自己没能更早地阅读他们,在这个下雪天,我又一次后悔,没能更早地阅读顾随,他们关于佛的研究,太让人服气了……结果是,我从我读书的家里,不能自禁地抬起了头,透过窗玻璃,还透过漫天的雪花,去瞭望不远处的终南山。
这是不错的,我居住的小区,在古城的南郊,天气好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终南山,苍劲而高峻,神秘而幽缈……我听人说,就在如今,终南山里有不少于500人的隐居者。
在这个壮阔的雪天里,我为他们操起了心,担心他们居住得可暖和?吃喝得可充足?这么操心着他们,我不自觉地伸出手来,做了一个火炉子上烤火的姿势来……这个姿势把我自己惹笑了,因为我的家里有政府统一的供暖设施,而唯独没有我要取暖的火炉。
隐居在终南山里的人,他们享受不到现代化城市的幸福,他们避世到山深林密的终南山里,那种传统的幸福,他们总该能享受到吧。这么想着他们,倒使我向往和羡慕他们来了。
隐居终南,不能仅限于个人的行为,更在于个人的修行,何况信息化了的社会,哪里是隐居的好去处呢?难找,太难找了,如果有那个念头,其实何处不能隐居?自己温馨的家,也可以的,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专注于一种学问或者别的什么,不都是一种很好的隐居。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心。
吴克敬
陕西省扶风县人,西北大学文学硕士。出版《梅花酒杯》《日常的智慧》《把窗子打开》《真话的难度》《渭河五女》《碑说》等作品集多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