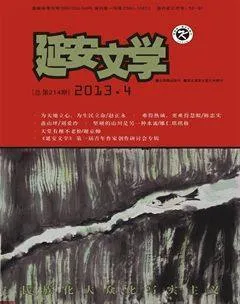天堂有棵不老松
2013-12-29谢京帅
很久以来,就想写写父亲,用自己笨拙的笔真实地记录父亲饱经风霜、艰难坎坷的一生。但每每提笔,又怕自己脆弱的心情无法表达出那种父爱如山的情感,所以未及成字,泪已潸然。因为父亲太伟大,而我却太渺小。但是,父亲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力量却时刻感染我,使我没有理由不写写我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有艰难曲折,忍辱负重;有坚强不屈,执着忠诚;有豁达乐观,大气从容……在儿女的眼中,历经坎坷、铮铮铁骨的父亲就是一部不老的传奇,侠骨柔肠、善良宽厚的父亲又是值得儿女一生敬仰的典范。
父亲像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永远屹立在儿女的心中!
一门英烈 仅存幼子
当年安定县(今子长县)李家岔枣树坪有一户谢姓人家。谢家的三兄弟老大谢德惠、老二谢占元、老三谢德元后来都以不同的方式被人们尊重和怀念,因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烈士。
1919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五),父亲谢绍生就出生在这个家庭。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家族,因为他的亲三叔、我的三爷爷谢德元就是谢子长,西北革命领袖,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而他的父亲——我的爷爷谢德惠,又是那个庞大家庭的“大掌柜”。当年的谢家,有收入丰厚的骡马店,有象征身份地位的私塾学堂,有足以供子孙安享富裕的田产,是“十里八乡闻名”的大户人家。三爷爷是我爷爷最疼爱、最器重的弟弟,他舍得花钱供弟弟上学,想方设法让过往客商给弟弟传授本领、增长见识。三爷爷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死都不回头的共产党员后,爷爷不惜拿出家中财产作为经费,招兵买马拉队伍,支助三爷爷“闹革命”。他自己也拉着拈香结拜兄弟任广盛(烈士任志贞之父)、刘海旺(后来的儿女亲家)、亲姑表刘存元(刘明山之父),成为三爷爷在安定农村发展的最早的4名共产党员,爷爷曾任安定西区区委书记。爷爷送妻家的兄弟进了部队,送侄儿跟随了三爷爷,最后,将貌堂堂、虎生生的五个儿子全都送进了“老谢”的“子弟兵”中,除暴安良,惩恶扬善。
1932年9月,陕北土皇帝井岳秀部张建南营偷袭了我的家乡枣树坪,扬言“赏银五百两,活捉谢子长,捉住谢家人,一个都不留”,恨不得斩草除根,铲除革命的火种。二爷谢占元、二伯谢福成、二叔谢绍斌及其他七名革命者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当时,三爷爷第二次担任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率部在陇东、照金、南梁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专门请了阴阳先生,雇佣几百个民工,丧尽天良地在我家后背山脊凿开一个一丈宽一丈深的沟壕,决意要挖我家祖坟,破风水,“斩断谢家龙脉”。当时家里男丁都跟了队伍,女眷和老人孩子四处躲逃。慌乱中,年幼的父亲与家人走散,从快乐无忧的“富家子”一下子变成了颠沛流离的“逃难儿”,饥饿、追杀、死亡如影随形。机灵的父亲隐姓埋名,一路讨吃找寻亲人。逃难到清涧县解家沟一带时不幸染上疫病,上吐下泻不省人事。多亏张姓人家好心收留,并用民间偏方保住了父亲的性命。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身子稍有好转,父亲就离开解家沟,绕过永坪,在蟠龙川一带靠打工糊口。一件老羊皮袄,既当衣穿,又当被盖;白天放羊,晚上给主人推磨,受尽了欺凌。直到第二年冬天,三爷爷受中央北方代表的派遣,担任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从北平回到陕北,几经周折,才在宝塔区张坪一带的羊群里找到了骨瘦如柴的父亲。三爷爷搂着他最疼爱的侄儿,心疼得直落泪。从此,父亲就跟着他最敬仰的三叔谢子长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时父亲年仅13岁。
父亲的第一支“枪”就是我的三爷爷送的,是用木头做身,用烟煤染黑的假手枪。生性要强的父亲暗下决心要用真本事从敌人手里夺一只“真家伙”。在景武塌战斗中,机智勇敢、冲锋在前的父亲果真缴获了敌人6杆枪,让人刮目相看。三爷爷也高兴得让父亲从战利品中选了一把手枪,作为对他的奖赏和鼓励。从此,父亲表现更加出色,战绩连连。父亲与他的三叔在残酷的战争岁月中尽享难得的“父子亲情”,这也成为他少年时期最难忘和最值得珍惜的往事。
拥有我的三爷爷这样的父辈是父亲一生的骄傲,同时也注定了父亲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从三爷爷投身革命后,家大业大、人丁兴旺的老谢家为革命付出的代价,绝不仅仅是财散物尽、家道中落,仅被敌人残杀的至亲骨肉即多达十余人,留下老小寡妇人数,虽不及戏剧中唱的杨家将12寡妇,但也差不多了。1931年秋,爷爷被捕入狱,肩上披枷,脚上戴镣,严刑拷打,受尽折磨。大伯为救爷爷,被敌人生生用乱棍打死。1935年5月,二伯福成在甘泉胡皮头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29岁。1935年12月,三伯绍安在榆林鱼河堡作战阵亡,年仅27岁。1933年11月,正在生病的四伯财娃被敌人在马圈坪抓捕,当即在院子里被铡刀铡死,年仅16岁。1933年10月,15岁的五伯被敌人暗害,直到第二年才在山上找到尸骨。那年大旱,田野里寸草不生,唯有掩埋五伯的田埂下长了一簇蒲公英。爷爷生了六个儿子,五个就为革命牺牲了。爷爷一家如此,二爷一家也是如此。1934年,在安定县城监狱中被敌人关押了两年的二爷,最终被敌人折磨而死,时年44岁。1935年3月,二爷的次子绍斌被敌人杀害于安定城西门外,年仅23岁。老谢家为革命不仅献出了儿子,还献出了女儿女婿。1934年,二爷的年仅9岁的幼女、我的玉梅姑姑,在躲避敌人的搜捕时,在山中病饿而死。1936年2月,爷爷的女婿、陕北红军中著名的勇将、红28军3团1连连长陈文宝,在军长刘志丹带领下出发东征,在绥德义合的大王庙与敌军史老幺骑兵遭遇,与杨琪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3岁。……白发人送黑发人,接连二三的残酷打击,即就是钢铁汉子也难以抵挡。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中,对爷爷打击最大的,无疑是我的三爷子长的牺牲。1935年2月,三爷爷由于伤势恶化,不幸逝世,支撑爷爷最强大的精神支柱终于倒了,从而彻底击垮了能干的谢家“当家人”,爷爷终于倒下了,一度精神失常。而奶奶的眼泪早流干了,她甚至都不会哭了,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奶奶才会从心底发出一声声呻吟,这声音比哭声都凄惨。父亲成为爷爷6个儿子中唯一的“独苗”,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一场又一场的灭顶之灾。年少的父亲别无选择地长大成人了,用依然瘦弱的肩膀撑起了谢家“少掌柜”那义不容辞、事实上也无法推辞的责任与担当。
三爷爷牺牲后,为了躲避敌人,先后被秘密埋葬过三次,每一次父亲都是至亲的捧牌孝子。
1935年11月,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将西北革命根据地调整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委。父亲的三哥、我的三伯、红4团团长谢绍安,被党中央任命为神府特委常委、军事部长。12月,刘志丹亲自给三伯写了命令,命令他率部护送新任的特委书记杨和亭等去神府苏区上任。走到米西鱼河(今属榆阳区)一带,与敌86师史老幺骑兵团的两个连遭遇,三伯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5岁的父亲赶着牛车,把三伯从几百里之外接回老家,在楼门洞口点起一堆火,慢慢地煨烘,硬是将已经冻僵变形的三伯的身子抚平,双腿揉展,穿上一套崭新的军装,仔仔细细地为三伯缠裹好绑腿,然后肩挎军用包,腰别盒子枪,全副武装,体体面面地背了口柏木棺材送走。
父亲还曾经在死人堆里认领战死的亲人,在荒郊野岭寻找被害的兄长,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机警地混进法场,找回身首分离的至亲尸骨……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一个十多岁的少年面对这一切所受到的心灵的煎熬与折磨。我只知道,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我的母亲去世时,一生坚强的父亲却对儿女们说:你们都不要穿白孝服了,见得太多太多了,怕了……
对党忠诚 至死不渝
父亲对党的热爱和忠诚是渗进了骨髓的,坚定地信仰共产党是他终其一生而不悔的执着选择。
父亲1933年13岁参加革命,到1983年退休,为党工作了整整50年。他1935年15岁入党,到2003年去世,党龄近70年,为党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他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父辈及兄长们能舍生忘死地干革命,那么在和平年代,他的儿女们必须做党的人,听党的话,为党工作。他曾经教育我们:不管干啥,入不了党,就说明没干好工作。我的兄弟们在部队必须入党,姐妹们在地方,也必须入党。那年我还在读高中,不满18岁,父亲就强烈要求我入党。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关心入党胜过关心我的学习,因而思想上有情绪。没想到特别疼爱我的父亲竟然半年不和我说话,直到我主动认错。我说学校一般不纳新学生党员。父亲说你的户口在村里,那就在村里入。我说我年龄不够。父亲就说刘胡兰15岁就是党的人了,你比刘胡兰大多了。从来不为儿女“走后门”的父亲破天荒为了我的入党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谷兰英,并希望她做我的入党介绍人。直到我积极上进,入党申请被批准后,他才欣慰地笑了。
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在文革期间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对待。红卫兵受人煽动,最初以“豪绅子弟”的名义对父亲揪斗、游街,后来又强加“保皇派”的罪名加以批斗,限制自由,要父亲闭门“思过”,交代“问题”。戴纸帽、跪板凳、挂牌子……父亲遭受了非人折磨。我清楚地记得,文革结束时,父亲一头浓发竟然全部脱落。随着遭受迫害的逐渐升级,父亲的身心受到了极度的摧残和折磨。我的舅舅知道后,就连夜把全身浮肿的父亲从扣押的地方救出来,背着行动不便的父亲,躲藏在80里外寺湾乡偏僻的张家渠治病养伤,才躲过了一劫。
七十年代后期,许多冤假错案都陆续平反昭雪,可是父亲的事却一直无人问津,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复出后,仍然被安排在基层供销社工作,一晃就是十多年,直到退休。很多人都说:按老谢的资历和能力,就算不被重用,也不能被“贬”,让人家不明不白地在几个乡镇供销社转来转去啊!人们都为父亲鸣不平。父亲却说:知足了,比起那些流血牺牲的亲人,起码还活着!其实,父亲的内心不是没有痛苦,不能尽自己的本事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应该是父亲最难过的事,但父亲仍然坚信,党和组织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一定会给他以公正的对待。父aae0ef0ec95efb2678e0f6b8bee6d5d3c6ed14efb7cb231aea7b0873ba141d99亲退休后,由于在京许多老干部的证明与呼吁,组织部门经过层层考察,决定父亲享受厅级待遇。其实那时父亲并不在乎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内心期待的是组织对他的公正评价和认可。他退而不休,依然想尽自己所能为党工作。当年延安革命纪念馆(旧馆)建成后,父亲仔细认真地参观了每一处展板。当他来到“刘志丹灯盏湾看望受伤的谢子长”的雕塑前时,双手抚摸着两位志同道合、战友情深的烈士,泪流满面。从此,他找到了退休后的新岗位——做一个忠实的守陵人,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的历史,珍惜幸福的生活。于是,每天早饭过后,父亲会随着上班的人流准时定点地赶到子长烈士陵园,打扫卫生,栽花种草,督查工程,还主动担任义务讲解员,为营造良好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发挥余热,十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
担当重任 义无反顾
三爷爷去世后,父亲在志丹爷爷的领导下继续战斗。1935年9月,红25、26、27军在永坪会师后,一天,父亲接到通知,说刘志丹点名要见他。父亲想,一定是布置重要的战斗任务。当他兴冲冲见到刘志丹后,却得知首长们希望父亲离开部队。志丹爷爷说:老谢家为革命牺牲得已经太多了,万一再有什么闪失,对不起“老谢”,得为“老谢”留条根儿啊!父亲一听就急哭了,死活不愿意。首长们开导他:谢家现在老的老,小的小,得有人照顾。你如果不回去,组织还要派其他同志去,否则不能让逝者安心啊!为了宽慰父亲,部队决定为父亲保留编制,政治待遇不变。
就这样,父亲以军人的身份,穿着军装回到了地方工作,同时担负起照料一大家孤儿寡母的重担。多少年后,父亲谈起往事,淡淡地说:虽然难舍部队,但那时那地,别无选择。党中央及各级政府时刻关怀着谢家人,想方设法保护烈士的家属,自己更应该为组织分忧。晚年的父亲经常练习毛笔字,他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时发现,“忠孝”两个字是父亲写得最多最多的。直到那时,我们才深深体会到父亲一生的心中藏有多少委屈、多少痛苦、多少无奈、多少沉重……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边区,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同时安排后方机关和人员东渡黄河。保卫局安排父亲带着家属随边区政府一起转移,过黄河时,由于河水暴涨,上游打仗,后有追兵,险象环生。父亲后来回忆说,他眼睁睁看着同行的一条船翻入河中,人员全部遇难。能够逃过一劫,真是万幸啊!
延安光复后,父亲重返故乡。家中粮食被国民党糟蹋一空,又遭大旱,颗粒无收,全家人吞糠咽菜还险些饿死。
1948年,中央选派一批革命后代去苏联学习,父亲也是其中之一。面对一大家老小艰难生活的实际情况,父亲毅然放弃了这人生难得的机遇。
解放初期,父亲担任县政协副主席,同时当选陕西省人大代表,并作为省政协副主席人选,由省委两次派专人牵着马从西安来家乡接父亲赴任。人马刚到家门口坡底下,奶奶一听就晕倒了,救醒后抱住父亲的腿不让走。面对失去五个亲生儿子,历经人生磨难,再也受不了任何打击的老母亲,父亲又一次选择了放弃。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的祖辈为革命做出的无私奉献。1954年,时值国庆5周年,中央特邀烈士后代赴北京参加游园庆典活动,父亲也收到了一封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的珍贵请柬。父亲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还在怀仁堂请烈士后代们看了梅兰芳演出的京戏,父亲也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北京之行是幸福难忘的,北京之行也使父亲更加深切地理解了自己肩头担子的分量。父亲说:现在的生活多好,可那些死了的亲人,一天福也没享过啊!从此,尽心尽力照顾好活着的亲人就成为父亲一生的心愿。
父亲亲生儿女8个,但他只亲自操办过三宗婚丧大事。
第一件是娶儿媳妇,就是1935年牺牲的我的三伯谢绍安的儿子结婚。三伯牺牲时,他的儿子还是刚出生40天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面对烈士的遗孤,父亲对这个侄儿倾注的是亲生父亲般的感情。侄儿要结婚时,父亲决定好好过一回事情。他托人专门从北京买回瓷质的碟、碗、盆、勺、筷,就连筷子架、白色花边的桌布也要准备齐整。摆八碗,喝烧酒,将侄儿媳妇用12匹高头大马从安定县孙家塔娶回家,整整过了三天红火喜事。父亲说,我得让三哥放心啊!
第二件是发葬我的奶奶。奶奶去世时,父亲也是披麻戴孝,家里摆了三天八碗,体体面面地送走了老母。父亲说,战争年代,老谢家死了那么多亲人,都是秘密发葬,没有过过事情。三叔在世时,母亲作为长嫂,对这个弟弟倾注了慈母一样的关爱,做饭、洗衣、洗伤口,站岗放哨传消息,为部队缝军装、做军鞋,为支持三叔闹革命,忍痛割爱将亲生的五个儿子和女婿全送到了部队,没享过儿女的福。她是伟大的母亲,革命的母亲,应该厚葬。
第三件是出嫁女儿。战争年代,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生下我大姐后不幸让病魔夺去了生命。尽管父亲和我的母亲给予了大姐更多的关爱,但为了告慰逝者,大姐出嫁时,父亲也破例把婚事操办得红火喜庆。
此后,父亲宣布,他一生中一定要亲自操办的几件婚丧大事都办完了,以后不论娶媳还是嫁女都不再操办。
商业奇才 造福百姓
父亲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工作,长期担任乡长。解放后转入商业供销系统,最早在我的家乡李家岔搞供销合作社。父亲由此走遍了李家岔的所有拐沟支岔,遍访民情。群众生活中最需要什么,货源在哪里组织,农民生产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农产品如何向外销售……父亲的心中总是一清二楚,工作总是那么得心应手。每次逢集,父亲位于供销社的宿办合一窑洞总是你来我往,热闹非凡。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四乡八邻都乐意到那儿坐一坐,拉拉家常。农民朋友高喉咙大嗓子能把窑顶掀翻,卷烟呛得人流泪,有的还时不时随口吐痰。可父亲不嫌弃,不厌烦,他常说,人不能离开老百姓。窑洞外老远,就常常能听到父亲极富感染力的朗声大笑和众乡亲无所顾忌的倾情交谈。父亲心里始终装着农民,把百姓的需要作为供销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因而深受群众拥护和敬爱。他所在的供销社货物齐全,供销适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亲的有胆有识,经营有方。
1980年,正值父亲在北京治病。他利用休养时间考察各个市场,发现北京的大商场货柜上挂满了款式新颖的男女成衣。目光敏锐的父亲一下子抓住了商机,当即采购了一大货车拉回了陕北。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未劲吹到偏远的家乡,有人担心小地方成衣不好销,怕积压赔钱。父亲却凭着多年的经验预测到良好的销售前景。他首先对男女售货员进行培训,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身材试穿各种型码的成衣,了解衣服的款式及特点。货一上柜台,果然不出父亲所料,购买成衣的群众络绎不绝,非常火爆,售货员根据试穿的型号为群众销售满意的衣服,不到一个月全部售完。从此,在老家的村落小道、集镇闹市,随处可见色彩鲜艳、时髦洋气的成衣扮亮的俊女子,和用美观大方、质地考究的的确良、涤纶武装起来的“时尚男”,他们一改过去买布裁衣的传统,羡煞城里人!
父亲是一个成功的经营者,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创业者。他先后供职于李家岔、安定、寺湾、余家坪、栾家坪等多个基层供销社。每到一处,总是白手起家,从基础建设到网点布局,从人员培训到业务拓展,凭着超强的能力和造福百姓的使命感,总是管理有方,成效显著,广受赞誉。
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嘱咐,不要张扬,不要麻烦人,我们没有过多地告知亲朋好友。可是,听到风声或几经打探得知消息的亲友们来了,他曾经节衣缩食支助过的学生们来了,在平时生活中被他人格感染的街坊四邻们来了。尤其是那些曾经与父亲情同手足的农民朋友,他们远道赶来,不停地念叨“好人啊,应该长命百岁”,为父亲哭泣,为父亲守灵。大雪过后陕北的寒风刺骨,花圈、挽帐伴随着留恋父亲的人们定格成一幅感天动地、至善至诚的画面,永久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父爱如山 大爱无疆
父亲对整个家族的爱是深沉的,认为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我们这个家庭的爱则是温馨的,是源于天性的自然流露。
母亲是父亲自己讨回的妻子。
说来话长。1934年1月的一天,恢复红一支队的重要会议在外爷家的土炕上召开。外婆特意给生活艰苦的开会同志们煮了些鸡蛋,还烙了饼子。那时,我的母亲尚未出嫁,与姐妹们平时是根本吃不上这些好东西的,不免眼馋,抓起鸡蛋想吃,被外婆一把夺回来。最后在我三爷爷的劝说下,外婆才将一个鸡蛋用线绳子划成两半个,分给她的孩子们。三爷爷看到这个情景,抚摸着我母亲的头,对外爷说:现在闹革命,让娃娃们都受苦了。将来日子好了,咱们做儿女亲家。没承想,三爷爷去世后,谢家也败落了。年轻的父亲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更是艰难度日。于是,他果敢地来到我的外爷家,重提当年的话题。重情重义的外爷让父亲在他的几个女儿中挑选,父亲一眼就相中了三姑娘——我的母亲。一进谢家门,父亲就告诉母亲:在咱们这个大家庭里,只有你是有丈夫的人。凡事要能吃下亏,不能与失去丈夫儿子的亲人比高低。母亲心地善良,吃苦耐劳,干活在前,享受在后,从不计较得与失。她对待每一个孩子都一视同仁,从不分亲生与非生。母亲还心灵手巧,就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能将各种布头拼接在一起,为我们剪裁、缝制漂亮的衣服,把儿女们收拾得干干净净,穿戴得光光堂堂。父亲常说,是你们的母亲让一个破碎的家重新焕发了生机,人口越来越兴旺,日子越过越好。
父亲生养了10个儿女,长大成人8个。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么多孩子,放到现在的话,早超生了。也有人说,不多,谢家为革命献出了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如果这些孩子给那些烈士们顶门立户的话,一家一个都不够啊!父亲则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将大山一般的爱倾注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关于儿女,父亲的心中还有一块不能碰的疤。我大哥3岁时,母亲生了一个女儿。我的这个姐姐聪明伶俐,乖巧可人,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然而,就在她4岁时得了急性肺炎不幸夭折。父亲接到消息后,连夜从几十里外的单位赶回来,抱着山洼里女儿的尸体,哭着喊着,陪了一夜。那晚天下着大雪。命运坎坷的父亲,人到中年,再次遭遇了生活的重创!
从此,父亲把孩子看得更重了,倾注的关爱也更多了。从我记事起,就没有看到父亲动过儿女一个手指头,说过一句重话。
大姐是父亲宠大的,小时候得了很严重的肺病,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父亲将爱女放在藤条篓中,抱在怀里四处求医,不惜重金购买进口药。“如果我不是父亲的女儿,在当时条件下,十个我也活不了。”每当大姐说这话时,满脸都洋溢着幸福与骄傲。
二姐说父亲很疼她。幼年的二姐身体瘦弱,父亲特意让母亲给二姐吃小灶。二姐上高中离家住校,父亲会定时去学校看望,并带去亲自烤的馍片和女儿最爱吃的红枣。
二哥三弟说,父亲关心他们胜过关心自己。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在同一个部队服役的兄弟俩要开赴前线。父亲坐了两天两夜的班车,专程前往部队看望儿子,给他们鼓劲壮胆!
小弟小妹是父亲最大的牵挂。父亲年老后,最小的两个儿女才刚刚结婚成家,又都在外地。父亲不时地念叨:“我老了,最放心不下的是老七老八。你们大的都要照顾好他们,引导他们,诚实做人,快乐生活。”
其实,我才是父亲的最爱。从我记事起,就是在父亲的背上长大的。他为我洗头洗脚剪指甲,穿衣喂饭梳小辫,父亲留给我的是最幸福的童年。每次该到洗头的时候,总是推脱不愿洗,就要等父亲回来。母亲没办法,只好叫人捎话,说你的宝贝闺女要洗头了。父亲只要接到口信,肯定回家。包包一放,第一件事准是给他疼爱的女儿洗头。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就是太想父亲了,盼他多多回家,才以洗头作借口来“争取”父爱。时至今日,想起热水在头上浇淋,想起父亲宽厚的大手在头上轻轻摩挲,我的眼眶总会湿润,心头总是荡起一股股暖流……
热爱生活 豁达宽容
艰难曲折的生活不但没有击垮父亲,反而让他更加执着坚强,更加懂得生活,善待亲人,感恩社会。这是父亲留给儿女又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一直以来,政府对为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谢家人多方予以照顾,父亲在感恩的同时,总是力所能及地减轻党和政府的负担。解放初期,每当他出差在外,接到政府领取慰问品的通知时,总是刚强地绕道走。在他看来,谢家的每一位烈士为革命奉献一切是应该的,连人都舍得给,财物有多少是个够啊!而战争年代,由于闹革命而拉下的许多亏欠却在他心里清楚地留下了一本账:某年某月,谢家的子弟兵路过哪个村,人家给送了多少粮草;某年某月,有谁给他三叔送过饭,放过哨;某年某月,哪家的儿子跟着他三叔闹革命战死了,后人生活困难需要照顾……父亲认为,这些“债”是谢家先辈们欠的,谢家后人应该力所能及地去回报。几十年来,他省吃俭用,竭尽所能,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从不抱怨,从不奢求,只图心安理得,活得踏实!
生活中的父亲是个极富情趣的人,他豁达乐观,爽朗的笑声伴随终生。少时的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但却博学多识,见解独到,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父亲的案头和枕边总是放着许多革命传记类书籍,每每读完一本,总要把体会讲给我们听。父亲穿着朴素,却大方得体。他将最钟爱的中山装穿到了极致,不论黑色还是他喜爱的灰色,一上父亲的身,立马就显得庄重威严,气度非凡。父亲的整洁也是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他的衣服从里到外,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年四季,总穿黑布鞋。鞋底磨薄了,鞋面磨破了,他还要洗得净净的,亲手补好,送给生活困难的老乡。
父亲一生从没有被困难吓倒,做事干脆利落,从容果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对自己要求严,对儿女的要求也严,从不为儿女的事托人情拉关系。他常常告诫儿女:不能忘本,更不能吃老本。父亲退休后,当时的关系在供销系统。由于效益不好,工资总是不能按时发放。他多次叮嘱儿女,单位困难,不要去催领工资,否则,上班的职工生活就更紧张了。
1980年,父亲身患重病,诊断为“胃癌”。大哥果断地把父亲送到北京,住进了尤祥斋奶奶任院长的西苑医院,派最好的医生为父亲诊治。手术前,长时间难以忍受的疼痛常常折磨得父亲大汗淋漓,老人家却咬着牙不吭一声。他的坚强终于战胜了病魔,两个月后,父亲康复出院了。他乐观地说:我这个人啊,大难不死,磨难都过去了,后面就该我享福了。
2000年,父亲再次病重住院,五天昏迷不醒。医生自感回天无术,下了病危通知书,让“拉回去,准备后事”。就在我们兄弟姐妹不知所措,哭天抹泪时,父亲却在第六天又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他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一觉睡得可真长啊!
这就是我那历经磨难,痴心不改,永远坚强,永远乐观,值得我们永远敬爱的父亲。
十年前的2003年1月8日(农历腊月初八),父亲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从此,天堂里多了一棵永远苍劲挺拔的不老松,而人间却少了一位疼我爱我的老父亲。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产,但他光明磊落做事、宽容真诚待人的风范长在,刚直不阿、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永存。父亲用无声的爱,教会了我们执着和坚强,铺垫了我们包容和坦诚的人生之路。父亲那共产党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精神,将是我们一辈子享用不尽的丰厚遗产。
有人说,石斛兰是父亲节之花,她具有秉性刚强、祥和可亲的气质,寓意父亲的坚毅、勇敢、亲切而威严,最能表达对父亲的敬意。而我以为,那高耸入云的青松,才是父亲形象的化身。有首老歌这样唱道: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四季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屹立在山中。
我以为,这歌正是为父亲量身定做的,唱出了父亲的品格、特质、气场!
时光易逝,父爱依然。父亲那熟悉而殷切的叮咛总是萦绕在我的耳畔,父亲那充满期待的目光总能在我遭遇挫折孤寂无助时,燃起奋发的信心和勇气。
父亲,就是天堂里的那棵不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