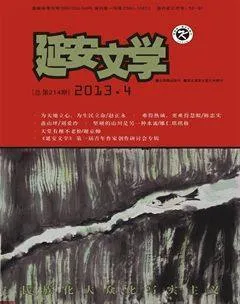写作生态和不痛苦原理
2013-12-29李江华
写作中的时间
我和刘全德算不上绝对熟悉,但我认识他。他晚上几点睡觉,这个我一般不打听。但我知道一点,他应该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写作。和众多上班族一样,每天朝九晚五,过着两头见不到太阳的日子,什么时候可以写一写呢?
也许他会说:在公交车上,在开会走神的时候,在地铁呼啸着穿过通州街区的时刻,在菜市场上,在屋子后边的菜地里看瓢虫爬过空心菜菜叶的时候,在匆匆灌下第一瓶燕京啤酒以后。坐火车,坐汽车,坐马桶,什么时间不能写作呢?
对,这是他的风格。把一个稿子熟悉到极致以后,抽一个极短暂的时间,迅速完成。只有极好的腹稿习惯,才能应对如此生活下的写作。
这不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写作的时代。也不是你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的时代。骑驴找诗和映雪读书,现在是小资风雅,是新闻事件,名士逸闻,而不是写作现实。
有一次,全德开玩笑似的说:除了国务院报告,他写过几乎所有的文体。
他在电脑键盘上和压缩过的时间搏斗,在遗忘到来以前和语言迅速成交。
坚持或放弃
还有,他必须写得足够快。出产的数量和质量又必须调整到大致均衡的程度。
写作正在成为规模庞大的职业,而文学的写作也已成为职业,但它属于贵族。
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成规模地写文学作品,代价惨烈。
除了身体好,还要心态好。最起码保证自己不生病、不发疯。这就是事实。
时间——速度——均衡,制约了刘全德这样的写作者。
也就是说,在如此生态里,他们长期写作的结果却往往是:写得少,写得精,写得身心俱疲。我不担心一个写作者的慢,我担心的是一个写作者会因此中断他的写作进程,那将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要知道,写作是一个时间游戏。在一生的某些时段,会出产某些特定作品。
刘全德又显然是一个有语言洁癖的人。如果写诗,他就是“苦吟派”;如果写论文,他就是“学院派”;如果写小说,他就是“有聊派”——不把任何一个无聊的词汇放到字里行间。可是,世上有那么多金子只供你一人锤锻吗?
这是一种带有时代印记的写作。写作的大众化,反而凸显、放大了它的时间代价。我们面对的是“不贵族,毋文学“的基本转变,这对历史意味着什么?
所以,刘全德面对的写作生态就是:要么放弃,要么永远坚持。
两者都是很痛苦的。
不痛苦原理
仔细读过全德的几个小说,我发现,他在小说中写了很多足够痛苦的事件。
《白日梦边缘》写一个中学生在畸形家庭里心理失衡,于一场混乱的殴斗中失手杀死同学兼朋友,过着亡命天涯的生活,后来选择了投案自首。《在美好的日子里》,写一个出外旅游的人回家后遇到“鸠占鹊巢”的怪事,而那个取缔他“丈夫”身份的人竟和他本人长得一模一样。这是一次真正的家庭危机和心理地震,当幻觉消失、真相大白后,他却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这里,还有新出的一篇,《土末村纪事》,越发出奇,写到一个叫作土末村的乡村世界里各种各样的怪人和各种各样的怪事。叫人愉快的经历几乎绝迹,写的是北方乡野的黑暗部分,不透光的那些事物。七口唾沫培育出的人祖爷,一骂惊天的奶奶,人形羊蹄的孩子,照得见妖魔鬼怪的青铜镜子,学猫叫的小白鸡,地主、游行、上吊、仇恨、嫉妒、梦语、穿越乃至死而复生、蒙太奇式的场景并置,真是极度魔幻,极度聊斋,但——也极其痛苦。
但读者读到这个文本的时候决不会难受,因为,这些痛苦是被化解过了,被参透了,也被作者本人强悍的内心消化过一遍。作为“表现出来”的痛苦,它必须是“高于生活”的、“升华”出来的一种面貌。要不然,狂笑唯使人晕眩,而长号适足以烦心罢了。生活和艺术,并不是泥沙俱下的关系,而是互相选择、互相摒弃的关系,甚至,是对立而不是统一的。在当今这个俨然是超现实般的世界上,艺术的基本原理不为所动地坚持着自己。没有艺术选择,也就没有任何艺术表现。在选择苦难作为写作主题的时候,一个作家更加需要适度引入这里所说的所谓“不痛苦原理”。
有一天,刘全德兴奋地说:他感到自己懂了点俄国文艺。我问:那是神马意思呢?他说:俄罗斯的灵魂,痛苦而折断翅膀的天使,发出坠落、粉碎之前的呼号,是那个民族灵魂的写照。我说:你这表达太拗口了,不好!
实际上,我赞同这一见解。
也许刘全德会很喜欢俄罗斯的艺术,并从中有所掌握。我相信是这样的。消化痛苦,并以动人的、美丽的形式表现这现实必有的痛苦里深深埋藏的爱恋,属于大地本身的伟大民族,总在呻吟中求索,这就是“不痛苦原理”的艺术立场。写得深入,尤其是在写到人性弱点的时候达到惊人而深刻的程度。不唯如此,还写得动人非凡,这就是痛苦贡献于文学艺术的最大意义。我感到,刘全德已经在俄罗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诞生的那些大师那儿察觉到这一基本事实。
正是这个,影响到他写作的性质。
这小说里有一个奋力推马车的细节,即来自于一幅俄罗斯绘画场景。
这种“不痛苦”或“反痛苦”的历史实质和哲学依据是:人类生活中最巨大的事变在特定时段里是无法更改的,此刻,世界作为客体总扮演着压抑和强迫者的角色。席卷其中的主体,来不及发出所谓“个人”的声音。一个作家,下一个作家,都只能唱出某一个声部。于是,作品的声调必然呈现为“非个人”的表演。当你表现一己痛苦时,你可以哭泣;但是,当你要表现属于全人类的、全宇宙的痛苦时,你只能微笑。我们在审视俄罗斯艺术的时候,不难领悟到这一点。
其次,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土末村纪事》里那些或隐或显的幽默。我想,这小说里的幽默正是面对痛苦的一种表达态度,也是一种艺术方向吧。这个小说里组织情节的艺术逻辑掺杂了中国“因果报应”的观念。因果报应是中国小说特有的一种情感逻辑,从积极方面说,它是应对人世沧桑的黑色幽默,是对“消逝”现象的独特解释角度。往往的,在需要对“消逝”表达巨大遗憾的时候,中国人不是耸耸肩膀了事,还要编出一个首尾俱全的故事去传说它,纪念它。孔子的临水一叹,是千古不朽的情感反应——“逝者,如斯夫!”在这个母题里,他肯定说的是一个民族性的惘然和奋发。只有对情感本身的完美施与极度关注的民族,才会把因果报应这种看起来很“消极”的思想观念带入、融化到艺术领域。静观万物和果报三世,这就是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文学,是中国山水的“静”与中国故事的“动”之根底。我以为,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人生兴味。传奇只是表象。传奇性是成熟者反观自我的童话态度。
最后,为什么要把中篇当长篇那样(此间写到七个男人、七个女人)去写呢?
我把这个疑问留下,交给读者朋友评判吧。
为什么写作
我问过很多人。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呢?“
当我抛出这个问题给刘全德的时候,他手机里整了这么一番话:
在语言被文字化以前,人类就发明了两种掌握世界的游戏,一是战争,二是宗教。在语言被文字化以后,人类发明了第三种游戏,这就是写作。对生命而言,战争好比是冬天,杀伐万物;宗教好比是夏与秋,自昏热走向静美。写作呢?必然是春天,对应着萌发、喜悦。写作是生命世界打开和结束的原点,是归零。
典型的东扯葫芦西扯瓢。我很无语。
我回过去:“那么,你为什么写作呢?”这次,没有答复。
我仔细读了读小说,找出这么两段,不知道能不能答出这个疑问:
刚读完《论语》,一场大饥荒来了。
每个人心里都眠着一只可怕的猫,春天会把她叫醒的。
(提示:连在一起读。)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到处埋钉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