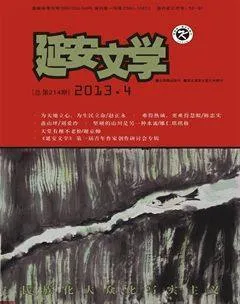暗色的胃
2013-12-29第广龙
第广龙,1963年生,甘肃平凉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参加《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出版五部诗集,六部散文集。
回民的锅盔
我说的锅盔,是大锅盔。多大?锅盖那么大,草帽那么大。不但大,而且厚,有四指厚,有砖头厚。这么大这么厚的锅盔,一个七斤重,买上一个,得两个手抱着,才能抱回去。要是吃,饭量再大的人,即使放到过去,也没有本事一顿吃完一个。
这种锅盔,出自平凉,都是回民做的。只有回民能做出这样的锅盔,只有回民做这样的锅盔买卖。这不奇怪,把小麦加工成吃食,这说起来容易,但叫人都买账,都接受,并且长期认同,回民有天赋,有能力。就说干粮,油炸的麻花、馓子、油饼;烙出来的圆的干饼、长的酥馍;蒸下的馒头、花卷,都是回民的味道好。吃的东西,说好,就是好,怎么个好,又无法描述。不好了,马上感受到,好了,是慢慢体会出来的,只是,一时都找不下合适的语言,说怎么不好,怎么好。回民勤快,吃得了大苦,泾河滩拉沙子,用架子车拉。车槽加高了,加的部分,高度比车槽还高,沙子小山一样高。前头毛驴,套长缰绳,使劲出力;后头人,扶车辕,肩膀上套短缰绳,也使劲出力。回民经营生意,也在行,皮子的生意,茶叶的生意,回民经营,都繁荣。餐馆一家挨一家,回民开的吃客多。在平凉,一个锅盔,一个卤牛肉,一个酿皮子(又叫凉皮),是回民的专营。人们只认回民的。
似乎没有专门的店面,街道上支起推车,一个锅盔立起来,让人看,知道是卖锅盔的,其他的平躺着,就等着买主来了。锅盔一个也卖,半个也卖,这样的时候少;多数是刀子划开,划成三角的小块,一块一块拿秤秤着卖。盘旋路有一家军工厂,早上上班那阵子,工人都是买五毛钱锅盔,边走边吃。这很让人羡慕,说,看人家,到底是大单位的,大清早就吃好的。
加工锅盔,真得费些力气。和面要和到家,手上没劲的人,干不了;团成这么大的面积,还要能定型,不松散,也考验功夫。还得用杠子挤,压,敲,捶,反复无数次,才让面团听话,随人的意图。烤制锅盔,是平底的铁锅,上头悬吊着可以移动的铁盘,也是平的,铁盘上头,堆一堆熊熊炭火,锅盔进了锅,铁盘盖上去,铁锅下头,也是一堆熊熊炭火,两堆火,都是炉火纯青的那种火,有穿透力,力道持久,面饼被上下两头的炭火烘烤,水分失去,身子收紧,团结了,瓷实了,终于,两面都如同盔甲,刺绣般是一圈一圈的焦黄。锅盔就可以出锅了。
我后来见过其他锅盔,像六盘山西边的静宁,出的是油锅盔,个头小一些,清油炸过,是另一种味道;还见过关中一带、陕南一带出的锅盔,更大更厚,夹杂了椒叶末甚至辣椒面,也是一种味道。像平凉回民这样的锅盔,我在别处没见过。这样的锅盔,里头没有放盐,没有放别的调料。就是纯粹的小麦粉,本地的小麦磨出来的,似乎天生可以用来做锅盔,被回民发现了,这样做了,似乎这样合乎了天意一般。人们吃锅盔,要的,也是这种纯粹的味道,粮食的自身的味道。平凉人吃锅盔,都是专门吃,跟前不要菜,锅盔上不抹油泼辣子。一只手捧着,另一只手护着,一口,一口,把锅盔吃下去。吃锅盔掉渣,护着的手接住,接一阵,也送进嘴里。吃锅盔不能猛吃,得细嚼慢咽,一小口一小口吃,不然,堵住喉咙,呼吸都受影响。我就经常见到有的人不停捶胸脯——吃锅盔给噎住了。吃锅盔,跟前,得有一碗凉开水。
为啥?吃锅盔常常被噎住得用水冲冲。锅盔硬,干,吃锅盔,吃着过瘾,噎住了也难受。不过,那也是舒服的难受。的确,锅盔穿过肠肚的感觉,是刺激的,满足的,也是难得的。有一句话,说有牙时没锅盔,有锅盔了又没牙。自然,年轻时不是想吃就有,人老了,吃锅盔容易,却咬不动了。说话漏气的老汉怀念锅盔的滋味,实在忍不住了,嘴里搁进去一小块,慢慢磨,中和半天,才敢咽下去。
这种锅盔,放得时间长,放不坏。夏天也放不坏。出门远行,如果在山里走,背一个这样的锅盔,顶一个礼拜,人不会挨饿,也不用吃发霉的食物。我小时候吃不上锅盔,就在锅盔摊子跟前站着看,戴白帽子的回民,没人过来时低头坐着,有人过来时赶紧起身,热情询问,这么看着,也是一种满足。后来,我外出工作,一年回去一次,假期结束,折返单位前一天,我都要买一个两个锅盔。带回去,切成四块五快,给人送,也自己吃。这样持续了几十年,一直这样,只要回去,一定带锅盔回来。在平凉,锅盔摊子还和以前一样,锅盔的味道,还和以前一样。吃锅盔就吃回民的锅盔,没有能代替的。
葱花面
我许久都没有吃过葱花面了,但是,只要想起来,那浓郁的香味,就浮动在我的鼻尖,伴随着的,还有一丝丝惆怅,一丝丝忧伤。
想起葱花面,我想起了家乡,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我那既明亮,又黯淡的童年。
就像西北长大的许多人一样,我也爱吃面,但在困苦的岁月里,一碗面,不是想吃就有的。有粗粮吃,能把肚子吃饱,已经是难得的福分。假如哪天吃面,一家人的重视程度如同一个仪式。在农村,争强日子,不愿被小看,有的人家,偶尔吃一会面,要站在自家门前的粪堆上,把面挑得高高的,让别人看,我吃面呢。吃面本是家常,却成了稀奇,以至于有人病倒了,不愿吃药,只是说,有这钱,美美吃一顿面,就好了!
在我们家,葱花面,就是病人吃的,老人吃的。有个头疼脑热,不算病,不影响说话和走路。睡在炕上起不来,吃别的,吃不下去,就能吃上葱花面了。家里人口多,煮饭的锅是大铁锅,水烧开了,下面,下一个人吃的面。最好是挂面,是那种细细的挂面。葱花是清油炝的,先切出一撮碎碎的葱花,准备下,然后炝油,不在大铁锅里炝,那样费油,是在舀汤的铁勺里炝。拳头大的铁勺头,倒进去一点油,手端着,从灶火眼里试探进去,悬在火头上,油煎了,倒退出来,迅速把葱花丢进铁勺,哗啦一阵响,还出现一些涌动的泡沫,跟着,葱花就熟了。面捞出来,添进去专门烧好的酸汤,添进去葱花,这时候,看到的是弯曲在一起的面,是清亮的汤,汤上面,油花点点,还漂着葱花,这时候,葱花面就做好了。真香啊,就是在大门外,就是过路的人,也能闻到葱花面的香,家乡人形容这香,有一个特别的字:窜。说葱花面香,就说,窜香窜香的。
印象里,我妈总是为吃的发愁。一家人要吃要喝,我妈从不抱怨辛苦,在伙房里劳作一天,我妈也高兴。只要吃饭时,不论干的稀的,一家人爱吃,我妈在围裙上擦着手,最后一个端碗,也是满意的。最怕的是没有粮食了,没有菜了,吃了上顿,缺着下顿,我妈慌张着,给我爸说,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记得我们家最难过的那一年,红薯干当饭,白菜帮子当饭,我妈的叹息声,那么轻,又那么无奈。
毕竟,饿肚子的日子,在我们家,不多。毕竟,我爸有木工的手艺,天天熬夜,做出的木活,能换来钱,换来玉米和麦子。比起其它人家,虽然谈不上宽裕,但总归没有出现过一锅清汤的情景。回想起来,我的饥饿感,更多的,是对于好吃的那种奢望,比如吃一碗葱花面。
我自然也吃过我妈做的葱花面。躺在炕上,懒懒的,一碗面端来了,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到了被重视,被关心。似乎这也是一种特殊。如今的独生子女,似乎不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像我有兄弟姊妹五个,在母亲眼里,都是她的心头肉,但谁病了,得到照顾,似乎也获得了额外的母爱,那种幸福的体验,大大抵消了得病带来的痛苦。稀溜稀溜吃着面,面条滑溜溜的,吃进嘴里,自己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汤热热的,里头的葱花,有那么一片两片,还带着焦黑,这更让香气变得浓烈。喝一小口,再喝一小口,一定要让舌头感受到烫,感受到烫的刺激,似乎只有这样,葱花面的香,才体会深刻,才能传递给身体的各个感官。这时,我妈在一旁会叮咛,慢慢吃,没人跟你争,吃了,发些汗,身子就轻省了。
过去的人,都是在嘴上挖抓。吃的诱惑,总是最大的。有时,即使没有病,我也盼着得一场病,好吃上我妈做的葱花面。可是,越想得病,病越是不来,让我很失望。那时,我多傻啊,就为了一碗葱花面,竟然这样动心思。
现在,我想吃面就吃面,各种各样的做法,甚至过去没有吃过的,也会尝试。有时在外头吃饭,摆一桌子好吃的,我也愿意吃面,先要一碗面吃,吃饱了,吃不动别的了,也不觉得遗憾。可是,这些年,我没有吃过葱花面,一次也没有。曾经那么向往的葱花面,我不再想吃了。吃的东西,也会吃伤人。有的人不吃肉,就是小时候难得吃一次,有机会放开吃了,拼命吃,结果以后见了肉,心理上排斥,再也不吃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吃的,记忆太深,却又容易引起难受,也不愿意再吃。我不吃葱花面,就属于后者。
都快七年了,给我做葱花面的母亲,过世都快七年了。
清汤羊肉
回到庆阳,一安顿下来,就想吃一碗清汤羊肉。离开陇东快十年了,这块地界留下了我太多的记忆,我生命的一些成分,一些骨血,是这面胸膛一般的黄土高坡给予的,这注定了我此生都会怀念,都会牵挂这里的沟沟坎坎。正是下午,太阳还没有落山,我一个人,从县城喧闹的北街,往冷清的东街走去。
庆阳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原来空旷的田家城,已经建设成了开发区,街道两边矗立着样式相似的楼房,店铺的招牌也亮晃晃刺眼。往城里走,要经过一座石桥,石桥两边,一边填平,堆砌出了一间一间的商场,这是我离开庆阳后才出现的,另一边还是裸露的河床,早先就断了水流,是一片片菜地,我在庆阳生活时如此,如今竟然还是老样子。那些年,我常常在晚饭后从桥头边的土坡下去,沿着菜地的地垄闲走,在五月的黄昏,随意散落的洋槐树开着繁茂的花,空气里含有淡雅而持久的香味。我就想起,再过十多天,洋槐花就该开了,还会有有心人从飞舞着蜜蜂的树下走过吗?当年在庆阳时,我曾经在一棵洋槐树的树身上,刻下了几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估计现在已经辨认不出来了。
从北街走到东街,十来分钟就走到了。庆阳是个小县城,又局限在山塬夹峙的一块洼地间,向外扩展,也受到许多限制,这也使得这个县城的风格内敛而质朴,轻易不会有颠覆性的改观。在十字路口,我下意识地向左拐,我吃惊地发现,十年前的羊肉馆,还在老地方,连招牌也还是那种木头的正方形,本色的木纹上,毛笔写着的“东街羊肉馆”字样,和我以前看到的没有区别。进去,还是三道隔间,靠外一间,坐着两个吃客,正抱着碗,咕噜咕噜喝汤。还是有些变化,外墙贴满了竹板大的瓷片,白花花的,桌凳也换成了新时的样式。墙上一张纸,写着饭单,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依次是:清汤羊肉,大6元,小5元;座锅,大12元,小11元;双盒,大12元;杂碎,大6元,小3元;刀炖烩肉,大8元,小7元;饼子,一个0.5元;羊汤,0.5元;熟肉,35元。以上便是这家羊肉馆供应的全部吃食。座锅是带骨头的羊肉汤,骨头上肉多,吃完,桌子上骨头堆一堆,吃座锅,不用要饼子,一份座锅就吃饱了。双盒就是比清汤羊肉的羊肉多加一份羊肉,一份清汤羊肉一两羊肉,双盒是二两,馋极了就要双盒。杂碎是羊下水肉、羊头肉。刀炖复杂些,就是给羊血里掺上麦面粉,搅匀称了,用勺子一下一下掠成面片薄厚大小,浸到盛了清水的盆子里,谁要便和羊肉一起炖,炖熟了吃。座锅和刀炖为什么这么叫,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但既然叫座锅和刀炖而不叫别的,那就一定有其道理。我自然还是要清汤羊肉,我以前每次来,都是要一碗清汤羊肉。原来一碗一元,我离开庆阳时,涨到了3元。羊肉涨价,清汤羊肉也涨价,水涨了船就高,人们还是离不开这一口。既然叫羊肉馆,便只有羊肉,没有别的,庆阳的羊肉馆都是如此。庆阳人爱吃羊肉,最钟情一口羊汤,街上最多的馆子,是羊肉馆,家家羊肉馆子都有清汤羊肉。庆阳人是啥时候开始吃清汤羊肉的?我没有考证过,但我可以肯定,当第一只羊被庆阳的青草饲养,就把清汤羊肉的吃法创造出来了。贫瘠的土地上,日月艰难,半农耕半放牧的生存方式,基本上靠天吃饭,饥寒的肠胃,享受不上大口吃肉的富足,多喝些营养的汤水,身子也一样被滋养而能够迎送冷热。实际上,许多可口的美食,都是缺少油盐的百姓,在烟熏火燎的灶火里创造的。人要是经常饿肚子,好不容易有一顿吃的,一定会费些脑筋,让自己的口腹舒服。我多次在乡下赶集,山窝窝里的人,都会骑着毛驴,翻山越沟,出来走动走动。镇子上,会搭起一座座临时的帐篷,一口锅,一只羊,生意便开张了,里头挤满了吃得一头大汗的人。这一天,肚子里装着一碗清汤羊肉回去,回到土坡上开凿的窑洞里,身子骨受活着,晚上睡觉都会睡的晚些,都会想着再干个啥。
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等着一碗属于我的清汤羊肉。我一下子简单了心思,全部的寄托,就是一碗清汤羊肉。这个时候,只有我和一碗清汤羊肉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羊肉馆里忙碌着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不言语,拢着双手在围裙前,有人进来探头看看,又收回身子,在灶间一下一下收拾碗筷。还有一个娃娃,八九岁,跑出跑进添乱。大人说一句,安静了,找一张桌子坐下,拿本子写作业。我看两个男的,一大一小,模样一样,明显是两兄弟。他俩我眼熟,却不认识我。他俩的父亲,我认识。我十年前到这里吃清汤羊肉,就是他俩的父亲,把冒着热气的大碗给端上来。就问老人是不是歇下了,说已经过世了,想起老人当年的神情,一阵怅然,总觉得什么留了下来,被继续传承着,似乎不光是这个羊肉馆。
清汤羊肉的做法,实际上很简单:把宰杀好的羊,干净了身子,拿利刃分割成小块,夜里在大锅里煮,调料有数十种,主要是生姜和盐,细盐最好,量适宜,适宜到尝不出咸味,为的是突出羊汤的鲜美。三四个钟头,肉可以出锅了,煮了肉的汤,浅下去了一截,须加足水,烧开了,让一直滚烫着,就成了这一天给清汤羊肉加的原汤。捞出来的羊肉,会分离出几部分,大件的肉,切成整齐的肉片,做清汤羊肉。放一些在碗底,也会略放些杂碎,用大锅里的羊肉汤,一遍遍浇滗,直到肉里也进去了温度,再把汤加满,调上油泼辣子,撒上葱花、香菜末,一碗清汤羊肉就做成了。说起来也真是容易,没有繁复的工序和花样,可是,吃客总能区分出哪一家的清汤羊肉味道正,喝出汤的好,吃出肉的好。怎么个好呢?不好具体描述,就是舌头的感觉,喉咙的感觉,肠胃的感觉。感觉是最真实的。于是,有几家羊肉馆,从早上开了门,到晚上关上门前,吃客就一直不断。我曾分析,优劣主要在羊肉,山羊中的壮公羊,当地人叫羯胡子羊,身板结实,高大,长犄角,好斗狠,多生黑毛,经过现宰现煮,保证羊肉的新鲜,而煮肉这个环节,主要依靠经验,用手、眼睛、鼻子、耳朵,来把握调料的不同用量,调整火候的强弱。羊肉熟透了没有,用耳朵听,听锅里的响声,也听得出来。经验是积累下来的,能传授,但不是写在纸上,主要靠揣摩和体会,悟性强的,可能一年就能上路,差的,十年还摸不着门道。通常,家族的沿袭最能保真,又被用名声加以巩固,包括为人是否厚道,发生过哪些传奇,甚至从羊肉馆连接到祖籍地,打通上辈子、上上辈子的故事。我来的这家,就有好名声,名声不是自己造出来的,是吃客的嘴,你一嘴我一嘴,一嘴一嘴吃出来的,是嘴里的话,你一句我一句,一句一句说出来的,比石头上刻下的字还要牢实,还要经久。
一碗清汤羊肉,让我知道,人的胃,是有感情的,这份感情,不掺假。人的胃,似乎生有眼睛,能认出相识的食物。我刚抿了一口热汤,我的胃,便苏醒了。碗里升腾的热气,在我的脸上弥漫,我依稀看见了十年前的我,也是端着一碗清汤羊肉,成全着卑微的口福,而把人生的荣枯看淡。过去的我,现在的我,都是如此,对坐在羊肉馆里的真实,对于吃饭,怀有最大的敬重。我一边吃着,一边擦头上的汗水,我明白,此时发热着的,不光是我的身体。配合清汤羊肉的饼子,是熟面饼,泡进汤里,迅速吸足了汤汁,依附了辣子油,虽说不用怎么咀嚼,滋味悠长在口腔里,胃里却有扩张感,十分的受用。吃高兴了,我还不走,想再看看,走进第二个隔间,这是操作间,我撩开苫在托盘上的布子,羊肉已经不多了,早上到现在,一天的光景该结束了。庆阳人一天吃两顿饭,早上九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农村的人,县城的人,都是这个习惯,学校也按这个钟点上学放学。现在,还是这样作息着。所以,我来的这个时候,吃饭的人已经不多了。第三个隔间里,放置了几个大盆,两个大盆里浸泡着做好的刀炖,另一个大盆里,是切成大小块的羊肉,有四个羊头,剥去了头皮,眼睛鼓突,像是在看我,我的目光赶紧躲开。这些都是夜里要下锅的,是给第二天预备的。就这家羊肉馆,一天要宰杀四只羊,差不多能做五六百碗清汤羊肉。我今天吃了一碗,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满足!
从羊肉馆出来,天色还亮着,我走在走过无数次的大街小巷,辨认着一堵墙,一棵树,我能够从一片墙皮,一根枝杈上看到过往。百货大楼的台阶,我坐过,政府大院旁的石柱,我摸过……我就像一个闲人,散漫地走着。不远处的盖帽山,簇拥着大片杏树、梨树,杏花已谢,梨花开得正热,一团团如蒸汽一般浮起。一阵轻轻扬起的尘土,也让我感到亲切。我的耳朵,听着方言,是我也会说的方言,身边传来的一声咳嗽,也让我想起什么。我看到的身影,似乎都是熟悉的,似乎唤上一声,就会有人转过身,朝我走来。就连娃娃脸蛋上的两团健康的红晕,这高原上风吹的记号,也让我喜悦。我在邮局旁边,看几个老汉下象棋,他们几乎天天在这里下象棋,天黑了才回家。十年前,就天天在这里牵车走马,如今还在这里越楚界,过汉河。他们还是十年前的那几个老汉吗?我看就是,只是胡子更白了,腰更弯了。东门口,卖麻子的老汉,还是那个十年前的老汉,还是那辆架子车。当地人喜欢嗑麻子,一把麻子扔进嘴里,麻子壳就不断跑出来,堆在下嘴唇上,嗑麻子的间隙,噗地吹一下,麻子壳就飞走了。嗑麻子,是当地人的嘴上绝活。十年前,就传说卖麻子的老汉靠卖麻子卖成了万元户,我看老汉还穿着黑棉袄,嘴里叼一根旱烟棒,不知老汉有钱还是没钱。但老汉的神态是安详的,甚至是超然的。车站拐角的电线杆子上的喇叭,正播放着庆阳新闻,播音员的醋熘普通话,在我听来是那么好听。如今,许多县城都把街道上的喇叭拆掉了,庆阳的喇叭还在,庆阳人的日子里,依然有喇叭的声音。庆阳有许多改变,也有许多不变。依我看,变还是不变,全在人的心思,要变,也是人的心思先变。变了的咋能都朝好变呢?人的心思还是平坦些好,平坦的心思,不爱变,自在,有分寸,不起劲做后悔的事情。
我不是庆阳人,但我在庆阳生活了二十年,庆阳是我的第二个出生地。我人生的重要年华,都是在庆阳过来的。我在庆阳挣到了第一份工资,我在庆阳成家,有了可爱的女儿……庆阳牵连着我太多的情感,有苦闷和失落,也有希望和快乐。这次我在离开庆阳十年后,遇见了一个机会,又一路心跳着回来,虽说时间匆匆,但一碗清汤羊肉,给了我安慰,我不难受了,觉得踏实了。我知道,一碗清汤羊肉,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但是,吃得东西,总让人踏实,对于我,更是如此。一个地方和吃的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一定是紧密和牢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