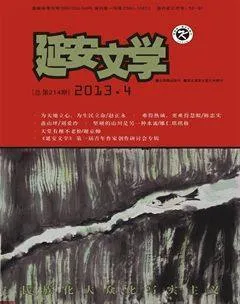漫游的思想
2013-12-29祖克慰
祖克慰,1965年生,河南南阳人。作品见于《北京文学》《散文选刊》《山花》等。著有散文集《乡村文化人》《有一种手语叫流泪》等。
一个人孤独地爬山
一个人,本身就很孤独。孤独的人,选择孤独地爬山,这有点不可思议。生活是多姿多彩的,选择生活方式也是多元化的。我们可以热热闹闹地生活,也可以孤独寂寞地生活。
可我总觉得,选择孤独,是不是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我无法作出回答。可以解释的是,一个人孤独地爬山,这样的人,一定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
我也喜欢爬山,我家乡的山,几乎有点名气的地方,我都去过。我爬山,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我们骑着自行车,带上炊具,在谈笑声中,与大山亲密接触,享受山带给我们的快乐。
不知为什么,我后来突然就不喜欢爬山了,几乎有十年,没有爬过山。最近两年,我突然产生一个人爬山的冲动,而且也不止一次地一个人外出爬山。一个人爬山,我没有找到快乐。面对大山,面对那些结伴而行的人,他们的热烈与快乐,让我更加地孤独。是不是生活太过喧嚣,需要一个宁静的环境,释放内心的郁闷。可不知为什么?在希望的宁静环境里,却无法面对孤独,这让我矛盾。
我无法解释。也许,对于孤独,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天生喜欢孤独,在一个人的天地里,他们的思想驰骋纵横,恣意地享受着孤独带给他的快感;有的人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们性情狂放,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丰富着自己的人生;有的人视孤独为时尚,他们行为怪癖,以独特的性格,张扬着自己的另类;还有的人,他们为着一种信仰,默默地选择了孤独。
我想起了小郑。一个很有诗人气质的女孩。不知为什么,她突然爱上了一个人爬山。一个青春女孩,本应该充满青春活力,快乐地生活,却选择了与孤独为伴。她后来不仅选择爬山,也选择了一个人生活。再后来,她选择了佛,选择了清淡的饮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她孤独地上班,孤独地爬山。全国很多名山大川,都留下过她的足迹;全国的许多有名无名的寺院,她都朝拜过。一个年轻的女孩,她所作的选择,让我无法理解。是什么让她选择了孤独?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的心一定受过伤,因为伤心,她厌倦了红尘,选择了远离喧嚣。可生活在尘世,又怎能逃脱世俗的纷扰,超然物外。
我没有受过伤,我的生活,平淡宁静,没有太多的烦恼,也没有太多的快乐。生活于我,就像宁静的小河,缓缓地流淌,我就是那河中游动的鱼,没有了大海的惊涛骇浪,也就没有浪尖上的那种起伏。我为什么选择一个人孤独地爬山?应该说,一个人的选择,是他喜欢并快乐的事情。可我的选择,让我更加孤独,为什么?
我曾经问小郑:“一个人的旅行,孤独吗?”小郑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孤独,所以不孤独。”我说:“我常常产生一个人爬山的冲动,可我爬山时,总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小郑说:“我爬山,是我心中有佛,与佛同行,没有孤独。你孤独,是你心中孤独,心中孤独,哪怕是与人同行,也会孤独。”
禅者认为,修行即是修心,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顾、一思一识都是心灵的写照。那么,我们之所以感到孤独,是不是因为心中孤独。我想,应该是的。小郑之所以经常一个人行走在大山中,没有孤独的感觉,那是在她的眼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佛的化身,与佛同行,何来孤独?
可我的心中有什么?或者说,我为什么爬山,为什么要一个人爬山?如果我爬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快乐,那我一定有一种快乐的心态,我所面对的,都是快乐事情;如果我爬山是为了锻炼身体,那我一定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因为我面对的是险峻的高山,需要付出汗水;如果我爬山是为了欣赏美丽的风景,我的心中就装满了风景,我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美的造型。
如此看来,我的爬山,只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我获得的也只能是孤独。
为什么孤独?是因为我的心孤独。就像为什么要流泪,是因为我的心中盈满了泪水,感动或者伤心着我。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孤独,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快乐。这决定于我们的心态,悲伤的时候,没有谁能发出开心的笑声;快乐的时候,又有谁会悲痛欲绝?
心态,决定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良好的心态,是赋予我们美好生活的前提。
在城市的黄昏里喝茶
黄昏,一切都将落幕,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字眼。可我看来,黄昏是很生动的,它让你产生许多联想。比如即将来临的月光,月光下的公园,公园合欢树下的情侣。对我来说,没有比黄昏更美的一段时光。我很在意,也很钟情这段时光。它让我感到愉悦,血液流淌畅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黄昏来临,这时候,没有特殊的事情,我一般都会坐在阳台上。其实,阳台上没有风景。眼前都是错落的楼房,千篇一律,没有一点新鲜感。赏月,似乎还早点,月还没有升起。倒是黄昏的落日,有点绚丽。遗憾的是,黄昏的落日,有点短暂。不过,这都不重要。此时,我坐在阳台上,只是喝茶。
一张桌子,一只透明的玻璃杯子,那一片片的叶子,就生长在里面,绿莹莹地生机无限。我看这些叶子,就像看见满山的绿树,它让我身心轻松。一只杯子,里面就是一片风景。这样的风景,我总是在黄昏里悠闲地欣赏。黄昏时分,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它让我看到了春天。
杯中的水,淡绿淡黄,那是被绿色染的。这样的颜色,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它让你不自而然地感到口渴。当然,这不是被污染的水,浑浊,散发着阵阵恶臭,你不会恶心。不过,你不要去想那些可恶的污水,那样,是没有胃口的。此时此刻,你就在大山里,你就在森林里,你看到的是一眼山泉,那水,是来自岩石深处的地下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一种诱惑在里面,挡也挡不住,忍不住就喝了一口,清冽甘甜,再喝一口,清香盈喉。
在黄昏里喝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它让人思绪飞扬,充满了诗意。落日的霞光,翻飞的茶叶,似乎都与诗有着某种联系。在落日的斜阳里,咂一口茶水,我突然想到了苏轼。千年前的苏轼,是不是也喜欢在黄昏里喝茶,我想是的。不过,东坡喝茶,身边少不了一个女人,他的红颜知己,一个叫王朝云的女子。因为有佳人相陪,东坡先生说:“从来佳茗似佳人。”
我是喝不出来诗的,这大概与没有女人陪伴有关。没有红颜,更没有知己,而我的老婆,是个茶盲,从不喝茶。所以,我永远也成不了诗人。成不了诗人只是一种遗憾,并不影响我喜欢诗人,比如戴望舒。想起戴望舒,就想起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而我现在所处的黄昏里,是没有雨的,也没有满脸忧伤的女人。当然,我希望有个女人出现,但那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充满着青春魅力的姑娘。
我只能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样的情景是不会出现的。倒是我的母亲,在我没有想她的时候,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给我提来一壶热气腾腾的水,在我透明的玻璃杯里添上一些水,然后悄然离去。可是母亲不常在我的身边,她在远离城市的偏僻乡村。
这个季节,正是秋天,稻子已经成熟,黄灿灿的稻穗遍布乡村,农人正在收割水稻。乡下的母亲,是不是站在稻田里,收割一年的收获。我知道,母亲是不会闲在家里,山洼里的那片稻田,一定有母亲的身影。我看见母亲佝偻着腰,一镰一镰,稻子在她的镰下,成片成片地倒在地上。母亲不时地站起来,用手捶捶酸困的腰,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可我分明看见:黄昏的余晖里,母亲一脸疲惫。
母亲并不知道,在城市里的某一个角落,在一个落日的黄昏,她的儿子,正坐在自家的阳台上,悠闲地喝着茶。他喝着几百元一斤的绿茶,像欣赏风景一样,看着玻璃杯里嫩绿的叶片,沉沉浮浮。她并不知道,儿子的一斤茶叶,差不多就是她一亩地稻子的收成。
在我悠闲地喝茶的时候,母亲忙碌地收割稻子。我不能阻止母亲收割稻子,母亲也不能阻止我喝茶。就算我有能力不让母亲收割水稻,母亲也不会放下手中的镰刀。母亲是农民,庄稼地就是她的战场。就像士兵,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一样。
执着的坚守,也是一种责任。母亲的责任,是侍弄庄稼,收获粮食。我的责任,是上班,坐在办公室里,做属于我的工作。我在阳台上喝茶,也是一种责任,是为我的嗜好负责,是为我身体里的某种需要负责。我不能永远生活在繁纷的工作中,也不能生活在杂乱的家务里。最佳的选择,就是在每天的黄昏,很短的一段光阴里,放松自己。而我放松自己的最佳方法,就是在黄昏里喝茶。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有些生活方式是奢侈的,是一种时间上浪费。可我们不能改变,一旦改变了,快乐就不属于你。就像我喝茶,时光在一口一口中悄悄流逝。可我不喝茶时,时光就停留不动了吗?没有。每天,时光都在逝去,可是,谁又有神奇的力量,让时光永驻?
在漂泊中渴望漂泊
漂泊这个词,可以作如下解释: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居无定所,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通常情况下,人们就是这样理解漂泊的。可我不这么认为,有些时候,漂泊,也意味着浪漫。可以想想,一个人,无忧无虑,行走在城市与名山大川之间。这样的漂泊,是不是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我也漂泊过,是在广州,承受了被抢劫、被辞退、流浪街头的辛酸,那是一段很短暂的漂泊经历。虽然我遭遇了漂泊的坎坷,但那段生活,时常让我怀念。我现在依然在漂泊,但不是我想象中的漂泊,我所谓的漂泊,就是从家到单位。这是一段不足200里的路程,我每月都要来回几次。我对这样的漂泊,没有感到浪漫,也没有孤独。
近距离的漂泊,让我多了一些牵挂。我在家时,惦念着单位,那里有属于我的工作,需要我做;我在单位时,想念着家,家里有我的妻儿。说实在的,我在家虽说惦念单位,可我不想去单位,在那里没有家的感觉。我在单位时却不想呆在单位,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干得再好,没人说你好。按说,单位也是家,一个热爱单位的职工,应该视单位为家,照此说来,我不是一个好职工。可我不这样认为,我是想把单位当作自己的家,可单位没有把我看作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他们把我叫做“临时工,”工资奖金福利待遇都低人一等。说白了,我就是一个“打工仔”,一个比较固定的“打工仔。”
十几年来,我就过着这样的漂泊生活,在大家庭的歧视下,卑微地工作、生活着。这样的漂泊,并不是我希望的漂泊。可我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我唯一能做到的,是维持现状。很多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变一种活法。譬如:辞去工作,寻找一份能够实现自我的工作,在和谐的氛围里,平等、公平、快乐地工作。现实告诉我,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是一个美丽的梦。再譬如:做一个纯粹的漂泊者,独自一人,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忘情山水,四海为家,终其一生。这更不现实,太多的牵绊,使我的想法比梦更虚幻,是一种纯粹的、不着边际的幻想。
我是一个半拉子文人,当然,这半拉子文人,是我自己封的。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对李白十分地崇敬,也对李白十分地羡慕。李白一生浪迹天涯,过着漂泊的生活,在我看来,李白的漂泊,就是我想象中的浪漫生活。我一度产生浪迹天涯的想法,就是受到李白的影响。可我知道,我不是李白,没有李白的名气,没有人邀请我,我也也不是富豪,没有浪迹天涯的旅费。
我常想,李白为什么能够浪迹天涯。李白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社会稳定,民风向善。对文化的崇尚,对文人的尊重,使李白不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热情款待,甚至赠送银两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在唐朝,侠义之风盛行,人们讲义气,重情谊,把友情看得很重,视朋友为亲兄弟。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李白才有了许许多多像汪伦这样的朋友,因为有了汪伦这样的朋友,才有了李白的浪迹天涯。
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我没有名气,没有人邀请我,更没有人赠送我银两;第二,我没有像汪伦那样的朋友。现在的社会,人情淡薄,所谓朋友,也只是一个泛称。哪怕你再有名气,到朋友家里小住三五日,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呆在朋友家里,一住就是半月,就难免遭人烦了。就譬如有朋友到我家,住上十天半月,作为朋友,我是不会烦的。但我不敢保证,我的老婆和儿女们不烦。
我说这些,并没有指责谁。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被物化了的时代,人们追求平静的生活这没有错。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生活,因为外人的侵入,而失去往日的平静。这不是谁的错,错就错在,丰厚的物质生活,颠覆了淳朴的民风。传统的农耕文明,正在被新兴的物质文明所替代。我们悲哀地看到,友情正在商业化。
现代社会,浪迹天涯的诗人不在少数。为了诗歌,他们选择了漂泊。然而,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他们的漂泊,注定以悲剧的形式结束。
我想到了海子,一个天才诗人。他从安徽怀宁高河查湾农村漂到北京,漂泊在北京的海子,没能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贫穷与孤独的海子,渴望在诗歌里飞翔,渴望灵魂的飞翔。于是,海子选择了另一种飞翔,让火车带着他自由地飞翔。
诗人陈嘉映说,海子高蹈他的理想走了,留下我们在歌舞升平中消费一切,挥霍无度。80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时代,是海子的时代,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
我还想到了另一个诗人,他叫顾城,那个执着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朦胧诗人。从1980年代开始,顾城过着漂泊的生活,后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再后来辞职隐居激流岛。1990年代,顾城杀妻后自杀。有人说:“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他为什么戴帽子,按照他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尘世间污染了他思想。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在分析中国诗人自杀原因时,有人认为:因写诗而思想,因思想而无望,因无望而寻思彻底解脱。无望来自他们的身体、贫困、孤独、思想!
这就是漂泊的结局。这是中国诗人漂泊的结局。这就是我想象中浪漫的漂泊生活。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养尊处优的时代,是一个滋生肥胖症的时代,人们摈弃了理想回到现实,没有人为了理想愿意牺牲尘世生活。我们渴望漂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实现理想,并不一定就是追寻贫穷、孤独、单调的生活,也不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
可遗憾的是,我们为了理想,在贫困、孤独中生活。我们的理想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人们希望看到一个纯净世界,眼睛里却尘土飞扬;人们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身体却悬在半空,没有一处栖身之地;人们希望快乐地生活,却身心疲惫,充满了忧愁。在无望的痛苦中,他们选择了逃避,让灵魂离开肉体,自由地升腾。
尽管如此,我那颗希望漂泊的心,仍旧一既如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