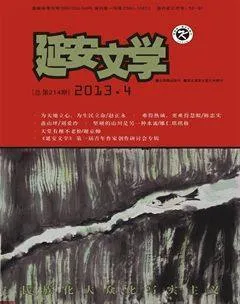城客
2013-12-29刘国欣
刘国欣,女,1987年生,陕西府谷人。四川省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届西南作家班学员,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著有小说集《沙漠边的孩子》。
少年死在了四月开初。她想让她新来的朋友看几眼,商量一下该如何祭奠。可是她新来的朋友拒绝了。倒是那个八十岁的老太婆,去站了一站。
她搬来是在二月末,房子在这个都市的繁华地段,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门边就是南郊公园,附近有条老街,还有个纪念三国人物的大祠堂。不管是冬天还是春天,这里总是有很多游客,人声鼎沸,络绎不绝。这个闲散的城市,人们似乎都是慵懒的,至少在外面看上去是,可是事实未必。——他们蜷缩在那里,忙忙碌碌,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她是个二十几岁的女人,飘落到这城市半年了,为了寻爱而来,但那个人死于一场车祸,与此死掉的,还有他的父亲,应验誓言一般。虽然事后想到那个人,还是会怀念,甚至流泪,可是,所有的好都磨灭在死前的那几天,也就没有什么了。完了就完了,没有一点犹豫、半点闪失,就那么毫不客气,一点也不做作地,死掉了。可是她不能瞬息转身,前方的道路被堵住了——也许本就没有前方。她一个人飘零,如同所有飘落在大都市的大龄剩女一样,迷茫无助,却还坚守着。因为习惯了都市的生活方式,因此就如这城市建筑的某块可以随意割舍的部分一样,比如一块砖,一片水泥,随时可以掀掉,搬到另一个地方,当然,也可以扔弃到垃圾堆里。但即便是这座城市的一块烂了的伤疤,也还是在那里。在这个巨大的母体一样的城市里,存在着很多烂疮,流着脓水。
少年是对门的。她所在的这条街,是条藏民街,以前她在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曾经在回民街住过,那条街小偷众多,她在那里被偷怕了。话说回来,十三朝古都嘛,这也很正常。来这里半年多了,之前在的地方,离她死去的爱人不远,附近有个少数民族的叫做什么甘孜州的办事处,经常有红衣汉子出入,因此来到这条藏民街,并不觉得十分害怕。之前住的地方,有很多负累,可是至少能经常见他,后来这个人死掉了,因此她也就搬走了。附近的邻居,包括经常光顾的饭店的老板娘,以为她情多,伤心,所以很体谅,走了之后经常发个短信安慰她,有时也说要来看看她。其实死亡,也许于她更好,很多时候,两个相处已久的人,不想分手的话,只能以死亡来完成美满,因为一切都驱到了尽头。
这个小区存在很多个年头了,整栋楼都很破旧,在繁华闹区的一隅作为破旧的见证存在着。很多这里面的人,是些外来的租户,要不就是些学生。这附近有三四所大学,一所技校,一所卫校,还有一所体育院校。她租到这里,除了离新找的工作单位近一点的原因,再就是房租便宜。同所有的城市一样,这座城市的一切都在暴涨,包括房价。房子自然是买不起的,那就只有租,但租也是个问题。她的一个同学,在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的西子湖畔,月租金就九百四,相比较,她只是那的一半多一点。因此有时想想,似乎心里满足,也就没有什么大慨叹,若是没有个对比,真不知道这生活如何过。但她却从来不想,那个女孩的工资三千多,她的仅一千多。
她租这房子的时候,附近卖包子店的人给她暗示过:“快要拆迁了。”但这又有什么呢?至少现在还没有动工。
房子确实破旧,这片区的几栋楼层都是破旧的,楼道的墙上到处是蛛网,以及肮脏的脚印,还有一些宣传纸,贴得满满的。若是以前的话,她会觉得这样才有人气,可是她搬来之后,才觉得这就像人快要断气的背景似的,整个一电视剧里表演颓唐场景的画面。然而看在房租便宜的份上,认了,有好就有坏,没有什么总是两相宜的。
对门,就是这死去少年的家。——不对,那时候少年还没有死去。
她搬来的时候是在深夜,十点多,因为她认识的出租车司机交班晚,而行李又多,所以才晚上十点多搬家。其实也不尽是这个原因,毕竟那个她爱过的男子,是死了的,而这个片区都是他们互相认识的朋友,她不想见他们,比如,饭店的老板娘,她见她们总是想流泪,但又不能殉情。表现的太悲伤,她又做不出来;表现的不悲伤,那又似乎不能满足她们窥探的欲望。因此,在料理完他的后事之后,就搬离了。
她搬来,夜里十一点的样子,走了琴台路,出租车师父把路走错了,绕了很久,然而她却觉得开心,因为琴台路是他们没有一起去过的,这样的话,他死了之后,还有一个安静的去处,在不能马上离开这座城市的几年里,至少还有个去处,没有被记忆打扰过。
这少年就是她搬来的那天深夜出现的,他从外面回来,快进小区的时候,停了停,嗫嚅着说了一句:“姐姐我替你拿点。”说着就把一个很重的包拿起了。出租车司机,在把东西放下之后就绝尘而去了,因为如果停得时间稍长,会被收钱。小区虽然破旧,但这方面还是正规的,毕竟,这是发财的生意。她租的房子,离小区门口得走二十几步,但毕竟不算远。
这少年,穿深蓝色校服,臂膀处有一圈白色,没有戴眼镜,但斯斯文文的,像个女孩子。也许他当时穿的是条蓝色牛仔裤,也许不是,总之,事情过了这么久,谁记得?何况还是在深夜。不过她记得那鞋子,白色的361°牌子的鞋子,在灯光下有着惨淡的光。她自己就喜欢这样的鞋子,以前常买。去年,在出租屋的地方,有个二十七岁的女孩被人给打死了,没有什么缘由,彼此不认识,只因为过马路的时候男子的摩托挂了女子一下,然后女子回了一句嘴,结果过了马路之后就被男子追到一家361°鞋店的门口,狠狠地打,抓着脑袋往水泥地上磕,就这样打死了。这件事曾一度轰动全国,很多人责备361°店里的员工,认为那两个店里的女孩该上前拉一拉,或者报警,至少别让凶手跑掉。新闻报道的过程,还特别表扬了一个八十岁的退休老头,因为他在这件事件的尾声,丢弃了自己的脚蹬三轮,追了凶犯好几十米。那之后,她对361°这个牌子印象更加深刻,只是不再买那里的运动鞋,总觉得不吉利似的。后来,那店里的女员工很快被换到别处去了。那个被打死的女孩,就在她所在的小区,灵堂摆了很久,头顶上一群绿叶子,爬山虎似的,是那个小区的一个特别景致。门边还有家蛋糕店,灵堂摆在那里,影响了一阵生意。她每天来来去去地走,对着那女子的照片有一个月的光景似的。那女子据说刚结婚,婆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个劲地说:“跟我儿子关系好着呢。半夜里想吃烧烤我儿子立即穿了衣服给她去买,说好了今年生孩子呢。”而镜头转至女子的母亲时,这个失去女儿的母亲,什么都说不出来,眼神呆痴,肿得像核桃。
后来那灵堂就不见了。
接下来的日子,她看见那少年的那双361°的鞋子,总是会想到这个事。有几次,真想脱口而出:“姐姐认为你该换双鞋。”可是始终没有说出口,她缄默着,如同保守着一个秘密。
她的东西多,基本是些书,都被装进麻包似的大包里。她习惯把这些东西搬来搬去。本来一些东西是给那个人的,可是死掉了,因此只能自己继续携带着。也许有一天会扔掉,但至少现在不成。
少年帮她运输了好几回。不交谈,什么话都不说,来来去去,几个二十几步。
后来,她看见少年搬完之后转身走了,再后来,对面门响。
接下来的日子,经常在走廊里见到那少年。
那个她搬来的夜晚,本来是难过的,可是因为少年的帮忙,让她觉得人世美好。第二日上该死的班,需要去那片坟场一样的地方坐着。那地方正进行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准备了好久了,在她进这个单位的时候,就已经在准备。有座红房子,拆了好几次,当她来的时候,又被一片绿布包了起来,每天有各种机器在响,小个子的工人走来走去。有一次,她被领导叫去坐了坐,领导似乎是有意又似乎是无心地说:“咱单位经济效益还是很不错的,你看那座红楼,每两年拆一次,每一次几百万……只要你好好干。”她当即就想,好好干也是一个样,工资超过两千就好了,但这个比较难,有那么多人在等待着,富丽堂皇只是少数人的,轮不到她。
第二次见少年,是个黄昏,他还是原来的那套穿着,她一下子就认出了。后面还跟着个倔强的女孩,似乎是他妹妹,背着小红书包,脖子围着红领巾。两个人一边踢地面一边走,小女孩走路一拽一拽的,男孩跟在后面,拍着个足球。
她开门,他也开门。晃荡就关上了。在此之前钥匙拿出来的时候,他腼腆地,略带微笑地叫了声:“姐姐也回来了?”她“嗯”,似乎想说什么,没有接着说下去。
她一整天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此,这附近的一切声响,眼光所及处,都是极仔细地可以烙印在她眼里心里的。她跟一个八十岁的老媪住在一起,这个妇女本来有套大房子,可是子女太多了,分不来,又没有人管她,索性就把房子卖掉了,租了这小间。城市里的人,都是精明的,尤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八十年的人。不过,老妇是善良的。
老妇没事的时候,就坐在客厅抽烟,一天一包,不过一套房子的钱,如果不被子女剥削,足够她抽到死。
有那么好几回,她半夜里上卫生间,客厅的灯没有开,她看见一颗星星在那里明灭,空气里闻得见那味道。开始她还害怕,后来就习惯了,老年人,睡不着是正常的,可是老妇经常扯她衣服,总是在第二日,扯住她说隔壁又打孩子了,打了大半夜,先是女孩子哭,又是男孩子哭,哭……总之,她睡不着。
断断续续地,她知道了邻居是一家什么人。而且那走廊上破旧的脚蹬三轮车也可以看出来。
在老妇不咸不淡的叙述里,她知道少年家是从乡下来的,现在所住的房子,也是租的,只有三十平米,一家人挤在那里,已经几年了。在少年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已经搬来了,后来有了妹妹,再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家人经常打骂哭号,经常有周围的人找楼管,可是没有人管得了。这座房子要拆迁了,所有人都是临时客,住到这里的人,都算不上什么上流阶层,因此关起门就是另一世界了,所以后来也就没有人过问。
那家女主人她见过,一米五三,胖,也是撅着嘴。她对她没有好感,因为嗓门太大了,半夜里还在那打孩子。——那个小女孩也似乎跟了她妈妈,小嘴总是撑得老高,头也昂得老高,好像谁欠她钱似的。楼道里遇,也从来不打声招呼。这一家子,只有这少年,见了人会微微笑一下,然后马上转过头去,腼腆得像个害羞的小姑娘。其实她不喜欢那家主妇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跟她死去的未婚夫的母亲很相像,都是矮子,一米五三不到,都撅着张嘴,眼露凶光。他的母亲她见过,就在死前的前一月,正式见的父母。那天她拎了箱子去找他,路上碰上了他们一家,说好一起吃饭的。他拖她的箱子,她生气,说是该提着,不然会坏了,就这一句,把那一米五三的娘给说坏了,认为她皮薄,一家子在饭桌上审犯人一样地审她,说是要是结婚了还如何如何。
那时候已经买了房子,正在装修。她自然不好说什么,息事宁人,又不是跟老妇一起过活。不过想到这个人,这个妇女,以后会抱着她的孩子,想到这个老妇会成为孩子的奶奶,想到遗传,要是也一米五三,那简直是可怕。
后来他死了,车祸。他借了公司的车子,去拉地板,车上还坐着他父亲,在拐弯处,倒车,结果就出了事故。两个人,一下子,没有缓和的余地。不过那父亲也许有,但最后还是没有挽救过来。
这也是一则新闻。这个城市,死掉的人,一般都会上新闻的,晚报或者日报,也可能是其他报,或者电视一角,也或者是网页上面的一条消息。她没有电视,在室内浏览网页,也看到了,血肉模糊的场面,父子两个压在下面,她心里想着那誓言终究是应验了,可是还是流了好一会的泪,为那少年时代一直爱着的人。
那誓言,是这样来的。她本就不相信誓言,可是逼急了也会说,以便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在一个月前,见了他父母。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女的,早在一年前,就和她未婚夫勾勾搭搭了,连房子的设计,都是一起筹划的。只是那女子是小学二年级水平,他觉得不合适,玩玩人家。用他的话说,就是学打麻将,他一直都很笨,娱乐活动几乎什么都不会,而公司有时是需要点娱乐的,因此他学打麻将。听起来是笑话,但绝对是真的。而这个女孩子,刚好做快递业务,跟他单位有联系,于是,就联系上了。有时,事件的开始,特别简单。
他瞒着她,去那个女孩的地方,甚至去人家老家,一去几天,这其间并不是没有争吵,然而男子的心理,其实是恨不能昭示天下的。他在半遮半露里,告诉了她:“只是个游戏,一米五八,大专学历,根本比不过你,我也只想学麻将。”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假的,当那个女孩找上门来的时候,才知道,她叫肖旭,只有一米五三,小学二年级学历,交过几个男朋友,家在资阳安岳的一个小村庄,十六岁就出社会了。那个女子给她打来电话,甜甜的口音,叫她姐姐,他也以此比拟,大有享受之感。那些个日日夜夜,都是谈判。他并不爱那女子,她知道,然而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头的,后来,查,再查,才知道这爱情,早就斑斑驳驳发霉了,不只这一个,还有卖电视的,甚至卖衣服的,各种,他就是这样的人,到处留了号码,利用公司的那些东西,来骗这些小女孩,比如,公司的购物卡,还有电影票。那个他所在的国企,同所有被政府控制的单位一样,有各种福利。他利用一切资源,在对她说是加班的时间,寻花问柳。
她觉得这个人忽然陌生了。一米六四的个子,九十多斤的体重,还是个性无能患者,学历没有她高,个子没有她高,家里资产除了一套贷款买的房子,再什么都没有,若不是少年时代一起走过来,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匹配她。这个人,一千二百五十度的镜子,又是色盲,她一想到这些,就觉得还是分手为好。分手,至少对于下一代,也是个交代。然而,在这个决定还没有完全做出之前,那个人,在开着公司的车,搬运瓷砖回正在装修的房子的途中,戛然而止了。
似乎是上天有意成全她的完满。
在此之前的某个夜里,那个女孩找过她。他们大吵,他说是她找的那个女孩,他怕她,总是认为她聪明,认为她有记者的头脑间谍的手段。她哭,他还是不信,于是,她就以父母兄弟的名义起誓:“若是我找的她,就我死全家;若是她找的我,就你死全家。”新人有新人的好处,因为很多空间是空白的,可以想象,那时候,他还一直以为那女孩跟他时是个处女,而且适合做妻子,很纯洁,于是,就查。后来就引出了那女孩的包养者,一个叫做小白熊的台湾佬,在深圳做生意,在前几年,就包养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别的男子。女孩恼怒,不甘心,认为自己带这个男人回老家,父母都是见过的,又怎么轻易就放弃,于是,说她欺负她,告之所有的相好者,于是,那个台湾佬,就不停地在网上骚扰她。
她以为他会管,毕竟,这是因他而起的,可他并不。因此,她威胁说要找到他单位去,要告之以他的许总和胡总。他是把这两个领导奉为神明的,暗地里却总是诅咒胡总死掉,因为这个人对他并不好。
这个男人,懦弱,且自私。以前并不是没有体现,比如出去买东西,她和别人吵架了,他并不出一言,只是静静站在旁边看,有时甚至合伙起来说她不对,让她息事宁人;比如,在饭店被人弄脏了新买的衣服,也是说她不注意;再比如,明明座位是自己的,被人占了,也是让她悄悄的,别说什么话……这个人,一直这样,她也是喜欢安静,认为可以一世祥和,然而却原来是无能。她其实并不是没有预感,以前,喜欢她的其他男孩子拉她拽她,他在旁边看,并不敢上去呵斥一声。她那时候其实是鄙视他的,一直是鄙视他的,因此,他出轨,或者死去,倒似乎遂了她的意。有时想想,竟然觉得安心,那个人,好在是死掉了,不然,那么漫长,她又是喜欢黏人的人,不大想改变,怎么受得了。
当然,这个男人也有他的好,安静,在角落里坐着,就像不活着一样,她喜欢那感觉。她想起他的时候,也似乎死了很久了,像是缅怀一个隔世的人,其实不过才几个月。
车子斜过来,他在驾驶座上坐着,血肉模糊,还穿着她跟他一起买的黑色衣服。那天她也穿着一件黑色衣服,像是悼念一样,两个人不约而同。他的父亲,也是一身黑色西装,胖胖的,一米七,压在了车下面,两个人,肠子都出来了。
是用黑色的装尸袋和什么夹子挑进去的,她看了那图片,见到他尸体的时候,已经被处理过了。别人说她不能看的,可是她还是看了,而且抑制不住地呕吐。他死去一段时间,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带她去吃饺子;也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怕她伤心,邀约去吃火锅。她看见那些包着的东西,锅里煮着的杂碎,一次又一次地呕吐。
她悲哀地哭,一整个一整个夜晚,她是不想他死的,至少不想如此死,可是誓言应验了。这就像轮回的宿命,有那么一些话,本是不能说的。结果呢?这就是期许的吗?
少年有时在楼道中间坐着,坐好久。她进进出出,他都在那里坐着,也许是忘记了拿钥匙,也许是在等他的妹妹。那个小女孩每次回来都是带着风的,从她的窗前过,呼呼地喘着气,两个人拉拉扯扯。这就是下午的好时光,她喜欢听他们说话,尖叫,声音大抵都是那小女孩的。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一般都是沉默的,他的沉默像如午夜的沉默,静寂无声,无限悲伤,好像几世几生都那样。
少年,他在那里,就如同一种悲哀的存在,一柱香独自燃烧,一座雕像独自微笑。
她每次看到他,都会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很单纯,却也很苦。孩子有孩子的狡黠,她也是。家里总是吵闹,无休无止,像一场永不停下来的沙尘暴。她能理解少年的孤独,因为她自己也有过,蔓延了她整个少年时代,甚至,青年时代。她二十五岁,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生好像立即弹下终止符,也愿意,万事皆休。——那是怎样的悲哀?
家里有吵闹声,少年就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如一个陷入黑暗的王子,是所有夜晚最孤独的王子。但是,没有人来拯救这个王子,鲜有人会哄他回去。有时她出去吃饭,看到他,想问候,想说你要不跟姐姐回来吧,可是她不敢。这条街,这个巷子,所有一切都是怪异的,包括八十岁的那个老媪,她也是怪异的,总是蓬头垢面,露着一双打探世事的眼,就如两个电筒一样,然而并不曾做些什么。她一整晚在客厅坐着,少年在客厅的楼道外坐着,这两个人,都是时间的钟,只有心在跳着。
他们都住一楼。一楼阴暗潮湿,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在阳台上养些花草。这里的阳台上,有海棠花、七姊妹、兰草、白玉兰、桂花、芦荟,还有枇杷树。老太太经常没事就去折那枇杷树伸出来的头,也掐旁枝。她看到那棵树像被人砍过的尸体一样,总是会想到曾经的恋人。可是她并不能阻止老太太这样做。老太太说她讨厌枇杷树,嫌弃长得太过旺盛,说是看着不舒服;还有棵腊梅,那索性是被砍了头的,老太太不喜欢它高过自己;另外,那七姊妹也鲜少开花,每次她站在窗前看,老太太就会走过来念叨,说这些花看着碍眼。隔壁,也就是少年家的阳台,也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花,胡乱地开着。春天来的时候,隔壁院子那桃花开了好一阵子呢,是那种不结果子的桃花,还没有全部凋零,少年,就吊死在客厅到阳台的门头上。
少年的母亲,是个擦洗鞋子的,她遇见过多次。门口是一排饭店,这个女人,一米五三的胖女人,三十多岁吧,看起来似乎是五十多岁,总是包着个头巾,低着头,一桌一桌地问:“擦鞋子吗?”一边还讪笑着。这条街,是条藏民街,来往的藏民多,也比较有钱,主要是这些人信佛教,因此喜欢周济。“唵嘛呢叭咪吽”充斥着,从街头到街尾。很多汉族乞讨者,专门到这条街上来安营扎寨,每天高声念诵的就是“唵嘛呢叭咪吽”。佛教的这六字经典,简直成了这条街的灵魂,因此她不得不怀疑,佛祖是不是乞丐出身,讨得这么多信徒。然而还是很诡异,这条街,一到晚上七八点,就极其冷清了。因此,少年的母亲,到底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她是不晓得的,她只知道,这家两口子,每天回来很迟很迟。
少年的父亲,是个脚蹬三轮车夫,这其实在都市里是被禁止的,时常见有城管将这些车子拉回去,一车子一车子。经常有些三轮车师傅,装成接送儿女或者孙子的样子,在车子后背上写上“接送孩子”的字样,可是,大多数人知道是拉客的,短途,讨价还价,三元或者五元起,每天都在街上转悠,如那些摩的师父一样。这事是不正当的,这职业是见不得正规部门的人员的,然而,总得吃喝吧,除此之外,只能在街头摆地摊卖小吃,那也随时有被收摊子的危险。乡下来的人,躲和藏是惯了的,只要不交罚款不交税,就是好事。这汉子经常半夜三更还在街上猫着,等着那些歌舞厅出来的人,有些人喜欢打的,但的车打不到的时候,还会坐这个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就喜欢坐这个,慢,休闲,感觉就像坐旧式的人力车,喜欢那享受,高人一等的样子。最主要,这些三轮车夫和摩的车夫,知道哪里是闹市区,哪里人最多,哪里最拥挤,最不好打的,他们瞅的就是这个空子。这个城市的人太多了,这个国度的人太多了,因此,这些车子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缓解交通拥挤嘛,又不制造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给相关人员“额外收入”。那些罚款大都不明不白,这些人又不知道要单子,即便知道,也不会要,因为开单子的话罚得会更多,底层人民有底层人民的智慧,这些人并不是愚笨的。
其实脚蹬三轮车很危险,又没有上保险,大多是无证驾驶。最主要的是,一旦出事了,不好找解决的途径。前不久,不就有一个女师傅蹬着三轮把一个行人给撞死了嘛。不过这职业倒是不需要什么投资。
那一日,就是少年吊在梁间的那一日,小女孩嗵嗵地敲门,并不曾喊什么“姐姐”之类的称呼,就是张着一张嘴,不停地大声叫,嘶哑地吼,然后她跟着过去,老太太也跟着过去,然后,就看见那少年悬挂在客厅到室外阳台的门上,舌头已经吊出来了,然而那印象仍然是斯斯文文的。
“赶快往下拉!”老太太指点着。于是她往下抱,急忙又掏手机打报警电话,接着她问那小女孩家里有没有座机。显然是什么都没有的。那她父母如何联系,也显然,联系不到的。都这个时代了,一家人,居然没有个手机!
小女孩怔怔地站在一边。警察很快就来了,比平时的凶险案及时很多,120的也来了,然而那面色早就僵硬了,而且在解救下来就没有了鼻息。120不带少年走,只看了看,摸了摸,然后揪开衣服,用一种她叫不上名字的仪器探了探心窝,。
那天晚上,这家里进进出出很多人,静悄悄的,少年的父母坐在那里,铁桩一样,这个夜晚没有什么吵声。
第二天,老太太去买烟,碰见了烟火店的,她几十年的老相识,说少年是死于自杀的,说可能是学校9ab5da9c4f7c8fc7558fe6c1eac7a288里受了委屈,说城市的孩子已经取消的费用他还得交,而问父母要,结果有了争执,说……这些都是老太太转述的,她并不十分确定,反正少年是走了的。
阳台上放着个兔笼子,那里面有三只小兔子,她每天隔着院子往过看,心里还替那少年高兴过呢。她觉得少年就该有少年的乐趣。她自己的少年时代,也喂过兔子和松鼠,以及小猫咪。
那兔笼子其实不叫笼子,就是纸箱子掏开几个口子,可是少年每次都热热情情的,经常摆弄他的笼子。她也经常在隔壁的阳台上看,看。这一幕在少年死后,她想起来过多次。
她无法把那个平日里腼腆地叫她姐姐的男孩,和一个喂着三只小兔子的男孩,以及那横在门上的尸体结合起来。
后来她还被叫去做了笔录。相关的人,穿着笔挺的工作服,认认真真一丝不苟非常严谨地写下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如一场审判。
过了几天,对门的人又很正常地早出晚归了,很少见他们的踪影,只是小女孩仍旧一个人走着,有时踢路边的石子,还是那么高昂,倔强,老太太站在阳台,她从来不打个招呼;她站在阳台,小女孩也不打个招呼,彼此碰见了,小女孩头都不低地走过去,她总是悲戚戚的。小女孩常常是一个人,总是那个红书包,已经是很久了的,而且,女孩穿的并不好。
她从外地来的朋友,只是担心她,认为她失了恋人,便来陪她一段时间。其实她们并不知道,她只是习惯那段彼此相守的感觉,跟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孤独是一个人的,天生的,宿命的,谁也替代不了,她无法回避。她一整晚地哭泣,人瘦了很多,知情的人,都以为是为死去的人,事实也许确实如此,不过她确实不怎么想念,她只是忆起那日看到的镜头,就想呕吐,就觉得活不下去。那,曾经也是一个人,一副躯体,就那样被毁坏了。然而那些他公司的同事,提起来的时候,还惋惜着那辆车子,不过也说到:“很可能是他怕挂到车子,才往后倒,结果翻了的。”她知道这是有这可能,他是不大开车的,三年也很少开一回,考过驾照已经几年了,也许还是不熟练,怕挂到车子的时候没有控制。然而,谁知道呢?他是已经死了的。那些来跟她说事情的人,还透漏,说是车子被拉回去,费用是保险公司出的,才一千多,并没有损失多少。他们用着一种似乎是同情的口吻,说人已经是死了的,要她往前看。也许,他们知道他并不只有她,但也许他们不知道,可是还有什么必要抖这些事情呢?
没有人过问她的悲伤,也没有人过问小区死掉的少年,或者有人过问,但也只是走个形式。这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南郊公园每天都满满的。很多少女已经穿起了裙子,露出一大截白腿,黑色丝袜在半截的白腿下面妩媚着。她也开始一轮轮地相亲。她相信,终有那么一个人,会碰上,凑合着,过下去。
只是现在还没有碰到罢了。
人们很忙,春去了夏来,有些人死了,有些人活着,就这么回事。不过,你们到底在忙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