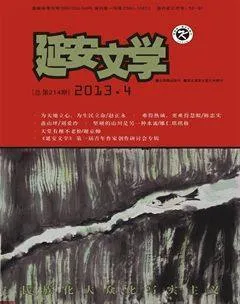怀念地坛边的那个人
2013-12-29小川
一
史铁生的去世还是好友洁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此时,我正在由西安返回兰州的火车上。我清楚地记得,6点刚过,列车员便在车厢里大声喊起来:起床了,起床,换票。我起床,穿好了衣服,迷迷糊糊地去卫生间,并在火车的摇晃中踉跄,几乎摔倒在卫生间里。虽然反应很快,过后,还是在我的后背和腰部留下了青紫的淤痕,用力过猛导致的非协调姿势扭伤了大腿的软组织。我想,今天看来不是好日子。
是的,这天,史铁生去世了。
去年10月,洁来家里,在我的书柜上发现了史铁生的《灵魂的事》,借阅这本书,到了年末她才还回来。书籍比借出去时憔悴许多,我奚落洁,你是怎么折磨了我的书?
这本书一直在我的床头,我出版第一本书时,就带着史铁生《灵魂的事》作为样书和出版社谈。我说,我就喜欢这种风格,素面应天,白纸黑字。后来,大多数的朋友都反对我,说这样很老气,没有时代感。我动摇了。
我和洁都珍爱着这本书,特别是洁刚看完这本书,还对史铁生敬仰不已的时候,史铁生竟然去世了。
我也很愕然。连忙上网搜索史铁生的最新消息。网上很安静,只有麦加和周国平写了关于史铁生的悼文,关于史铁生去世的反应并不很大。正如他说的,“轻轻地来与轻轻地走”。
我不觉得史铁生先生是“轻轻的”,我一直敬仰他,在我的心里,他虽折掉了羽翅,却一直在飞翔,所以,知道的他的人无不敬仰着他。
我又把《灵魂的事》捧在手里,更加逐字逐句地看,我觉得,他的灵魂就在字里行间,就在我的手上。我下意识地虔诚。
我开始寻找那本2005年的日记本。那本日记记载了我在北京的心情——在图书馆买到《灵魂的事》的心情,以及在北京去团结湖的枝末细节。我耐着性子翻遍了书柜,没有;三个大抽屉翻个底儿掉,也没有。晚上,我又去了办公室,终于在办公室找到了那个日记本,翻到了那一页……
2005年9月5日的日记是这样的:
傍晚,我去了团结湖。
的士的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团结湖中路。
在团结湖中路我走了一个来回。我无法打听,如果人家问我找谁,我无法回答。
团结湖在北京市地图上只是一个点,可是到那里才知道实在无法找到。我侥幸地期待一种不期而遇,希望能看到史铁生先生在那里沉思或者干着别的什么。这一切只为一个看似轻飘飘,却又相当沉重的理由:我敬仰史铁生先生!
我还给北京市作协的同志打了电话,希望他们可以帮助我见到先生。
当然,即使已经去了,却洪武收获。那是一个黄昏,我与团结湖公园的售票员攀谈:有坐轮椅的残疾人经常来这里吗?她说有。我想那一定是史铁生。我向她说了史铁生三个字,她说不知道,说不认识。她又怎么能知道呢?
傍晚的团结湖公园游人稀少,来这里的都是老人,要么是孩子。老人们的锻炼显得争分夺秒,专注得不得了,一看就在和生命赛跑。此时,史铁生一定在家里,他是不会知道一个陌生的人,像个孩子徘徊在那里,期盼着和他的不期而遇。我虽荒唐,但确实可以令自己安心,回到宾馆倒踏实地睡去。
二
我没有办法,找不到当初阅读《灵魂的事》的笔记,确切说,已经耐不住性子等待找到它们的时候。只得重新阅读。
“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别说他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如此说,但史铁生还是感恩着自己的命运,就因为那个荒芜而寂静的园子。他那么容易微笑,那么容易感恩。《灵魂的事》里,问号很多——果真如此吗?是这样吗?现实怎样?正当与否呢?美的含义呢?根据什么呢?至今还在?为什么不是?什么才是?哪有尽头?谁说了算?天堂会永远无忧吗?什么是我们?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所以他说:“我是一个愚顽的人,学与思都由于心中的迷惑,并不很明晰学理、教义和教规……”
这些问号也如自言自语,娓娓心境道来,也亲和如彼此的探讨。
是史铁生多次谈到《毛姆随想录》、刘小枫。可刘小枫对铁生的评价有失公允。
那个死神终于不再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他站了起来带走了史铁生。铁生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从容地说:“我正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
于是,史铁生不用再让文字走进他的昏睡,也不用再让自己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没有衰弱,没有被桎梏的不安与痛苦,他真正地脱离了残废的躯壳,俯瞰一切,听所有的梦者诉说。他在生不如死的躯体上,活出了灵魂的巨人。
《皈依是一种心情》,57小节;《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助》,10小节;《说死说活》,14小节;《灵魂的重量》,62小节……所有文字都是围绕生命、精神、肉体、性本质的关系,说白了,地道的灵魂的事。
天堂唯乐,贪官也乐,天堂尚远,钞票却近,况乎见乐取小,岂不倒有风度?我是说,以福乐相许,信仰难免混于俗行。
一个美好的方向不是计算出来的,很可能到是梦想的指引。总之,人为什么不能以万物的和谐为重,在神的美丽的作品中“诗意地栖居”呢?诗意的栖居是处于对神的爱戴,对神的伟大作品的由衷感动与颂扬,唯此生态才可能有根本的保护。经济性的栖居还是以满足人的物欲为要,地球则难免劫难频频,苟且偷生。
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很多人这样问,特别是三毛,越问,越是纠缠不清,所以,她自己主动解脱。但是,对于人的生命,“自杀是一种自由,但不是美德。”
但史铁生说:“要是史铁生死了,并不就是我死了……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会到来,但那时我还在。”这一天真的来了,所以,我也觉得他还在。
正因为“凡我笔下的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待机而动”,所以,我难免虔诚,我捧读的岂止是你的书,你的文字,还有你的灵魂。因此,我懂,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是怎样度过时间上冰冷的刻度,所以,“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遭遇的黑暗更是辽阔无边”;所以,大概是你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你推向了“形而上”;所以,你说,“我们其实永远都在主观世界中徘徊”。
地坛应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我忽然明白了,团结湖的公园过于喧闹,先生肯定会比去地坛的次数少很多。
我的目光里闪回着,看到你曾是羞涩的。你带了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要是有人走过来,你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你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你很要面子。
你也诉说爱情:“豪华汽车之于男人,良辰美景之于女人,都在性的领域。因为那仅仅还是喜欢的状态。喜欢的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的,正如荷尔蒙的分泌之有限。人的心情多变,但心情的多变无可指责,生活本来多么曲折!”我讨厌水性杨花的女人,但人心真的嬗变,于是,我在先生这里找到了注脚。谁让“满意的爱情并不很多,需要种种机遇”。
谁知道,史铁生的病是不是误诊?当他第一次住进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病房时还能走。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三个月不到,病反而厉害了,开始拄拐——
主管大夫每次都说:“好吧,别急”、“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直到有那么一天,全科的大夫都来了,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对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
21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
21岁、29岁、38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
定案之时,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
我也曾这样求过神明,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满心敬畏,但神明不为所动;
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都写下了“上帝保佑”。
他暴躁过,独自一人到地坛去“撒野”,发泄愤怒。
……
这样的结局,铁生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他如此乐观。然而,他确实是挣扎过来的人。
来世!来世吧!你别忘了你曾经的“好运设计”,不丑、不笨,健壮的体魄像豹子一样机敏,
热爱音乐,喜欢艺术,热烈地享受你的爱情,再不会有任何遗憾。因为,上帝已经让你遗憾过。上帝不会让一个人的几辈子都是遗憾的。
我希望医生们,真的弄清了你腰椎里面出过什么事,给你,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那双角膜,放在谁的眼睛里,是不是能看到你的存在呢?不用再对自己不满意了。你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并且给我们留下了精神的圣经。
他说他喜欢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用作品照亮了宇宙。而我,喜欢史铁生,他照亮的是我的心灵。这个声如钟,坐如塔似的男人,在他粗糙的脸庞上有着最动人的质朴的微笑。他真的无所羁绊了,他仍旧轻轻地来去……
三
有一个可以让所有喜欢铁生的人欣然受之的消息——天津那位接受史铁生肝脏移植的患者,本已生命垂危,而他妻子正身怀六甲。现在,铁生以自己的无言爱意,成全了那一户陌生而又亲近的人家。
史铁生“头七”的时候,他的好友医生凌峰哽咽着告慰——“你肝脏的受赠者已度过了排异期。”史铁生把他的生命传递给了另一个人,他的死保住了尊严。
西单图书大厦,是我与《灵魂的事》邂逅的地方。大厦里的人摩肩接踵,很是嘈乱,虽然是夏季,但空调的冷气低得不近人情,U领体恤露出的肌肤让我感受渗到骨头里的凉,直想咳嗽。一楼的门厅摆放的大都是“枕边书”,信手翻看一本,没几页就发现引号引错了位置,这多少让人觉得扫兴。我还是用心地在那本书上打了折痕,为的是让人可以轻松看到这本书里存在的错误,为要买这本书的人负一点责任。
在这里,《灵魂的事》封面素雅,白纸黑字在满目招摇的华丽中反倒抢眼,引人注目。从此,这个犹如从遥远天际飘来的陌生的名字,从未远离。那清澈、平静的文字浸润我心的时刻开始,史铁生便成为我文学阅读中不能忘怀的片段。最为打动我的是这个盘踞在轮椅上的人,思想恢弘地,以真诚的方式思考自己、思考人生,虽无意热烈展示,却容我们仔细旁观、品味,同时,也为我的心灵洞开了一扇深邃的大门。
然而,这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作家,却始终进入不了“专业作家”体制,他的身份因其业余只是一位“合同制作家”,以致于上海作家陈村曾在BBS上贴出文章,替身患重疾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呼吁,希望支持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使之能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史铁生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对于21岁起就下肢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近40年,然后是肾病、透析,无休止的透析对他来说,是无法挑战也无法忽视的困难。他的妻子本身也是残疾人,他们有多少财力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用呢?文学是一件奢侈的事,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支持,那就玩不起了。
如今回过头来看,史铁生的毅力不仅来自残障的肉体,更来自精神。病痛的折磨使得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极其有限,但就是在这种难耐的病痛生涯,他的作品一篇接着一篇,创作量之大,让健康于宝马笙歌的作家们颇有愧怍。看来,健康的身体未必就有健康的思想,残缺的身体未必带来思想的残疾。
在一篇有关史铁生的采访中,题目是这样的:逃避灵魂是写作的致命缺陷。史铁生说:文学就是要在肮脏中寻求干净。我多么喜欢《灵魂的事》,也如此敬仰来自灵魂的文字与思想。
对于我们同时代,一个健康的中国作家去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灵魂的事怕是越来越少,大家都忙着赚钱,灵魂?开什么玩笑?能挣几个钱?
越是喧闹,我越是逃避。在满是功名利益之下的面孔中,我的眼睛只能看见史铁生——一位思索人生性灵的心灵创作者,成为无法媲美的一代名家。他脸上,又露出了他有时碰见最高兴的事情时那种多少带点痴气的表情:完全孩子气的得意、满足,以及一丝丝的调皮、淘气——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
坦然赴死,你能够
坦然送我离开,此前
死与你我毫不相干
……
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
永恒复返,现在被
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
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