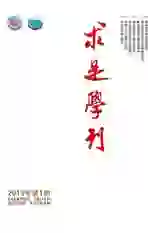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
2013-12-29马新彦邓冰宁
摘 要:现代化通信工具在带给人们无限便利的同时,也为侵权者的侵权带来了效率。但面对以损害波及面大、个体侵权数额小、侵权主体隐蔽为特点的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颇感力不从心。美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产生的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历经几十年的审判实践验证具有极为显著的制度优势。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可以填补侵权行为造成的一般侵权责任无法填补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而且能够激励受害人积极主张权利,并且以最小的成本遏制恶性的侵权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需要设立开放性和指导性的一般条款,明确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认定标准,并应赋予现代化通信工具运营商不真正连带责任。
关键词: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社会性损害的民事救济
作者简介:马新彦,女,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法学研究;邓冰宁,男,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民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85-11
现代化通信工具的发展与广泛运用,“地球村”的预言已然成为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人与人之间交往频率与速度的提高而展现出无比繁荣的景象。然而,现代化通信工具在带给人们无限便利的同时,也为侵权者的侵权带来了效率。侵权行为人坐在房间里利用手中的通信工具即可在他人的损失中获利。电话、传真发送广告、诱使他人回拨电话套取电话费、诱使下载软件套取资费等即为典型事例。这些侵权行为具有损害的波及面大、个体侵权数额小、侵权人隐蔽等特点。损害的波及面大表明,侵权行为不仅有私人利益的损害,更有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个体侵权数额小决定了受害人主张权利的成本大于其所获得的赔偿,从而无法激励受害人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的积极性;而侵权人隐蔽又决定了公力救济的成本过高等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互联网侵权责任的特殊规则,开启了信息时代侵权责任法规制现代化通信工具侵权行为的全新课题,但面对这些损害波及面大、个体侵权数额小、侵权人隐蔽等特征的侵权行为却颇感力不从心,使得侵权人获得暴利后仍能逍遥自得。本文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逻辑强制和体系规范之内,设计和论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期有效治理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的侵权行为。
一、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的类型及其特点
(一)行为类型
现代化通信工具本身的危险性造成他人权益的损害(如生产销售一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手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行为人利用现代化通信工具针对特定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如在互联网上诽谤他人名誉、泄露他人隐私)已经得到《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较为完善的救济,故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本文所称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意指行为人利用现代化通信工具向不特定众多人实施的使众多受害人遭受损害,自己获得巨大利益的恶劣行为。
1. 利用现代化通信工具向众多人发送垃圾广告
行为人通过窃取、购买或者号码自动生成系统等手段掌握大量座机、手机号码,以及传真号码等,并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向众多不特定人发送垃圾广告。通过此种方式发送广告较之通过媒体发布广告,具有成本低、收效大的优势。然而,对于无意接收广告的人却是一种灾难,在美国的一起案件中,行为人通过传真连续几个月内向同一位受害人发送近百封内容是宣传金融服务的垃圾广告1,严重干扰了受害人的日常生活,受害人不仅仅因为接收垃圾广告而遭受精神损失,还因损耗打印纸、墨粉、电力而遭受财产损失;通过电话发送垃圾广告,尽管不会发生打印纸、墨粉等损耗,但仍会给受害人正常生活或工作造成干扰,如果受害人接收时在异地或在国外,受害人还将遭受电话资费的损失。
垃圾广告传播的另一种更便捷的方式是通过网络发送,这种传播似乎不会打扰受害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但仍会导致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通过网络发送垃圾广告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通过窃取电邮地址或自动生成系统发送垃圾广告至受害人的电子信箱中,尽管各大网络服务商已经将邮件进行分类,但是仍有分类不准的可能,导致一些重要文件归类于垃圾邮件中,而垃圾邮件归类于收件箱中。阅读、甄别、删除垃圾广告给接收者造成时间、电力,以及网络资源的浪费,甚至有可能遭致误将正常邮件当作垃圾邮件删除或屏蔽的不幸,由此导致受害人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另一种是通过网络直接发送至电脑页面,只要网络有链接,商家的广告便不断地跳跃在电脑屏面上。不断跳跃的商家广告常常遮住工作页面,使受害人的工作状态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危害受害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2. 诱使回拨电话以套取话费
行为人利用窃取的电话号码或自动生成系统获取的电话号码,以各种手段诱使机主回拨电话,从而套取电话资费,手段繁多且不断更新。常用的手段是群拨电话,并在极短时间内挂断,诱使机主,尤其是等待重要来电的机主回拨电话。另一种手段是窃取QQ号及身份等信息,发送短信:“某某,我想你了,有时间给我回电话”,待回复电话时里面响起资费昂贵的音乐。最近频频使用的手段是拨通电话,播放语音:“这里有你的刑事传票,限你24小时内前来领取,否则将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欲知详细情况,拨打电话××××××号。”这种近乎卑劣的手段在给机主造成电话资费损失的同时,还会给缺乏法律常识的机主带来恐慌和心悸。
3. 诱使下载软件获取资费
行为人获取个人信息,发送下载软件的通知,并有意造成无偿下载的假象,导致受害人下载软件费用的损失。行为人以某品牌手机及经销商的名义发送以“服务信息”为名的短信信息,通知下载消毒软件,受害人相信是该品牌手机的特殊服务,下载了软件,结果扣除资费50元,非但如此,下载的软件为病毒软件,导致所有的短信无法收取,造成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精神损害和机会利益损失。
4. 变相强制消费获取资费
通信公司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向众多手机使用人增设名目繁多的服务项目,同时为取消这种有偿服务设置了极其烦琐的程序,并告知手机使用人可以通过其设置的程序取消增设的服务,依据《合同法》第22条的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如果手机使用人未按要求取消服务,似乎可以认为使用人对增设特殊服务项目的要约的承诺,通信公司收取服务费用具有正当性。但是,对于因年长或工作繁忙而无暇或无能力按照其设置的程序取消服务的使用人而言,等同于被剥夺了自主决定权,被迫接受通信公司增加的有偿服务,致使手机使用人的财产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手机账户慢慢转移至通信公司,甚至给使用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与上述侵权行为一脉相承的另一种行为是强迫受害人承担因拒绝继续接受行为人发送的信息或取消有偿定制而产生的费用。通信公司向众多手机使用人发送垃圾广告,甚至不属于垃圾广告的一般信息,并告知如果不想继续接收此类信息,可以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拒绝接受”;或者,通信公司增设有偿服务项目,告知使用人依照其设置的程序短信回复拒绝接受服务。表面上人性化的服务暗藏着利用短信收取费用的目的,以一条短信一角钱计算,全国若有一亿手机使用人回复此类短信,仅此一项,通信公司即可获益一千万元人民币。
(二)行为特点
1. 行为貌似合法
行为人的行为尽管给广大的受害人造成财产以及精神的损害,行为人也从中获得不应当得到的巨大利益,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无法律明确禁止利用现代化通信工具发送广告等行为。因此,行为人自称其行为不具有不法性,而堂而皇之、明目张胆地在行为中获取暴利。这已成为在现行法框架下对行为人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的巨大难题或障碍。
2. 行为隐蔽
行为人多以无记名号码或者貌似于95×××、100××类的特服号码向受害人发送广告或者信息,行为极其隐蔽。受害人无从得知行为人是谁,在何处。寻找加害人的成本远比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大。
3. 行为导致的单个受害人的物质损害小
单个受害人在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中遭受的损害主要表现为微量的电力、印刷成本、时间利益、短信费用、电话费用等物质性损害。依据我国传统侵权法理论,“对于极少量的财产损失或极其轻微的人身、精神损害,法律则不认为有必要进行补救”[1](P123)。这种数额不大的损害因其欠缺法律上的可救济性因此会被侵权责任法所忽略。而且,即便是可以予以救济,也因为诉讼成本远高于经诉讼得到的赔偿,受害人宁愿遭受损失,也不愿意向行为人主张权利。
4. 行为人不当获益巨大
行为人向不特定的众多人实施侵权行为,所有被行为人猎取号码的人均在行为人侵害范围之内。行为人在每一个侵权行为中都将获得巨大利益。以回拨一个电话获利一角钱计算,一亿个回拨电话即可获利一千万元。
5. 社会利益损害严重
行为人利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给社会大多数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是破坏。在美国的一起案件中,行为人雇佣一名广告人在2006年6月短短两天的时间内向8336个医疗机构或者与之相关行业的受害人发送宣传自己销售的医疗设备的垃圾广告邮件1,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众多医疗机构或相关行业的正常信息传播,严重破坏了整个医疗行业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共享的正常秩序和运行机制。
二、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美国法先例
手机和互联网作为现代化通信工具的代表均诞生和繁荣于美国,美国也最早深受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之害。自1991年美国联邦《限制使用电话设备法》(Restrictions on use of telephone equipment)规定了故意或者明知向众多人发送垃圾广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此后,其他相关法律也相继出台,如2003年的《控制垃圾黄色信息和垃圾促销信息法》(Controlling The Assault Of Non-Solicited Pornography And Marketing)和2010年的《防止滥用电话促销法》(Telemarketing Sales Rule)等。几十年的审判实践经验证明,对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既可以有效地填补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又能够激励受害人主张权利的积极性,并且以最小的成本遏制恶性的侵权行为。在制度设计上有其成功之处,值得我国借鉴。
(一)关于行为的不法性问题
通过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巧妙地掠夺众多人的财产,以获取自己最大利益的行为,应当得到法律的制裁和规制。而行为的不法性是科以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首要前提。
美国《限制使用电话设备法》对通过电话、传真、电脑或其他设施发送广告需具备的条件做了严格规定:第一,向已经建立商业关系的客户发送广告;第二,收信方基于与发信方之间存在商业关系自愿提供号码,或者收信方在电话本、广告或因特网上自愿留下自己的传真号码以供联系;第三,广告本身符合商业广告的硬性要求1,如广告内容必须于第一页清晰明了地表明,发送人在发送这种商业广告之前必须获得接收人同意等。非具备上述条件,通过电话、传真、电脑或者其他设备向未经同意接收广告的人发送宣传自身商业能力以及财产或者服务质量的广告属于违法行为2,这类广告被称为垃圾广告。3
《限制使用电话设备法》47 U.S.C. 227,(b) (2) (D)规定:如果发送方在发信时留下了拒绝继续接收此类信息的联系方式,接收方通过此种方式取消定制时必须承担费用的,则无论发送方发送的信息是否构成垃圾广告,也会因为迫使接收方承担有偿联系的费用而被定性为垃圾广告,具有不法性。
《联邦贸易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15 U.S.C.45(1)规定:任何通过不正当的方式竞争或影响交易的行为,以及任何通过不正当或欺诈的方式影响交易的行为,均违反本法。因此,类似于通信公司以各种名目实施的强制消费行为违反了《联邦贸易法案》15 U.S.C.45(m)(l)(A)的规定,具有不法性。
(二)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
1. 发送商业盈利性质的垃圾广告
违反前述法律规定之情况,即是向他人发送垃圾广告,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如果行为人以盗窃、购买或利用号码自动生成系统或地址自动生成系统获取的号码和地址大规模地向不特定的众多人发送广告时,即使发送的内容并不满足垃圾广告的要求,也必须承担发送垃圾广告时所必须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自动生成系统”通过特殊功能的设备有序地产生、存储和生成电话、传真号码或电邮地址,再通过该设备的特殊功能拨打电话,群发短信、电子邮件或传真邮件。4通过使用这种自动生成系统,行为人不必去了解每一个接收者的具体信息,而只要进行“地毯式”的大规模发送行为即可达到自己传播信息的目的。除了上述垃圾信息大规模侵权的行为之外,由于这种利用号码自动生成系统的侵权行为所威胁的潜在受害人甚多,而且行为人的心态又多是故意或者不计后果,因此,美国法制裁这种行为时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科以惩罚性赔偿责任。
2. 冒用他人身份获取利益
现代化通信工具的高速发展,使行为人更加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人身份信息,并且利用电子商务的漏洞假冒他人,并利用假冒的身份侵害他人权益,最终造成大规模的私人损害和社会性损害。典型的冒用他人身份获取利益的案件是冒用他人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设立并反复使用的信用卡、银行账户、抵押贷款、汽车借贷、保证金账户、手机银行、水电费账户、支票账户或储蓄账户。美国法通过实体法将冒名顶替他人的侵权行为从一般司法救济中独立出来,并注重加强对于受害人的救济。[2]行为人在发送电子邮件时,即使发送人地址、身份或使用的姓名为虚假,只要内容和主题均为真实的,就会因为冒用他人身份而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1
此外,美国法不仅规定了直接侵权行为人必须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也规定了相关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对使用自己服务的消费者的身份信息负有保护义务。例如,当消费者可能因身份被盗窃而蒙受损害时,那些收集和管理消费者信用信息的机构必须及时对消费者提出警告2,一旦相关服务的提供者未能履行这种义务导致消费者蒙受损害,就必须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一旦服务的提供者故意违反这种保护性义务,将导致惩罚性赔偿。
3. 通过诱使接收方有偿回拨电话套取电话费用
发送方纯粹地以诱使回拨的方式诈取通信费用,将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首先,行为人需要承担违反《限制使用电话设备法》47 U.S.C. 227, (b)(1)(B),(C)规定的责任。此外,依据《联邦贸易法案》15 U.S.C.45(m)(l)(A)的规定,行为人应当为自己每一次的违反行为承担不超过10 000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例如,在U.S. v. Comcast Corp案3中,被告电信公司和第三方合谋,拨打了900 000次诱使回拨的电话以诈取资费,因此,法院判决被告承担900 000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4. 通过欺诈性链接的电子邮件套取由此产生的资费
依据2003年《控制垃圾黄色信息和垃圾促销信息法》15 USCS §7704 (a) (1)的规定:“任何人通过商业性、交易性或者其他关系下的电子邮件向其他受保护的电脑传播包含或者附带标题信息为重大误导性或虚假性内容的信息均违反本法。”如果行为人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包含诱使接收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点击并因此产生资费的链接,将承担违反该法的责任。4
5. 强迫接受有偿服务或者强迫有偿取消定制
行为人强迫受害人接受某种有偿电信服务5,或者尽管是无偿服务,若取消该种服务必须支付因取消服务产生的费用时6,亦严重侵害众多受害人的消费自主权,同时对社会大众的自由、自主和生活安宁也造成了严重威胁。行为人需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
美国法采用法律规定与法官裁量权相结合的方式认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具体有三种认定方法。第一,原告可以证明实际损害的,在实际损害的三倍以内确定惩罚性赔偿额。《电话用户保护法案》、《限制使用电话设备法》以及《控制垃圾黄色信息和垃圾促销信息法》均规定法官有权在原告举证的实际损失的三倍以内予以认定。原告可以证明的实际损害包括物质损害、精神损害和纯粹经济损失。物质损害包括因接收垃圾传真和电子邮件而耗费的打印纸、墨粉以及电力7,因接听垃圾广告电话而浪费的电话费(尤其是国际漫游费用),因手机诈骗损失的财产和因强迫定制有偿服务或有偿取消服务损失的财产等;精神损害包括接收垃圾广告导致的精神痛苦,阅读垃圾短信和电邮带来的烦恼困扰,因诱使回拨导致的强烈的厌恶感;纯粹经济损害包括接收传真并阅读垃圾广告浪费的时间、因接收传真或邮件耽误工作或接收其他更重要的传真或邮件的机会,受害人因为阅读垃圾广告、删除垃圾广告浪费时间、影响工作或生活等。第二,原告的损害无法计算,或者虽能计算但不足500美元,以500美元确定惩罚性赔偿额。《限制使用电话设备法》47 U.S.C. 227第(b)(3)(B)规定:“私人可以对违反本法的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请求赔偿,或者当实际损害不满500美元时依500美元起诉。”第三,损害赔偿额以250美元为基数乘以违法次数计算。2003年《控制垃圾黄色信息和垃圾促销信息法》15 USCS § 7706 第(f)(3)(A)规定:“损害赔偿的数额为250美元乘以违法次数。”
三、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
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的上述特征,为一般侵权责任的适用带来理论难题与制度障碍,行为不法与行为的隐蔽位居之首。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认清这种行为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性,并以法律予以明文禁止,不法性的问题将不难予以解决;只要我们运用高科技的手段确定行为人的身份与位置,一般侵权责任的障碍也不难予以排除。“单个受害人损害数额小、侵权人获益巨大、社会利益损害严重”所带来的制度障碍,唯有惩罚性赔偿方可予以解决。
(一)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前提
损害赔偿责任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害,而不是惩罚。因此,凡惩罚性赔偿正当性的证成者均竭尽全力论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损害填补功能。美国学者格林里夫(Greenleaf)是公私法划分的坚定支持者,他拒绝在作为私法的民法领域承认执行部分公法功能的超额赔偿。[3]而惩罚性赔偿之惩罚功能,抑或损害填补功能的论证,源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高于一般损害赔偿的数额”性质及内容的界定。如果“高于数额”被认定为“非损害”,惩罚性赔偿便是超过受害人损害的超额赔偿,被告将因侵权而遭受惩罚;如果将“高于数额”界定为损害,惩罚性赔偿便是填补损害,而不是超额惩罚。美国有法官和学者多认为惩罚性赔偿不存在任何惩罚的功能,而只是为了填补原告遭受的有形损害以外的无形损害。[4]主张原告获得的赔偿应当同其蒙受的损害精确相等,从而否认惩罚性赔偿造成了超额赔偿的客观结果。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一般损害赔偿不能填补侵权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害,因而必须由惩罚性赔偿制度使行为人承担其侵权行为的全部成本。[5]对于损害填补功能的论证不乏填补金钱难以衡量之损害、满足复仇需求、填补个人尊严损害等多种学说。当侵权法于 20世纪走进繁荣时期,惩罚性赔偿在精神损害赔偿以外的更广泛的领域被适用时,社会性损害填补理论成为一时占统治地位的学说,该说是理论界对司法判例趋势宏观归纳整理和提炼的结果,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填补受害人本人以外的社会性损害的功能,原告只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代表享受对于社会性损害的填补,可以通过后续辅助性的技术手段分割这些损害填补,从而使所有社会成员得以共享。[6]原告只需证明除原告以外的社会上多数人均受到被告同样行为的侵害,法院即允许陪审团以原告的实际损害为基数,以多数人的损害为参考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1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美国广为人知的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案2、Campells v.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案3以及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案4代表了这一时代惩罚性赔偿填补社会性损害的新趋势。由于社会性损害填补理论主张的惩罚性赔偿不过是通过原告填补与原告处境相同的其他人的损害,遭到学者诸如原告代表其他人受益违反正当程序原则、原告受益不当等质疑。[7]对此,另一种新的诠释有力地回应了这种批评,从而使社会性损害填补理论得以升华。新社会性损害填补理论认为,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破坏了自由社会的秩序,使其拥有高于他人的“自由”,从而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背叛了主权国家宪法及法律的制度体系。因此,这种将自己置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不法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受害人的私人利益,还有国家的利益。[8]在恶意或故意的侵权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可以使那些因为诸种原因无法或难以被追究公法上责任的主体承担金钱责任,还可以节约司法成本,避免刑事处罚对企业活力的扼杀。惩罚性赔偿制度中超过一般侵权责任的赔偿不仅对私人受害者有利,也有利于社会和国家。[8]总之,惩罚性赔偿填补因侵权所造成的全部损害与一般侵权责任能够救济的损害之间的缝隙。
在我国,学者几乎都认为“高于数额”为“非损害”,这不仅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反对者提供了锐利武器,也使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赞成者作茧自缚。笔者认为,“高于数额”为可见损害背后的无形损害,包括难以用金钱衡量的受害人私人精神损害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我国已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予以救济。但是,侵权人存有恶意并以极端恶劣的手段侵犯受害人权益,受害人遭受了大于一般过失情况下的精神损害,以及依现行法规定对受害人遭受不予救济的精神损害,需要惩罚性赔偿予以最完美的救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的五种欺诈行为、《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填补的,则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虽然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非受害人私人的损害,科以被告人惩罚性赔偿责任将使原告获得大于其所遭受损害的赔偿,但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仍为“损害”,借助惩罚性赔偿予以填补具有正当性。当侵权人的恶意行为不仅仅使受害人蒙受损害,而且给整个社会的交易环境、生存环境带来损害时,适用惩罚性赔偿使赔偿权利人所获赔偿承载社会整体利益,也不应当给以否定性责难。总之,所谓的“超额”赔偿实际上是对可见损害背后无形损害的赔偿,只是因为无形损害难以用金钱衡量,而以可见损害的合理倍数予以计算。法学家们需要认真研究的不是惩罚性赔偿的存与废,而是“倍数”的合理性,以及一般赔偿责任无法填补哪些侵权行为造成的受害人私人的损害,尤其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需要惩罚性赔偿予以救济。当然,惩罚性赔偿不乏对于恶性侵权行为的惩罚功能和阻却功能。因为“效率有时候要求的是禁止该行为,而不是承担责任”[9]。与其蒙受损害后寻求救济,不如一开始就避免发生这种难以弥补的损害,法律进行损害赔偿救济追求的第一目标是阻却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阻却目标恰恰是通过让被告承担同他行为相应的损害填补责任的方式实现的。[10]当一般侵权责任所提供的救济同行为人造成的损害不符时,不仅导致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济、损害得不到填补,也导致被告承担的责任不足,从而发挥不了应有的阻却与惩罚功能。
(二)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填补之损害
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所导致的无法以金钱衡量的无形损害,一般侵权责任无法予以救济,只能由惩罚性赔偿予以救济。第一,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干扰了受害人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由此导致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第22条将侵害受害人人身权益作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导致的受害人精神损害显然不在《侵权责任法》22条救济范围内,无法得到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救济。即便这类行为侵害了原告受现行法保护的物质性人格权益,但是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不能达到“严重”,仍同样得不到现行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依现行法无法救济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需要惩罚性赔偿予以救济。第二,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导致的损害完全超出私人原告和不能确定身份与数量的受害人所蒙受的个别损害的范围,整个社会的生活、工作秩序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6];更有甚者,行为人以现代化手段获得暴利并逃避法律责任,也严重践踏了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使自己获得了高于他人的“自由”,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背叛了主权国家宪法及法律的制度体系。因此,这种不法行为损害的绝不单单是受害人的私人利益,更有国家和社会的利益。[8]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的损害填补局限于私人视角,忽视对社会性损害的填补,不仅使行为人逃避部分责任导致阻却效率不足,也无法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一般侵权责任因其成本甚巨而难以涵盖这种因违反社会规范和道德造成的社会性损害,因为,如果在民法领域以社会规范和道德取代一般侵权法逻辑体系,将面临法律制度崩溃的风险,“以社会规范取代法律逻辑的高风险在于,要么彻底矫正社会上的此类行为,要么使法律本身丧失公信力”[9]。这种代价实在太过高昂,使得法院必须依据侵权法逻辑而非社会规范和道德判断一般侵权责任,从而也要忍受一般侵权责任所导致的阻却不足。[9]在这样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只有建立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方能填补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全部损害,才能使行为人承担与其恶性相适应的责任,真正实现侵权责任的阻却功能。
(三)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价值
1. 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激励受害人主张权利
一般侵权责任在原告意识到了损害的存在,但是因为可得的损害赔偿太低或者受害人自身处于弱势地位时,难以发挥有效地激励原告起诉的功能。[6]在大部分的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受害人依据一般侵权可以获得的救济都十分有限,导致受害人起诉的意愿降低,由此导致行为人逃脱责任的恶果。通过建立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有效地激励小额受害人积极起诉,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如同美国学者Owen先生指出,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助于在极端恶劣的侵权案件中对不法行为人的确认;可以作为促使实际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作为“私人检察长(private attorney general)”追诉不法行为的奖励,这种情况下惩罚性赔偿超过受害人可见损害部分的数额就是一种“悬赏”,使得所有应当被惩罚的不法行为均得到追究,以彰显正义[11],“由此,那些在刑法领域仅仅得到部分彰显的正义,可以通过私人追诉人将不法行为人诉诸法院的公共服务行为,以被告承受的私法上的罚款方式得以完全彰显”[11]。通过科处惩罚性赔偿,可以激励受害人积极寻求侵权法保护,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从而有效治理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
2. 惩罚性赔偿制度能有效助成公权力对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治理
行为人的行为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无疑应当首先受到公法的规制与惩罚。然而,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隐蔽性决定公权力治理的成本过高和过难。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激励受害人行使权利而将部分行政成本转由受害人暂时承担并最终由行为人承担,有利于在不增加行政负担的条件下实现法律对不法行为的有效规制,不仅使原告获得了更多的司法资源,也大大提高了被告承担责任的几率。[8]此外,在庭外和解确定数额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存在使得这些和解协议中必然包含惩罚性数额,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损害填补责任。美国的司法实践经验证明,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使那些因为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从而难以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金钱责任。这些主体的不法行为虽然侵害了公共利益,但是因为其复杂性和隐蔽性往往难以追究。惩罚性赔偿也使那些行政机关受限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而难以顾及的不法行为得到了有效追究”[8]。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改变了国家对于司法资源的分配,使得那些本来被国家忽视的侵权案件获得了更多的司法救济。
可见,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对私人受害者有利,也有利于社会和国家,“使侵权人所承担的的责任真正与其不法行为的损害后果相适应,对于保障社会经济秩序、节约诉讼成本和避免刑事处罚扼杀企业活力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公共利益得到了最好的维护”[8]。
四、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计
(一)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般条款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将呈扩张性、开放性的发展趋势,立法者无法预料有多少种类的行为构成大规模侵权。鉴于此,应当在《侵权责任法》中将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一般条款的方式予以规定:“利用现代化通信工具进行大规模侵权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如此设计,不仅遵循《侵权责任法》简洁明确、清晰易懂,节约立法资源的一贯传统,为具体特殊规则的设计预留足够的空间,而且利于清楚明确地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地位,以昭告社会,彰显这一制度重要的损害填补与惩罚、阻却功能。
(二)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惩罚性赔偿较之一般损害赔偿对侵权人而言是一种严厉的责任,美国法历来将行为人的极端恶劣的主观心态作为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兼顾公平,限缩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1。学者对行为人恶劣的心态描述为恶意(malice)、故意、莽撞、不计后果,以及对他人的利益无视或者漠不关心等,只有这样的主观心态方可科处惩罚性赔偿。[12]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一般情况下,当被告的行为出于恶意(malicious)、压迫性(oppressive)、重大过失的(gross)、肆意(willful)、莽撞(wanton)时可以科处惩罚性赔偿。”[9]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的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也要求侵权人主观有过错。因此,惩罚性赔偿责任为过错责任。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亦应采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明知自己行为的内容,也知晓这种行为在给自己带来便利或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将给众多人造成损害或困扰,仍然执意为之,为其有过错。
(三)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源于惩罚性赔偿责任对社会性损害的填补功能。现代化通信工具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除具备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外,还应具备特殊要件,即大规模侵权。而认定大规模侵权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第一,受害人数量。受害人数量巨大,直接结果是侵权人因侵权获得巨大利益,整个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巨大影响,具有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第二,反复实施侵害行为。受害人人数虽然有限但侵权人反复实施违法行为,给受害人造成巨大伤害,由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第三,手段恶劣。行为人使用号码或地址自动生成系统发送短信、电邮、拨打电话或发送传真,无须考察接收人的数额,即可认定大规模要件成立。
(四)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
借鉴美国惩罚性赔偿额三种认定方法,笔者认为,鉴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利益损害,因此,惩罚性赔偿额应以实际损害的二十倍予以计算确定,实际损害不易或无法计算的,或者实际损害数额极小,但侵权人获益巨大的,以10元乘以违法次数确定惩罚性赔偿额。
(五)现代化通信工具运营商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现代化通信工具的运营商拥有管理运用现代化通信工具的设备和技术水平,有能力预防、发现和控制大规模侵权行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有能力查清侵权行为人的身份、地点。更重要的是,运营商在行为人使用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行为中,自己也获得了运营收益。因此,运营商负有义务管理、防范大规模侵权行为的发生,大规模侵权行为一旦发生,运营商有可归责的原因。因此,在侵权行为发生时,原告人可以向运营商,也可以向侵权人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原告人向运营商起诉主张权利的,运营商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或者,运营商作为被告被诉之后,可以追加侵权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直接由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赋予运营商不真正连带责任可以督促运营商改进服务,预防和制止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也可以有效地追诉侵权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赋予运营商不真正连带责任,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方能得以贯彻实施。如果运营商与侵权人恶意串通实施大规模侵权行为的,运营商应当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运营商独自实施大规模侵权行为的,运营商独自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需要相关配套法律相衔接,即立法机关应当为各运营商在可能出现现代化通信工具大规模侵权行为时规定作为义务。可借鉴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案》(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依据《公平信用报告法案》16 CFR 681.1的规定,所有涉及保管和汇总他人身份信息的主体,包括银行、律师楼和医院等,只要与他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就必须依据本行业的情况,确立可能存在身份盗窃的判断标准,这些标准就是竖立起一面面“红旗”。一旦发现了应当判断为身份盗窃的行为,义务人必须马上采取这一实体法所规定的措施防止和减轻损害,否则义务人就被认为是违反了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们的过错也像一面面红旗一样昭彰。参见Nicki K. Elgie: Identity and Data Loss: The Identity Theft Cat-and-Mouse Game: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Latest Maneuvers. 4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645, 2008-2009 Winter)和参酌《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的规定:第一,运营商必须建立配套的管理机制,有效监督他人是否利用自己提供的服务从事侵权行为;第二,在出现可疑情况时,运营商应当及时通知当事人和主管机关;第三,运营商在损害发生时必须控制和尽力减轻损害;第四,运营商必须为受害人追究行为人责任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包括提供服务记录、行为人个人信息和本公司运营方式等资料。
参 考 文 献
[1] 张新宝.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 Nicki K. Elgie. Identity and Data Loss: The Identity Theft Cat-and-Mouse Game: An Examination of
the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Latest Maneuvers[J].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ety. 2008~2009,(4),Winter.
[3] Michael Rustad. Thomas Koenig: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Reforming the Tort Reformers[J]. 42 Am. U. L. Rev. (1993).
[4] Thomas B. Colby. Beyond the Multiple Punishment Problem: Punitive Damages as Punishment for Individual Private Wrongs[J]. 87 Minn. L. Rev. (2003).
[5] B. Sheila. Two Worlds Collide: How the Supreme Court’s Recent Punitive Damages Decisions Affect Class Actions[J]. 60 Baylor L. Rev. (2008).
[6] Catherine M. 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al Damages[J]. 113 Yale Law Journal (2003).
[7] Marc Galanter. Shadow Play,The Fabled Menace Of Punitive Damages[J]. 1 Wisconsin L. Rev,(1998).
[8] Dan Markel.Retributive Damages: A Theory of Punitive Damages As Intermediate Sanction[J]. 94 Cornell Law Review,2009,January.
[9] Robert D. Cooter. Punitive Damages,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Analysis[J]. 60 Law & Contemp,1997, Summer.
[10] Steve P. Calandrillo. Penalizing Punitive Damages: Why the Supreme Court Needs a Lesson in Law and Economics[J]. 78 The George Washington L. Rev,2010.
[11] David G. Owen. A Punitive Damages Overview: Functions, Problems and Reform[J]. Villanova Law Review,1994,(39).
[12] Dorsey D. Ellis, JR.. Punitive Damages :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w of Punitive Damages[J]. 56 South California Law Review,1982.
[责任编辑 李宏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