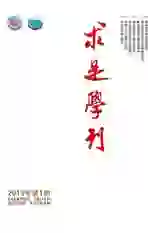论泰州学派美学的“生”范畴
2013-12-29邵晓舟
摘 要:在泰州学派的美学中,“生”规定着美的特征。血肉之躯承载的生意淋漓的生命是“生”范畴的根本含义。美从一开始就与“生”不可分割,人之“生”作为具体而微的缩影,凝聚和赅备宇宙万物之“生”。“生性”、“好生”和“生机”三个层面,蕴藏着“生”的道德性、情感性和自由性的超越力量。人类日常生活实践千头万绪,能成其为美的,唯有符合“生”这一特征的部分。
关键词:泰州学派;美的特征;生;生性;好生;生机
作者简介:邵晓舟,女,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师,从事古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泰州学派平民生态美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0SJB720015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35-06
在我国思想史版图上,诞生于明中叶的泰州学派是一座独具特色的高峰。泰州学派很少直接论述审美和艺术,然而哲学问题和审美问题往往是重合的,美的境界常常是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作为儒家传人、王门后学,泰州学派也将“美学理论融汇于其探讨宇宙天道、人生天性的学术理论中”[1](P257),而“生”范畴则被其视为美的特征。
可以说,我国的各大传统思想流派都对“生”的范畴进行过精彩的阐述,集中到泰州学派立足的儒家话语体系中,“生”更可谓举足轻重。在与“道”、“命”、“德”等六类范畴的互动中,其内涵得以展现:“‘生’首先是指事物的长、进,指个体事物的自我生成,即自身形态由隐蔽的转变为显现的,或者指一事物生出另一事物。”进而“儒家逐渐将‘生’与宇宙天地的大化流行联系起来,将之视为天地万物的根本,并根据现实伦理生活的需要,赋予了‘生’以深刻的德性内涵”。[2](P24)“生”作为被赋予伦理内涵的自然现象,甚至成为儒家理解和处理天地物我关系的出发点。泰州学派的论述也由此起步。
1.何谓“生”
在泰州学派的言说中,“生”除了用作“初生”、“所生”、“化生”、“形生”等表示诞生、产出等义的动词之外,最基本的用法当是“舍生杀身”[3](P29),“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4](P118)等表述中的那样,指宇宙间万类生灵得以存在和活动的最根本属性和能力——生命,而与“死”对举。我国传统哲学对“生命”的探讨同样莫衷一是,在泰州学派看来,血肉之躯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依托和载体,一旦“杀身”,那“生”也将不复存在。因此,“生”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物质性特征。
但“生”又并不仅仅是可闻、可感、可直接触摸的具体物质,它更是蕴含在躯壳内的创造力和驱动力。周汝登曾以草木为例:“人于草木,以根为本,以杪为末者非也。生意其本,根与杪皆末也。”[5](P117)从物质层面看,植物的根是本,枝是末,但这只把握了表象。质言之,肢体、枝叶都是末节,而生命的内在动力“生意”才是真正的根本。失去它,宇宙会僵化凝固、万物会死亡凋零。“生意”虽不可把捉,但切切实实地存在。它具有普遍性,并不专属于某一事物,而是源源不绝地遍覆周流于宇宙之间,所谓“化工生意无穷尽”[3](P59),万物都浸润着它的恩泽,所以圣人才能由“庭前草色”而领悟到“生意一般”[4](P102)。
据此可以归纳,血肉之躯承载的生意淋漓的生命是“生”范畴的根本含义。泰州学派进而通过生命的对立面——“死”来丰富“生”的范畴:
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盖谓死莫非生,而鬼无非人也。夫知死无非生,则古即今,今即古,而万世斯一矣;鬼无非人,则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统矣。[4](P339)
这段有着六经印证吾心意味的阐述说明泰州学派对“死”的态度——死犹生。这不仅指认识层面上的“视死如生”和实践层面上的“事死如生”,更进一步传达出:既然天地物我都融贯着无处不在的“生意”,那么生死幽明、古往今来、已知未知,所有的一切也都不再截然对立、迥然孤立,而是彼此相通共容甚至相互转化的。“死”何尝不是“生”的另一张面孔、另一种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天地间无物不“生”,“盎然宇宙之中,浑是一团生意”[6](P26),宇宙就此化为浑融的生命整体。
2. “生”的状态
在泰州学派看来,无处不在的“生”表现出如下状态:
首先是“生生”,表示“生”各赋完形、永不枯竭的状态。王栋一言以蔽之:“造化之生物不息而品物咸章也。”[3](P176)这句话涵盖了“生生”的两个层面。第一层是“天机到处自生生”[7](P171),描述了生命在宇宙这完满整体间不可遏抑、奔流涌涨的状态,因此,“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云者,生恶可已也”[6](P10-11)。第二层则是“生生成象”[7](P15),“生生”不仅是生命力的丰盈增长,更是生命体的扩散累加。形态各异的万类生灵不断繁衍又彼此依存,展现出宇宙整体内在的宏大而精妙的有机结构。
其次是“生化”,表示“生”变化莫测、灵动圆妙的状态。生命的增殖绝不是简单复制、数量累加,世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可见“生”繁衍增长的过程也是生命个体不断演变进化的过程,即所谓“万象万形之生生化化也”[7](P14)。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本身就蕴藏着不断自我改变、自我完善甚至自我超越的潜能。这种潜能随生命的轮转自然运行着,活泼泼地,没有一刻僵化凝滞,更无须外力抑制或助长,其自然圆融的奥妙至今也无法穷尽,所谓“生化圆融之妙,自达之顺而靡滞矣”[4](P200)。它不仅使个体或族群更加趋近完善,也使作为生命整体的宇宙无限趋近和谐。
3. “生”的属性
泰州学派进而追溯,“生”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宇宙间生命“生生”不息、“生化”不已。
首先是伦理性的“生德”。泰州学派继承了“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传》)的基本观念,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则浑然亦只是一个仁矣”[4](P92)。万物生灵之所以能共存繁衍,全赖于天地的生长载覆。而这绝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作为整体的宇宙对生命的珍爱、怜惜、尊重与护佑,所以方学渐断言:“此道生生,毫无杀机,故曰善。”[5](P95)这份浑然之“仁”折射出至善之光辉。这仍是儒家一贯的赋予“生”以伦理内涵的思维方式,但泰州学派进而有针对性地强调:“今虽匹夫之贱,不得行道济时,但各随地位为之,亦自随分而成功业。苟得移风易俗,化及一邑一乡,虽成功不多,却原是圣贤经世家法,原是天地生物之心。”[3](P186)即使普通百姓,若能自我完善,成己成物而移风易俗,便是对至善“生德”的顺应效仿。至此,泰州学派将天地大德与匹夫常行合一,将至善之仁的超越性和日常行动的实践性合一,显示其独有的平民特色和平等倾向。
其次是规律性的“生理”。韩贞有诗:“一段生生理,天然妙莫穷。许多人不识,错用一生功。”[7](P169)宇宙是复杂的生命整体,混沌却不混乱,因为有天然玄奥的“生理”妙运其中。“生理”是可以认识和把握的规律,并具有普适性:“盖天道人心,总原是一个生理。”[4](P184)细绎之,天之生理“是一元之理,百物之所生也”[5](P98)。这规律以生命整体系统的动态和谐为根本,支配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而人之生理当顺应它并更加具体:“人之生理,自心与身。礼法养心,衣食养身。养身养心,身心兼□。生理经营,信行天理。”[7](P41)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体认和遵循天之“生理”,涵养精神心性并合理满足需要欲求,这便是对宇宙人生本质规律深刻而全面的把握。
泰州学派对于“生”的阐述,体现出儒家一以贯之的伦理色彩,而又能从物质性的角度去探寻生命本质,从整体性的角度去描述生命现象,从实践性的角度去把握生命规律。从而以其富有生活气息和平民色彩的独特言说方式赋予“生”以崭新的意义,丰富了儒家的范畴系统。
1.“生”是美的特征
泰州学派视“百姓日用”为美的本体,并以此为基点建构起美学思想体系1,而“生”则作为标志性的显著特点规定着美的特征。
“百姓日用”语出《周易·系辞下传》,指人类的生存生活实践,包括目视耳听、喜怒哀乐、言动行止、饮食男女、事亲抚子、生计营谋、交际应酬等,很大程度上涵盖了生理本能、身体官能等层面。泰州学派注意到并肯定了这些一直被忽视甚至贬斥的部分中隐藏的超越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松动甚至消解了美与生活之间不可逾越的藩篱。
然而应当看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和现象并非全都是美好的,有些甚至还不乏粗杂丑恶,因此,泰州学派也并未不加区别地一概而论,而是作了明确的分判:
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浑融透彻,只是一团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见云为,莫停一息,本与乾元合体。众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谓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觉圣贤的明训格言,呼而觉之,则耳目聪明,顷增显亮,心思智慧,豁然开发,真是黄中通理,而寒谷春回。[4](P28)
作为宇宙这个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人浑融秉有至善“生德”,所以能在纷纭万状的日常点滴间并不刻意着力却往往应对自如,发而中节。这种毫不勉强便灵明如流的状态暗合“生理”,不曾觉察就已经混融透彻,一经觉悟更是光辉显亮,从而能与乾元大道合一,而达到终极的审美境界。究其根本,人们日用常行间的这份美好灵明与生俱来,其根源正是生命本原周流不息的乾元“生意”,更表现为现实中生生化化的一系列具体形象。因此,“生”可以描述和规定“百姓日用”永远生长变化而时刻和谐中节的显著特点和根本属性,人类日常生活实践千头万绪,能成其为美的,唯有符合“生”这一特征的部分。
2. “生”作为美的特征的理论根源
泰州学派以“生”作为美的特征,通过描述伏羲始创乾卦从而体悟生命奥妙的过程,泰州学派形象地表达出,在生命源头处,美与“生”就已并肩携手:
盖伏羲当年亦尽将造化着力窥觑,所谓:仰以观天,俯以察地,远求诸物,近取诸身。其初也,同吾侪之见,谓天自为天,地自为地,人自为人,物自为物,争奈他志力精专,以致天不爱道。忽然灵光爆破、粉碎虚空,天也无天,地也无地,人也无人,物也无物,浑作个圆团团、光烁烁的东西,描不成、写不就,不觉信手秃点一点,元也无名、也无字,后来却只得叫他做乾画、叫他做太极也,此便是性命的根源。[4](P80-81)
这段论述极具想象力和文学性。假想中的观察者——伏羲通过类似宇宙爆炸般的灵感迸发体验,突破了表象的外壳而窥觑到生命的真相,那就是天地人物共同的开端根源——“乾画、太极”。所谓“乾画、太极”也只是强名,可以说与《周易·乾》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之“乾元”同义。它难以简单描述,却从一开始就有着美的形态——“圆团团、光烁烁的东西”,既浑沦又晶莹,既圆融又明亮,更蕴藏造化纷繁浩荡的生命形式的无穷力量。在泰州学派心目中,这就是生命根源所呈现出的直观形态。可以说,生命自源头处就已具有并显现美的特性,美从一开始就与“生”不可分割。
而在这段论述中,有一个重要的飞跃尤具审美意义——当伏羲看透乾元资始的同时,他对宇宙万物的认知也由常人“天自为天,地自为地,人自为人,物自为物”的表象层面,上升到“天也无天,地也无地,人也无人,物也无物”的本真层面。这种天地人物皆无并不同于释家禅门所谓“本来无一物”的空花泡影,而恰恰是一种天地人物不分你我的契合融会——宇宙万有“浑作”了生命整体,共同透射出“乾元”的圆澈光明。这极富审美意蕴的状态正是宇宙的本相。在这个意义上,无天无地、无人无物实际上就是天中有地、人中有物,天地物我在“生”之中交融,在美之中合一。出于美而归于美,这便是“生”作为美的特征的理论根源。
3.“生”作为美的特征的具体表现
作为美的特征的“生”具有了抽象的理论根源,泰州学派进而论述其具体直观的表现。宇宙作为整体,蕴含着彼此各异又相互依存的无数个体,万物既在生命源头处共有“生意”,又各具其“生”。但并非所有事物之“生”都可以视为美的特征。
盖仁之一言,乃其生生之德,普天普地,无处无时,不是这个生机。山得之而为山,水得之而为水,禽兽得之而为禽兽,草木得之而为草木。天命流行,物与无妄,总曰“天命之谓性”也。然《礼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所以独贵者,则以其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也。[4](P178)
山水、草木、禽兽各得其“生”,又真实无妄地表现出各自之“生”,但它们懵然遵循生命本能,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8](P97),其“生”往往浮浅支离而不能“率此天命之性而成道”。能够完美而透彻地印证折射大道的,只有人之“生”。因为人不仅能以灵慧的心神领会生生大德,更能从实践层面与大道生理无间暗合,因此可自豪地宣称“宇宙在我,万化生身”[3](P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才独贵于天地之间,唯有人之“生”才能作为具体而微的缩影,凝聚和赅备宇宙万物之“生”。
因此,人们更要意识到:“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3](P50)这不是将天地父母进行简单的类比,而是传达出泰州学派这样的理念——世间生灵虽然自其父母处得到不同的外形,看似纷纭繁多差别巨大,但追根溯源都拥有同一个生命源头,彼此理应如相亲相爱的骨肉手足般不分你我。所以独贵于天地间的人更有责任和义务,“以最贵之灵、生生之德,而统三才、一万世,则盈天地间,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4](P339)。而从超脱功利的角度来对待万物生灵,以自身为灵魂核心,担当凝聚起宇宙这一多样统一的和谐生命整体。一旦如此,人之“生”将展现出真实完满而纯全的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也将就此摆脱得失利害的束缚,自然而然地荡尽粗疏丑恶的部分,化为“百姓日用”之美而彻底展现出“生”之特征。
细绎之,人之“生”作为美的特征,其意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1.“生性”
“生”的第一个层面是“生性”,即人类与众不同的生命特质。首先,泰州学派认为要理解它,“须是先识‘性’字,性是心之生理,于中自具五常之德,自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3](P179)。所谓的“生性”首先是“理”,是包含在人生命中的天理大道、生生之德。其次,这种“理”在“心”,即人的思想、思维中自然而然地运行和体现,它圆融完满、和谐中节,刚柔相济、从容自由。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理”中“自具五常之德”,人的“生性”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仁、义、礼、智、信的美好品质。因此,作为生命特质的“生性”之伦理天赋决定了人生而卓荦于万类苍生之间。
这样的论述并非泰州学派的独创,孔孟先哲早已自信而乐观地宣称美德根芽就蕴藏在人类天性之中。但也应当看到,长久以来道德规范早已被道学家们异化为外在于人的教条,甚至是压抑束缚人的天性的枷锁。而泰州学派却还原了伦理美德的本来面目:“刘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书》不云乎‘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夫衷,中也,降衷为性,故性即是中。仁义礼智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时出,正所以中也。”[3](P180)
作为生性的“中”,是“喜怒哀乐之未发”时,“无所偏倚”的状态[9](P19),是人类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根本的生存境界,上至圣人下至百姓,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美德便由此而从生命深处自然而然地涌出,不假外力也不容做作。于是,所谓纲常被直接纳入人真实无妄的“生性”,成为人得自天道、发于内心的本质能力。人既有这种本能,就无须外力规范束缚便言行和谐中节。于是,“生”的第一个层面“生性”,是本能性和道德性的融合,使“百姓日用”显现出真实的美善合一的特征。
2.“好生”
“生”的第二个层面是“好生”,即人类对待生命的态度。首先,“至于四时之行、水土之化,无一物不有所自生,则无一物而不好生”[4](P134)。“好生”与生命本身是紧紧扭结在一起的,万物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不须学习,也不可遏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生者也必定有情有爱,因为生命本身就是生灵无法抛撇舍弃的爱之根源。
因为“盖天地以仁爱而生物,则所生之物,莫不得是心为心”[3](P194)。对生命的珍爱正是万类得自宇宙天地的本能天性,更是苍生生存立足的基点和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然而如果说禽兽草木爱惜性命还只是停留在本能层面的“贪生”的话,那么人类的“好生”便是出于此而又高于此的升华结晶——人类固然与禽兽草木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却绝不仅限于此,人们首先更懂得追溯生命之源的感恩。
颜钧说:“天地生民,人各有身。身从何来,父母精神。”[7](P39)撇开物我皆然的天性,人的诞生成长都得自于并依赖于生身父母。人既然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更应该感恩赐予自己生命的父母,这种最朴素真挚的感情便是“孝”,它绝非“在礼度上逐节求中”的“外面妆饰”[3](P193),这份感恩之情进而推展为对延续生命的子女的无私慈爱。从本质上说,“孝”与“慈”都是人类对于“生”的执着,是随着血缘不断转化传递的“好生”之情,赅备人类全部情感。正所谓“盖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而己身,己身而子,子而又孙,以至曾元,故父母兄弟子孙是替天命生生不已显现个肤皮,天命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长慈子孙通透个骨髓,直竖起来便成上下今古,横亘将去便作家国天下”[10]。这发自内心的感恩、绝假纯真的慈孝遍布于天地之内,成为连接构成人类世界的纽带:“其四海九州,谁无子女?谁无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谁不浓浓蔼蔼浑是一个也哉!”[4](P205)在骨肉血缘间传递的“好生”之情是最基本却最坚固的凝结力,它更拥有强大而温柔的浸润作用,能溢出血缘的界限遍及整个人间。
进而,如王襞所言:“盖人生皆本天地一元之气造化者,故同根之念,自出于天理之至情。”[3](P235)既然“好生”之情人人都能深切体会,那推己及人,四海一家、万众一心的大同世界终会成为现实。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仁慈体谅心肠、宽广包容胸襟,如果能推广到人类社会以外的更广阔的世界,对于非人类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人同样能以“同根之念”去体察它们对宝贵生命的珍惜,那整个宇宙将在这份“好生”之情中重拾其和谐的整体性。唯有人类有能力将各爱其生的“贪生”升华为民胞物与的“好生”,从而令天地间万类苍生一同欣欣向荣、生长畅茂,化为和谐畅达的美的画卷。在泰州学派的美学中,“生”的第二个层面“好生”是本能性和情感性的融合,“生”之中饱含着感染人、打动人的情感特性,春风化雨般地蕴含弥散在“百姓日用”之中。
3.“生机”
“生”的第三个层面是“生机”,即人类生命的存在状态。生命周流不息、永恒运动,一旦僵化凝滞就代表生命终结。万物苍生均如此。而对于人而言,“大抵心之精神,无时不动,故其生机不息,妙应无方”[3](P149)。人类生命的灵妙不仅表现在鲜活自如的躯体本能上,更显现在灵动不止的“心之精神”上,它主宰着人们从容中节地周旋于“百姓日用”之间,将生存实践转化为美的创造。这便是所谓的“生机”,正如王艮所言:“寸机能发千钧弩,一柁堪驱万斛航。”[3](P58)微而隐的“生机”表现在个体上,是身心的灵明活泼;表现在群体上,是族类的进化完善。
人类个体在“生机”的主宰妙应之下既能自然而然地符合大道的本质规律,又不知不觉地呼应着生命的根本目的,人的生存过程便呈现为一系列活泼灵动、新颖鲜活的具体形象。它无须任何外力的驱动,不容任何刻意安排,完满美好、玲珑微妙并源源不绝。就像王艮一再引用先贤的言论强调的那样:“无思”、“无为”,“无意、必,无固、我”,“无‘将迎’”,“无‘内外’”[3](P38),“不忘、不助”[3](P36),等等。任何外力都会成为牵制和束缚“生机”的绳索,只有任由它纵横驰骋的时候,人的日常生活才具有浑然天成地顺应天道的审美意义,达到所谓“随感而应,而应之即神”[3](P52)的自由境界。
人类群体由“生机”主宰下身心灵明的个体构成,这就是“生生不息之国本”[3](P52),通过每个人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践,人类社会能得以处于永不止息的变化发展之中,从而拥有了不断完善、无限趋近审美之境的可能。而当群体中所有人都能体认并依循“天机”,便能展现出“生生而自不容于或已”,“化化而自不容于或遗”[4](P79)的宏大力量,而在日用常行间将支离零散各自为政的万物,重新凝聚成生意贯融的整体。在这里,泰州学派勾勒出一幅处于永恒变化发展中的宇宙图景,无数生动的个体组成素朴圆融、生意周流的和谐世界,品类繁盛、朝气蓬勃的美的表象背后,自有“生机”默然运行其中。在这个意义上,“生”的第三个层面“生机”,是本能性和自由性的融合。在它的左右下,“百姓日用”之美浑然天成地展现着人类本质的创造力量。
泰州学派美学大胆地将美的特征范畴“生”安置在血肉之躯承载的物质和本能基础上,进而从生意氤氲的生命根源入手,寻觅其伦理性、规律性特质,描绘出宇宙这一生命整体间万类苍生“生生”不息、“生化”不已的景象。“生”在源头处便已与美同行,而人之“生”是其具体而微的缩影,“生性”、“好生”和“生机”三个层面蕴藏着“生”的道德性、情感性和自由性的超越力量。符合“生”之特征的人类全部的日常生存、生活实践,便是“百姓日用”之美。
直到今天,人们在承认可以把审美的态度引入日常生活的同时,依然有理由忧虑:“日常生活审美化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把美学带入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将美学贬为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技术的阐释。”[11](P16)身体本能、生存生活、情感欲望等感性层面要素成其为美的合法性仍存在争议。而泰州学派却以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浑沦圆彻的思维方式,诉说了另一种可能:“生”与美并肩同行,美与人类的生命活动、生存实践也许原本不存在区隔,美的光芒也许并不仅仅闪耀在彼岸,在“百姓日用”的洪流中,也许早已存在着自由的审美境界,蕴藏着美终极的救赎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姚文放. 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张舜清. 儒家“生”之伦理:一种思想资源的意义[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0,(4).
[3] 王艮. 王心斋全集,陈祝生主编[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 罗汝芳. 罗汝芳集,方祖猷等编校[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明儒学案·下,沈善洪主编[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6] 罗汝芳. 盱坛直诠[M]. 台北:广文书局,1967.
[7] 颜钧. 颜钧集,黄宣民点校[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朱熹. 四书集注[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10] 陶望龄. 罗近溪先生语要[M].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
[11] 周宪. 美学的危机或复兴?[J]. 文艺研究,2011,(11).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