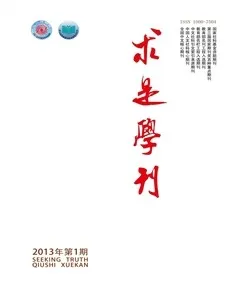柏拉图为什么需要另一个世界?
2013-12-29徐凤林
摘 要:舍斯托夫从存在哲学的视角,关注柏拉图关于超验世界、洞穴比喻、精神视力、死亡练习等主题。超验世界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与现实世界的必然性做斗争;洞穴比喻对“清楚明白”的理性主义真理标准提出质疑;精神视力要超越肉体,在生命的边界寻求真理,使哲学思考成为“死亡练习”。
关键词:超验世界;精神视力;洞穴比喻
作者简介:徐凤林,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哲学、东正教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05-07
我们常说,哲学来源于生活,或者援引马基雅维利的名言——先生活,然后进行哲学思考。这句通俗易懂的话常常被用来作为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佐证,即物质生活是精神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换一个角度看,这句话也完全可以进行唯心主义的解释,关键在于怎样理解“生活”。生活不仅仅是饮食起居等外部条件和活动,生活是人的完整生命,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的精神直觉和情感体验。许多重要的哲学观念就是从这一完整生命内部诞生和被揭示出来的,哲学家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以自己的天赋成功地找到了用来表达这些直觉和体验的语言和概念。人们常常以为哲学家是在用概念推理体系证明自己的世界观,其实,哲学家是在力图以理性和知识的形式表达自己在生活中已经获得的超理性的直觉和感悟。这一点在俄国哲学家舍斯托夫对柏拉图的评论中得到了鲜明表现。舍斯托夫对柏拉图的论述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他在柏拉图二元论、洞穴比喻、精神视力、死亡练习等概念和形象中看到了一个共同宗旨,就是通过揭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来同此世的必然性进行斗争。
一、超验世界
在哲学史家的笔下,柏拉图哲学的最主要贡献是他提出了理念论。理念论在认识论意义上将世界二重化,划分为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但在舍斯托夫的解释中,柏拉图哲学还在价值论意义上把世界二重化,即不仅有经验现实世界,还有超越于现实存在的世界,即价值世界,或者说应有的世界。
舍斯托夫认为,柏拉图的二元论世界观或超验世界的思想,不是他在闲暇时或书斋里的随意想象,而是为了解决一个切身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不公正地判决毒死,身为学生的柏拉图因自己老师的死而悲痛和愤慨。这是切身之痛,他不能无动于衷,无法不说,无法不写。“他在《克力同篇》、《斐多篇》和其他一些对话中都写了这件事……一直包含着的只有一个问题:世界上真的有这样一种强力,它能够彻底和永远迫使我们同意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毒死了吗?”[1](P20)换句话说,事实真理是不是全部真理?事实真理是否能够彻底地和永远地决定人的观念和价值?有没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好人苏格拉底不会被判刑和毒死;有没有这样一种力量,它能够战胜冷漠无情的事实真理——必然性,能够给善的最终胜利提供保障?回答这一问题成为柏拉图哲学关于两个世界的二元论学说的基础和根源。
超验世界“是这样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柏拉图及其后继者只是为了这种东西才走向哲学”。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是必需的:与可见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也就是粗暴力量注定胜利、安尼图斯和美立都(审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法官)取得胜利的世界一道,还可以找到另一个世界,超自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最智慧的人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才有理由把苏格拉底对法官说的那番话当作真理来颂扬,苏格拉底说:“法官们,你们要相信死的幸福,要深刻体会这样一个终极真理,即好人不可能发生任何坏事,无论在他生时还是死后,神明永远不会忘记他。”(《申辩篇》41D)这是柏拉图学说的基础和根源:好人不可能发生任何坏事……只有在除了所有人能够达到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并且这才是最主要的和唯一现实的世界的情况下,苏格拉底才能不昧心地向法官说出他所说的话。[2](P231)
舍斯托夫把柏拉图描述为基督教思想家。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成为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在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世界里,苏格拉底的话所表达的理想和信念是谎言和空谈。亚里士多德不关心苏格拉底的命运,他关心另外的东西,那就是普遍的和必然的真理。他相信,“毒死苏格拉底”的真理和“毒死一条狗”的真理同样不容任何人的和神的反对。毒芹不区分苏格拉底和狗,所以,“被迫只能跟随现象的和被真理本身所迫的”我们,就应当在自己的间接或直接判断中,不在苏格拉底和狗之间甚至苏格拉底和疯狗之间做任何区分。
然而柏拉图则具有另外的哲学诉求。他虽然在知识领域与亚里士多德同样清楚地知道,事实真理和必然性是不可战胜的。他曾经说过,甚至诸神也在必然性的权力之下:“诸神不和必然性做斗争。”(《普罗泰戈拉篇》345e)但是,知识领域不是柏拉图的全部世界。哲学家还有情感和意志。这是柏拉图思想的潜在动力。
柏拉图毕生都在同必然性做斗争。由此产生了总是使他备受指责的二元论,产生了那些令他的友人痛心、敌人高兴的矛盾,由此也产生了令亚里士多德愤怒的悖论。柏拉图不满足于那个使他的伟大弟子的求知欲得到满足的真理源泉。他知道,宇宙之父和创造者是很难发现的,即便我们发现了它,也不可能把它告诉所有的人。1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地试图克服困难,战胜这一不可能性。有时令人觉得,仿佛正是这些困难性吸引了柏拉图,只有在这种不可能性面前,他的哲学天赋才觉醒,以便进行真正的活动。“要敢做一切”,越是对在普通人眼里可能性很小的东西,越要敢于有所成就。要使苏格拉底摆脱那个永远吞噬了他的永恒真理,那个对他和对疯狗都一样的永恒真理,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也许,哲学和哲学家不应当想任何别的东西,只应当想怎样夺回苏格拉底。既然别无他法,就应当去求神……因为受事件的自然进程所支配的聋的“必然性”听不见他的诉求。但是,与“必然性”相反,神能够并且愿意听劝说,在神的法庭上,不可能的和不合理的东西成了可实现的和合理的东西。神完全不像必然性那样思考和讲话。神说: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东西都可能被分解,但只有恶人才愿意把完美结合的和维持很好的东西分解开。所以,一般地说,你们是生成的,所以不能保住不分解和不死,但你们不会遭到分解和死亡的命运,因为你们已经照我的意志(τηζ εμηζ βουλησεωζ)获得了比你们与生俱来的坚固性更强的坚固性。1
柏拉图为从死亡那里夺回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而勇敢地同必然性做斗争,他为此诉诸宇宙创造者,类似于基督教的上帝。当然,柏拉图所说的宇宙创造者和基督教的上帝有很大不同。但柏拉图的话也可以进行基督教哲学的理解。基督教哲学世界观是二元一元论。上帝创造的世界本来是至善的,只因人的意志自由的误用才使恶和必然性进入世界。只有上帝的全能和力量能够战胜必然性的统治,能够为善的胜利提供最后保障。信仰者因此而获得了坚强的精神和生命的希望。不仅如此,在舍斯托夫的基督教信仰观中,上帝的全能是真正的全能,甚至能够超越事实真理,可以使“已经发生的事件成为没有发生的”,使苏格拉底的死成为不存在。这是一个用人的理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世界和神圣秩序,如果从这个神圣秩序反观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众人就仿佛被捆缚在柏拉图所描述的洞穴中。
二、洞穴比喻
人类自有思考能力的时候起,就在努力区分真实与虚假。然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这是一个莫衷一是的哲学问题和宗教问题。柏拉图和黑格尔的观念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假?基督教的天国是真实还是虚幻?世间万象是真实存在还是万物皆空?对这些问题不同世界观有不同的回答。
舍斯托夫的真伪观可归属于宗教存在哲学之列。存在哲学反对把人定义为“理性存在物”,而主张人的本性在于“非理性”,人的内在主体感受,人的激情、意愿成为人的生命的最真实内容,而理性观念和道德规范成为非真实的。舍斯托夫尖锐批评理性主义哲学的抽象真理和说教,力图追问和揭示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真实和存在真理。这样的真实和真理在哪里?不在笛卡儿的“清楚和明白”中,不在康德的“普遍必然判断”中,不在生活的中间状态,而在生命的“开端与终结”,真理是与“生从何处来死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用舍斯托夫的话来说:“开端和终结,就是不要中间。不需要中间不是因为中间本身没有任何用场。中间是骗人的,因为它有自己的开端和自己的终结,它与一切都相似……我们将走向开端,走向终结——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既达不到开端也达不到终结。我们将确信,真理终将成为比最美丽的谎言更为人需要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或者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终极真理。”[3](P6)
但人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清楚明白和普遍必然判断的中间世界。只有少数哲学家和思想家不以中间状态的世界为满足和唯一的真实世界,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因渴望另一个世界而焦虑不安。舍斯托夫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看出了这一点。
的确,只有柏拉图这样的深刻思想洞见,才有可能说出这样的比喻。在一个洞穴中有一群囚犯,他们手脚都被捆绑着,身体也无法转动,只能背对着洞口。在他们面前有一面白色的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火光把他们自己的影子和他们与火堆之间的事物的影子投映在那面白墙上,他们只能看见墙上的这些影子,而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因此,这群囚犯以为他们看见的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大家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在囚犯们看来,这个逃出去的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他们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2
在这个比喻中,有两个主体和两类对象。两个主体一类是众囚犯,一类是逃出者;两类对象一类是人和事物的影子,一类是真实事物。两类主体本来在什么是真实世界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如果大家始终是囚犯,没有人逃脱,也就不会发生分歧,幻影的真实性就不会引起怀疑。于是,所有人都在这个影子世界里相安无事,在无真无幻或亦真亦幻的洞穴世界终其一生。但有幸或不幸的是有人逃出洞穴,知晓了真相,于是产生了疑问和争论。这个比喻的最深刻寓意在最后:当知晓真相者向囚犯们揭露影子的虚幻并指出真实之路的时候,囚犯们居然不相信,反而嘲笑他愚蠢。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可以问,我们自己是谁?是那个知晓真相的逃出者,还是以幻为真的众囚犯?如今,人类早已经过了理性和知识的启蒙,进入了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毫不怀疑我们自己的身份是那个逃出者,清楚地知道真实世界。我们似乎完全有权判定众囚犯和逃出者关于真实与虚幻的观点哪个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是理性,是科学。但舍斯托夫的问题是,理性和科学能够成为生命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舍斯托夫的看法是:笛卡儿的“清楚明白”和启蒙主义的理性标准并没有消除生命的神秘,生活于科学知识世界中的我们不是那个逃出者,而是众囚犯!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真理,我们都永远不能否认笛卡儿的“clare et distincte”(清楚和明白)。然而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永恒的神秘,永恒的不可透性,仿佛在创世之前,就有人决定永远关闭人通往他最需要和对他最重要之物的道路。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我们的思维所达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与我们生来就被投入其中的外部世界是不可比量的,而且与我们自己的内在感受也是不可比量的。我们拥有科学,甚至可以说,这是不仅每天,而且每小时都在发展的科学。我们知道许多,我们的知识是清楚明白的知识。科学有权为自己的巨大成就而骄傲。完全有理由认为,科学的无往不胜的步伐是任何人也无力阻挡的。任何人都不怀疑也不可能怀疑科学的巨大意义,但原初的神秘之“雾”并未消散,甚至更浓了。柏拉图未必需要更改他的洞穴比喻的哪怕一字一句。他的焦虑,他的不安,他的“预感”,即使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中,也找不到答案。我们的在“实证”科学之“光”中的世界,对他来说仍然和当初一样,是昏暗可怕的洞穴,而我们仍然是被捆住手脚的囚犯,他必须重新作出超人的努力,就像搏斗一样,才能冲破这样的科学所创造的真理,这种科学“梦想着真实存在,却不能清楚地看到它”(《理想国》第七卷,533c)。简言之,假如来到今天,亚里士多德会赞扬知识,而柏拉图则会诅咒知识。[1](P2)
柏拉图不以日常经验和科学知识为满足,甚至怀疑其真实性,为此而焦虑不安;舍斯托夫借用柏拉图的比喻断言科学不能清楚地看到真实存在,否定笛卡儿的真理标准。笛卡儿认为,凡是在理性看来清楚明白的就是真的。清楚明白成为一切直觉和演绎知识的标准和特征,也成为真知识(真理)的标准和特征。舍斯托夫则认为,理性的清楚明白不仅不是生命真理的标准,反而是人达到真理的障碍。“洞穴里的人清楚明白地看见了在他们面前通过的一切,但他们愈是坚信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们的处境愈是无望。他们需要的不是寻求看得清楚明白和信得坚定,相反,他们需要体验巨大的怀疑,巨大的不安,需要极度的内心努力,以便挣脱把他们捆在那里的锁链。这种‘清楚明白’诱惑着所有人,被所有人认为是真理的保障,但在柏拉图看来,则是永远掩盖真理从而使我们看不见真理的东西。‘清楚明白’不是把我们引向现实存在,而是引向虚幻之境,不是引向存在之物,而是引向存在之物的影子。”[1](P32)对于生命真理而言,理性认识的清楚明白不是标准,而是诱惑,是锁链。
舍斯托夫为什么反对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否定了这个通行的标准之后,舍斯托夫自己的真理标准是什么?不可能只是神秘莫测、模糊不定吧?按照我们的理解,舍斯托夫这里要强调的是存在哲学的真理与科学真理的不同。科学真理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存在哲学的真理则具有个体性、内在性和精神性。生命的终极真理是信仰中的多元真理。真实-真理是个体的自由体验,从内向外的真理体验。舍斯托夫坚决反对把外部的普遍必然判断作为全部真理的唯一标准强制所有人接受,特别是作为哲学真理的标准。但这种生命的终极真理是很难加以证明的。舍斯托夫也看到了柏拉图曾遇到的这个难题:“如果你要问,柏拉图是从哪里得知这个的,他是怎样猜出,洞穴人(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所看到的不是现实,而只是现实的影子,而在洞穴界限之外的某个地方有真正的生活,——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那么你得不到回答。柏拉图不能证明这一点,虽然他为寻找证据已精疲力竭。他为此想出了辩证法,而且在自己的全部对话中都竭力通过辩证法之路,迫使自己想象中的对话者承认自己的启示的真理性。然而在这里,正是在这里,由于柏拉图想把他所得到的启示变成强迫性的、人人必须遵守的真理,所以才把自己暴露在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之下。”[1](P32)
或许也是为了寻找洞穴墙壁的影像与洞穴之外的真实生活的有力证据,柏拉图想出了“精神视力”的概念。
三、精神视力与死亡练习
柏拉图看见了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毒死这个事实。正因为他不得不“亲眼”看见这个事实,所以在他心里才第一次产生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无法消除的、令人不解的怀疑:“自己的眼睛”就是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的源泉吗?进而,自己的眼睛是唯一的视力吗?柏拉图提出,人不仅有肉体视力,还有“精神视力”(η τηζ δταυοιαζ οψιζ)。这样,真实-真理的标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人有两双眼睛,有双重视力,那么,谁来决定哪种视力看见的是真实-真理,哪种视力看见的是虚假-谬误呢?无论真实-真理向肉体视力显现,还是向精神视力显现,两者都是“允许的”。哪个更有优势呢?这要看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肉体视力是属肉体的,而肉体受感官快乐或痛苦感觉的驱使和强迫,因此,肉体视力也受制于必然性和强迫。柏拉图说:“人的灵魂在由于某种东西而感到极度快乐或极度痛苦的时候,就被迫认为使他产生这种感受的东西是最明显的和完全真实的,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每一种快乐和痛苦都仿佛有自己的钉子,把灵魂钉到肉体上,把灵魂固定住,使它与肉体相似,所以灵魂就开始认为,肉体以为是真的东西就是真的。”(《斐多篇》83E)
看来,灵魂-精神的视力是被迫依附于肉体视力的。如果精神只是被迫服从于肉体的真理标准,那么,这个真理标准就是有问题的。精神视力应当脱离肉体的束缚,有自己的自主洞见。“当肉体的眼睛不灵的时候,精神的眼睛将更加敏锐”(《会饮篇》219A);“灵魂最能思考的时候,是在它摆脱了一切干扰,不听,不看,不受痛苦或快乐影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不顾肉体,尽可能保持独立,尽量避免一切肉体的接触和往来,撰写钻研实在的时候”(《斐多篇》65C)。因此,舍斯托夫认为,“‘精神的视力’在柏拉图那里不是别的,正是企图摆脱的‘必然性’之统治的一个勇敢尝试,此必然性在当时而且直至今日仍然是人类思维的支柱。……‘精神的视力’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视力了,就是说,不再是对现成的或设定的真理的消极观照和接受了”[1](P25)。精神视力具有了超越肉体的全新意义。
那么,怎样超越肉体视力,达到精神视力呢?柏拉图到生与死的边界那里去寻找解答。舍斯托夫重新解释了柏拉图关于“哲学是死亡练习”的思想。对柏拉图来说,肉体视力是与“强迫”和“成为被迫者”的思想紧密相连的。苏格拉底被毒死只在靠肉眼获得真理的世界上才是永恒真理,所以在他看来仅仅减弱肉体视力和一般肉体存在已经不够了。只要我们以肉体方式生存,我们就在必然性的权柄之下,我们可能受折磨,被迫承认某种东西。既然在这个世界上,那个在我们看来是世间最高尚最美好、我们最想要的东西(真理)强迫人、折磨人,把人变成被赋予意识的石头,那么,我们还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吗?我们应当逃离,尽量快速地逃离这个世界,头也不回地逃离,不问向哪里逃,不管前面将有什么等着你。你要烧掉、撕下、根除你身上的一切沉重的、使你石化和屈从的、把你拉向可见世界的东西。不仅肉体视力,而且整个肉体性都应当从人身上去掉。但怎样做到这些?谁能做到这些呢?柏拉图回答说:这是哲学的事业。但这里所说的哲学已不是科学,甚至不是知识,而是“死亡练习”(μελετε θαυτου)。柏拉图说,一切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在为死和死亡过程做准备(αποθυησκειυ και τεθυαυαι)。当然,柏拉图马上补充说,哲学家通常对所有人都掩盖这一点。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尽管柏拉图在《斐多篇》的对话中大声宣布了这一思想,但亚里士多德没有理解柏拉图的“死亡练习”,其中的秘密也没有人揭开。
舍斯托夫把哲学作为“死亡练习”的含义理解为对抗强迫性、必然性的有力手段:“肉体”和所有同肉体相关的东西,都服从必然性,都惧怕它的威胁。当人可能害怕的时候,就可以恐吓他,把他恐吓住以后,就可以强迫他服从。但“哲学家”到过生命的边缘,经历过死亡学校,他把“死亡过程”(αποθυησκειυ)看作现实,把 “死”(τεθυαυαι)同样当作未来的现实——对于这样的哲学家来说,上述那些可怕的痛苦已经不再可怕了。柏拉图接受了死并和死结交。因为死亡使肉体视力减弱,它能在根本上摧毁什么也听不见的“必然性”和使“必然性”赖以维持的全部自明真理。灵魂开始感到,它可以不再服从和听命,而是能够指挥和命令。人在物质世界的生活不仅要面对外部的自然强迫,而且要经历自身的疾病、衰老和死亡。所有磨难中最大的不幸是死亡。只有在经历过死的考验、受到过死亡训练的人,才能获得超凡的生命勇气。
但是,舍斯托夫承认,柏拉图即便在生死边界处,在“死亡练习”中,也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也就是真正有能力对抗必然性的东西。按照舍斯托夫的理解,只有基督教的上帝具有这样的力量,只有上帝的“受造真理”能够对抗非受造的“永恒真理”。或许可以更确切地说:柏拉图没能成功地把他在可能的知识之外所找到的东西带给人们。当他试图把他所发现的东西展现给人们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他眼里奇怪地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也就是理念、普遍观念。而全能的活的上帝是不可说的。柏拉图自己也清楚,“世界的创造者是很难看见的,展示它是不可能的”。不可说之物之所以不可说,是因为它在其本性上是和体现相对立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说的创造者又不得已只能体现为概念和知识,而知识意味着被迫,被迫就是从属,是丧失,是被剥夺,其中归根到底隐藏着一种可怕的危险,“人的自我满足”——对必然性的平静接受和快乐服从。服从必然性的人可以得到理性的自我安慰。但是按照存在哲学家的观点,这时人已不再是人,而成为“被赋予意识的石头”。“被真理本身所迫的巴门尼德”,反思真理的巴门尼德,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巴门尼德,不再是富有生命力的、反叛的、不安的、不妥协的巴门尼德,因而不再是伟大的巴门尼德。[1](P39)因为生命的根本属性和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人的精神自由。
四、理念与个体
如前所述,舍斯托夫对柏拉图的关注有其独特视角。但在通行的哲学史上,柏拉图哲学的最重要思想不是理想世界、洞穴比喻、精神视力和死亡练习,而是理念论。什么是柏拉图的理念?有哲学史家解释说,理念是通过对事物的抽象而形成的普遍共相,亦即事物的类概念或本质;理念是个别事物存在的根据;理念是事物摹仿的模型。舍斯托夫的解释与这些观点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舍斯托夫认为,只把恒常不变的东西看作是真正现实,而把变动不居的、充满随意性的人类生活看作虚幻,这是人类思维的一个根本缺陷。柏拉图世界观的根源就是人类思维的这一根本缺陷。[4](P34)人类自古就体验到世间万物变幻无常,个人命运毫无定数,从而努力用思维来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和不变本质。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就把万物皆归于水。柏拉图也力图在永远变化的可见之物之下找到恒常不变的本质,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企图,也就是发现了理念。可见的、永远与自身不相等的、多姿多彩的现实不是真的实在。实在之物应当是恒常不变的。因此,事物的理念是实在的,而事物自身是虚幻的。从柏拉图时代起,正是那些教导人们不变之物优越于变化之物的哲学家取得了最大成就。但按照舍斯托夫的存在哲学的观点,世界的最大现实是人的生命,而人生的最大现实正是变动不居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这是首要的。而一般固定不变的概念和理念则是不现实的,次要的。
第二,理念不是抽象的类概念,而是现实的精华。舍斯托夫也看到了柏拉图理念论有早期和晚期的区别。在柏拉图年轻的灵感时刻,理念论向他展现出来的本质正在于,理念是现实的精华,是“超乎寻常的”现实存在,而它的外部形象则只能提供模糊的表象。只是到后来,当他被从外部强加了这样一个任务,即要使理念成为所有人的永恒财富的时候,也就是在向任何一个有对抗心理的、爱争辩的人证明那本质上无法证明的东西的时候,简单地说,就是不得不把哲学变成“科学”的时候,柏拉图才越来越多地牺牲了现实性,而把对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的一般原则放到首位。[5](P179)这时,理念才成为非现实的一般原则,成为事物的类概念。数的理念论是最后阶段,因为无法想出比算数更加显而易见的东西了。因此,如果起初柏拉图有理由说现实事物只是理念的影子,理念是更加具有现实性的,那么,最后他得出了相反的看法,理念在他那里成为现实事物的影子。
第三,理念不是抽象本质,个人的理念就是个人本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时指出,柏拉图及其追随者是通过给一些具体的词加上“自身”这一方法来得出其理念的,这样就有了“人自身”和“马自身”等。舍斯托夫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察非常细致,也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观察没有达到亚里士多德给自己提出的目的,也就是让柏拉图的理念声誉扫地,而是能让人更轻易地深入到理念的最有价值的隐秘本质。这个最有价值的隐秘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柏拉图对个体性的爱。理念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一个外壳,最重要的东西是掩盖在这个外壳下面的现实个体。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也有类似思想,他不仅谈论人的理念,而且谈论苏格拉底的理念。既然有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的灵魂,就应当有苏格拉底自身。普罗提诺不想把苏格拉底湮没在人的一般概念中。他突然感到,物自身正是苏格拉底,此时此刻的苏格拉底,教导柏拉图和被雅典人毒死的苏格拉底。哲学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活的苏格拉底。(普罗提诺《九章集》5,7,1)“对个体性的爱在柏拉图那里比在普罗提诺那里表现得更加鲜明。对柏拉图来说,一般理念只是一个外壳、一副铠甲,他用这一外壳把他生命中最珍爱的东西对外人、对大众掩盖起来。最好的东西是幸运者在特定时刻应当和善于用自己的特殊眼睛看见的,而且,无论什么理论被建立起来,他们都能看见这种最好的东西。而对大众,应当给他们看的是那种‘一般之物’,这种东西总是可以用‘一般的’眼睛看见的,是可以向所有人展示的,也就是理念。”(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译文略有不同)柏拉图最珍爱的东西是个体性,是具体的、鲜活的个人。普遍理念只是体现这些鲜活个体的外部形式。
参 考 文 献
[1] 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 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M].北京:三联书店,1989.
[3] 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4] 舍斯托夫.无根据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5] 舍斯托夫.钥匙的统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