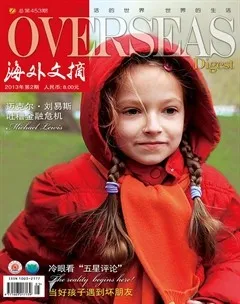表扬的学问
2013-12-29坡·布莱森


如何培养出托马斯那样的孩子?
托马斯是五年级学生,就读于竞争激烈的334公学,学校坐落在纽约西区84号。最近,托马斯将本来不多的沙褐色头发剪短了,看起来像新版007(他带了一张丹尼尔·克雷格的照片给理发师看)。托马斯常与同校的五名同学一起玩。他们都是别人眼中的“聪明孩子”,托马斯很满意这个小团体。
从蹒跚学步开始,夸托马斯聪明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当申请进入安德森幼儿园时,他的天分就在统计学上得到了肯定。这家幼儿园只在报名者中录取1%的拔尖人才,智商测试是必须的。托马斯不但进入了这1%的行列,并且在1%中名列前茅。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托马斯的聪明没有转化成相应的自信。他的爸爸注意到,托马斯从不尝试无法胜任的事情,有些事情他能很快理解,但如果不是这样,他几乎立刻放弃,认为“这不是我擅长做的”。托马斯只瞟一眼,便把世界上的事情一分为二——他天生擅长做的与不擅长做的。比如三年级时,老师教授英语草书体,但托马斯却发现自己写不好。当老师要求用草书体完成家庭作业时,托马斯干脆不写作业。他的爸爸努力给他讲道理:“听着,你聪明,并不意味着不用做出努力。”
在智力测试中明显占优势的孩子,为什么对学习中的挑战缺乏信心呢?
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天才学生(智能测验中排名处于前10%的孩子)中的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要求过低,他们低估了努力的重要性。85%的美国父母认为,告诉孩子“你很聪明”非常重要。不断的赞扬像肩膀上的天使,确保孩子不会妄自菲薄。然而,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给小孩子贴上“聪明”标签往往会导致他们表现不佳。
过去十年间,针对赞扬对孩子们的影响,心理学家卡洛·德韦克(目前就职于斯坦福大学)和她的团队对纽约12所公立学校里数百名五年级学生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在跟踪采访中德韦克发现,那些认为先天智商是成功关键因素的孩子,大多轻视努力的重要性。他们的推理过程是,我很聪明,不需要付出努力,付出努力会让他们觉得耻辱。然而,强烈的自尊心并不能提高分数或者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它甚至没能阻止人们酗酒,更没有降低任何形式的暴力(有强烈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的人大多对自己评价很高)。
总的来说,表扬的确可以发挥作用,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但表扬应该是具体的,不能是空洞的称赞。表扬必须基于某些事实——孩子通过努力掌握了一些技能,或展现出自己的天赋。一旦孩子听到表扬却觉得那毫无价值,他们不仅会鄙视不真诚的表扬,还会鄙视真诚的表扬。
此外,表扬的真诚态度也很关键。正如成年人能看穿明扬实贬的奉承或虚情假意的道歉,孩子们同样能捕捉到表扬的潜台词。只有七岁以下的幼儿会对表扬信以为真:稍大点的孩子与成人一样,会对表扬心存疑虑。此外,在12岁之前,孩子们不认为被表扬是件好事——事实上,这说明你缺乏能力,老师认为你需要更多鼓励。这也是很多青少年对表扬十分蔑视的原因,他们甚至认为那根本不是表扬,而是老师的批评。认知科学家丹尼尔·T·威林汉认为,老师表扬学生可能会在不经意间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了天赋的极限,而批评学生则表示他的表现还可以再改进。
对于经常被夸聪明的孩子们来说,维护形象成了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他们求胜心更盛,且更乐于战胜别人。在一项研究中,孩子们要做两次难题测试。两次测试之间,他们有一次选择机会:选择学习第二次测试的新解题法,或选择查看自己在第一次测试中的排名。时间只够完成其中一项。被夸聪明的学生选择了看他们的排名,而非用这个时间准备下次测试。
升入中学后,在更激烈的竞争中,一些小学时学习出众的学生不免感到力不从心。那些将自己早期的成绩归因于天赋的人,无疑将继续掩耳盗铃。在接受采访时,很多学生承认,会“认真考虑是否要在考试中作弊”,而不是要更加努力。学生开始有作弊倾向,是因为他们尚未找到应对失败的办法——只有更努力,才是对失败最有力的回击。
科学家曾训练小白鼠走迷宫,在它们到达出口前吝啬地坚决不给奖励,以此锻炼小白鼠的持久性。一个人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过于频繁的奖励,便不会有持久性,因为一旦奖励没有了,他们便会放弃。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我曾经以为“赞美狂人”只是一种说法,可事实并非如此——猛然间我发觉,我一直在让六岁儿子的大脑形成对频繁夸奖的依赖。
不再如此频繁地表扬我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如果拿我做例子的话,戒掉表扬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很微妙。第一阶段,在其他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赞不绝口的大潮中,我的旧瘾复发。我不希望儿子卢克感到被冷落。感觉就像一个戒了酒的人又继续在社交场合中端起酒杯。我成了一个社交性赞扬者。第二阶段,我试着用德韦克建议的具体表扬法。我表扬卢克,但我会尝试夸他的“处理方式”。不过,说来容易做来难。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头脑里,处理是什么意思呢?在每天的生活里,他的大脑80%都是在处理他的公仔。
但卢克每天晚上都有数学作业,并要大声朗读一本拼读书。如果他精力集中,每项任务要花5分钟左右,但他很容易走神。因此,我表扬他注意力集中,而没要求休息。要是他很认真听话,我也会表扬他。球赛之后,我表扬他过人传球不错,而不是只说“你踢得真棒!”要是他很努力地抢球,我会表扬他所做的努力。
正如研究结论所说,这种有针对性的赞扬让他明白明天该怎么做。这种新型赞扬的效果非常显著。
说实话,当我儿子在这种新的赞美方式下感觉良好的时候,痛苦的却是我。事实证明,我的确是一个“赞美狂人”。仅仅表扬他的一种特殊技能或者一项任务,总让我感觉不够。我常不由自主地用“你太棒了,我为你骄傲”来表达我对他无条件的爱。
赞扬已经成了治疗现代育儿焦虑症的一种灵丹妙药。除了安排好孩子们从早餐到晚饭的生活之外,我们到家时,还要有升级版活动。在共处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希望孩子们听听白天我们没能说的话——我们在你身边,我们支持你,我们信任你。用类似的方式,我们将孩子置于高压环境中,我们寻找能找到的最好学校,然后不断赞美,以缓和环境中的紧张气氛。我们对他们期望太多,却把自己的期望隐藏在频繁表扬的光环下。如此的表里不一让我很不自在。
终于,在戒除表扬的最后阶段,我意识到不告诉儿子他很聪明意味着:我把他对自己聪不聪明的判断权交给他自己。直接表扬就好像过早公布作业答案,剥夺了他自己得出结论的机会。
但是,要是他的结论是错误的,怎么办呢?我真的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他自己决定吗?在他这个年龄?
我依然是一位焦虑的母亲。今天早上送卢克上学的路上,我试探着问,在学校里碰到困难时,你的脑袋是什么感觉?“它像肌肉一样变大了。”像以前一样,他的回答直接命中靶心。
[译自美国《纽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