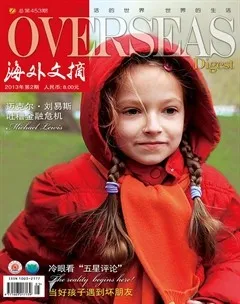冰雪王国的美丽与忧愁
2013-12-29尤里·列舍托


在俄罗斯东北部最遥远的地方坐落着一个迷人的冰雪王国——楚科奇自治区,它独特的极地风光常常令人心驰神往,但同时也因其严酷的居住环境和原始的生活方式而成了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俄罗斯《国家地理》记者带我们走进楚科奇人的生活,领略那里的美丽与忧愁!
砰!一秒前艾迪克还在愉快地享用着茶和面包,突然间这样低沉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有了!”这位棕色眼睛的猎人笑道,“是海豹?走,看看去。”
艾迪克随手将枪扔在雪橇上,一路小跑到冰块边缘。皮艇在水面摇晃,岸边20米内的水面泛着血色,壮丽的白令海就这样被海豹的鲜血撕成两半。眼前的一切不由得让人想起人类求生的简单法则——要么杀,要么被杀。我问他:“不觉得这些动物可怜吗?”他反倒惊讶道:“可怜?那我们吃什么?这是传统,这就是生活!”这位身穿传统毛皮大衣的海边猎手眼中满是难掩的兴奋。他常常笑,但只要谈到他们的生活时,这个48岁的男人就会变得很严肃:“楚科奇人爱吃海豹肉,我的五个孩子也是。”
艾迪克驾着小艇驶近他的战利品,把它吊在钩子上,拉到岸边再拖到雪橇上,沿路留下一条血痕。“今天是个好日子。再等等。不抓上三只我是不会死心的。”他用望远镜看向远处,冷冷的海面泛着点点涟漪,下一个猎物出现了。这里是太平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距莫斯科上万公里,捕猎海兽依然是居民们生活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用来谋生的手段,更是艾迪克心目中精神层面的活法——只有在海中捕猎,他才永远不会在这遥远的世界里迷失自我。
在来捕猎的前一天艾迪克交代我该穿什么、带什么,并允诺早上8点来接我。但早上4点我的手机就响了:“天气好了!该走了!马上!”我的抗议无效,因为“天气好!”就像一句咒语。天气好,生活才会好。天气好就可以捕猎海豹,可以放牧鹿群,飞机也可以起飞。否则就只能等待,有时一等就是好几个星期。艾迪克说:“耐心是猎人要具备的一个重要品质。”
十分钟后艾迪克驾车来到了我的住处。他生怕错过好天气,驾着他的雪地汽车在浮冰群上飞驰。巨大的冰块或蒙着蓬松的白雪,或透着微蓝的莹光,俨然是北极惟一的主宰者。这里的冬天长达八个月,直到6月才开始短暂的极地夏季。
我们来到了海边。不过一个小时,我的四肢已冻得不听使唤。零下20度的刮风天,堪比零下36度。已经是四月底了,但真正的春天从未来过。近晌午的时候雪橇上已经放了三只结冰的海豹,猎人的狂热终于得到了满足……
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洛里诺村,这里毗邻阿拉斯加,距美国圣劳伦斯岛和克鲁森施滕群岛200公里。村子坐落在山上,视野极佳。表面看在这儿生活很艰难,因为时常有暴风雪降临。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北边火山环绕,洛里诺村有着让人嫉妒的气候,它的无风天比相邻村落要多得多。在村子里那东倒西歪的木棚下生活着约1500位楚科奇人。艾迪克拿起望远镜站到凳子上观望天气变化。他断定:“海上变化无常。天气不好。”这位行家里手预测会有一场暴风雪。果然,夜里暴风雪就来了。
早上5点,狂风的嘶吼中夹杂着奇怪的声音——不知是哭声还是呻吟。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个人躺在雪堆里。这是15岁的阿廖沙。他一身酒气,穿着短袜和薄薄的外套,蜷缩在雪堆里哭泣。他的双脚已经冻僵,我帮他把扔在一旁的旅游鞋穿上,试着将他扶起来送到旁边的小屋。二楼的门半掩着。沙发上俯趴着一个女人,地板上丢着一个空瓶。阿廖沙扑到她身旁睡了。那天我还送了一个女人回家——喝醉的她找不着自家的大门。前一天他们都领到了救助金,也就有了买酒钱。楚科奇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酒。
“现在已经好多了。有的家庭也不喝酒的。”莉季娅是艾迪克一家的朋友,她对此保留自己的看法。厨房的水壶里咝咝作响,屋外是零下20度,刮着风。今天打不成猎,惟一的娱乐就是作客。“我以前喝酒也很凶。现在我们的生活好过些了。人们看到了希望。”眼前这个柔弱的小个子女人坦承。希望也许正源自2001年俄罗斯商业大亨、现任英国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的到来,担任区长的他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让楚科奇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学校、医院、房屋等生活设施拔地而起……
“为了我们的新生活干杯!”艾迪克豪气地说道,转而面向妻子,“薇卡,把装内脏的桶递给我。”艾迪克在车库里分解海豹。在微弱的灯光下,他花了三个小时麻利地把昨天捕到的海兽刷洗干净,内脏烘干。艾迪克用烘干的腌海豹肠来代替土豆片。薇卡赞道:“真是美味啊!”
学校里年过半百的值班员摇着手中的铃铛宣布下课。不多久走廊上便挤满了二年级学生。楚科奇族和俄罗斯族孩子(阿布拉莫维奇任职期间楚科奇州经济复苏,不少俄罗斯族家庭迁来了洛里诺村)站成一个圈,跳起了圈圈舞。男生女生一起唱着拍子旋转,然后停下来,选出两个人,用力一推,俩人就撞上了。大伙儿都哈哈大笑,玩得兴高采烈。随着上课铃声敲响,斯文的女教师莉季娅微笑着关上教室门。过了一会,她用楚科奇的问候语向孩子们问好,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第四天暴风雪终于停了,窗外挂着一轮月亮。早上3:30我们出发前往冻土带。今天要采访的第二队人马只有两个人——28岁的牧人卡瓦斯和比他大八岁的妻子丽莎。他俩都穿着毛衣,面带微笑。丽莎的正式职务是帐篷女工。他们住在用帆布做的临时居所里,真正用鹿皮做的帐篷在几天前被大风吹跑了。
12只狗在帐篷入口处晒太阳取暖。进了帐篷后,我愣住了。丽莎简单地解释了一下:“这样比较方便。狗食在外面煮,我们的饭在这里做。”地面倒扣着两个桶。主人坐在桶上,让我们坐帐子边上的“沙发”——雪橇扣过来余出部分铺了块鹿皮。“别让风吹着了。”丽莎关切地说道。虽然帐篷内是零下10度,但总比外面暖和些。
他们的儿女都在村里上学,学会了楚科奇语,跳着圈圈舞,忘却了帐篷、鹿儿,甚至是冻原。丽莎往茶里倒了点炼乳,叹道:“没了他们在身边感觉很难过,但又没人能在这儿给他们上课,所以就把他们留在村里了……对不起,我们该打电话了。”
丽莎掀开帐篷,钻到了帐子里。那两米长、半米宽的小地方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还是通信处。“卡瓦斯,摇起来!”丽莎叮嘱道。卡瓦斯坐到“架子”上开始转动手柄。“架子”指的就是发电机,三个支脚的迷你发电站,有点像儿童自行车。坐在上边摇动把手就可以发电了。“再说一遍!”兹……兹……“我听不到,瓦利亚,再说——一遍!”与世界通话——其实就是跟附近的养鹿队和洛里诺村农场大本营通讯。丽莎和卡瓦斯每天都要跟这个我素未谋面的瓦利亚和其他人通三次电话。对话内容基本就是:“天气好吗?你们那边怎么样?”丽莎还设法要到了绳子来修被暴风雪弄坏的帐篷,订购到了燃料。
除了捕猎海兽,养鹿也是楚科奇人的一项传统产业。苏联时期一个养鹿队能养上5000-8000头鹿。而现在卡瓦斯总共有不到800头。有的被狼叼了,有的被盗猎者偷打了去。年轻人很少愿意以放牧为生,而老牧人一个个死去。养鹿的传统正渐渐消失。
“我们该回去了”,艾迪克对我说道。向卡瓦斯和丽莎道别时,他们送了我们一袋鹿肉。
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走遍了这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时光的木马缓慢而寂静地旋转,楚科奇人艰难而又倔强地生活在这被人几近遗忘的角落里……
[编译自俄罗斯《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