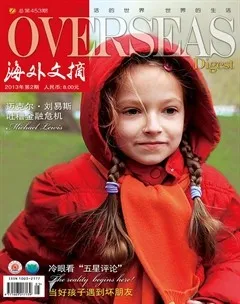硝烟中的自由记者们
2013-12-29莎拉·托波尔


在汹涌的海面上漂泊了两天后,一条小渔船将两名资深记者、几个造反派士兵和鲁斯·夏洛克带到了被围困的利比亚米苏拉达市,这里是利比亚内战爆发的中心区。渔船靠岸后,晕船的乘客刚准备登岸,密集的炮火便对准了渔船。无人知晓枪弹到底来自于政府军,还是分不清敌我的反政府势力。年仅24岁的夏洛克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进行着战地采访报道。
这条渔船是第一条在利比亚海岸登陆的船只。利比亚内战是夏洛克作为自由记者参与的第一次战地报道。与同行的其他记者最大的不同是,夏洛克没有任何资金支持,没上健康保险,毫无急救知识;她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在战区开展最基本的新闻调查。
夏洛克是一位身材娇小,金发碧眼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为苏格兰的一家报社整理战地新闻。她对这份事业充满期待,迫切希望和资深记者们共赴前线。正常情况下,新闻记者在前往战区前都应当接受为期五天的训练,以掌握在战争环境下生存的技能,并由所属的新闻机构给予全程的资金支持。夏洛克想成为一名成功战地记者的愿望十分强烈,以至于在没有接受任何培训和资助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旁人都觉得她失去了理智。
夏洛克在利比亚整整待了九个月,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搜集素材。2012年,夏洛克获得了英国新闻奖的最佳新人奖,并被《每日电讯报》聘用。夏洛克的故事在新闻界是个例外——完全摆脱了行业聘用新人的惯用模式,凭借自身对工作的执着和冒险精神取得成绩,获得认可。
是什么促使战地自由记者甘愿犯险
驻外采写战地新闻的全职通讯员一度能够得到电视台或报社提供的全程资助,然而这一时代早已远去。为了削减费用,媒体们纷纷鼓动自由记者为其采写新闻。雅尼内·迪·乔瓦尼从事这一行已经有20多年,他也是美国《新闻周刊》的投稿人。据他介绍,自由记者最早出现于科索沃战争,但发生于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让这一状况日趋恶化。在这场运动中,来自开罗的大批自由记者跳上开往利比亚的汽车,闯进战地前线后就陷入了困境。此后,各个新闻媒体纷纷缩减新闻采集预算,使独立记者获得了更多的采写机会。然而,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记者只是贸然进入这个危险领域,他们未接受过相关培训,也没有全职新闻记者配备的全套战地采写装备,比如头盔、防弹衣、卫星电话和急救箱,甚至连健康保险都没有。
保护记者组织的常务董事乔尔·西蒙说:“完全依靠自由记者采写战地新闻的现状正发生着变化。”西蒙强调保护记者组织的任务主要是为自由撰稿人提供资金支持和必要的装备,无论从局部地区还是全球来看,自由记者的工作条件与待遇都远远低于全职记者。西蒙感叹道:“要是他们不慎落入险境,根本得不到完善合理的后方援助!”
既然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年轻人热衷于自由记者这一行业呢?这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觉得报道战事是出于对行业难以抑制的激情。虽然媒体支付每篇报道的酬劳很少,但这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都愿意自掏腰包承担所有费用。只不过战区的自由记者们远没有好莱坞影片中描绘的那样被光环所笼罩,他们只是希望将战争的真实场景呈现在人们面前,不夹杂任何功利之心。
“阿拉伯之春”运动初期,很多初出茅庐的自由记者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踏入的是个“雷区”,可能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也门爆发抗议游行时,政府随即禁止外国新闻工作者进入也门采访,只有一些年纪较轻、经验尚不丰富的自由记者留在前线继续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劳拉·卡西诺夫评论道:留在也门战场上的自由记者太多了,他们冒的风险太大,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带着发表战地新闻的热切愿望,年轻的自由记者往往混淆了安全与危险的界限,在没有任何战地新闻采访经验的前提下就踏入了火线。
作为自由记者的好处是能在战场多停留些时间以写出深度报道,可以自主选取报道体裁,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与全职记者的激烈竞争,动作稍微迟缓就会丧失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想方设法地削减采访的相关费用,这些劣势让即便是有一定经验的自由记者也举步维艰。
今年38岁的詹姆士·弗利过去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工作过,与他同行的另外两名自由记者去年在利比亚被政府军扣留了六周。当时他们乘坐的造反派的汽车遭到政府军队伏击,摄影师安顿·哈默尔当场身亡。弗利承认自己所属的团队当时如果不过分深入造反派占领区,就不至于遭遇劫难。可如果不这么做,他们所采写的报道比起正式记者的就毫无新意和亮点,在后方的编辑眼里就缺少新闻价值。
自由记者的优势就在于出发速度更快,停留时间更长,关注角度更近。弗利在战区最后三个月的采访生活是在叙利亚度过的,大部分时间待在叙利亚西北部被围困的阿勒颇市。他与一位26岁的女摄影师尼克尔·彤合作,她也是去年在叙利亚开始接触到战争题材的报道和摄影。他们在这里投入了大量时间,但所得报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甚至付不起每天二三百美元定影剂的费用。更可悲的是,在丹尼尔之后,又有一大批毫无经验的年轻自由记者盲目进入叙利亚,马上就被眼前的情景所吓倒。“他们害怕是正常的,我在利比亚待过一年来到这里依然感觉害怕。”丹尼尔说。
媒体一方并不希望自由记者冒如此大的风险,不想承担相关的责任。27岁的凯蒂·保罗是在约旦首都安曼工作的一名自由记者,她主要向《新闻周刊》投稿。凯蒂今年夏季在进入叙利亚战场之前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境。大部分编辑都劝阻他们不要冒险,但是如果他们真能获得独家内幕,这些编辑们又会争相约稿,信誓旦旦地向记者保证这些文章能够被发表。
保罗这样的年轻自由记者从未接受过战区的急救和前线战报撰写培训,因为全套的培训费用高得吓人。即使自由记者费尽周折申请下来一笔经费,他们也要自己承担一定比例的培训费用,还要自付到美国和英国培训地的旅途费用,出版社更不会掏腰包来补贴他们。再加上稿酬少得可怜,一些在中东地区的自由记者便陷入了恶性循环:他们平日里省吃俭用,处境堪比饱经战乱的难民。保罗愤懑地说:“一些知名媒体付给我单篇文章的报酬不过100-500美元,而每篇文章需要一到三周的时间来准备、采写和加工,那点稿酬简直微乎其微。”
有些时候,自由记者还会遇到生命危险。31岁的奥斯汀·泰斯是在叙利亚工作的自由记者,他主要向《华盛顿邮报》和报纸出版商麦克拉奇投稿。今年八月中旬,这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大马士革郊区遭到扣押并受到了非人的虐待。要不是美国国务院出手营救,泰斯恐怕都没有机会将自己的这段难忘经历写成纪实报道。
自由记者的困境能否改善?
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大批的年轻自由记者就像是炮灰一样被送到战区,根本无人顾及他们的死活;而有经验的新闻记者认为根本犯不上去冒险。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呢?有人提出:应当让新闻媒体的编辑采取约束机制,只从接受过培训并配备安全防护装备的自由记者手中获取新闻资源。如果编辑们不这么做,只能使这个行业陷入恶性竞争的怪圈,助长自由记者的不良冒险行为。也有人提出:应当成立专门的基金会,为自由记者购买健康保险及其他必备的防护措施。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提议至今未能实现。
美国普利策危机新闻报导中心的高级编辑汤姆·亨得利认为:自由记者并没有真正掌握新闻报道的要领,也缺乏与编辑和顾问之间的深度沟通,很难保证新闻的水准。媒体们随意获取稿件只能降低自身的采编报道能力,所获得的新闻也缺乏深度。
23岁的自由记者劳伦·博恩在报道埃及革命的过程中有幸得到了一笔外部资金支援,并且得到了普利策中心专家的悉心指导。就在上周,她还在美联社获得了一份实习职位。这些丰厚的条件让她工作起来如鱼得水,丝毫不必为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担忧。博恩说:“未来职业发展道路何去何从,我们也感到很迷惘。难道要当一辈子自由记者?还是可以在全职新闻记者退休后接替他们?此外,新闻业界格局变化得很快,谁知道我们目前效力的新闻媒体十年后的出路如何?我们现在只能完全依靠自己去开创事业。”
[编译自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