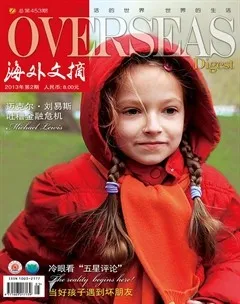哈莱姆——复苏的伤痛之区
2013-12-29陈晓洁/译

“老实讲,我们并不富有。这里的房租虽不便宜,但至少还算合理,能接受。”莱斯利只想用这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搬迁的理由。这位成功的建筑师为何要在年过六旬之际卖掉在传统富人区切尔西的房子转而在哈莱姆买下一套五居室的公寓呢?诚然,莱斯利的新住所位置相当不错,地处哈莱姆南部最繁华、房价最高的汉密尔顿高地弗雷德克道格拉斯大道上,但再好的位置也不足以让友人们平静地接受两个地地道道的欧裔精英从“富人区”搬到“贫民窟”的事实。“朋友们都在问我们图什么。”莱斯利与丈夫乔恩互换了一下眼神,两人默契地相视一笑,因为这里的人们向往平静自在的生活。假如时光倒退50年,回到莱斯利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60年代,她肯定想都不敢想自己今天的决定,那时即便是踏进哈莱姆区一步都是“很恐怖”的事。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没有白人会冒着被扒光、被打伤甚至被杀害的危险进入“哈莱姆黑人区”。
变革是随着大批中产阶级和社会上层阶级的到来而产生的,所以这一变革又被称作“地区贵族化”。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在哈莱姆西部汉密尔顿高地的私人宅邸,或是中央公园和弗雷德克道格拉斯大道附近的高档公寓安家。他们当中有过群体生活的大学生,有单身的艺术家、音乐家,也有拉家带口的作家、金融分析师,就连比尔·克林顿也曾于2001年在哈莱姆设立了工作室。这些哈莱姆区的新居民虽拥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家庭状况,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白种人。从2000年到2010年,哈莱姆区的白种人比例已经从2%增长到了9.8%。
“必须感谢上一任市长,是他把哈莱姆彻底清扫了一遍。”
追根溯源,哈莱姆变革的最初动力还是来自一批富裕的黑人。20世纪90年代,一些在二三十年前随大批居民一起迁出的哈莱姆中产阶级黑人重返故土,他们年轻、活跃,把廉价买来的老房子装修一新。你也许无法相信,90年代哈莱姆的某些街区为了吸引居住者,甚至把房子的售价定到了——1美元!此外,哈莱姆区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服务行业,招揽未来的纳税人。哈莱姆区的绿化面积变大了,街道变宽了,夜晚也变亮了,慢慢的,又重焕出生机。GAP、星巴克、来爱德等众多大型连锁店相继在哈莱姆区落户,一些小型商店也闻风而来。2002年,来自法国的面包店Ambassade开张营业,“哈莱姆的情况忽然间就变了”,面包店经理约翰·阿玛多回忆说,“人们可以晚上出来散步,而不必再担心会被侵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前任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是他把哈莱姆区彻底清扫了一遍。”焕然一新的哈莱姆成为无法承受曼哈顿高房价的纽约客们的最佳安身之处,当曼哈顿房地产价格如火箭般蹿升时,哈莱姆的人口迁入潮流随即加速。
曼哈顿中心区一套三居室的租金在每月3400美元左右,而面积相同的房子在哈莱姆仅需1600-1700美元。再加上交通便利、生活气息浓厚两项优势,哈莱姆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心城区外迁人口,尤其是年轻大学生和艺术家的首选之地,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六七十干脆就直接在哈莱姆扎根工作了。在这些年轻人眼中,哈莱姆区的最大魅力莫过于低廉的物价和多彩的夜生活:你可以在莱诺克斯或希瑞纳俱乐部欣赏爵士乐、在阿波罗剧院观看舞台剧、在吕西安或塞利维亚餐馆品尝大餐,或者更简单一些,在街头随便找一家小咖啡店吃一点特色食品,哈莱姆的不夜族最不缺少的就是选择!
如果说哈莱姆欢腾的夜生活是年轻人不可抗拒的牵引力,那么优美的城市环境就是举家迁入者们难以抑制的向往。哈莱姆的楼房大都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有700多座已经被列入历史和建筑遗产。这里没有高于六层的建筑物,住宅区的采光不知要比中心城区好多少倍。宽阔的绿化带、热闹的街道,哈莱姆仿佛是专门为三口之家量身打造的。除了自然环境,哈莱姆的生活氛围也别具一格,“街上熙攘的人群中有说英语的,有操非洲方言的,有说法语的,偶尔还能听到西班牙语。”莱斯利谈至此处变得兴奋异常,“大家都会微笑,交谈分外轻松自在,这简直太美妙了!”女建筑师回忆自己在切尔西度过的7年,竟想不起跟任何一位邻居打过招呼。
多文化交融之地,和谐共处的试验田
如今的哈莱姆区不仅吸引着在此成长的黑人知识分子重归故乡,也吸引着其他名人的到来,比如著名导演阿尔伯特·梅索斯。5年前,阿尔伯特·梅索斯在哈莱姆创建了一家电影资料馆,专门招聘一些家庭困难的年轻人做馆员,为他们创造更多接触电影艺术的机会。紧接着,阿尔伯特·梅索斯又开辟了一处展馆,以展览和开办教育项目的方式为不同社会阶层的交流提供平台。隆德尔饭庄的老板大卫·隆德尔是土生土长的哈莱姆人,他说:“比起20年前,我们有了更多的文化和休闲娱乐场所,并且是我们黑人自己在当老板,白人一统天下的时代被推翻了。”
经历了大批居民外迁的绝望,今日的哈莱姆重新看到了希望,它要承受一次巨大的变革,发展出一种适应21世纪需求的生活模式。这话听起来有些抽象,也许我们可以从位于125街的“红色雄鸡”餐厅找到较为具体的答案。“红色雄鸡”餐厅始建于2010年,是哈莱姆区最火爆的餐馆,食客需提前数天预约才能排到座位。餐厅老板马克·萨缪尔森的事业在不惑之年达到顶峰。作为一名出色的厨师,马克·萨缪尔森是报纸、杂志的常客,2009年他还应总统奥巴马之邀为到访的印度总理筹备国宴。马克·萨缪尔森是一名出生于埃塞俄比亚的孤儿,三岁时被一个瑞典家庭收养,他曾在法国求生,在纽约推出烹饪书籍一举成名之前还曾辗转过奥地利和瑞士。马克·萨缪尔森的烹饪才华与他接受多文化熏陶的经历不无关系,他的生存之道或许恰恰包含着哈莱姆未来发展的可借鉴之处。他说:“哈莱姆最需要的答案绝对不是‘拒绝改变、排斥新居民和抵制投资’。我们在哈莱姆扎根就意味着身兼两项使命,既要保护哈莱姆区犹太、意大利、非洲、加勒比文化交融共存的历史,又要开创哈莱姆区新的生活。哈莱姆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别的,就是它体现在饮食、音乐、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才是哈莱姆人真正应该维护和发扬的对象。在我们的餐厅,你可以看到埃及人的旁边坐着一对同性恋情侣,也可以发现白人家庭的旁边是两个虔诚的黑人信徒。”
其实不止是在“红色雄鸡”,哈莱姆的大街小巷到处是不同种族、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共处的景象。多文化交融的哈莱姆渐渐成为和谐共处的试验田。宽容,在哈莱姆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也正是这种有人情味儿的群体生活模式让越来越多的造访者最终选择留下来。
“哈莱姆,美国黑人历史的缩影”
哈莱姆人口结构的变化引发的社会变革对长期生活在这片传统黑人区的非洲裔居民造成极大冲击。他们的居住历史被看作是哈莱姆抹不掉的经济和文化伤疤,所以他们拒绝接受“区域贵族化”这种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说法。
30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哈莱姆区黑人生活的法国电影工作者马尔蒂娜·巴哈特说:“地区贵族化的进程很可怕,而且毫无节制。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时竟有人直接拿来100万现金要买下他的宅邸!这绝不仅仅是钱的事。哈莱姆黑人们的集体生活消失了,朋友们聚在一起玩牌、听音乐的小酒吧关门了,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不得不各奔东西寻找更便宜的住所,街道两旁的小商铺被奢侈品商店和高档饭店取代,完全变了样子,让人生恶。哈莱姆区就是美国黑人历史的缩影。”
但诸如此类的批判在哈莱姆复兴的拥护者眼中毫无价值,他们认为有人走,就意味着还有人会来。
[译自法国《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