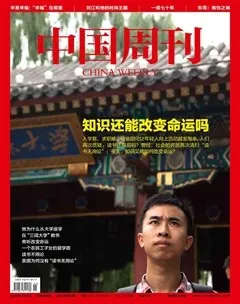华夏幸福:急进隐忧
2013-12-29

上市后的华夏幸福迈入了高速扩张的快车道,地方政府城镇化的强烈需求让其“土地生意”充满无限可能,但另一方面却是潜藏的危机。
廊坊党校大院最深处,蓝色墙面的四层小楼就是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的发家之地。楼内的装潢略显老旧,不少办公室里都挂着土地规划图。
五年前,这家主营中央空调、销售额几十亿的公司转做工业地产,其“产业新城”的概念很快俘获地方政府、投资者和监管层的心,华夏幸福因此迅速跻身房地产百亿俱乐部行列。
近来,在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不断加码的背景下,华夏幸福却持续其高速扩张态势,这引发外界对其未来的担忧。
急进中的华夏幸福,能够一路“幸福”下去吗?
“吃北京的粮食,下廊坊的金蛋”
如今“以城带产,以产促城”、“产业新城专家”等等光环,已经成为了华夏幸福的注脚,追溯十年前,这一切开始于河北廊坊市南部的一个并不发达的县城—固安。
《中国周刊》记者在廊坊采访过程中发现,当地人都认同“过去有两个廊坊”的说法,即“北三县”和固安,北三县是指香河、三河、大厂,这三个地方和北京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而南面的固安相对发展薄弱。
早期的固安一度并不受房地产开发商的青睐。
据业内人士透露,2002年6月华夏幸福决定投资运营固安工业园区,条件就是与地方政府签订排他性的委托开发协议。当时,还有智囊团给华夏幸福高层支招,“吃北京的粮食,下廊坊的金蛋”,即通过开发工业园来提高固安和北京一体化程度。
这一招,为初入地产行业的华夏幸福带来了转机。
到2005年,固安工业园区占到固安县工业产值的5%,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50%。
毫无疑问,固安经济的半壁江山是由这个产业园区带动的,如今固安通过近10年来的产业新城建设迅速崛起,并以年均40%的经济增速跃居廊坊市10县区首位。
固安工业园可被视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商业模式的发展雏形。十年间,固安工业园实现了与首都北京的快速发展紧密对接,形成电子信息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三大产业为依托的产业园,并配套建设固安规划馆、创业大厦、福朋酒店、孔雀广场等多处生活服务设施。
继固安之后,华夏幸福不断承接工业园项目,为地方政府规划开发工业用地,这才开始了园区开发运营与城镇开发建设相济的“产业新城”模式。
“固安的成功,让华夏幸福基业有了非常强的政府公关能力。”业内人士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除了政府大力支持外,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成功也不能忽视其区位选择上的精心布局:京津冀区域辐射区,交通相对便利,加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周边地区有了承接产业和技术转移的需要。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北京的人口外溢和产业外溢给华夏幸福带来了可观的发展机会。
此后,华夏幸福基业不仅明确了产业地产项目为公司经营主业之一,也开始确立了其围绕北京周边县市打造工业园的主要发展思路。
2013年,河北省政府全力打造的“环首都”经济圈概念的火热似乎也证明着华夏幸福的战略远见,坐拥首都经济圈发展的政策优势与地域优势的华夏幸福基业无疑就成了赢家之一。
赚足每一个环节
对于任何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而言,输赢的关键还是在于“钱从哪来”。作为土地运营商,华夏幸福几乎赚足了每一个可能盈利的环节。
从政府手中拿到项目与政府签约,垄断片区一级开发,这是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模式中最为核心的环节。这一过程中,华夏幸福基业要完成包括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产业促进、品牌推广和综合服务。而政府通过收税和卖地赚取收益并支付公司一级开发的成本。
据媒体公开报道,从华夏幸福和地方政府所签署的协议来看,在公共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政府要保证建设总投资额的15%作为华夏幸福的建设利润;在土地整理上,政府需要将土地整理成本的15%作为华夏幸福的土地整理利润;设计规划、咨询等服务费由双方按照成本费用的10%计算。
“目前,国内还没有太多开发商采用这样的土地经营模式,”龙创基业企业服务中心总经理高富强对《中国周刊》分析说,“在众多做工业地产的公司中,华夏幸福承担了开发商和运营商的双重角色”。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地产分析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由于产业地产周期比商品房要长很多,规划设计不可能一次完成,因此设计费用和咨询费用的利润通常会有一定的弹性,而且空间较大。”
其后,二级开发中,华夏幸福要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发展产业,并为园区提供服务。这一部分收入其实是产业园区项目收入中最为可观的部分。据媒体公开报道,按照协议,政府要将委托区域内当年入园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的45%支付给华夏幸福。公司近三年财务报告中,产业发展服务一直是产业园运营营收最大、毛利率最丰厚的重要业绩支撑点。
于房地产公司而言,虽然土地一级开发的利润率不及商品房开发,但可以通过有利的出让条款,减低在二级、三级开发中的成本。比如,华夏幸福最大的营收来源—配套住宅孔雀城,就是通过一级开发中的低价拿地进行商品房开发和销售营利。
“它们在做的是低价买高价卖的土地生意,”高富强说,“华夏幸福基业近几年的迅速扩张,与廊坊地方政府不无关系”。
业内人士分析,其实这样的模式对政府和华夏幸福而言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双赢”:政府前期零成本投入,只要园区顺利运作、入园企业增加,就能实现GDP的提升,而华夏幸福不仅可以获得政府外包的园区招商、运营和服务等政府职能,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会给予华夏幸福廉价的住宅用地作为补偿。
由此,产业服务、城市运营、城市建设、地产开发四块业务被华夏幸福基业在“最好的时机”下组合在了一起:借大城市功能溢出与人口溢出之势,通过规划服务、产业招商服务对接政府需求,获取代建收益与服务收益,华夏幸福不仅在不同阶段进行低成本、高效率、高溢价的地产开发实现多重收益,还形成了长期园区开发和短期商品房销售相结合的盈利模式。
不可复制的“政商关系”
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模式在“环首都经济圈”发展得风生水起之时,如何实现模式复制却成了备受业界瞩目的问题。
产业地产是否存在足够的市场空间无疑摆在首位。
2013年,华夏幸福开始北上辽宁、南下长三角、挺进华中,先后在沈阳、上海、无锡、天津、青岛、大连、西安、兰州、重庆、武汉等地开始进行自我复制。
今年下半年,走出北京的孔雀城开始收获,九月下旬,沈阳苏家屯孔雀城开盘,首期推出200套,销售额约为2亿元。
但这些在华夏幸福基业整体营收中显得杯水车薪。2013上半年,华夏幸福总营业收入87.84亿元,而环北京地区营业收入为87.65亿元,占总营收99%以上。
对此,克而瑞信息集团城市运营顾问中心副总经理徐和锋分析说:华夏幸福走出北京后营收不佳是因为产业地产项目资金回笼周期较长,“产业园资金周期一般是八到十年,因此短期还不能够评估华夏幸福基业在‘环首都经济圈’外的业务经营状况”。
并非所有人都保持乐观。
高富强认为,虽然未来经营状况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但“华夏幸福不可能在其他城市拥有在廊坊的政府议价能力”。
一方面,华夏幸福在廊坊积累的足够的政府资源和招商能力未必可以在其他城市复制,至少不可能在短期实现。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定位于产业园开发综合服务的华夏幸福作为政府服务提供商,它的的首要客户是围绕大城市交通枢纽的小城镇。这些地方政府有城市扩张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但由于财政收入偏低,对于开发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才会愿意将一部分利润让渡给民营开发商。
媒体报道称,“环首都经济圈的地方政府相对比较弱势,在沈阳、青岛、无锡乃至更多一二线城市,45%的落地投资额分成恐怕很难实现,这给华夏幸福进一步的模式复制和利润保障带来了难题。”
曾有投资人士评价,“该公司园区+地产的模式扣紧了在财政压力较大和地方经济增长乏术的情况下,市县级政府追求GDP和政绩的‘命门’”。
但在华夏幸福的扩张版图里,合作的政府由县级市、城镇转向地级市、甚至直辖市,与这些资金实力充足的政府谈判,华夏幸福势必跳出原先的模式寻找新的共赢方式。
除政府谈判能力之外,产业园二级开发中,华夏幸福基业的招商能力也并不被高估。
基于投资聚焦于住宅的现实,开发区的招商本就工作困难重重,而且产业园招商资源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对开发商能力的挑战更大。
此前媒体披露,华夏幸福位于大厂和怀来的工业园区招商引资难度增加,企业入驻数量低于预期。
而华夏幸福基业在2012年6月投资75亿,整体开发“无锡(南长)国家传感信息中心”产业园项目,政府只负责园区建成后企业管理。
最终,华夏幸福选择了分片开发方式,第一笔投入仅为5亿元。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做法可以规避二级开发资金回收慢的风险。
应该说,华夏幸福正在走出的不单单是“环首都”的地理概念,更是急切需要走出垄断土地开发形成高溢价的“高杠杆运作”模式。
资金链的“定时炸弹”
带有垄断色彩的多级土地开发虽然可以实现高溢价,但无法回避的是对资金的高度渴求。
今年9月,华夏幸福基业抛出的定增方案融资60亿,再次刷新了房地产企业再融资的纪录。这60亿,对于华夏幸福而言,是喜是忧?
克而瑞信息集团城市运营顾问中心副总经理徐和峰强调,华夏幸福正处于业绩高速释放期,这才形成了股价逆势而上,一路走高。
基强联行一位陈姓基金经理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华夏幸福与地方政府利益捆绑过于紧密,政府投资方向的改变给公司资金回收带来的变数很大。而长期高负债又会吞噬公司利润,为了尽快摆脱对高成本信托的依赖,华夏幸福才会不断寻求高额融资填补资金空缺。”
记者发现,过去五年中,华夏幸福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是银行贷款和信托融资。在华夏幸福财报中显示,2012年共有十六笔融资、贷款总计金额36.76亿元,而今年上半年,信托融资18.9亿元。
上述陈姓经理指出,“上市公司外担保金额超过净资产的一半,就说明这家公司有财务风险。”
而记者发现,华夏幸福基业担保金额占净资产的比例为119.75%。与2012年担保金额比例89.2%相比,华夏幸福担保资金规模一再扩大,已经让外界看到了其资金链的潜在风险。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半年报显示华夏幸福的应收账款为19.64亿元,相对于2012年同期的10.76亿元,2011年同期的3.06亿元又明显激增。
陈经理分析,大量应收账款不仅占压了资金也是企业潜在风险的另一个方面:“巨额的应收账款存在呆坏账的可能性”。目前,华夏幸福基业对呆坏账的准备为0.46%,“如果真实呆坏账超出准备,将会是资金链的一个定时炸弹”。
有分析指出,巨额的应收账款就是源于华夏幸福的业务模式,市场销售冷淡和地方财政吃紧,这让地方政府的回款速度下降,而最大的风险则由华夏幸福来承担。因此,华夏幸福在享受相比普通房企和园区开发商享受更高的毛利率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规模的应收账款所蕴含的潜在风险。
也有分析指出,华夏幸福所面临的风险还包括宏观政策。
2011 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房价过高、过快增长的调控政策,高富强指出,“对从事城市地产经营业务的华夏幸福而言,政策的影响甚至会比资金问题更难避开”。
而在更远的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低价土地的成本红利一定会渐渐褪去,华夏幸福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