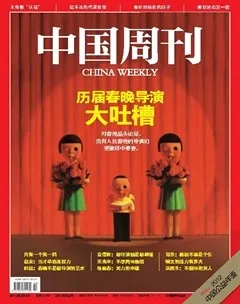王振耀 中国公益谈创新尚早
2013-12-29
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受全面危机的一年,那么痛定思痛的2012年应该怎样评价?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政策上进一步放开,大额捐赠的频现,民间组织的积极改革,表明2012年的中国慈善事业迎来了转折。然而,面向2013以及更长远的将来,中国慈善事业仍旧存在相当多的认知误区,这成为阻碍公益健康发展的羁绊。
Q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A =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您认为2012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发展情况如何?该如何进行评价?
2012年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之年。几个亮点:首先,政府的政策有了突破,广东全面放开,社会组织注册的准入条件、门槛大大降低,在全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第二,政府2亿的(购买社会服务)招标,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过去对整个民间组织持防范、管理,现在掏钱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逐步信任。这2亿不仅是量的变化,还是一个质的变化结果。第三,政府鼓励宗教进入慈善界。去年2月,中央几个部委下发文件,鼓励宗教进入慈善事业,这是政府第一次发文。
还有比较大的转折点,比如百亿捐赠的承诺。过去大额捐赠,指的是一千万、一亿。现在有几个企业家承诺捐赠过百亿。这些承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
所以说,2012年势头很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开放和支持,民间的富豪行动很积极,此外,民间组织也涌现出积极改革的势头,如邓飞的免费午餐;儿慈会天使妈妈团队;应急救助的网络,比如儿童大病的4000069958热线开通,去年运行得很不错。这样的转折很不容易。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2012年的中国公益进程,您认为应当是哪一个?
大转折,或者是提升性的转折点。过去,政府对民间不理解,民间对政府更疑虑重重。去年,一个结构性的变动就是政府和民间开始有良性的互动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政策空间一直是公益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您认为目前中国公益事业的政策空间到底有多大?
大致上,我们民间社会用了现在整个政策空间的10%,大量空间我们还不太会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大部门民间组织没有咨询专业机构,对政策空间理解不到位,用得不到位。比尔·盖茨曾亲口跟我说,幸亏他有专业团队,后来建了基金会。他开玩笑说巴菲特就不如他。难道巴菲特没有钱吗?当然不是。我们很多人上来就开始干慈善,没有专业地做慈善的意识。
一直以来,公益领域呼吁改革的声音不断,目前政策是否也存在缺陷?
相关政策确实有一些缺陷,像绳索,把大家锁住了。从法律上来说,第一是主管单位难找,外国机构进来也很难。第二,慈善事业规定的高标准。中国慈善业的规定是世界级的,我们是把理想当成了现实。比如(慈善事业支出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要求基金会的钱当年就得用光、用掉。全世界都是5%。新加坡原来想学中国,学了几年发现不对,就把它废掉了,发现中国的规定太高,学不了。比如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行政成本规定,要求不超过募集资金的10%,弄得大家普遍造假。中小型基金会的秘书长为了行政费用天天愁。一个慈善组织做起来,先愁它自身生存问题,它怎么会有大发展呢?第三,税收的相关规定。如捐钱的免税问题,如基金会的盈利要不要交所得税?全世界都不大交这笔税,但我们交得不少。这造成一些现实的难题,有些企业家捐赠的是股权,这笔捐赠要交税的话多达六亿元,人家怎么捐。有个企业家捐两亿元,手续办得迟一点,各种滞纳金、缴税,加起来差不多到六千万元。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全社会该反思。
总之,我们公募管理行为滞后于社会大众的要求,滞后于善心。还给善心设了很高的规定,注册门槛200万元,美国、欧洲都没有门槛。注册机构还要有级别,分中央、省两级,级别很高,想在一个县城里行善的话都很难。这是当前相当突出的一个问题。
如果未来政府继续松绑的话,应当从哪方面着手?
改革的方向就是向国际社会看齐,不说绝对看齐,也要参照,不要弄出人类社会还没有的标准,我们最好别高于人类社会目前的经验。现在管理体系滞后于人们的善心需要,管理体系门槛太高了,造成了后遗症。
专业性不强,一直是人们对很多慈善组织的一种评价,您觉得专业性的内涵应该包括哪几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你觉得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为大众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专业化很重要,比如现在咱们说儿童问题,香港有个教授专门研究流浪儿童的救助,他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后半夜值班,发现哪些孩子会这时候出来,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分析孩子的家庭,流浪的原因,就不会粗暴地一定马上送孩子回家。但现在我们法律还是这样,必须把孩子送回他家。最近有新闻说流浪汉冻死大街,有批评说公益组织官僚主义,但主要有公益组织团队不够专业的原因。
专业的问题,是否也包括公开透明的问题?
组织自身的专业性包括内部管理体制,包括公开信息的需要,这对中国知识界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咱们的大学里面都没有这种训练,所以组织也是停留在粗放型上。以儿慈会为例,企业会计多,机关会计多,真正慈善类组织的会计、专业财务人员极少,所以他就不会核算、公开,经过哪些程序,不太会。
但公开透明也不是每个细节都公开,公开得一丝不挂,我是反对的。比如说国外公布人员的工资标准,绝对不会公布职位上具体人的名字。咱们公布这个秘书长某某某的工资是多少,这个就不合适了。人家可能明天就离开这个职位了。发票怎么能每一张都公布呢,但是人家的发票用途写得清楚,写着你吃饭花了多少钱,请的谁,内部都能查看,所以国外不是一丝不挂。但,国外的程序是公开的,你开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是公开的。咱们内部恨不得不准发表不同意见,那恐怕就不行了。
您曾在过去的采访和演讲中多次强调,公益事业要发挥普通人的作用。然而目前仍有很多普通民众认为,公益只是政府的问题。您认为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何在,应当如何解决?
公益只是政府的事儿,这观念来自计划经济,是贫困时代形成的一种理念。贫困时期,民间的组织能力是很弱的,一切都依赖政府。但实际上从全世界来看,像欧洲,开始确实靠政府,但是实际上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欧洲现在正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我们观察,他们大量的养老院,由政府办向民间办转移。其实,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多事。
现在社会上对公益评估呼声很高,您觉得公益项目评估应该由谁来做比较合适,另外怎么做才能达到真实、客观?
我认为公益项目的评估应该由社会第三方来评估。评估要有一些刚性的指标才行,包括公益项目覆盖的面、受惠的人群、持续的时间等。不能说服务一个人的项目,我说好就好,服务一万人的项目,有一个人说不好就不好。有些刚性的指标,然后有第三方进入,由社会来评估。为什么有的项目社会捐款踊跃,有的项目社会反应很冷淡,其实大众心里有一杆秤。
您认为未来一年,中国最需要的公益创新点是在哪儿?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企业家也好,还有公益组织也好,他们说未来可能从创新2.0时代步入3.0的时代。
可能需要步入1.0时代,而不是2.0。因为中国公益的根扎得不深,谈创新,还早一点。我鼓励大家创新,但现在最重要的创新应该是和社会服务结合起来。现在要重复美国100多年前的历程。把人家最初1.0的项目给列出来。
中国公益必须扎根于社会,就是给社会大众提供服务和解决社会服务,和残疾人、儿童、老人、精神病患者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解决起来,才会产生出中国巨大的创新。比如免费午餐项目有多少创新,它的创新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