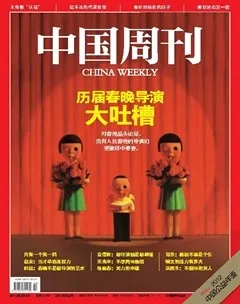站在现代慈善的门槛上
2013-12-29周昂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问题在哪儿?”
这个问题,放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受访者可能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2008年之前,人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问题”。而今天,人们可能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透明度的问题,组织建设的问题,政策环境的问题,专业化服务的问题,观念的问题,等等。
2012年5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在北京发布的2011年中国公益事业盘点,其标题被命名为“走向现代慈善”。诚然,人们或许从没像今天这样关注公益慈善事业的现代化。特别是2011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民间力量的成长的背景下引爆的“郭美美事件”,令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于是,在整个2012年,我们可以看到,“后郭美美时代”的公益慈善人们已经开始加快脚步,努力地触碰“现代慈善”的那根金线。
在信任危机尚未平息的情况下,“公开透明”再次成为公益慈善领域变革的切入点。
体制内的反思
2012年1月8日下午,在2011中国慈善年会上,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等112家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发起“透明慈善联合行动”,根据该行动,这些组织彼此约定,积极响应民政部颁布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并以此为标准,开展公益慈善信息公开工作。
半个月前的2011年12月16日,民政部向社会颁布了旨在对捐助信息公开时限及方式作出规范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一些过去面目模糊的指标得到了量化,例如,日常性捐助信息,应在信息公开主体收到捐赠后的15个工作日内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息;重大事件专项信息,应在收到捐赠后的72小时内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息,或按有关重大事件处置部门要求的时限和要求公开等。
2012年,民政部陆续出台了若干有关公益慈善领域的法规,可以视为2011年暴风骤雨过后的一种来自体制层面的反思。在《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的基础上,2012年5月,《慈善捐助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已经完成了第一稿起草。2012年7月,民政部印发《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在《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出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指导。
至于这些法规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培峰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搞公益慈善事业搞了几十年,直到2011年《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公布,才有了第一个有关信息公开的详细的指导性文件。”他认为,如果这个指引早些出台,之前在公益领域闹得沸沸扬扬的的公共事件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2012年7月与网友的一次座谈中,王振耀指出,英国在150年前的1853年就建立了一个国家慈善委员会,对各个慈善组织都有行业标准,而且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儿童类、残疾人类、老年人公益事业都有各自的信息公布标准——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规范显然来得迟了些。
不是不想公开透明,而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中国公益慈善面临的道德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专业化困境。回顾2012年,中国公益慈善领域发生的几次公众质疑事件,也越来越清晰地指向这一点。
透明是个专业问题
2012年6月,山东德州13岁男孩杜传旺在汽修厂学手艺,却被两名工人将高压气泵塞入肛门充气以致重伤。事情传到网上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并引起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天使妈妈基金的关注,在该组织的介入下,杜传旺被送入北京一医院救治,相关募捐也得以展开。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孩子得到救助的同时,网上对“天使妈妈”基金的质疑也一浪高过一浪,很多网友对“为何舍近求远到北京医治”、“社会募捐的善款是否被挪用”等提出疑问。
“为什么会受到质疑,因为公益组织做得还不够专业。”王振耀认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振耀详细剖析了这件事背后蕴含的公益组织体制性问题,即“天使妈妈”基金“每走出一步都缺少不同意见的人的参与和协商”,“不同的意见需要尊重,如果公益组织体制不完善,矛盾就会放大。这种调节矛盾的方式应该以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是出了事儿,马上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不同意见的代表参加。”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公众的质疑。
这一年,公益慈善领域另一个引发广泛质疑的公共事件,是“儿慈会”巨款神秘消失事件。2012年12月10日,网络爆料人周筱发帖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度财务报表里“至少有48亿巨款下落不明,神秘消失”。儿慈会当天即回应,系财务人员将一笔数额为4.75亿元的“银行短期理财累计发生额”误写为47.5亿元所致,然而这个说法显然难以服众,而儿慈会承诺公布的银行对账单,也没有如期公布。
同样,王振耀将这次事件归结为公益慈善的体制、专业化、技术和程序问题,“我认为,实际是公益组织的管理体制不行,过去都是简单地行行善,简单地通报情况就行了,现在看来这种方法不行了,需要现代的管理体制,要有专业化的人才。公益不专业,小数点就会错,不专业不行了。”
好在,2012年,从官办到民间组织,一些透明专业化的尝试已经开始了。与以往相比,它们不约而同地选用了“第三方监督”这种现代慈善的方式,而不再“简单地行行善,简单地通报情况”。
例如,这一年4月,由媒体人邓飞创办的著名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基金也正式组建了监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参照国外知名慈善基金运作,由10位捐赠者代表、知名学者和媒体人组成,主要职责在于监督大额善款使用、管理受助学校和公开信息。与此相呼应的是,12月7日,“郭美美事件”后饱受诟病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宣布正式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旨在加强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项目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十六名委员志愿服务,不会从红十字会收取任何报酬。
一些值得关注的第三方平台也开始进行信息披露,8月29日,由基金会中心网开发、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提供咨询,反映我国基金会的透明水平的“中基透明指数”正式发布,上线试用。这是中国公益行业首个透明度量化评价系统,年底,基金会中心网又首次发布了“中基透明指数2012排行榜”。
2012年,在公信力营造工作中,体制内外显然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不再惧怕“围观”,而是直面争议,引入“围观”。
在公益慈善组织注册方面,来自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更加振奋人心。
社会组织登记破冰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古来有之。早在宋代,一些宗族内的慈善行为便已经开展,例如对族内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民国时期,政府开始设置专门的慈善机构来管理慈善救济,并制定了相关制度。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在灾荒和战乱的难民救济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到了新中国,由于高度计划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大陆原有的慈善组织或解散,或瘫痪,公益慈善事业被政府包办,一些改造后的组织被附以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例如红十字会。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并不存在所谓“民间组织”的概念。事实上,大多中国普通老百姓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是以一种啼笑皆非的方式。1995年,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坊间开始迅速流传一些“西方妇女组织”要在北京举行“裸体游行”的小道消息,这个传言宣称,为了防止这种“伤风败俗”的事件发生,政府已经发给游行路线周边的居民们一些布块,让他们一旦遇到裸体游行者,赶紧把她们包裹起来。于是,“民间组织”与“裸体游行”一起成为那年人们的谈资。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由王行娟女士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非营利民间妇女组织——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作为唯一一家没有中国部委领导的草根组织公开亮相,引来了外国媒体的蜂拥报道。结果,上级单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与其切断了联系,由于没有“主管单位”,王行娟不得不将这个组织变为工商注册的有限公司,名称改为了“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红枫的遭遇,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被很多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一再重演。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三类,分别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范,这三个法规对社会组织的登记都实行“双重管理”制度,也就是社会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才行。由于这些组织是非营利的性质,出了事又往往要主管单位承担责任,因此很多单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愿担当这些组织的挂靠单位。而如果像红枫这样选择工商注册,相关税费则是很大的负担。
这样的环境给众多民间公益组织带来了苦恼,例如广东东莞的“坤叔”助学团队,从2005年起便一直以“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的名称向主管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却一直因找不到主管单位而无法成功。据该组织创始人,被称为“坤叔”的张坤讲,每当被问到自己是属于“哪个单位”的,他这个“黑户”都哑口无言。
不过,从2011年开始,广东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改革已经开始提速。2011年8月,东莞市民政局在一次会议上透露,当地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不需再找业务主管单位。特别到了2012年,广东省再度迈出了一大步,5月,广州市发布《关于实施“广州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社会创新观察项目的工作方案》,规定5月1日起,各种社会组织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2012年7月1日,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正式开始实施,标志着广东全省范围内的社会组织都实现了直接登记注册。
“准入条件、门槛大大降低,这对社会组织的注册问题,在全国开始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对于2012年广东省在“放权”方面的尝试,王振耀如此评价。

呼唤专业化服务
放眼全国,在整个2012年,“放权”成为了公益慈善领域的基调之一。这一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促进社会组织依法规范健康发展,简化登记程序,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目前,除了广东之外,北京、吉林、四川、青岛等地均先后推出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此外,2012年2月底,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六部委还发布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首次对宗教慈善进行了专门规范。
在为社会组织松绑的同时,政府也开始用更加实际的行动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2012年3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中央财政首次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热词,这个概念源于英国,指的是政府将公共服务以招标的形式外包给社会组织,通过购买它们的服务,既实现公益慈善的目的,又减轻了政府负担,同时也避免了政府亲力亲为造成的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
早在中央试水之前,政府购买服务的地方实践就已经开始了,例如去年2月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政府便表示已将130余项职责交给社会组织或事业单位,同时在中国率先试行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而此后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再度向社会组织释放出了重大利好。
“中央财政它做出这样一个信号,从过去对整个民间组织持防范、管理(的态度),现在是发现我要掏钱购买,这2亿不仅仅是2亿,它是一个认识。”王振耀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在政府为社会组织松绑、并开始以实际行动购买社会服务的背景下,公益组织怎样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势必成为2013年行业内的焦点。
专业服务首先需要专业人才,2012年9月,中国首个慈善事业管理专业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开班,12月,由民政部指导、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和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在京启动,都为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尝试。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公益行业如何留住专业人才。一个长期困扰公益组织的问题是,行政成本到底应该有多高?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10%,而境外公益组织收取管理费比例通常要远远高于国内公益组织。怎样让公益人活得更有尊严?
王振耀认为,民间公益组织一定要把自己的服务对外展示出来,“其实大量的行政成本应该是做服务的成本,你服务的成本拿得多,就应该”,“一定要有专业化的服务,一个专业组织第一是服务,服务提供不上来,光说你的组织作风如何好是不行的,老百姓是不认账的。”
如果说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走向现代,那么2012年,它已经站到了现代这道门槛上,公益人开始学会如何构建公信力,政府开始学会扶持民间力量,但这一切,都需要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巩固。
进入2013年,公益慈善领域的第一个重大新闻来自河南兰考,一场大火,七个不幸丧生的孩子,让袁厉害这位“爱心妈妈”闻名全国,民间收养行为的不规范发人深省,政府的不作为令人痛心,怎样合理引导民间善行,令悲剧不再发生?新的一年,中国人将在思考中继续解答公益慈善现代化的命题。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