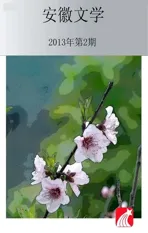超越生死的时间之旅——以艾米莉·狄金森的几首诗歌为例
2013-12-12陈涛
陈涛
一、死亡、时间和艺术
希腊神话中酒神仆人西勒诺斯回答米达斯王的逼问,要他说出对人类最好的是什么。西勒诺斯嘲笑道:可怜的浮生啊,对你最好的东西是你永远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其次好的,就是立刻死掉。生命是悲哀的。然而希腊人通过艺术的救赎之路,发现生命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从而得出了人生的相反结论:最坏就是立刻就死,其次坏就是早晚就要死。[1]11-12艺术使得原本悲哀的生命有了值得活下去的意义。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曾说过,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而恰是这根看似柔弱的芦苇,却有着足够的生的坚韧:虽时刻面临死的在场,但却不为所迫;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他也断不会停止思考。生死问题是人类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它直接涉及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终极关怀,涉及人类的价值观乃至信仰。生命的意义与时间紧密相连,是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艺术用生命在空间形态上的生成与毁灭,来表现时间那飘忽不定的足迹。我们有必要阐释死亡、时间和艺术三者的关系。
死亡是人类终极的失落,也是永恒的失落。死亡既熟悉又陌生;感觉清晰又模糊;实在又虚幻。死亡让人疑惑,让人恐惧,只因为它无可挽回,也就无可毁坏;不可逆转,也就义无反顾;不能尝试也就耐人寻味;无所不在,也就不必躲藏。死亡让生命更加可贵,才不会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因着死亡,人类才能看见未曾见过的。死亡造成了世界的断裂,但就在这断裂之处才看见了原来存在的关系。死亡必然涉及时间问题,引出了人的生命感。在人的生活世界里,人才开始思考 “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过去”、“生命的过往是怎样的”。面对死亡,面对存在,面对生命的经验、过往的历史经验,人不得不思考死亡与时间的联系。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532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即是时间性的存在。作为有限的个体总是期图超越时间的无限。然而,现实却是时间的流逝,人的各种超越,都无法摆脱时间的转轮而驰向死亡之乡。时间否定了有限个体。“艺术的中心是人的生命形式,艺术是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获得无限性的终结。”[3]86时间与艺术的结合让时间获得了一种自身的肯定。虽然人作为有限者,无法抗拒死亡的宿命。人对于死亡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然而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联系着时间形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然而,“人通过艺术这一中介向无限超越之时,时间的流向发生了变化。人在体验之中,不再像日常生活时间是由过去走向未来,而是以未来朗照现在。他携带生命的全部过去和现在进入未来之中,并以未来消融了全部时间,根据自我内心所体验的内在时间重新构筑一个新的时空(境界)”。[3]88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家能够把感性个体引出有限时间的牢笼,臻达绝对超时间的永恒,让顿悟的一刹那定格为永远。
二、生死时间之旅在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体现
如何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诗人有着不同的答案。对死亡与死亡后来生的可能性的思考盘踞在诗人的头脑里,如何跨越死亡这座人人必经桥梁,来真正认识死亡本身的特殊性,横亘在了每个人面前。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千七百余首诗作中,有六百多首以死亡为主题。她在“死亡”的否定中寻求“永生”。她希望通过突破死亡与时间的对立来揭示生命在时间流逝中的延续。然而人类的个体存在总是一种时空上的存在。个体生命在空间形态上消逝,意味着作为以个体存在的线性时间的终结。任何个体的都不能逃脱个体消亡时间的最终到来。对于艾米莉·狄金森来说,如何能够从永生的未来观照此刻当下,挣脱个体线性时间的束缚而获得超然成为其死亡主题诗歌的重心。死亡在她看来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和词,而是个体生命的有限与宇宙生命的无限,个体生命的线性时间与宇宙生命的循环时间的对立统一的载体。
狄金森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4]中把自己对于死亡与时间的理解进行了充分的诠释。“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He kindly stopped for me-/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And Immortality.”“死神”在此处已经不再是一个狰狞的魔鬼而是一个优雅的绅士,死亡已不令人恐惧。“我”的不断前行使我不能为了他而等待着,而他则“好心”地为“我”停车,“接我上马”,载“我”走上另一段旅途。而在这死亡的马车上有“永生”与我共行。作者通过借用人生旅途的隐喻来揭示生与死只不过是两段不同的行程而已。“We slowly drove-He knew no haste/And I had put away/My labor and my leisure too,/For His Civility-”“我”回报死神的“儒雅”以撂下尘世的牵挂,不再匆忙,“徐徐前行”走向另一段旅途。在途中她经过了孩子们在“嬉闹”的操场的喧嚣到落日西沉的凝视,在一系列的隐喻中作者再次顾盼了人生:学校—童年,庄稼—壮年,落日—暮年,在时间的慢镜头中咀嚼着些许对于生的牵挂与忧伤。在这节诗中作者用了“ring”这个圆形的形象表现了生命的轮回与永恒。“We passed the School,where Children strove/At Recess-in the Ring-/We passed 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We passed the Setting Sun-”
然而“西下的太阳”带走生的热度,留下了死的冰凉,“露水”提醒着“我”衣薄体寒。“Or rather-He passed Us-/The Dews drew quivering and chill-/For only Gossamer,my Gown-/My Tippet-only Tulle-”此时在暮色穿行中,寒意袭来,“我”触到了死亡的冰冷。就在这时,马车停在了一座从没见过的房子前,一处奇特静谧的令人神往的安息之地,而不是阴森恐怖的地狱之门。“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A Swelling of the Ground/The Roof was scarcely visible-/The Cornice-in the Ground-”马车的停顿带来了思想的顿悟。死亡是一种未来之境,它超出了此刻当下。时间的冰冷的刻度已经失却了意义。对于死亡而言,几个世纪等同于一天。在死亡的坟墓空间里人类获得了时间上的永恒与躯体的永生。个体线性时间而言的终结只不过是这宇宙时间暂停的音符而已。“Since then- ’tis Centuries-and yet/Feels shorter than the Day/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Heads/Were toward Eternity-”这首诗与其说是写死亡的历程倒不如说是对于永生的获得过程。
人类出生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有限生命的个体方式存在着。死亡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人类无从体验死亡的深沉,但对于死亡的恐惧与生俱来。人们试图挣脱个体时间的束缚阻止青春流逝、岁月匆忙。他们渴求着超越时间获得一种时间上的永恒,并将这种渴望外化为岩画与教堂却依然无法回避死亡。人类如西西弗斯那样倔强地抗衡着生命沙漏流沙。就这样,生命的意义联系着时间形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既是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艾米莉·狄金森在结尾之处的“永恒”呼应文章开头处的与“我”同行的“永生”,以期借助语言来突破生与死的决然界限。生命在空间形态上的生成与毁灭表现了时间飘忽不定的足迹。死亡与时间同一却恰恰展现了生命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地延续,在生命的感知中时间不再沦为钟表上的冰冷刻度。
在《钟停下来了》[4]这首诗中,狄金森通过让钟表中的小人“puppet”的不能继续他的鞠躬“bowing”来喻指一个人的死亡凝聚在钟表的刻盘上。人的生命的有限通过指针的停止而得以表现。“A Clock stopped-/Not the Mantel’s-/Geneva’s farthest skill/Can’t put the puppet bowing-/That just now dangled still-”这个时候的钟表盘是一团糟。“An awe came on the Trinket!/The Figures hunched,with pain-/The quivered out of Decimals-/Into Degreeless Noon-”谁也不能拯救这个垂死的小人,医生不能,钟表商人也不能。“It will not stir for Doctors-/This Pendulum of snow-/This Shopman importunes it-/While coolconcernless No-”对于“puppet”的死去的反应只有一种漠不关己的冷淡。然而在人类长达几十年的与时间的不可调和的傲慢对立就体现在了这里。“Nods from the Gilded pointers-/Nods from the Seconds slim-/Decades of Arrogance between/The Dial life-/And Him-”因为,在指针的滴答声中,秒针的行走缩短了人与客观时间的差距,人永远无法真正实现对于时间的傲视。
人走到了终点,而时间却依然继续。在“Crumbling is not an instant’s Act”,通过描述人在时间中的衰变过程,表达了时间于人的消磨。“Crumbling is not an instant’s Act/A fundamental pause/Dilapidation’s processes/Are organized Decays./’Tis first a Cobweb on the Soul/A Cuticle of Dust/A Borer in the Axis/An Element Rust-”崩溃坍塌的只是一时的表象,诗人通过类比蜘蛛结网、门轴生锈来喻指其过程是一个“有组织的” 的 “腐败”。 “Ruin is formal-Devil’s work/Consecutive and slow-/Fail in an instant,no man did/Slipping-is Crash’s law.”这种毁灭的过程无形中销毁了人,而人对此却不曾察觉,只有在最终才意识到堕落的规律是时间的“渐变”累积。在科林斯·斯多科的《艾米莉·狄金森与现代意识》这本书中曾提到:
Time for Emily Dickinson is not qualitative historic time,but the timeless time of the mechanized celestial system and of the social-historic systems conceived as endlessly repetitive like the repetitive production process of our system,Time as measured mathematically by the clock and calendar.[5]
他认为在艾米莉·狄金森的时间观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意识到的时间是应用钟表和日历来量化了的时间,而时间作为宇宙系统中的一员却只能是无时间的时间。这种时间会以一种重复的形式循环出现。这种时间观直接影响到了她在死亡诗歌中对于死亡与时间的理解。在《七月的回答》[4]这首诗中,狄金森以祈使句开头,对七月拟人化,希冀从它能得到时间存在的答案。“Answer July-/Where is the Bee-/Where is the Blush-/Where is the Hay?”然而七月并没有作答。作者引入了五月,可结果就像是水中捞月一样没有任何的回应。在诗歌的结尾处只有“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一切都在 “此处”。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诗人通过摘取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来勾勒出了一年的四季,比如:“Bee”,“Hay”,和 “Blush”—夏,“Seed”和 “Bud”—春 , “Snow”, “Bells” 和 “Jay”—冬 ,“Maize”,“Haze” 和“Bur”—秋。
Answer July-
Where is the Bee-
Where is the Blush-
Where is the Hay?
Ah,said July-
Where is the Seed-
Where is the Bud-
Where is the May-
Answer Thee-Me-
Nay-said the May-
Show me the Snow-
Show me the Bells-
Show me the Jay!
Quibbled the Jay-
Where be the Maize-
Where be the Haze-
Where be the Bur?
Here-said the Year-
四季就像在玩小孩捉迷藏一样彼此寻找着对方。“年”的一句回答“就在这儿”回答了一切的问题。生命在四季中更迭变化着,而“年”就像是一个看客,坐看庭前花开花落,细品人生百味。“年”的岿然不动证明了时间的强大与稳固,生命在时间看来只是一出接一出戏的上演而已。时间与生命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那么死亡与时间又是怎样的一层关系?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诗歌伊始,作为刚出生的“我”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意志和最充分的自我完善的时间,“我”才能与“永生”和“死神”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即时间的渐变打磨,“我”渐入暮年,来到象征坟墓的“房子”前,我此时才意识到了“永恒”是整个行程的终点。由时间的渐变到命运主题突转的创作手法多次出现在她的诗歌创作中,反映了作者思想的累积变化的过程和作者更看重的是生的过程,对她而言死亡只是人生交响乐曲中的一个休止符而已。
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死而生才能获得一种生命的真谛。不惧死者才能获得真正的新生。死亡在她看来只是人存在的另一种形式。借助于死亡这一个形式获得一种超脱,这种超脱是对个体线性时间的超脱。将时间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受个体时间的约束。对于死亡的肯定也就肯定了永生,而获得了时间上的永恒。然而死亡是横在每个人头上的德谟克利之剑,任何人都无法预知死后的事情。“生命中最确定的事实是我们都会死亡,最不确定的事实,死亡何时降临。”这句古老的拉丁谚语提出了一个摆在人类面前永恒的时间与死亡的问题。死亡的无处不在需要人们直接去面对。正是这样的一种无知才能让人对于死亡会有那么多的恐惧。人在时间的衰变中褪去了生的鲜活色彩。
三、艾米莉·狄金森的超越生死的时间之旅的本质
艾米莉·狄金森本人对死亡与时间的二律背反持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她困顿于个体时间的注定消亡的事实,另一方面她又执拗于个体时间能通过一种死亡的模式而获得的时间上的永恒,让个体线性时间溶于宇宙无限循环的时间体系中。生命在时间的钟摆中摇摆着合为一体。一方面,诗人可以像约翰·多恩那样豪迈地对死神说出 “死神你莫骄傲”:“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天,死神你将死去,而我将获得永生。”另一方面,虽然诗人自由的心灵之鸟可以翱翔于天地之间,而同时又受缚于无法规避的必死的地心重力和人类有限的视阈。那么诗人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触摸这宇宙”。这恰恰是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技巧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即从不给其诗歌一个确定的结尾,而是总醉心于诗歌意义的含混性。狄金森选择的是不选择,在不选择的含混中包容了意义的无限可能性。
她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原本就在于她所探求论题的问题性。正是生死这个不可简化的问题把人类对自身的质疑蕴藏在最深处,通过这种置疑建构着思考的和谐性。思考的人向自己提出各种问题,自己回答的过程也就是自己理解的过程。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把各种材料联系起来。这一行为增长并发挥了自己的判断力。人生之两极生存与死亡,恰如上下、左右一样,都只有通过对方才能获得其规定性,获得其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没有生,根本就无所谓死,死亡的意义和价值就根本无所依托,无从实现;另一方面,离开了死,人生的整体性和有限性就无从体认,人的超越人生有限性、追求无限或永恒的热情也就无从激发,甚至人生意义或价值的大小也无以评判。
生死与时间的对立统一使得狄金森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她只有借助作为有限无限的超越性中介——艺术来完成对从有限的彼岸到无限彼岸的追求。死亡是有限生命的自我意识。死亡是生命的终了。然而,从生命的深层意义来看,死亡就不是单纯的中介,同时也是意义的完成。如果生命的目的是在实践与完成个人的使命,若一旦掌握或领悟到天命的意义,则即使面临死亡,也无所畏惧。
《论语》曾有言“未知生,焉知死”,也许用在狄金森这就是“未知死,焉知生”。死亡是人生所有不可能中的唯一可能,人必是要面对。虽然死亡是个伤感的主题,但只要勇敢地去直视面对,死亡并不可怕。永恒的获得不是通过不死,而是以无限的追求超越无限,达到永恒。生命的意义不在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意义的充盈。死亡的清明消解了生命的幽暗。人类永恒的生命力在人生诗意化中那些忘我陶醉的瞬间。突破永恒,突破死亡,这也许才是艾米莉·狄金森超越生死的时间之旅的要旨所在。
[1]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伯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王岳川.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4]Emily Dickinson.The Complete Poems of Emily Di ckinson[M].New York:Back Bay Book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1.
[5]Kenneth Stocks.Emily Dickinson and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A Poet of Our Time[M].New York:St.Martin’s,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