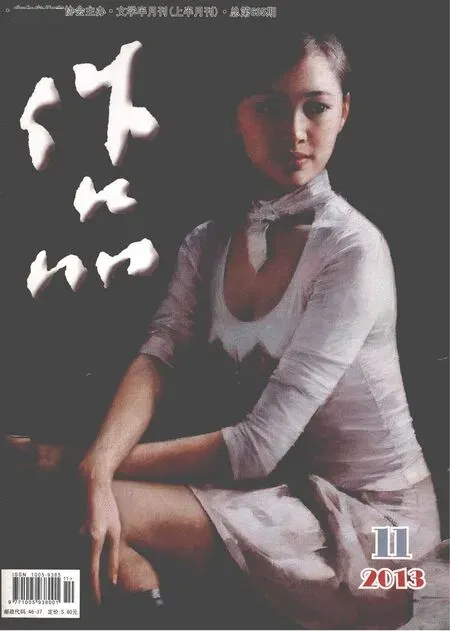山色三分
2013-12-04陈元武
☉陈元武
一 水墨山色


僧人避世远尘,多选择山水佳胜静僻处筑庐,结木为寺,依山伴石,林泉幽幽,清风明月,鸟鸣喈喈,风雷雨电,坎款镗嗒,音声幽缈之外,是内心强大的道场。静得乐,闲得趣。僧人远尘嚣,多赖于山水之妙境。怡心悦性,陶然自适。这仿佛僧家禅里的“静月可侣,清风为伴“的大圆满的境界,禅师也不喜欢在市井里混迹,因为市井五颜六色,六意濡染,难免让机心偏颇,容易走火入魔。可见静修何其难,持一种心静平和的状态何其难哉,只能远诱惑。山水无心,故得永恒,当年比干被纣王剖心,求于菜贩:菜头(萝卜)无心可活否?菜贩答:菜头无心则烂,比干再问:那人无心则何?菜贩答:人无心必死,比干就死了。人有心,因此难逃轮回之苦,山水无心,故无忧乐欢忭,山水不老,人生易老。原来有心与无心,就是这么大的区别。只是不知道,那层层变化的山色水光,那时时不同的山色风景,是何因缘?佛家讲的凡事必有因缘,水墨山色,可是某种因缘所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思返。看来,还是随缘而起,随缘而灭。像春夏山色,像雾岚之来去。
二 山色随心



山水南北有分,就是南方,山水也不尽相同,江浙山水,多婉约隽秀,秀的是神韵,是风采,是文人式的山水,而巴蜀和闽省,山高路险,峰岭连绵,往往令人畏其险途。这样的山水是奇瑰而大气的,是浑朴纯然的美,说不上山何其婉约秀美,除了闽北武夷山风景外,多数的山是谈不上绝佳风景的,但这样的山仍然呈现一种大气而浑朴的美境,雾岚,烟霞和丛林,乱石耸峙,如戟指天,或者如老僧般浑然不动,如磐石。石多是浑圆而质朴的,说不上其色璨然,质朴而绵久,不知春秋,无论魏晋,是玄武岩,是久远的地质奇观。闽西和闽北偶有喀斯特地质,石灰岩造就万千的山色风景。石灰岩是贫瘠的山岩,其上几不长大树,偶有短树亭亭,郁郁成林,远观近睹,皆有风姿。松树长在这样的山上,也变得极有风雅气度。闽省特有的金钱松和华南松,让这些山具有无限的韵味。像山水画里的风物,像大师笔调的树,狂劲,奇崛,优雅,古典。弘一法师在闽时,游历了诸多名胜,曾在永安城外崇胜寺驻锡,寺后就是一片孤岩,岩上有若干秀雅的松,像天然的盆景,美无可名。至今该寺仍有弘一笔迹,像片云挂松,像皎月临空。寺外楹联上,弘一法师娟秀的字迹:片石寸松晨昏雨霁春风秋月无非般若,清声雅唱钟鼓罄钹鸟鸣竹喧急瀑浅湍莫非菩提。法师是即心见性的高僧,身外物皆心外物,随心而生,万般风花雪月,或者随心而灭,雷电霜雪。一杆风幡在飘动,是心呢,是幡呢?谁在动?
三 山色三分


世界经典插图选登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的插图。


凡画山水:平夷顶尖者颠,峭峻相连者岭,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悬石者岩,形圆者峦,路通者川。两山夹道名为壑也,两山夹水名为涧也,似岭而高者名为陵也,极目而平者名为坂也。——依此者粗知山水之彷佛也。
观者先看气象,后辨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多则乱,少则慢,不多不少,要分远近。远山不得连近山,远水不得连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断岸坂堤,小桥可贵,有路处则林木,岸绝处则古渡,水断处则烟树,水阔处则征帆,林密处则居舍。临岩古木,根断而缠藤;临流石岸,欹奇而水痕。”
这些画论皆强调一个多层次的画面,山水灵动,不能刻板,重复,山形水流,都是因时因势而变的,山水不需要设色,其形态自然曼妙,无需刻意为之,画面的布设,追求层次感,丰富感和变化无穷的意象。山色三分,两分是随心,不,是三分随心。王维强调的是意在笔先,运筹帷幄之间,山水存于胸臆之内,山水绝胜,妙笔得之。回过头来,看范宽的画,其画无不精确壮观,尽符法度。山水之色,何止三分,繁冗之表,是他严苛的艺术追求。在范宽的画里,山水是十分的。他的心性,他的追求,他的感悟,他的灵巧构思,他纯湛的画技,加上墨分五色,正好是十分之妙。如此宏制,后人叹为观止。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里则是呈现另一种风格,一分是禅,两分是悟,一分墨色,一分山水本分,一分则是天与机杼,是无法复制的过程。黄公望是近佛的人,他的内心里多的是禅和淡泊随缘的佛性,因此,机锋尽泯,不露声色地交待了他的内心世界——如此宏大,如此婉约,如此的宁静而悠远。
数分山色,其实山色何止十分?十人写山十人不同,山水是一种表象,是内心之外的一种存在,画因人而异,但山水仍然是山水,它永远在我们的纸笔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