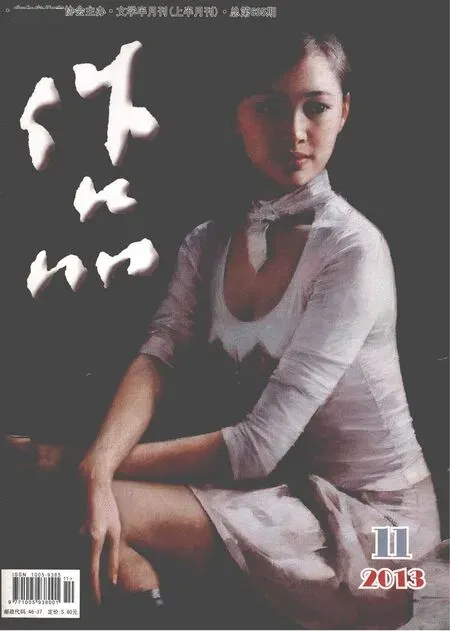省府大道
2013-11-15☉朱强
☉朱 强
在南方,我常常试图通过一些古老巷子去寻找某座城市的记忆。可是,当走进去,发觉两旁高墙壁立,兽形的门环把脸耷拉下来,潮湿的空气使墙垣发酵、滋长出层层暗苔。我左右拐弯数次,一无所获,在另一个巷口,被它用力吐出,孤零零的,结果被遣返回了闹市。在省府大道,我的经历却迥然有别,它处处像长有钩子似的,把我给勾住了,尽管它看上去腰围粗壮,身长笔直,像一根巨大的烟囱,可是它最终给予我的印象,却完全是一条迂回曲折的古巷。
省府大道上抵顺外门立交桥,西通广场,首尾相去千米。景德镇陶瓷店、省冶金设计院、金融大厦、省府大院、药栈、酒家、咖啡馆、学校、钢琴房、书店……它们像两排精美的篱笆,将这条路的天空隔成了一个长条形状。《清明上河图》里也有一条类似的街,不同的是那条街的两侧——拥挤的都是些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这些屋宇房梁斗拱粗实巨大,低矮,贴近地面,士绅、官吏、行脚僧人还有挑夫们在街上摩肩接踵,呼朋引伴,勾心斗角,吐痰,吆喝,衣裳……市声嗡嗡哼哼。所有一切,距离天空都很遥远。
省府大道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每晚我在社里看书到深夜,有时因为看书而错过最末的一趟班车,无奈之下,等待我的便是十几里的夜路。夜晚的大道看上去十分静美,它眼神清澈,使我思想里飞舞尘埃得到安静。恰当此时,白天路上各种喇叭里的噪声被夜晚埋葬,天空被水流洗得格外透亮。时间过了夜晚十点,白天大街上奔跑的车辆也消失了,夜色中,某个咖啡店身材看上去十分高挑,气质与平常迥然不同:整面墙窗口里的灯发出亮光,光线昏浊,饱满,像一些习惯熬夜的眼睛,布满血丝。
夜晚是不适于充分暴露自己的,想起各种潜在威胁,赶忙加快脚步,走出那片明亮。前方有三五个小木屋,从两边的建筑物群中凸出来。看招牌是一些服饰店,意境很美,夜晚走在空街,这个细节会让人的脚步不自主地放慢;几个门面漆成青灰色,干净,素雅,旁边有一株榆树,它白天为这几个小店撑起一片阴凉,晚间就和附近的路灯形成一些碎碎的光影。最难得的是,在几个小木屋背后没有高楼,适合望月。
这些年,建筑物在南昌不断长高,它们把省府大道围剿成一个狭长形的天井,唯独在这个缺口,才让行人们的眼睛与月亮有机会接触。我每晚从此缺口路过,那一刻,天空的颜色、树的剪影、咖啡厅窗子里的灯,所有事物的温度融入双眼,让我觉得天空的这一枚月,就是四百年前天瓦庵的那个月亮了。
说到天瓦庵的那个月亮,时间要回溯到明天启七年四月。绍兴府里的张岱在天瓦庵读书,某天,和朋友在山里面看落日,这时候,朋友向他建议何不在山中望月。他觉得这般甚是风雅,于是大家都在山中逗留,不久,天上捧出一张玉盘,草木光怪,山体呈白色。可是他们没走几步,就听见半山传来呼呼喊叫,后来得知,是仆人和山僧摸夜路找来了。大家很担心张岱在半路上遇虎,手上都持着火燎,刀鞘与木棍,以防不测。这一闹腾,让山下的村民以为是盗匪成群结队地从岭上经过,因此都屏住呼吸,假装熟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个事件按理说与省府大道的月亮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即便疯子也知道,这两个月亮相距遥远,怎么可能扯到一块?现在它们扯上关系,是因为在我的个人阅读史中,存有某段难忘的经历,05年春天,我对于张岱的喜欢发展到掏心挖肺。比如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无所事事,我便捧书在怀,翻来覆去。幸好现在的书既不用线装,更不用韦编,统统都改用胶装了,不然三绝九绝都有可能。我喜欢张岱并不因为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而是他所描绘的环境恰好满足了当时我的某种心理需要,当时我身上有着很重的雅癖,这直接导致我在现实里凡是见到任何一种自然风物都会不由自主地与张岱的文字扯上关系。因此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月亮,来自于天启七年的这一幕很自然就会爬上眼帘,根本没有办法抹掉。说起来,文字就这样匪夷所思,它时常把一些躲藏在时间暗角里的故事一把给拉出来,让面前一个简单的事物意义变得极其丰富。同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常常对我的联想进行垄断,甚至于施加暴力,当我看到风花雪月,美人,天空,飞鸟,苔痕,酒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魔球把我的思想吸引过去,不自然地情绪将朝着某一个方向靠近。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惯性。
另一个细节的展开在新公园路口站台。这儿至少聚集了数十个趟次的班车,月台背后有条小路,顺着这条路直走,可以看到人民公园的后门。月台旁侧的一个花坛,整天有穿着制服的工人在里面服侍花草,所以这些花草生长得十分肥厚。竹篾在外围支了个一尺多高的篱笆,再外围还有一圈长条形的青石,供人坐憩。槐树在这里一手遮天。枝干扭曲着,向上,向前后四方伸长着。它有时从街店的屋檐笔直穿过去。
我时常乔装成在那里等人,坐在石头上剥指甲,如此便不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事实上也没有谁会注意我。退一步说,哪怕当时就是有人对我的行为产生了兴趣,他们短暂的兴趣对我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足为道的。因为当时所有打量过我的人,在我的这一生当中,我们之间很可能仅仅是一面之缘。譬如我那天看到一个女疯子在街上挥动一件外衣,胸前挂着两枚下垂干瘪的乳房。她自己一直在对着过路人傻笑,没有人知道她傻笑的内容。过路人看着她的这番举措也止不住发笑,他们的笑内容是明确的,尽管当时这个画面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但此印象很快就会被记忆里别的类似的场景给覆盖掉。
生活中当你觉得别人很在意你,往往是因为你太在意自己。当你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别人身上,你自己脸上便不自然地产生了害羞,愧疚与难堪,这些表情就像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个精致的游戏。许多的人活着,没必要在乎别人怎样看你,即便别人在意你,那个所谓的在乎,也是你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就像你在街上行走,那些或红润,或枯槁,或青涩,或暮气的脸。你一边走,一边就在遗忘,即使记住,你和他,他和你,也很难说再见。
另外,在新公园路口,还可以看到一些拉客的摩的,它们样子很像一些瘦马。的哥的两条黑腿跨在上面,这些身材粗大的男人之间彼此很少讲话,脚上挂着两个大拖鞋,松松垮垮,粗而结实的胳膊,竖起坚硬的毛发。各自默不作声吸烟,一个上午就在彼此冷冰冰的对抗中度过。当然对于这个月台来说,主角并非他们,没有谁敢拍着自己的胸脯说,自己是这个月台的主角。街头任何一张面孔都可能被倏然出现的几十张面孔冲到很远的地方去,挎竹篮的,持伞的,抱书的,挑担的,推大板车的,他们拥挤着,偶尔遇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互相停下来寒暄两句,然后又被人流冲散。太阳从槐树叶交错的缝隙中筛下来,有一个背景走过去,一条亮斑在他身上急速上升。
现在一条街道的气质往往让你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过去我们可以直接称呼一条街为米街,柴街,纸巷,张家巷,李家胡同。这种街巷拥有着大量重复的门店。他们的表现形式十分单一。你可以通过第一家店铺的模样推想出任何一家。但目前这个街道却更像是一首变奏曲。其中某一段路上——并列着各种行业的研究所,勘察院,设计院,高大而冷酷的大理石门楼让你感觉到里面的空气神秘兮兮的。你几乎看不见有人从里面走出来。偶尔出入的,也是一些黑得发亮的轿车。这些门楼看样子像一排巨大的黑洞,这些黑洞因为它太大了,太显眼了,行人对于它有足够高的警惕,它没法将行人给卷进去。马路的对面同样是这样一些高大而结实的大理石门楼。他们相对起来就没有这么阴森了。相反,让人觉得很热闹。在那儿所上演的一场场热闹剧中,你看到的却是一种极端的严肃。那儿有穿军绿色服装的警卫持枪把守,这些绿军装像一棵棵常年落地在那儿的树。偶尔会簇拥过来一些民众,他们拉扯着很大的标语,主题鲜明。这个标语像古代衙门口的一面很大的皮鼓。这些人尽管很冷静地围坐在那,但鸣鼓的声音却往往惊动四方。江西人好讼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那时候走在街上,时常可以看见村夫野老、走卒、贩丁将一支笔插在耳背或脑后的发髻上,他们这样做倒并不是要彰显肚皮里有多少墨水,他们带笔是为了方便诉讼,出门若碰到件什么纠葛麻烦,立马就能拔笔写成状子,递交官府。这样一些被士大夫们睥之为“珥笔”、“簪笔”的斗筲之民很让官府里的老爷们头痛。从这里面可以知道,江西人极其希望有一个能够主持公道的声音。他们一方面是属于易屈服的那种,通俗地讲便是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又确实不容易屈服,他们渴望有那样一个高高在上的王——能够站出来说句公道的话。尽管有时候这个王所说的公道话也是不公道的。但他们觉得王的位置毕竟在上,相对污吏来讲它的评断当然是更为准确。所以即使被统治,也觉得有一种在替自己说话的优越感。
同样是这条路上,靠近师大的那个地段含义就远没有这么深奥了,它看上去更像是一条街。街的状态完全是松弛的,敞开的,像一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自由走动的女人。使你对她有一种无法抑制住的欲望。每一个商店都要把你的视线给抓过去。脚步也感觉到它强大的牵引力。琴房,书店,洗头房,食品铺子,小吃面馆,在这个位置上——行人摩肩接踵。根本没有花草、植物立脚的份。它像一个巨大的操场,从早到晚一直骚动着,始终无法安静下来。要说这里之所以成为一片街区是因为在这里恰好有一个高等学府。所有的这些热闹都是从这个学府里输出的。它像一个强大的核,许许多多的事物你说是追随它也好,寄生在它的身上也好,总之它凝聚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让这条大道在这个位置凸显出一种特有的气质。一条马路往往是依靠这样的几个核而展开的。那些商店随着这些核的兴盛而兴盛,衰亡而衰亡。在一家医院的附近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街的两侧花店与水果店、药房鳞次栉比的样子。而要是在火车站门口,地方特产店一定是铺天盖地的存在着。当初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聚集在这里,有时候因为年代太久了,那个使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早已经不在了。但这条街的形象却已经被嵌入这个城市居民的头脑里。譬如买皮鞋就应该去那条街上瞧瞧。
城市就像一所房子,开始几根孤零零的柱子竖立起来。然后再有木板、泥巴墙、檩条、砖瓦参与进来,不断地对它的表情进行完善,使它拥有一副属于自己的面孔。最终,它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的表情也异常丰富,要记住这副面孔,反而十分困难了。可是,它毕竟是由人建造的,要改变它的面孔,往往决定于某些人的一个闪念。现在我已经很少走省府大道了,因为地铁施工的缘故,一些几十年的大树被砍断手脚,连根拔起,移栽别处。大道两旁的绿色被一概抹去,街道变得明亮起来,像有一扇天窗被打开。公交改道,某些地段被封死,店面转让关门,原先的那副面孔一下子便陌生起来;让人觉得城市就像一个积木游戏,建造与拆毁,都在一念之间,有时,游戏索性就不玩了,转眼之间,那儿就成了一条荒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