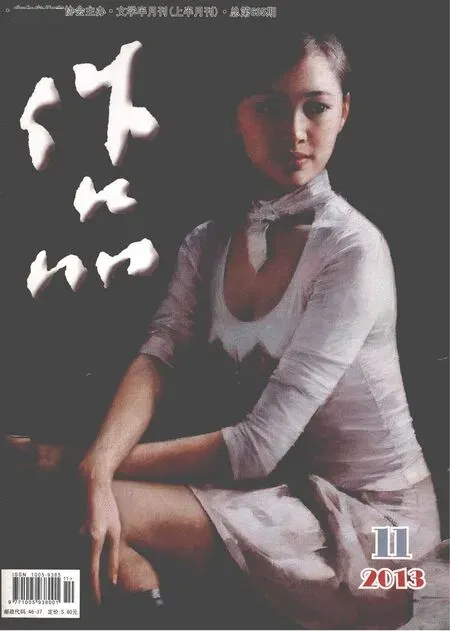月亮所照之处
2013-11-15◎颜语
◎颜 语
一个化着浓妆的小丑从幕布后伸出头来,转一圈眼珠,耸耸红色的圆鼻子,又缩回幕布后去。暗红色的幕布一阵掠动,静下来后,幕布终于又撩起一角,刚才那个戴黄色假发的小丑大踏步走出来,聚光灯马上跟来。他咳嗽一声,拽一下衣领。面对满场观众,他似乎怔住了,吞一下口水,飞快地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他的同伴并没有跟着出场。他朝身后使劲招手,面对观众笑了起来,那诡异的红色大嘴唇边像生出了两只钩子。过了半晌,他又回头看,着急地把幕布拉开一条缝,伸进头去。然后另一个戴着绿色假发的小丑,扭扭捏捏地走出来。他们俩都穿着花花绿绿的上衣,红黄色相间的裤子又肥又长。绿色假发的小丑踩着自己的裤脚,差点儿向前扑倒,他双手提着裤子,向前迈了几步,又分出另一只手来扶住他的假发,一步步向他的同伴靠过去。
“就是他!我认得他,那个绿色头发的小丑。”小女孩兴奋地喊,一边又拍着坐在她旁边的男孩的腿。他们坐在观众席的第六排。
“所有的小丑都一个样。”男孩莫霖说。
“就是他!我说过我有预知能力。”
“你已经说过九十九次了。”
莎莎努了努嘴,继续说:“我梦见那个小丑鼻子上开出了一朵鲜红色的玫瑰,那朵花不断长大,攀上他的头顶,然后突然变成一团火,大火发起怒来,要烧毁小丑,它把小丑团团裹住,小丑就把火团撕开一道裂缝,从里面走出来。我梦见大火!你必须相信我。”
“噢!这里没有人不相信你,因为今晚的压轴表演就是喷火。”男孩装出怪异的笑容,像木偶似的机械地左右摆动头部。
两个小丑叽里呱啦对讲了一遍台词,背书似的一板一眼。紧接着,就有一头关在铁笼里的狮子被推上舞台,它还懒懒地躺在牢笼里,连眼皮也懒得睁开来。工作人员退场后,足足有半分钟,驯兽师才走进舞台,挥舞着手中的鞭子。追光灯打在他身上,衣服上的纽扣反着刺眼的光。
驯兽师用鞭子甩了一下铁笼,那野兽嚯地跳起来,在牢笼里转圈,它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配合一点,在人群前装出凶猛的样子来。它像打哈欠似的吼叫了一声,场内开始有部分人兴奋地喊叫起来。驯兽师又甩了一鞭子,它不耐烦地又吼了一遍,稍微用了一点劲。它早已习惯了自己的一声吼叫,便会引起一大片观众的热烈回应。对此,这已经再也不能引起它的自豪感了。驯兽师打开牢笼,它扭着屁股慢吞吞走出来,场内开始有观众议论:“它的脚瘸了!”事实上,它并不喜欢干跳火圈这项工作,骨头老了没劲,跳得低一点,偏一点,便会把自己引以为傲的胡须也烧掉。等到老狮子表演完毫无惊喜的跳火圈,再次懒懒地扭着屁股钻进它的牢笼时,观众席已经淹没于一片唏嘘声之中。有的人嚷道:“退票!退票!骗子!”
驯兽师和他的野兽退出舞台,得不到半点掌声。那两个小丑又提着裤子上场来,叽里呱啦一遍。随后请出了魔术师和他的一群助手。
助手们忙着布置道具,魔术师这边说:“你们听我说,今晚我将会表演最高难度的魔术,一切都因为你们而精彩!你们听我解释,我将会把我的助手……”他伸开手介绍他左边正忙着和其他人一起推大车的胖子。那胖子听到之后,挥了一下手,然后又咬着下嘴唇使劲推车,眼睛都快挤成一条线,脸憋得像一只压扁的红皮球。
“塞进一只箱子,然后我会用一把刀,把箱子对半切开。”他又指了一下他脚边的那只横躺着的黑色箱子,大约有一人高,一臂宽。
“他根本就不在那只箱子里,他不是进那个我们看到的箱子,而是另一只,那是障眼法!”底下有观众大声揭露。
“你们听我解释……不是那样的,你们听我解释,这里只有一只箱子。”魔术师结结巴巴地说。
“照我说,今晚最他妈神奇的表演,就是那个死肥佬竟然可以被塞进那只小黑箱!”有人嚷道,黑暗之中不知声音出自何处,像是从播音器里窜出来的。观众像被点燃似的,哄笑开来。
“不是那样的,你们要是不相信,就上来,我把你塞进箱里。”魔术师恼怒起来。
“我他妈就蠢到等你切死吗?”声音来自另一个方向。
“什么鬼表演,一个劲儿解释来解释去的!”
莎莎咯咯大笑,露出她的那两颗小兔牙。莫霖紧捂着耳朵。他想起今早,阿姨一边用筷子敲着饭碗,一边严厉地质问他:“你不会想去看马戏团表演吧?”
男孩低头沉默地扒着早餐。
事实上,男孩并不是十分情愿到这里看猴子啊狮子啊什么的跳来蹦去。那是昨天晚上,莎莎说:“我看见你拿了剪刀,你剪了我家的电话线。我还知道你偷了夏叔叔杂货铺里的火柴盒,你每次去都会偷一些小东西。你把偷的东西都藏在一只鞋盒里。”她盯着他看了一会,然后挑起一边眉毛,视线傲慢地越过他的肩膀,看向他背后的杂物架。
莫霖紧闭着嘴,瞪大眼睛,后退一步,又眯起眼睛,重新审视他的小表妹。
男孩推开夜晚的窗户。沿着月光的指引,越过重重低矮的民居、连绵起伏的黑影般的山脉,他们看到远处马戏团搭建的帐篷尖顶高高耸立,直刺向夜晚的心脏,像一声有力的不可违背的号召。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闪烁着,流动着,像织在小镇上的一条条血管,不断地输送有毒的血液。偶尔会听到空气中飘过来的乐声,呜呜咽咽的“啦啦……啦啦啦……啦……”声音在往下坠落,坠落……沉下去就无影无踪了。夜空中层云浮动,暂时遮蔽了月光,帐篷从视线里隐去,只看到各种小灯光伏在阔大无边的夜空底下。浮云游去,柔和的银白色月光重新洒向大地,又见到那帐篷鬼影般蓦地出现。
这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表演团愿意到这么个闭塞的小镇出演。马戏团来到此地的三天前,也就是上周三,男孩莫霖才从大城市回到帕洛小镇。他背着一只灰色的肮脏破旧的小包袱,爬山涉水,循着记忆中的地图,找到阿姨家,在清晨敲开了她家的黑色铁门。这是他的出生之地,尽管他不愿意承认小镇对他的重要性,但这是他生命开始的地方,他的灵魂之地,他的梦回之地。不管出发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走着走着,便回到这里。
他推开一扇扇门,一扇扇窗,都似乎见到昨日遗留的痕迹,它们似乎在等着他回来检阅。一切如昨日重现。时间只是这么轻轻地翻过去,他却已然九岁。
四岁半之前,男孩一直在这个小镇上与阿姨一起住。四岁半的某一天,一个从大城市里来的女人,自称是男孩的母亲,连哄带骗、软硬兼施地把男孩带到城市里去。男孩见到崭新的家,崭新的卧房,崭新的一切,然而却没有哪一样让他感到亲切。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该来到那个地方。
那儿有一个与他同样大的女孩,莫莉,长得跟他有点相像,衣着光鲜,但神情疏陌,甚至是冷淡。大人们让他称她为姐姐,事实上,他们是双胞胎,她只是比他早半个小时来到这个世界。他与姐姐一起生活的几年,彼此之间说过的话可以全写在一张白纸上,不外乎是:“爸爸(妈妈)找你,叫你快去。”或者“他们说不用等他们回来吃晚饭了。”再或者一句冷冰冰的:“我不知道。”
一个叫“爸爸”的男人,偶尔会带他出去散步,给他介绍地球上地域面积最大的三大国家,那是男孩第一次打开对世界的思索之门。他们会给他过六一儿童节,但在男孩吃坏了肚子,发高烧的时候,却让他在床上躺着,独自与病魔战斗。甚至有时候会任由男孩一个人蹲在阳台上哭泣,哭过一整夜。在那里,男孩获得的一切都是不稳定的,包括爱与亲情。
他重新把注意力投向舞台。那两个小丑慌慌张张走下去,随后,表演喷火特技的人姗姗出场。那特技员穿一袭镶嵌着银片的深紫色天鹅绒长袍,拖到地面上,像是用窗帘匆忙改制的。他向观众深深一鞠躬,举高两手又放下来,暂时稳定了观众的不满情绪。那些嚷着退票的观众也不得不坐了下来。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将会倾尽全力为你们带来今晚最精彩最难忘的表演!”他向观众做出几个夸张的手势,两只手挥舞着,“等一会儿,你们就会亲眼看见,大火从我的口里喷出来。”
他等场内安静下来之后,示意助手走过来。那助手拿着一根烧得旺盛的火棍,在旁边候着。他举起袖子,快速地掠过面前,那助手把火凑到他嘴前。他张开嘴,停了一会儿。
一束小火——比预料中要小得可怜,从特技员的口里喷出来,像一条刚孵化出来的小蛇,蠕动一下,便一命呜呼。场内喝倒彩一片。他闭上嘴,高举手臂,放下来,示意观众安静下来。
“好戏在后头。”他说。然后故技重施。这一次,他张大嘴,过了整整一分钟,都没见到有一丝火星从他嘴里喷出来。场内再次涌起不满情绪。
“好戏在后头!”他开始有点着急了,干脆把暗藏在袖子里的塑料罐掏出来,猛地喝下一口里面的淡黄色透明液体。倒是前排有观众先火了起来,辱骂着爬上舞台,挥着老拳向他蹬过去。台下的观众也壮起胆,接着又有两个,三个……十多个人爬了上去,趁机捣乱。
特技员和他的助手被吓得逼到角落,圆睁着两双可怜兮兮的眼睛,跌倒在地上,气势立刻矮了一截。助手大嚷着把他手里的火把扔向暴怒的观众,特技员哇的一声哭出来,这一次,火舌像一条忍无可忍的猛龙,飞窜出来,爬上那块挂在侧面的暗红色幕布。
很快,在台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这条饥饿的龙已经吞掉了大半边幕布,它从一条繁衍出两条、三条……连成一窝,它们张着血盆大口,噬咬着整块帷幕。顶上的木架燃烧起来,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嚯地烧断了一根木条,狠砸下来,在人们的脚前摔成两截。这时,人们才被吓醒过来,四处逃散。
台下的观众涌动起来。往下望去,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像暴风雨中黑暗的海洋,呼啸,翻滚,此起彼伏。
那个喷火特技员早就逃得不见踪影。台上乱成一窝蜂,纷纷嚷着:“找水!快找水!”可吓得动不了腿的人仍然呆若木鸡地站着,动得了腿的人,喊着找水,跑出去就再没有见到有端着水回来的。
场内,呼喊声、尖叫声、哀嚎声、奔跑声、物体砸落声……如一支失去控制的交响乐团,纷纷自鸣自奏起来,撕裂着在场者的神经。而在这些疯狂的噪音之中,有一个安谧而沉稳的声音,如死神的笛声般悠扬地吹奏起来,那是火的嘶鸣声,由小变大,由轻变重,最后几乎压过了所有惊慌失措的声音。它是最冷静,最优雅的主宰者,它垂下眼睑,扬起嘴角,看着如蚁窝遭难般四处溃散的人们。
“我们快走吧!”莎莎说。
“不急。”莫霖说,他安稳地坐着,像是等着看一场真正盛大的表演上场。他的神情中有一种异常的镇静——与火对抗的镇静,他似乎在思索着、计算着如何漂亮地赢下这一盘棋。莎莎自己也不敢逃,重又坐下来。
他们后面四排的观众已走得所剩无几。人们把各条楼梯挤得水泄不通,嚷着,辱骂着,互相推搡着。惊慌使他们失去起码的理智,没有人愿意为守秩序而暂时放弃一丝逃生的机会。他们的脸上被火光映红,被愤怒与惊恐扭曲,他们的脸,无论男女老幼,都成了同样的一张脸。
黑色的潮水互相搏击与吞噬,黑色的恐惧越发激愤。张望过去,底下有两处地方陷落了下去,首先是一个人绊倒了,接着附近的人也跟着一个个绊倒,人踩人堆叠成一个谷。其中一个谷疏散了,而另一谷,蔓延开来,演变成一片河滩。
莎莎又央求道:“我们快逃吧!”
男孩沉默不语。
场里的观众走了大半时,大火已经完全攻陷了整个舞台,并且向最前的一排座椅发起进攻。它尝试着舔舐了一下塑胶座椅,然后迅速引领全军扑过来。空气中充斥着浓烈的刺鼻气味。
观众冲毁出三个逃生口,可其中一个刚被大火占领了,他们不得不放弃,绕道而逃,分散跑到另外两个逃生口去,或拥挤着从进来时的大门口出去,那里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人踩人事件,小山包似的尸体堵住了门口,只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然而大门外也一样的慌乱。
大火不但往四面烧窜,还野心勃勃地往大帐篷顶上烧去,对面的木架已被烧毁,帐篷倾斜了下去。
莎莎扯着莫霖的衣袖,呜咽道:“快逃吧!”
“坐下。”男孩面无表情地说,他语气僵硬,不容商量。
女孩试图走出座位,扶着烫热的楼梯铁栏杆,向下俯视,那里除了未燃烧的尸体,就是火的小兵小将,它们逐渐组织起来,清除那些已失去灵魂的俘虏。火的主力军已经包围了右侧最下面的三排座椅。
“你什么都有。”男孩说。
莎莎回过头来,试图听明白他说的话。
“你什么都有,所以你也什么都没有。”他的眼睛死死盯住大火的心脏,魂魄像是被诱惑去了。此刻,他想起那些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出现过的人们,可爱的和可憎的,那些可憎的人却不可理喻地占领了他的理智。他闭上眼睛,想起他是如何仓促地从大城市那地狱般的家庭里逃出来,坐夜车,翻山岭,涉水路,只为回到他的灵魂的归属之地。然而故乡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张开怀抱,在道路的尽头迎接他的归来。
他看见邻居那个胖太太,以高分贝音量笑着走进来,说:“我听说,你那孩子回来了?”
她冲进屋里,看见男孩缩在角落的沙发上,把自己圈成一团。
“嘿,你就是那个男孩!我认得你,我以前抱过你。你那时候还到我们家偷吃,以为别人看不见呢。你现在还是那么自以为是吗?我见过你姐姐,她和你完全两个样,她那么乖巧听话。”胖太太连珠带炮地问。男孩又把自己往角落缩去一点,瞪大眼睛,从下往上看着她。她俯下身来,凑近他,用一根胖得香蕉似的手指指着他的鼻子问:“你回来了,你妈妈怎么说的?她允许你回来的?”她满脸肥肉,沟壑与沟壑之间泛着油光,红色的血管清晰细致,白色的细毛根根竖立,蒜头鼻子耸动着,喷出的热气直扑向男孩的脸。男孩痛苦地看着她,眨巴着眼睛,似乎她要是再用手指指着他,他就要一口咬断那根该死的手指。
“姐姐的事不关我事。我的妈妈死了!”
“怎么说这样不吉利的话。没有妈妈的孩子是一条没人要的狗,污脏可怕,要流浪街头,还要饿肚子的。”
“那你是一头猪,一头死肥猪!”男孩尖叫着,双手挥舞,两腿乱踢。
胖太太嚯地板直身体,圆睁眼珠,那黑色的眼珠子慢慢向中间靠拢,活像一头被马蜂蜇了鼻子的猪。
“这孩子要不得!”她嚷道,“陈太太,你听听他说什么,你真该听听,这孩子简直太恶劣了。太可怕了!你怎么就不赶他走呢!”
男孩咚咚咚地跑上木楼梯,震得整栋屋子地震似的响,然后又蹑手蹑脚地走下半层,攀在楼梯转角处的栏杆上,从缝隙间往下看。
陈太太从厨房那头伸出头来,说:“哎……”然后她又压低声音说:“我赶他走他就无家可归了。他毕竟是我的孩子,他一生下来,我就抱他睡觉,抱他吃饭,他就像我的半个儿子。我怎么忍得下心来?私生子可怜呐可怜……”
“他姐姐和他完全两个样,双胞胎,性格却差个天跟地,她可温顺多了,我前年见过她一面。”
“那孩子也可怜,完全不敢见人,去哪里都躲,我抱她一下,她居然颤抖得厉害。我真不知道他们家是怎么回事,两个孩子都怪里怪气的。我常常跟我姐说,心情不好,不要拿孩子出气,孩子嘛,毕竟小,不懂事的。”
“那你打电话问过你二姐了吗?那男孩怎么自己跑了回来的?”
“我猜是我姐打了他一下吧,他就赌气离家出走了。”陈太太又压低声音道:“我打过电话了,我跟你说,那孩子竟然剪断了电话线。”她拉着胖太太往厨房的另一边走去。
烈火吞噬了前三排座椅,似乎觉得有点饱了,于是放慢速度吞吃第四排座椅,但仍然是毫不迟疑地逼近他们。
莎莎惊恐地望着莫霖,蓦地发现他比大火更恐怖。她哆嗦着转了一圈,发现他们附近的楼梯已完全被大火夺取了。不能从楼梯逃走。而距离他们最近的,还没有被大火占领的,就只剩下一条狭窄的斜坡,由栏杆和一排排座位形成的一条滑梯似的夹道。栏杆疏朗,左侧就是地下,倘若从那边滑下去,纵然是可以抵达地面,但六层楼梯高悬,一不小心,从左侧漏出去,便是粉身碎骨。她不敢滑下去,太陡了,她会死在半途的。她嚎哭着说:“带我走吧!我好怕!”
男孩用锋利的眼神扫视了她一下,很快又盯着大火看。莎莎怔了一下,噗通一声跪倒,用膝盖爬着回来,拽住男孩的裤脚,撕心裂肺地哭喊:“走啊……走啊!”
“你必须要尝一尝‘一无所有’的滋味,失去一切,然后你才会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重要的!”男孩盯着大火喃喃自语。
“我想要出去,求求你带我出去……”女孩已经哭哑了嗓子。
“我一无所有,但你什么都有。”男孩低语道,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来的声音,压抑,沉闷,沙哑。有一种黑暗的力量,在他心里,掀开了常年禁闭的盖子,伸展开它那无数条毛茸茸的黑色长腿,爬了出来。
“我求求你……”
火逼近了第五排座位,发现还有两个新鲜肉体在自己的包围之下,顿时精神大振。火的心脏,是一位神灵,他讥讽男孩的安于被困,又对他的安于被困感到可惜。渐渐这种可惜之感,激惹了他自己,他烧得越发旺盛与凶猛。
男孩看见炽焰之中,火光照映出自己的一张脸。黑暗的情绪像皱纹似的爬满他的脸颊和额头,使他变成一个九十岁的老头。他开始觉得自己全身冰冷,好像陷入了冬天的沼泽里,他越是挣扎,就越是往下陷落。他不禁颤抖了一下,像小狗似的蜷起身来。九岁本该是探索世界的年龄,可他的小世界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他把所有通往外面的门窗都关上了,里面纵起火来,他无处可逃。他目睹自己的世界一点点被大火吞噬。
火烧成一片刺眼耀目的光。男孩觉得那明亮的光是在严厉地拷问他。他用双臂抱紧自己。在这一个临界点上,他忽然明白,原来他多么喜欢那些令他焦灼、伤心、愉悦、欣喜的一切。他喜欢所有的这一切。第一次,他感到自己心里时常作怪的小顽童变得温和了。第一次,他的灵魂终于妥协地跟他站在一起,不再剧烈地抗争,不再使他处处难过。
男孩感到所有的都被推翻了,真正的“一无所有”,所有的,也许只是剩下来的生存本能。
人群仍未疏散开来,挤在远处看消防人员对帐篷遗骸的处理,它被烧成灰后又被大水浇得通透,灰烟弯弯扭扭地升上天空。
一位太太在乌泱泱的人群中搜寻,只要见到小孩,她就冲过去。
“我的孩子呢?在哪里?”她的喉咙因为喊得太多了,变得沙哑。陈太太抓到每一个人都要问,可又不像是问,自言自语。人群被这个疯了一样的胖女人冲出一条小道。她挤到废墟边上,脚一软便跪了下来。
“我的孩子哟,我的孩……”
她猛然看见一个男孩站在五步开外。正是莫霖。他左侧的头发被烧了一小片,此外,就是皮肤被熏黑了,像一个从煤坑里爬出来的穷孩子。他正死死盯着烧得焦黑的残余。在消防员赶来之前,大火已胜利烧毁了整个帐篷。
陈太太扑过去,抓起男孩瘦弱的肩膀猛烈摇晃。男孩的脑袋被摇得似乎快要掉下来,整个身体都在晃荡,像中了千万颗子弹。她急切地问:“莎莎呢?我的孩子呢?”
莫霖转过脸来,看见她,有一刹那他脸上露出一种释然和喜悦,然而很快就消失了,张开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他变得面无表情,像一张蜡制的脸。
“你说话呀!我的孩子呢?她是你的表妹啊!她是我亲生的孩子啊!”胖女人说着说着,就苦笑起来。
莫霖漠然地盯着她看。
“她在哪里?”陈太太呜呜咽咽起来。
“她是我的孩子……”
“她是我唯一的孩子!”
“我只有一个孩子哟!可怜我的心!”陈太太断断续续地说,腾地涌起一腔怒火。
“你这个踩心肝的!枉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丢下我的孩子不管!没良心,被狗吃……狼心狗肺!”陈太太抽泣着,抡起手臂想狠掴男孩一巴掌,顿了顿,又放下手来。她像个漏气的气球,坍了下去。
“没心肝……你这个……魔鬼……”胖女人趴在地上,蜷成一坨肥肉,此刻她浑身无力,像个苟延残喘的人。悲哀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此时,消防员从人群的另一边挤过来,大喊:“谁的孩子?”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她哭哭嗒嗒地揉着眼睛,指着地上的那个女人说:“妈妈!”
消防员弯下腰,一松开手,女孩就冲向那匍匐在地上的胖女人。胖女人怔了半晌,还没有反应过来。她以为自己死了。小女孩搂着她的脖子大哭。
男孩悄悄转身离开,从人群中挤出去。
到人群散了大半时,陈太太想起男孩不见了。她一边给女孩擦去脸上的烟灰,用五指梳理女孩凌乱的头发,一边嘴里嘟囔着。她仍然对男孩感到恼怒,越想越觉得道理在她的这一边。
陈太太站起来,给莎莎拍拍衣裙上的灰尘,又给自己拍一拍,牵起孩子的手,站到路边去。她想立刻带自己的孩子走,离开这个鬼地方。她张目四望,在疏散开来的人群中搜索男孩的身影,要是那该死的身影不即刻出现,她发誓她不会再管他的。她有十足的理由弃他不理。
男孩消失在十米外的一个转角处。
陈太太抱起孩子,急匆匆跟上去。她不得不跑起来,全身肥肉乱颤,呼哧呼哧——她觉得自己的老肺都要掉下来了。
她终于看见男孩了,在前面一个人慢腾腾地走着。
“滚回来!”陈太太嚷道,“我没时间跟你瞎晃。”
男孩头也不回,还是以那种慢腾腾的速度前进。漫无目的,遇到岔口,他就随意地左转或者右转。有时候他会弯下腰来,捡起路边的一颗小石头,扔远去。他把两手插在卡其色裤子的口袋里,一边走,一边用两条瘦腿踢着路边的什物。
陈太太放下手中的孩子,牵着她的手走着。她不敢追得太紧,怕他反而一溜烟跑远了,只是远远地跟在后面。
“老天爷可怜我!跟我回去吧!你以为你是谁啊?”
男孩停了下来,往路旁一间房屋的院子看去,土黄色水泥栏杆上摆着两盆青葱的植物,在微风中摆动着小叶片,如同一阵热烈的欢迎。男孩看得出了神,就像盲眼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听到她们的脚步声逼近,他跳了起来,往前跑去,跑了十来步,就慢下来,以先前的速度走着。
小女孩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帮一下忙,在这种场合之下,不管是帮谁,她觉得自己都能够获得一点赞赏的。她摇了摇母亲牵她的那只手,天真无邪地仰望着她的母亲,说:“小表哥生气了。”她很高兴自己为母亲指明了这一点。
“闭嘴!”陈太太恼怒地看了她一眼,甩开她的手。
男孩现在来到公路边,他左右望一眼,决定到公路那边去,另一边是长满齐腰高的狗尾草的荒地,微风过处,野草在月光下微微摇摆。在两辆私家车飞驰而过之后,男孩小跑穿过了公路。站在路对面,他第一次回头望了她们一眼,好像担心她们跟不上来。
月亮如同一位忠实的陪伴者,跟随着男孩,把如水般的月光挥洒在男孩身上,给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陈太太借着月光,看向对面的男孩,以及他身后的那片跨越黑夜边际的荒草地。
只有十米宽的公路,对此生只到过小城两次的陈太太来说,就像一条滚滚长江。公路地处偏僻,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车辆也不多,可偶尔会有一两辆车,夺命狂奔似的飞驰过去。陈太太觉得那真像是一辆辆黑色的灵车。它们的出现就是为了要她的命的。
陈太太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有点后悔,不该在男孩后面粗声粗气地喊他回家。
“你回来吧!你走丢了,要我怎么跟你妈妈交代?”
男孩反而转身跑开,却突然被绊了一下,两手撑地,向前跪倒。也许是膝盖磕破了,他蹲着,检查起自己的膝盖来。遥遥望去,男孩蹲着的小身影,有那么一瞬间,让陈太太心软了下来。
见男孩重又站起身,陈太太急起来,隔着一条大马路喊道:“别走,等等我呀。”她抓着小女孩的手腕,踉跄地往公路中间走出几步。
一辆小汽车飞过,像是在她们面前刮过的一阵飓风。陈太太吓懵了,脖子僵硬地后仰,后退到路边去。小女孩开始哇哇大哭起来。
“别走啊。”她哀求道。她放下小女孩的手,弯腰跟她说了一句,就自个儿往公路中间走去。她像是要走下冥河似的,战战兢兢地走出一步,试探一下,万一有什么不测,就可以迅速缩回去。
她颤抖着身子,好不容易走到路中央,每踏出一步都左望右望,看着前面的男孩,又担心地看看身后的小女孩。她从没有这么害怕过。惊怕击溃了她长年累积的信心,她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到路的那一边。好遥远,另一边总是另一边。她怀疑起自己的视觉来,连带怀疑起自己曾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她怀疑起自己的真心,是否也如同不堪一击的信心,那么轻易就溃败了。她真的想过去男孩那边吗?她真的无愧于他吗?她觉得自己应该首先无愧于自己。如此漫长的一条路。这是她人生中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条路,长到足以让她重新活一次,看清自己。
一辆大卡车打响喇叭,呼啸着朝陈太太冲过来。她吓得反而拔不动腿了。卡车一路猛刹车,发出拖长的尖利的刮擦声。陈太太闭上眼睛,迎接她的命运。
卡车冲到几乎贴近她的面前,才终于刹住了。她两腿一软,丢了魂,瘫倒在地。
司机从车窗那伸出头来,怒叱道:“猪猡!眼睛长屁股去啦?你他妈想死,别连累我!”
陈太太脸色苍白,觉得自己很委屈,可她又要盯着男孩,生怕他跑远。
司机“呸”了一声,倒一下车,拐个弯,从她身后擦过去。
陈太太乞求原谅地望向男孩,喊道:“孩子啊!我的孩子!”她坐在路中央,像个无助的小女孩,向男孩伸出一只手,等待被拯救。
男孩神情严肃地看着她,倒像是个大人。他似乎终于明白了,爱也许没有他想象的那般纯粹。爱是一条泥水河,滋养的同时带来痛苦。
男孩低下头,当他抬起头时,他转过身去,并不回头望一眼。他迈开步子,慢慢地往荒草地的深处走去。此时,月辉隐去,马路对面一片模糊,模糊又渐渐被吸入庞大的宇宙的星空里。高高的狗尾草淹没了男孩的身影,陈太太看着他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再也见不到他了,绝望如潮水般袭来,她看不到尽头。
片刻之后,月亮从乌云中升起,幽幽的光华被汇聚而来,如同一面被擦洗过的银镜,深沉地、温柔地照映着大地,以及那些在黑夜里游荡的孩子们。荒草深处,响起“沙沙——沙沙沙——”的声音,由远及近,犹如从梦里返回,微弱,却是笃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