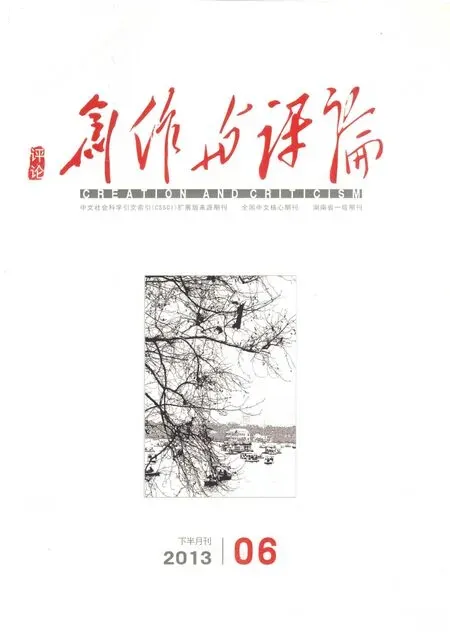挽歌与传奇——试谈新世纪汉语长篇小说中的“蛮夷戎狄”之风
2013-11-23颜炼军
○ 颜炼军
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一股意味深长的潮流:许多作家写出了少数民族故事,而且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这其中有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 (三部)、《伏藏》,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何马的《藏地密码》 (多部),安妮宝贝的《莲花》,何小竹的《藏地白日梦》,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冉平《蒙古往事》,阿来《空山》,宁肯的《天·藏》等。这些风格题材各异的长篇小说,都涉及少数民族社会或历史文化,在读者中刮起了一股“蛮夷戎狄”之风。它们有的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市场,有的获得内行人的好评。一言以蔽之,阅读“少数民族”,成为这个世纪最初十多年里独特的故事消费景观。
这些小说讲述的故事,与建国之后几十年间汉语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少数民族故事不同,它们不再将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作为革命叙事或革命抒情的一部分,也不再将它们作为反叛主流叙事美学的素材,而是将它们建构为与现代性困境对称故事。
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如下两种:一是关于少数民族遭遇现代化的经验。比如《空山》、《额尔古纳河右岸》、《水乳大地》这样的作品,都以不同的少数民族现代化经验为书写对象,再现了在文化碰撞、毁灭、蜕变和新生过程中,惨烈而幽微的历程。与此形成有趣对应的,是另一类以“图腾”“密码”“白日梦”“莲花”等为核心意象的小说,它们不约而同地在这一时期面世,并广为流传,显示了中国现代城市文化生产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特殊需求。现代城市文明脱离了与天空和大地的直接触摸,消解了漫长的农业社会积累的神话体系和象征体系,不断地创造自身的神话和传奇。而为了保持活力,新神话和传奇的生产得不断地启用以游牧或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这两种关于少数民族故事的相反的虚构姿态,显示了当代汉语小说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双向关系,是少数民族故事在当代汉语小说中被讲述的两种基本逻辑。
二
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题,这一主题也以各种方式推动着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变迁。在国人的现代性反思日益深入的当下,少数民族遭遇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边缘性,给当代作家提供了讲故事的绝好素材。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中,新世纪以来,这方面值得圈点的长篇力作,有阿来的《空山》 (三部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范稳的《水乳大地》。这三部小说颇具有地域上的代表性:它们分别以东北、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为素材,讲述了百年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遭遇现代化的种种故事。
《空山》的副题是“机村传说”。“机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在藏语中又是“根”的意思。对于这一隐喻凸显,显示了作家对于现代化给少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乃至地球上每一个不可避免地遭遇现代化的村庄的担忧和伤感。阿来在关于此书的创作谈中说,“多年来,一直想替一个村庄写一部历史,这是旧制度被推翻后,一个藏族人村落的当代史。在川西北高原的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那些群山的皱褶里,在藏族大家庭中那个叫嘉绒的部族中,星散着许多这样的村庄。”①这部小说以浓重的笔墨构成了一部多声部的村庄史,微观地展示了一个藏族村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世纪末的巨大变化。笔者在关于此书的一篇评论曾概括这部小说的基本内容:“机村是一个偏僻的四川藏地村庄。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几十年间,机村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迁。几十年中,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现代化的幽灵交织着浸入机村,加速了机村延续千年的观念与制度体系的崩溃和蜕变。新时代引发的,是对传统事物的迅速破坏和弃置,对文化多元性的漠视和拒绝。在《空山》中,阿来竭力说出这空前剧变给机村带来的裂痛,精微地再现了被卷入历史搅动中的无数个体的各种命运。”②
《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空山》的故事主旨有相似之处,但与作为藏族的阿来不同,迟子建是以外来者的姿态,来再现鄂温克人百年历史变迁的。为了拉近外来者与本土人之间的关系,迟子建将所有词语的光芒都聚焦到一个无名老人的讲述中。依靠这位鄂温克族老祖母的自白,作家以一个家族的变迁和衰落为视点,娓娓讲述了生活在东北的鄂温克人近百年来的生活和历史。在弱肉强食的现代战争和种族纷争中,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洪水猛兽的冲击下,这个曾经以森林为家,以渔猎为生的民族所生活的世界被破坏了。他们被迫迁到城市里,被迫定居,年轻的一代以各种方式参与甚至淹没到滚滚尘烟中,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有人因打架斗殴而入狱,有人因精神崩溃而回到森林中自杀,更多的人则成为城镇贫民。“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③迟子建在小说后记中感慨道。小说展示了他们的方方面面:有人与自然相处的温暖和悲壮,有生命在大地上的绽放和凋落,有神灵护佑下的生活的肆意和宿命……这些,都不可挽回地成了消逝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往事。可以说,鄂温克人的故事,是当今世界上无数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命运的缩影。
与阿来和迟子建一样,范稳的《水乳大地》也拉开了一个巨大的阵势,讲述了滇藏交界处卡瓦格博雪山之下,澜沧江大峡谷之中一百多年来发生的故事。故事中有藏族、纳西人、法国佬、汉人,有藏传佛教、东巴教、天主教、共产主义;有活佛、土司、祭司、神父、土匪、军阀、国军、红军、解放军、红卫兵等,现代世界催生的一切力量与这个角落里的传统事物汇聚融合。这里出现了天主教神父与喇嘛之间斗法,土司与军阀之间的争斗,国共之间的矛盾,各种现代事物的涌入……这一切,都充分展示了少数民族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境遇和悲壮。
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百年以来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区域遭遇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将主流历史和文化遗忘的经验丰富而感伤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它们象征着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数丢失、遗忘的部分。人类自作聪明地发展到今日,无数种人类曾经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消失。在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失去了大地的温暖,失去了天空的蔚蓝,失去了神灵的护佑,在被人类自己制造的事物拥堵的城市里,我们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孤独。历史上的每个族群在与自然、宇宙和自身相处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经验,不再能成为我们的生活的参照,他们至多只沦为人类学家的研究标本或作家的故事素材,最后化为现代文化消费中的过眼云烟。即使有再多的写作来追怀,这些写作本身无一例外都成了主流社会的文化消费品。但这些写作依旧是可敬的,我相信,随着我们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日趋严重,将有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参与到这一行动中。
三
与上述小说表现少数民族遭遇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凄婉和悲壮不同,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另一类当代小说,则讲述了生活在现代化、城市化中的人们,是如何借助少数民族文化,重新虚构精神的归属和远方的天堂的。这其中又有两种小说品类:一种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作为建构城市生活浪漫主义情调的作料;另一种则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作为反思当代主流社会文化精神的隐喻资源。
比如,在女作家安妮宝贝笔下,西藏是一个精神的归宿和流浪的天堂。她对现代都市白领的生活有一段精彩的描述。④无数人纷纷前往藏区,“那些走在路上的人,从世界的某个角落,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飞机、火车、火车、客车、自行车、徒步……汇集到这个高原城市,停留之后又分散进入西藏的不同地区。”⑤安妮宝贝以当代都市小资特有的忧郁和罗曼蒂克,描写了这些迷失于现代生活的人,是如何以各种现代交通工具,抵达“藏托邦”的。在她笔下,拉萨成为一座能够以超脱的角度来观察现实虚幻特征的城市。⑥就连这里的雨,也如同神迹,不被窥探。而藏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则是治疗城市生活的忧郁和枯燥药方,是感伤罗曼蒂克得以尽情展开的巨大背景。与安妮宝贝异曲同工,何小竹的《藏地白日梦》把一个都市精神流浪者的白日梦安排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藏区,小说着重探讨了白日梦的生成、破灭乃至周而复始,在我们的精神困境中占有的特殊位置。白日梦与藏地之间形成了隐喻关系,显示了当代消极浪漫情绪的象征化常常求助于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这种求助在伪浪漫主义追求中更明目张胆。比如作家何马的《藏地密码》,这是最近几年最为畅销的虚构文学图书之一。在读者的追捧和出版商的运作下,作者写出了整整九本连续性小说,它号称是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安妮宝贝笔下那些进西藏的人们攻略西藏的必备书之一。书里的各种故事和关于西藏的传说、历史和知识,帮助了无数人建立自己心中的西藏形象,解开了他们心中的藏地“密码”,同时也以好莱坞式的故事逻辑,将藏文化神秘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众多关于少数民族的小说中,姜戎的《狼图腾》和杨志军的《藏獒》在读者中掀起了持久而特殊的反响。狼是许多北方草原民族的图腾,而藏獒是藏族人最为亲密的动物伙伴。在这两部小说中,无论是狼的故事,还是藏獒的故事,表达的首先是对人类与自然界相处的无限怀念;但是在许多别有用心的、有过度阐释癖的读者看来,它们往往被视为当代主流社会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隐喻,作为动物学和生态学意义上的狼和獒被遗忘了,作为社会和人性的隐喻意义上的狼和獒,却被热烈追捧和肆意夸大。《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这本书的挽歌气质:
我终于提笔写《狼图腾》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因为我对草原的热爱。我亲眼见过原始草原的自然风貌,也目睹了草原的毁灭和整个游牧文明的毁坏,这样的剧变让我非常痛苦。离开草原几十年后,我看到更多的破坏,更大的灾难正在逼近;正因为如此,记忆中曾经美丽的草原离我越来越近,对它的感情和怀念越来越深。
《藏獒》的作者杨志军在谈论《狼图腾》时,褒奖了其挽歌气质,也批评消费过程中造成的阐释偏颇:
我读过《狼图腾》,它是一本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的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者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视为楷模。试想,如果我们都变成狼,岂不是马上就要走向悲剧了吗?我想说的是,《狼图腾》是一部不错的文学作品,但那些由偏读偏见衍生的所谓的狼文化,却是一堆人类的精神垃圾。
不管是《狼图腾》还是《藏獒》,作者写作初衷与文化消费结果之间的错差,显示了当代小说对于中国经历的复杂现代化过程的再现,容易陷入的困境;这完全符合《莲花》中那种将少数民族文化视为精神归宿和流浪天堂的文化消费欲望。读者们从这两部充满了挽歌气质的小说中萃取狼性文化和獒性文化,并被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折射了当下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需要不断发现和生产陌生的叙事隐喻体系,来命名当代中国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困局;另一方面,这些叙事隐喻体系所构成的传奇故事,则可以缓减消费社会时代的日常生活的枯燥,成为都市浪漫传奇的延伸。也因此,各类边疆少数民族的传奇故事,现在依旧不断地在出版面世。
四
作家纳博科夫在被问起洛丽塔这个人物时,曾说过一句俏皮话:“我的小姑娘那悲惨的命运必须与她的可爱与清澈一并考虑。”⑦纳博科夫深谙浪漫与残酷之间关系。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语小说家大规模虚构少数民族故事的运动中,面临的也是浪漫与残酷的纠结。只是,这里是历史的残酷与浪漫之间的纠结:一方面,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挽回的丢失,是人类社会竞争和历史命运中不可缓减的残酷,而且这在当今世界更为剧烈;同时,它们的丢失过程作为挽歌,又具有难以比拟的消极浪漫性。种种残酷的崇高之美,种种壮烈的传奇,最容易成全写作,被读者追捧,可谓怨深者文易绮也。
挽歌与传奇的交织,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困境的特殊反映。在当代小说中,关于革命、文革、历史转型和消费社会风云激荡中的诸种人性和世相的作品,可谓多矣;但把中国现代化进程视为民族、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多元一体”(费孝通语)的结构的小说表现,还远远不够丰富和深刻。上述这两大类型的小说作品,顶多是一种悲壮而先天不足的开始,它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还没有进行足够有震慑力的呈现。比如,上述小说所依托的经验观并没有对主流历史观构成有效的、独特的冲击,它们要么缺乏更为深刻的历史观,要么过分依附于经验本身,更糟糕的是,有些作品甚至陷入了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死胡同中。这样的困局,大概只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对于这一困局的认知水平的折射,我们不能妄想小说家能够胜出一筹?
少数民族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的处境,也是一个世界性困局。在中国这样的后起的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少数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是现代化难题中尤其重要的一环,它应该是今后包括小说家和所有社会精英们应该着力思考的问题。记得上个世纪上半期,历史学家顾颉刚在考察中国疆域沿革史时,曾有如下感慨:“在昔皇古之时,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尽精力,辛苦经营,始得今日之情况”⑧,顾颉刚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的感慨,饱含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几十年中国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建构。而现在,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运动的加速推进,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国家主义危机和民族主义危机,还有文化生态的危机,但这两种危机的解决,却时常产生矛盾。
小说家如何顾及各个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在汉语古典文化传统中,还是在中国现代汉语小说传统中,可资当代小说家更好地表现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借鉴的资源不多;无论是拉美文学还是欧美少数民族族裔文学,它们虽然在当代汉语小说家优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表现力这一任务上,提供了较多的启示,但由于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这种启示显然不大可能用来弥补汉语小说表现少数民族时遇到的缺陷。需要开启新起点,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走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汉语小说之道。具体地说,在上述这些充满了“蛮夷戎狄”之风的小说已经开启的小说之路上,我们期待在挽歌和传奇之外,出现更有小说力量的作品,钻石般地总结我们时代的少数民族经验,黄金般淬锻出这“少数”,进而成为改善人类生活和精神走向的精神基石,成为汉语作家为小说世界开辟新的天地;质言之,还需要有更精妙的语言,更好的故事,来命名少数民族世界中一切尚未命名或被低劣地命名的事物。
注释:
①阿来:《一部村落史与几句题外话》,《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3期。
②颜炼军:《合唱的“空”难——读阿来<空山>三部曲》,《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
③迟子建:《从山峦到海洋》,见《额尔古纳河右岸》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
④⑤⑥安妮宝贝:《莲花》,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70页、第12页、第21页。
⑦【美】纳博科夫著,唐建清译:《独抒己见》,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⑧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绪论,商务印书馆,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