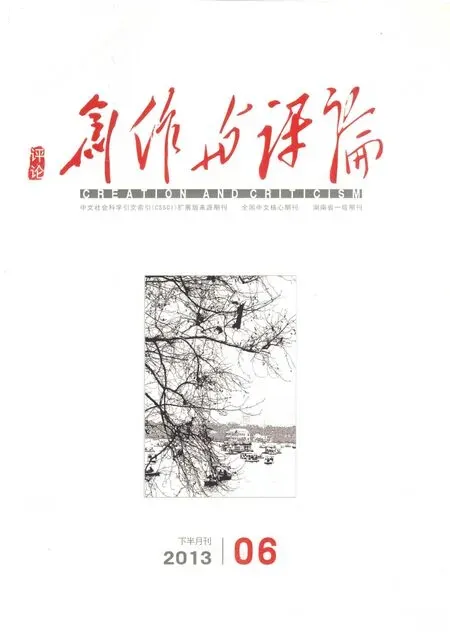废墟上的诗意——评电影《一九四二》中的救赎维度
2013-11-23○雷奕
○ 雷 奕
人类文明的进步伴随着历史的阵痛与抽搐,人类有理由为了自己创造的灿烂文明而骄傲地自诩为万物灵长,但历史前进的脚步下无时无刻不徘徊着残暴的幽灵。启蒙主义者相信理性和科学会开启新时代的荣耀,洗涤文明程度不高的过去曾经犯下的罪恶,可鲜血并未减少。战争、暴政、种族灭绝,混乱和邪恶似乎从来没有离开人类历史黑暗的渊薮。一边建造,一边毁灭,这是历史进程中令人困惑的二律背反。不仅人为的残忍摧残着无辜的生命,还有意想不到的天灾如地震、海啸,也加剧了生命的伤痛。有了灾难,就需要救赎。救赎,就是人在追寻生命意义的一个问号:面对生命的磨难、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威胁,人们该如何寻找救赎的道路,救赎在外部还是在自我,如何在善恶之间抉择,如何确认生存的意义?向灾难索要意义,是人的本质生命冲动。电影艺术将灾难以及对灾难的询问集中体现在画面上,它引导观众去思考,去询问,这是灾难片的价值所在。与以往的类型片相比,好莱坞模式一般借助英雄人物挽狂澜于即倒,而中国电影传统则倚重集体的力量。电影《一九四二》则提供了与之不同的思考方式,它并不指明一条看得见的救赎之路,而是运用细腻的电影语言,潜在地展现了不同向度的救赎维度,总体说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宗教救赎、道德救赎、女性救赎。这些多维度的救赎伦理,散落在故事的喧嚣之中,交织成几条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意义线索,多层次地展现出导演对救赎问题的关注,也正是因为有了对救赎问题多面的叩问指向,电影《一九四二》才多了一些有待回味的“诗意”。
一、宗教救赎
宗教起源于人类对超越日常生活神秘力量的崇拜。早期社会,宗教帮助人们解释世界存在的缘由,提供一系列道德规范,并且承担制度审判功能,人们依靠宗教建立社会联系,形成社会文化。宗教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文化现象,面对生命状态中的种种残缺、恐惧以及人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宗教带来了心灵慰藉和俗世行为指导。以宗教国家为例,基督教继希腊罗马文化之后,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统治长达千年之久,它以“上帝”为本体,以原罪与救赎为基本命题,以爱、仁慈、忍让为精神要义,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化的社会组织、伦理规范。不可否认,每种宗教的存在都为生存难题提供了解救的方法,但中西方因信仰不同而各异,前者的信仰主要以日常生活的伦理纲常为依托,后者则信奉上帝的恩宠,因为人先天存有罪恶、缺陷,所以人无法救赎自身。与中国文化宗教相比较,中国儒道互补型的文化传统都否定人身上原有的罪孽,儒教的修身成仁、格物致知,是以自我人性完备为基础的,它以主体的自我意识来调节道德标杆,而不需要外在力量的参照。“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道教的清静无为返璞归真和佛教的解脱涅槃虽然承认人自身与历史上的恶,但却是通过消除主体执念,消解主体意志的方式达到超越的境地,这种虚无主义式的心理调节运动实际上也削减了人面对灾难时对自我进行审视与剖问的紧张感和强度。传统文化这种求诸于己的内省模式,拒绝了领受超验世界的启示,面对荒谬和无辜受难,它有的是个人主义俗世生活的生存哲学,“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在儒释道三教之间进行微妙而合理的心理调适,而非基督教式地,将灾害看成是上帝对于人类本性罪恶的惩罚,从而具有普遍的、超越个体的意义。由于将历史受难看作与终极意义无关的“事件”,中国传统看待灾难的方式是天灾人祸、乱治交替的历史循环,而不是将伤痛纳入到自身的生命哲学中来,但对每个基督教信徒来说,灾难是与整个民族的民族创伤记忆融合在一起的:那些无以言说的恐怖、令人战栗的痛楚、无辜的牺牲与受苦不仅仅是一桩历史事件,而是形而上人的生存意义的起点。
《一九四二》里有浓郁的基督教宗教气氛,不仅设置了小安牧师这个小说中并不存在的人物,而且在影片中还有几段委员长在教堂祷告的片段,甚至在未删减版里还有传教士施粥救灾的场景。加入基督教因素,不仅因为这是历史资料的真实背景,而且也伴随着导演对灾难和自我的深入认识。中国传统的宗教观拒绝了超验的追寻,基督教却提供了一种别样看待灾难的眼光,这种别样的眼光,意味着在另一种层面上思考生命与苦难的关系。然而,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基督教的救赎失效了。影片通过反讽的修辞方式表达了宗教在极端灾难下的无力、空洞:小安神父在安葬逃荒路上死去而不肯闭眼的乡亲时请了瞎鹿拉弦子,赞歌唱完之后,死人仍无法闭上眼睛。这双无法合拢的中国老人的眼睛,她的无辜受难,正是对人祸天灾最无言最有力的控诉。传统弦乐器呜呜奏鸣如泣如诉,它象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在基督的弥撒仪式中显得怪异而不和谐。小安笃信基督教,但在令人无可忍视的残酷面前,他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超出任何理智和信仰所能承受的灾难,其惨烈强度几乎让人沉默。小安最后的出场镜头就是在十字架下和神父一起沉默祷告。
信仰危机后的出路何在?西方基督教在经过科学理性和人本主义思想发展成熟阶段后,面临着全所未有的信仰危机,现代启蒙家尼采喊出上帝之死的口号,抨击基督教精神是一种以怨恨为心理动机的“奴隶道德”。他指出:“奴隶在道德上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具有创造性和价值: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直接发出行动作出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象性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一种高贵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从反方向寻求价值的行动就是一种怨恨,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①尼采在对基督教和资产阶级文明批判中发展出唯意志论的超人哲学,从神本世界转向人本世界。其仰仗的意志力,虽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却是神位的另一种替代,不过在这种意志神力下,人的主观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宗教有无的纠缠折磨中度过,最后他让他笔下的基里洛夫用自己的意志开枪向上帝的意志提出对抗。现实中极度的黑暗与残酷将信仰的火烛撼动,也在文明的废墟中将意义的追寻推至亟需回答的地步。它将面对灾难时背向灾难的目光扭转到灾难和个人的联系上来,显示出灾难的意义与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不可分割的。小安这个角色并未回答如何得到救赎或上帝是否可以依赖这样的问题,但至少他大声喊出了魔鬼钻入内心的疑问和痛楚,他尝试着将历史中的灾难化为内在性悲剧的痛苦,这是影片对基督救赎这一命题作出的探寻。
二、道德救赎
在灾难面前,道德的效用到底有多大?不同的道德观念决定着怎样不同的救赎姿态?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内含在普遍统一的信仰或宗教规范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道德的重要作用,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注重血缘和宗族关系的整体道德观念,要求个人服从家族、整体、国家,在道德应用上,又强调道德与政治的融合,君子自成其身,“修身、齐家、治天下”,君臣父子忠孝节悌等三纲五常道德规范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整合政治文化秩序的基本纲领。在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结构里,政治与道德是合二为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需要道德君子的出现,道德的实现必须依赖政治的强力庇护。“君子道德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涵,无论政治问题还是自然世界问题,都由君子道德来解决,公正的社会秩序赖君子人格来确立。”②好的个人道德不一定会有好的政治,但好的政治下必然会有好的个人道德在支撑,这种建立在君子个人德性完满基础上的道德标准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政治和个人道德目标一致的历史语境下,二者的合力稳固了社会秩序,但当二者出现不一致的时候,也就是政治秩序无法保障君子道德实现时,个体该如何得到救赎?圣人教导应该怀揣道德,避开坏的政治。“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无论入仕还是避世,个人道德的圆满自足始终是被认可与尊崇的。总体言之,传统的道德观建立在君子道德自足的基础上,并以君子主观的圆满道德为标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很小,两者之间缺乏张力机制,一旦遇到政治灾难,道德要么臣服政治要么远离政治,而无法与政治开展有效的抗争与互动。
相比较而言,西方道德观念并非建立在个人道德圆满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人本身具有的理性思辨能力。西方道德思想发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共和城邦,政权由自由民选取的公职人员掌握,道德的内容主要围绕个人和城邦的关系展开。西方道德传统一方面来自于基督教义的道德内容,一方面来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对人自身理性的认知。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就是知识”到亚里士多德的“我爱我师,更爱真理”再到康德的“自律的纯粹道德形式”,西方道德观里始终充满了对人性本身所具有的理智认知能力与判断力的确信。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判断能力,灵魂才能够不倦地保持对美好情操的渴望与对真理的热爱。所以即使有被判死刑的可能,苏格拉底仍坚持真理,因为真理是超越政治的永恒事物,即使有宗教法庭,也不能退却布鲁诺捍卫真理、捍卫人的德性的决心,因为这种道德观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它不以个人意志或个人政治际遇的沉浮而转移。
电影《一九四二》中的道德救赎思想主要体现在外国记者白修德和中国官员李培基这两个角色上。李培基入身仕途,为灾情请命可谓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但官场斗争、党派倾轧、政治利益各种纷扰,致使这位儒士最后发出应该及早卸甲归田的悲叹。白修德出于职业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悲悯,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逃荒前线进行实录采访,并且竭尽所能将真相公之于众,让委员长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下达救灾命令。如果不是白修德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孜孜不倦追求真相的勇气,灾情也许还会加重。作为观众,能够理解李培基放弃道德理想时的无奈与苍凉,但更会欣赏白修德身上不断求证事实真相的正义和德性。然而,每种道德救赎都是有限度的,白修德也不是力挽狂澜的历史英雄,他个人的努力虽然促成了救灾的实施,但时局的混乱、非法勾当的猖獗、私心的泛滥、政治资本的较量等各种复杂社会因素致使救灾工作并没能有效地展开。“在群体的政策违背个人意愿的时候,社会生活中的强制因素才会显露出来。人的善良意志与理性只能部分地去调和这些不同的社会哲学和政治态度,而不能将其完全消除。”③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下道德救赎的不同方式,以及各自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限度。
三、女性救赎
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对女性文化的深入研究,女性渐渐凸显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女性文化从男权社会中解放出来,从被压抑的边缘文化身份中摆脱出来,展现了其独特的性别魅力。女性主义批判男性主义中心文化,尤其重视女性性别经验的特殊价值,开拓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建立起区别于男性的女性诗学,追求在平等基础上差异视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女性主义为现代社会批判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它与整个人类追寻平等自由的步伐一致。回顾人类文明史,不论中西方,女性确实经历了被压抑被排斥被劣等化自知或不自知的痛苦,从女性视角考察人类文明的缺陷与蒙蔽是根本性的,它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批判力。
中国两千年来深远悠久的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主体的掩埋和毁灭是残酷的,儒家文化所制定的男尊女卑思想严重地扭曲抹杀了女性生命意识,女性的文学形象要么是经过男系文化渲染过滤后的文化标签如孝女贞妇,要么就是怪奢淫逸的祸水荡妇,在中国传统思想背景下,女性群体背负着文化痼疾的重荷,在男性文化的指挥棒下跳着玩偶舞蹈。压迫越是深重反抗越是剧烈。二十世纪在中国社会进入文化政治的大变革时期,现代女性观念的渗入使人们意识到掩盖了两千多年之久的麻痹、痛苦,女性意识开始苏醒,启蒙者们以极大的热用借助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
冯小刚近年来的电影特别重视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他对女性话题的关注,而且这些女性形象多跃出了男性思维的框架,增添了更多属于女性自身气质的言说方式与内容,如《唐山大地震》中的充满意味的母亲女儿之间的情感纠葛。《一九四二》同样也在灾难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人物,最为突出的是名为花枝的中年农村妇女。《一九四二》是关于战争、政治的宏大叙事,而这位花枝,犹如一朵野雏菊绽开在逃荒路上车轮碾压过的泥路旁。它是脆弱的,然而它自我保有生命价值的确信,并且以自我独有的性别意识进行生存与思考,花枝的生存意味是来自女性本身的。
表现女性意识最突出的一个主题是母性。母性是女性意识的源泉,对孩子的爱,“是对他者的爱,是并非对自身的爱,而是在专注、温柔、忘我之中的缓慢、艰难、快乐的尝试”,④这种忘却自身的爱,是对整体制度化社会文化的遗忘与背反,它包容、柔和、圆满,充满温情,并以无私心排斥了功利与斗争,它的道德行为不依赖战胜与之相反的动机,而是来源于没有对立冲突的内部的自由闲适。社会学家西美尔认为,女性的自足和自治性来源于女性的母性特征,这种母性包含在自身之中,因此女性具有比男性更为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按照舍勒的比喻,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像娴静的大树,男人就像树上乱嚷嚷的麻雀。西美尔在论述女性文化困境时把现有文化分为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客观文化指的是科学、艺术、法律、习俗等文化形式或文化规范,主观文化指的是对灵魂财富的分享,个体灵魂可以通过外在的文化形式教化自己,外在形式却不依赖灵魂,虽然在文化创造初始,文化形式由人类灵魂发出,但在客观文化发展过程中,外在文化越来越脱离个体灵魂,成为具有男性特征的文化价值规范,整套文化由男性占主导地位,而女性文化与个体灵魂与本真存在具有更为天然的联系。在电影里,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的强烈对比体现在瞎鹿夫妇身上。当丈夫瞎鹿出于传统忠孝观念,为给母亲治病而偷偷想卖掉自己的女儿而非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时,花枝奋力而出阻止了他的行为,后来又在生存威胁下,出卖自己的肉身以换取儿子与女儿的生存希望。这种爱无关乎道德操守,而是女性本质所要求的。花枝身上的母性特征超越了传统男性文化的藩篱,她用灵魂的温度抚慰着受难亲人,用坚勇的爱、无私的牺牲昭示了另一种无言却动人的文化样态。
总体而言,《一九四二》从宗教救赎、道德救赎、女性救赎等多个维度间断地展现出对灾难中人性、文化、制度的思考,它超越了灾难类型片对灾难的直接呈现,表达出对生命与存在意义的探寻倾向,是一部以无诗意的故事说有诗意哲理的电影。
注释:
①尼采:《道德谱系》,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页。
②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③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④覃媛元:《母性:女性写作不应遗忘的圣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