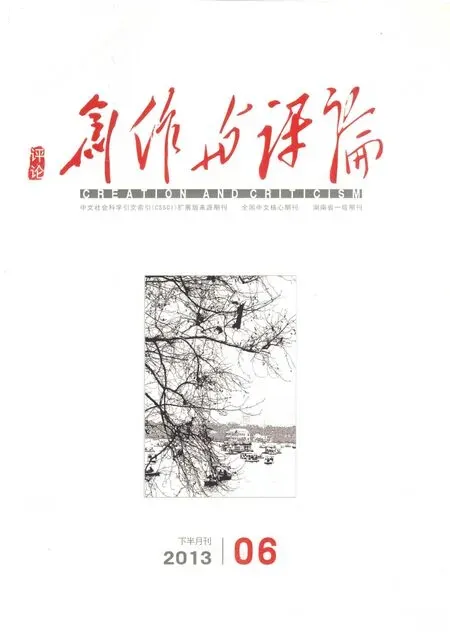立足民族生存的历史重构——评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
2013-11-23陈彩林
○ 陈彩林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影视作品走红之后又推出相应的文学作品,这种文字与图像配套运行的创作模式早已是中国社会的一道文化景观。即便如此,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冯小刚据此导演的电影《温故一九四二》 (后改片名为《一九四二》)仍然极大地吸引了国人的眼球。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在根本层面所要深思、回答的问题是一致的,即: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三千万人逃荒,三百万人饿死,这一历史事实应该如何呈现。
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采用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方式试图使小说在一种心理冲击中带给人以历史还原感与真实感。虽然在创作过程中他对一些细节性的局部现实事件作了适当的改写与虚构,但是这种改写与虚构却不是对于历史的随意歪曲与戏说,而是为了最大效果地将1942年河南大灾荒带给三千万人的生存苦难这一主体历史呈示出来,其间蕴含着强烈的历史重构意识,一种立足民族生存、与官修正史截然对立的民间历史重构意识。
作为导演的冯小刚对于刘震云小说的忠实不在于人物与故事情节,事实上二者在编剧时都作了大幅改动,把本来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基本上与报告文学无二的小说改变成了以老东家范殿元(张国立主演)一家、瞎鹿(冯远征主演)一家与蒋介石(陈道明主演)政府体系为主要聚焦点的荧幕故事,这无疑是为了加剧图像优于文字所具有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冯小刚在电影中对刘震云小说的再加工与刘震云在小说中对1942年一些细节性的局部历史事件的改写与虚构在内质上却是一致的:就历史事实而言,都是为了更具震撼效应地将1942年河南大灾荒带给三千万人的生存苦难呈示出来;就历史理念而言,都是为了凸显出立足民族生存、与官修正史截然对立的民间历史重构意识。
刘震云与冯小刚用文字与图像对于1942年的历史重构深层拷问的正是民族生存的思想问题。此时的1942年河南大灾荒就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我们民族尘封已久的心灵事件。而刘震云与冯小刚聚焦1942年正是为了拂去民族心灵上层层累积的使人模糊的历史灰尘,将民族真实的生存情状活生生地呈示出来,让这一心灵事件辐射出它本应有的历史精神效应。
当刘震云与冯小刚以民间的眼光透视历史,站在多数人生存的角度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时,这三千万中国人真实生存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三千万中国人真实生存的历史就呈现在白修德与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拍摄的“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的照片上。为了还原这段“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的历史,刘震云以采访当事人与搜集过去的报道、资料来说明,冯小刚则聚焦于逃荒之旅来再现,二者相得益彰,点面结合,共构出一部三千万中国人真实的生存史,一部与宋美龄访美风姿翩翩、仪态万方截然不同的民间历史。
首先,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共构出一部灾难深重的民族生存史。灾难深重到什么程度?就范围而言,其严重性莫过于大面积的逃荒。刘震云在小说中借白修德《探索历史》一书描写了当时灾民扒火车被轧死、轧残、沿途血迹斑班的逃荒情景。冯小刚在电影场景中花钱最多的地方也是这绵延无尽的逃荒长龙。逃荒的场景越是宏大,灾难就越是深重。而这种时刻与死亡相伴的逃荒其典型性绝不仅仅局限于三千万河南人,更不仅仅局限于1942年。单就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形成的被广泛接受的“闯关东”的社会习俗就足见逃荒是作为中国人生存的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如同闯关东一样被广泛接受的另一逃荒习俗,还有远溯汉代、兴于明朝至清末的“下南洋”。只是闯关东以山东人为最,下南洋以福建、广东人居多。与“闯关东”、“下南洋”构成中国人逃荒史中三足鼎立的另一社会习俗还有“走西口”。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事实上,“闯关东”绝不仅仅局限于山东人,“下南洋”绝不仅仅局限于福建、广东人,“走西口”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山西、陕西人。从逃荒的地域方位看,“闯关东”辐射东北,“下南洋”辐射东南,“走西口”辐射西北。也就是说,逃荒是中国人整体性生存的历史存在,它已经积淀为中国人生存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约定俗成为一种中国人生存的符号(社会习俗)。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审视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便会真实地浮出水面,才不会淹没于诸多壮伟的历史符号之中。
其次,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围绕上述逃荒共构出一部冲决人性底线的民族生存史。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与导演的冯小刚当然知道仅仅有宏大场面的渲染与烘托是不够的,焦点必须是个体与细节。冯小刚用冯远征主演的瞎鹿与女儿的对话这一细节回答了逃荒最原始的内涵,而这一内涵正是对真实生存状态的原初提炼。当女儿铃铛问“爹,啥叫逃荒呀”的时候,瞎鹿顺口回答:“不愿意饿死,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逃荒就是人回到最原初的本能生存状态,一切都是为了“吃”,这个“吃”就是寻点吃的,就是不饿死就行。吃,当然是人生存的第一要务。当瞎鹿对神父安西满(张涵予主演)说“逃荒一个月了,家里大人小孩已经十天水米没打牙了,每天都是吃柴火”的时候,当电影镜头再现出灾民将树皮、树枝、木头捣碎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见人是在何种情况下求生的,这时人的生存完完全全返回到动物,再谈“尊严”已经是极其奢侈的事情了。一切都围绕“吃”展开,都围绕活命展开。当人的生存核心全部集注于“吃”的时候,人性便变得如此粗糙,连流泪都是极为奢侈的事情。人性底线被彻底冲决莫过于卖人、人吃人、狗吃人。活下去的过程就是人性被一层一层剥落的过程,直到人的生存彻底返回兽性,那便是人开始吃人,而且是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甚至是比虎还毒的自食其子。倘若回溯历史这却不是文学家与艺术家的猎奇而是这种生存图景原本就绵延于民族生存的历史之中,刘震云与冯小刚聚焦于此就是要把这一使人不能成其为人的民族生存史的面目更加醒目震撼地凸现出来,因为它被另一种历史遮蔽得太久、太深。
再次,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在展示逃荒惨状、人性冲决的同时又进一步共构出一部拷问为政者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的民族生存史。虽然从史料看对于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国民党政府也做了一定的救灾工作,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与中国历史上很多灾难相同的内在原因。刘震云与冯小刚聚焦政府体系,塑造官员群像正是为了揭示这一点。刘震云在小说中借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道出了1942年河南人之灾的实质也是人祸,即“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苛政是民族生存的另一种形态。在猛于虎的苛政之下,在中国人的生存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比鲜明的生存图景,早在中国历史最繁盛的唐代杜甫就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作了最简洁直观的揭示。1942年也不例外,一边是三千万人踏上死亡之旅的逃荒,吃的是树叶、野草、树皮、树枝直至吃人,而另一边则是刘震云与冯小刚反复再现的政府官员的吃。正如刘震云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中国的政府官员绝不会因为灾民们在吃野草、树叶、树皮、树枝乃至去吃人,而会像美国记者白修德那样“不忍心吃下去”,“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对此,冯小刚在电影中将李雪健主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置身于摆放着精美菜肴的饭桌前,而他口中说出的却是“没想到一场旱灾,给河南拉下这么大饥荒”。就像中国政府官员的言与行一样,中国人的生存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这种强烈反差的情景之中。上述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体系的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在“只有甩包袱(灾民),才能顾大局”与“日本人真是太恶毒了,他们居然给灾民发粮食”的电影台词中得到了最集中的揭示。中国人的生存在“大局”面前是脆弱的。服从大局是中国为政者执政实践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当要牺牲民众的时候,当要榨取民脂民膏的时候,“大局”便是最好的遮羞布。世界上真有比千千万万老百姓生存更为重要的“大局”吗?那么,和饿死三百万人相比,摆在委员长面前的这种“大局”又是什么呢?当然是“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大局”、“大问题”刘震云在小说中也同样作了详细地叙述,概括起来有“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对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归根结底,“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陈道明显然了悟这其中的真意,因此面对白修德所说的人吃人、狗吃人的事,他准确地将导演、编剧的意图内敛于中国政治家特有的举止与语调,恰到火候地以平静的微笑练达舒徐地说出委员长的台词:“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鲁迅向来提倡“正面文章反看法”,因为民族生存的真实形态往往从反面才能看得到。
最后,文字与图像的《温故一九四二》又在诸多拷问面前更深层共构出一部启蒙国民性的民族生存史。三千万逃荒的河南人在切肤之痛的血淋淋的事实面前终于明白“在危险苦难时刻,国家、民族、领袖、主义,一个比一个不靠谱”。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三千万河南人“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刘震云在小说中展示了这一两难抉择的心理过程。1942年的历史再次证明铁一般的真理:抛弃人民的政府,也最终被人民所抛弃。抛弃人民的政府是靠不住的,那么上帝呢?当电影中憨直的神父安西满目睹逃荒路上人一个一个死去,在祈求上帝时等到的却是一颗炸弹的时候,他的信仰彻底崩溃了,那声绝望的“如果斗不过魔鬼,那信他还有什么用”的仰天喊叫便是最后的答案。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哪怕我们去抢。在只知道逃荒,甚至易妻而食、易子而食与揭竿而起之间,刘震云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沾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此时,我们再来看冯小刚在电影中聚焦大户被抢的场景的时候,才会领会其中的国民性启蒙意味。“揭竿而起”实则是自我对于命运的把握,不是逃,不是乞,更不是“在亲人间相互残食”,不必将希望寄托于抛弃人民的政府,不必苟活于侵略者的蹂躏之下,不必祈求于虚无的上帝,我们的命运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活不下去,那就“揭竿而起”,将原本是我们自己种出的粮食抢回来,将原本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抢回来。与其苟活于世,甚至苟活而不得,不如“揭竿而起”,活出一口气,活出一个真正的人。
刘震云与冯小刚以文字与图像真实勇敢地返回1942年,重构出一部绵延于历史时空的苦难的民族生存史、冲决人性底线的民族生存史、拷问为政者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的民族生存史、启蒙国民性的民族生存史。我们借助二人的文字与图像重温这一民族生存史恰恰是为了使我们的民族生存在历史之镜的反照中更好地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