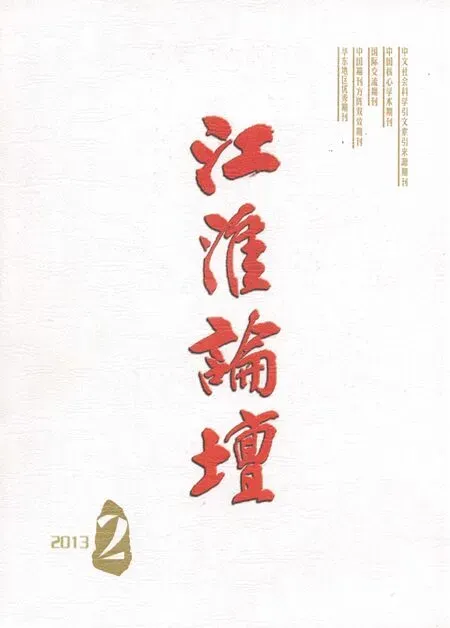双性合体:英美女性科幻作家的乌托邦理想*
2013-11-16李倩陈兵
李 倩 陈 兵
(1.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阜阳 236037;2.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08)
双性合体:英美女性科幻作家的乌托邦理想
李 倩陈 兵
(1.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阜阳 236037;2.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08)
双性合体是人类文学的母题之一。作为有着强烈性别意识的一类作家,女性科幻小说家们在自己的幻想作品中都摈弃了双性合体中的男权意识,对双性合体进行了女性主义的阐释,表达了她们两性和谐平等的乌托邦理想。本文以三位典型女性科幻作家的双性合体思想为切入点,分析其代表作中这一理想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从而梳理出双性合体思想在女性科幻作品中的流变,认为双性合体思想因为这些女性主义文本的演绎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具开放性。
双性合体;女性科幻作家;女性主义;乌托邦理想
“双性合体”是人类文化中一个古老而影响深远的主题。在西方,双性合体有着深厚的神话基础和悠久的宗教渊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嬗变的过程。最初,双性合体的原型是以创世神话中众神的面目出现的,如《圣经》中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出了人类,主神宙斯吞吃了怀孕的妻子以便亲自生出孩子。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来看,这些早期的双性合体形象充满强烈的男权色彩和排斥女性的倾向。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带有双性合体色彩的普罗米修斯以反抗强权的战士、自我牺牲的殉道者和人类保护者的形象出现在众多浪漫主义者的作品中,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或当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or The Modern Prometheus,以下简称《弗兰肯斯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到了20世纪,心理分析理论从人类精神层面分析双性合体。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双性合体的产生、发展和缘由,认为它和同性恋以及自恋情结有很大关联。荣格认为人的情感和心态具有双性合体的倾向,借用了两个拉丁语词 “anima”和 “animus”对双性合体进行细化描述。但是,这种分析角度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芙提出了全新的双性合体的概念:“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从此,文学作品中的双性合体超越了神话形象和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被赋予女性主义内涵。20世纪60和70年代,英美诸国女性主义运动和科幻小说发展相结合,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女性主义科幻作家。双性合体因其强烈的幻想色彩和性别意识,吸引着这些思想锐利的文本实验家在她们的科幻作品中对其进行后现代主义的阐释和演绎。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此类女性主义科幻作品都以未来世界或异类世界为背景,折射出女性作家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想象。因此,这种科幻小说可以被称为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其中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厄休拉·勒魁恩的 《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和乔安娜·拉斯的《雌性男人》(The Female Man,1975)。这两部作品以激进的态度和全新的角度诠释了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双性合体。本文以三位典型女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玛丽·雪莱的 《弗兰肯斯坦》、厄休拉·勒魁恩的《黑暗的左手》和乔安娜·拉斯的《雌性男人》为研究文本,分析其中的双性合体理想的相似和差异。由于社会文化语境、文学潮流和作者思想的不同,双性合体的乌托邦理想在上述三部科幻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建构,但是却凸显出清晰的发展脉络。通过剖析这三个女性乌托邦作品的意义和不足,本文揭示了双性合体在女性科幻作品中的母题意义,可以对以后的女性主义科幻文学研究和文本批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多层次的双性合体思想
《弗兰肯斯坦》创作于19世纪初,当时虽有一些女性作家跻身文坛,但是整个社会风气对女性写作依然持怀疑、讽刺和压制的态度,甚至身处浪漫主义运动中心的玛丽·雪莱也常常在P.B.雪莱和拜伦两大文学巨人的阴影笼罩之下缄口不言。因此,虽然是在丈夫的鼓励下完成《弗兰肯斯坦》的,小说初版时,玛丽·雪莱依然采取了非常审慎的策略掩盖自己女性作家的真实身份和小说的真正意图,以逃避社会舆论可能给予她的打击。所以,小说以当时流行的哥特小说为外壳,把对普罗米修斯形象的颠覆、对浪漫主义的怀疑和对男性霸权的拒斥层层包裹起来,使得其中的双性合体思想呈现洋葱式的多层次纵深结构。后世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如爱伦·莫尔斯、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芭芭拉·约翰逊和安·迈勒等人透过这层层外壳,敏锐地探查到了《弗兰肯斯坦》深藏的含义。
小说中最明显的双性合体建构是以弗兰肯斯坦的造人故事为框架的。弗兰肯斯坦的造物主形象延续了上帝和普罗米修斯的双性合体的原型意义,他既是父亲又是母亲。而且,出于建构男性同性社会的欲望,弗兰肯斯坦有意造出了一个雄性后代。但是神话中的上帝和普罗米修斯不但造出了人类,还给予他们关爱和照顾,在这一点上,弗兰肯斯坦和上帝以及普罗米修斯完全不同。他有创造的能力却无爱的勇气,对自己的造物先遗弃后追杀,最后自己也惨死于茫茫冰原之上。这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剥夺女性的生育权,违反大自然的生殖规律,妄想仅仅以技术来建立一个单一男性的乐园。这个企图的最终失败反应出玛丽对男权主义双性合体理想的讽刺,也是对浪漫主义者所歌颂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怀疑。
小说的第二层双性合体思想体现在弗兰肯斯坦这一浪漫主义典型人物的形象之中。历代的批评家们早已发现,弗兰肯斯坦身上具备诗人雪莱的许多性格特点和气质。和雪莱一样,他博学多识,思维敏锐,为追求理想不惜身涉险地。这种对梦想的执著让弗兰肯斯坦生活在纯粹的抽象理念之中,使他对亲朋好友的需求置若罔闻,成了不孝的儿子、不忠的朋友和冷漠的恋人。对弗兰肯斯坦的描述反应了玛丽内心对丈夫身上自私一面的隐忧。在这隐忧之下,又暗藏着玛丽的希望:男性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不能以理性、理智或理想为借口脱离社会和家庭,而必须像女性一样考虑到家人的利益,男性的性格中需要有关爱、体贴、细腻等女性特点,拥有柯勒律治所谓“半雌半雄”的伟大头脑。而这样兼备两性优点的人物就是弗兰肯斯坦的挚友克勒瓦尔。克勒瓦尔是弗兰肯斯坦的对立面,集中了雪莱身上的所有优秀品质,却没有雪莱的缺陷。他既勇敢忠诚又温柔细腻,是玛丽理想中的雪莱。但他最终被怪物杀死,其实就是被弗兰肯斯坦的男权思想所害,折射出玛丽对这种理想最终的怀疑和悲观态度。
《弗兰肯斯坦》一书中隐藏最深的体现双性合体特点的人物就是弗兰肯斯坦创造的怪物。他是男性躯体和女性命运的奇特组合。由于弗兰肯斯坦的变态心理,怪物身躯巨大,拥有男性的强壮和敏捷。他是弗兰肯斯坦男性欲望的外在映像。但是怪物的命运却是女性化的。他因为容貌丑陋、身躯畸形而遭到其父母——弗兰肯斯坦的抛弃和社会的歧视,而女性则是因为性别的丑陋而被视为怪物。他不断地问:“我是谁?我究竟是什么?我又从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这种对身份和认同的寻求也正是历代女性苦苦追寻的,使怪物形象从女性主义角度看更具普遍性。所以,怪物其实就是一个象征,他“本质上就是一个隐喻的女性和一个被男权和父权逼疯的女人”。玛丽借怪物的命运表达她对当时女性处境的关注,也隐隐地透露出对自己身世的哀叹。
从以上层层剖析可以看出,《弗兰肯斯坦》的双性合体理想被深深包裹在科学幻想、哥特和恐怖等文本外壳之中。故事背景是18世纪末的欧洲,是个“现实的”世界,主要人物都是男性,女性人物形象平板单一,处于男权阴影的压制之下,都是沉默的“她者”。从这一点来看,《弗兰肯斯坦》似乎并不是一部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但是玛丽·雪莱通过女性的缺席无处不在地描写了女性,在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女性主义阐释、对弗兰肯斯坦浪漫主义理想的批判和对怪物的悲惨命运的刻画中隐晦而巧妙地表达了她的双性合体理想。因此可以说,《弗兰肯斯坦》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它开创了女性科幻小说书写的先河,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意义也会历久弥新。
二、厄休拉·勒魁恩的《黑暗的左手》:大胆的思想实验
《黑暗的左手》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西方国家兴起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号召女性作家从女性自身的经验出发,建构自己的语言模式,扰乱和颠覆象征父权制的男性话语,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等级对立结构,试图结束女性被束缚的历史。而幻想小说成了女性主义作家建构理想乌托邦的最佳文本。勒魁恩就是在这个社会语境之下把自己对女性问题的关注通过科幻小说表达出来的。因此,相对于《弗兰肯斯坦》中隐藏极深的双性合体理想,《黑暗的左手》的双性合体想象可谓大胆。小说用冷静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双性人构成的异星世界——冬季星(格森星)。格森人的外表和地球人相差无几,但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处于中性或无性的状态,只有在特定的克慕期才会呈现性别变化。这种变化是无规律的,任何一个格森人都有可能成为父亲或母亲。因此,在冬季星,“没有强势/弱势、给予保护/被保护、支配/顺从、占有者/被占有者、主动/被动之分。……人类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二元论倾向已经被弱化、被转变了”。对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不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而是把对方看成真正的人。这种双性人社会的设想有力解构了人类社会的男女二元对立,从根本上动摇了男性霸权的社会基础。
没有性压迫和性歧视的冬季星似乎是所有女性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但事实上它并非无忧无虑的世外桃源。虽然星球上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也有仇恨、偏见、背叛和谋杀。因此有的批评家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黑暗的左手》并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因为小说没有描述一个乌托邦式的国家,小说中也没有任何女性人物出现。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则认为,书中对双性合体的描述不够详尽,观点不具有革命性,而是对女性主义目标的背叛。这种反对的声音是有道理的。比如,在整部书中,勒魁恩用男性代词“他”来指代格森人,整个文本的统治性声音是男性。如果故事的亲历者是一名地球女性或者格森人,那么可以想象,在以男性读者为主导的20世纪60年代的科幻领域,这部小说就不会那么受欢迎了。因此也有论者把《黑暗的左手》称作“为男人而写的女性主义”。故事中的第二个主要人物——卡亥德王国首相伊斯特拉凡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双性人,如金利所说,他是“光明与黑暗,恐惧和勇气,寒冷与温暖,女人与男人”的统一体。但是整部小说中,伊斯特拉凡留给读者的印象首先是一个老练机敏的政客,运用他的智慧和勇气与政敌斡旋;然后是一个坚韧勇敢的冒险家,以他的不屈意志陪伴金利穿越茫茫冰原。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抚养孩子、如何做家务。他身上的女性特质只是间接模糊地出现在这些男性特质的间隙中。因此,小说中的这个双性合体社会就显得缺乏说服力和可信度。以上这些“缺陷”可能不会让《黑暗的左手》成为激进的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但是,1969年的勒魁恩才刚刚开始像一个女性一样写作,在这部小说中史无前例地直接描写了一个没有性别差异的社会。因此,此书更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实验,其中体现的批判力、想象力和文学价值使其成为了女性文学以至整个人类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
三、乔安娜·拉斯的《雌性男人》:激进的女性主义乌托邦
《雌性男人》完稿于1969年,但由于其极端的女性主义观点,到1975年才得以出版。乔安娜·拉斯同样受到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新浪潮运动的浸淫,但是她的思想更为激进。《雌性男人》不仅仅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更是宣扬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和女优男劣的思想,以幻想的方式宣言实现女性彻底自由的唯一途径是消灭男性。相对于《黑暗的左手》,《雌性男人》中的双性合体思想更加激进,乌托邦色彩更加鲜明。小说采用多元时空和时间旅行等科幻元素和貌似杂乱无章的叙述方法,讲述了四位来自不同时空的女性的故事。珍妮生活在过去某个性别压迫深重的年代,胆小温顺。乔安娜生活在1969年的纽约,是一名聪慧独立的大学教授,她想摆脱一切父权的束缚,努力实现自我价值。杰尔生活在不久的将来,是个专门猎杀男性的杀手。杰妮特来自千年以后的纯女性世界威尔勒威(Whileaway),此时地球上的男性已经消亡,女性在没有男性霸权的单性社会中过着幸福和平的生活。很显然,这四位来自不同时空的女性其实就是被男权分裂了的同一个女性自我,是一个整体,这一点从她们的名字(Jeannine、Joanna、Jael、Janet)也可以看出来。她们身上浓缩了整个的女性进步史:压迫—觉醒—反抗—解放。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一个问题“我是谁?我的商标是什么?”和《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的呼喊如出一辙,凸显了历代女性追寻自我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的呐喊和吁求。
小说的四位女主人公中,只有珍妮被彻底塑造成了符合男权标准的典型女人,其他三位身上都或多或少体现了双性合体的特征。乔安娜拥有独立意识,聪颖能干,希望得到和男性同等的待遇和认可,但是她所在的父权制社会却要求她做男人的附庸。杰尔从生理上讲是女人,却拥有男性的体魄和力量,勇猛好斗,崇尚暴力。可以说,她是有着女性躯体的男人,思维方式也是男性化的。她生活的世界是现实社会的极端版,男女两性互相仇恨,女人邦则以屠杀男性为己任。这个充满仇杀的世界远非理想,所以拉斯进一步刻画了她心中完美的乌托邦——威尔勒威。这里没有了男人,女性之间恋爱、组成家庭,卵细胞结合技术代替了两性繁殖,儿童教养完全社会化。这个社会没有性压迫和性歧视,女性完全从生育和家务中解放出来,享受充分的自由,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杰妮特强健自信又富有爱心,是完美女性的化身和拉斯的双性合体理想的最高体现。在杰尔和杰妮特的激励下,乔安娜最终变成了一个“长着女人面孔的男人,拥有男人大脑的女人”。通过描写乔安娜和杰妮特的全新形象,拉斯完全颠覆了以往男性沙文主义的双性合体理想,因为“那些由男性提出的革命性的双性合体理论——即使这些男性和女性主义事业结成了联盟——往往幻想的是第一种双性合体,即男性被女性补充,而不是第二种:女性为男性所补充。事实上,这些理论在可笑的潜意识中简单地把女性的劣势视为理所当然;女性的躯壳不可能容纳男性的智慧和精神,而男性的身体可以被女性的感情和体格所填充”。因此,《雌性男人》中的乔安娜和杰妮特成为女性主义双性合体的最终、最完美的理想。
由于《雌性男人》另类的风格和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刚一出版就引起巨大反响,成为20世纪70年代最富战斗力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为拉斯引来了很多批评和争议。正如阿特贝利指出的,杰尔的女人邦对男性的仇杀和虐待反而使得男性成了被压迫的他者。小说赞美纯女性的乌托邦社会威尔勒威,但会有人感觉这是在宣扬两性分离,只能会加剧现实社会中两性间的偏见和误解,给女性运动带来不利影响。毕竟,人类社会就是由两种性别构成的,理想的社会根源于两性的共同努力与和谐相处,而不是一方迫害、消灭另一方。小说留给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故事的第一章,杰妮特告诉我们,威尔勒威的男性在数千年前死于一场瘟疫;在故事的末尾,杰尔却说是那场男女之间的终极战争消灭了所有男性,瘟疫之说是个谎言,“威尔勒威的鲜花是在我们屠杀的男人的尸骨之上盛开的”。杰妮特的祖先撒谎是为了让后代 “能够虔诚地相信瘟疫,并心安理得地使之符合道德标准”。这样一来,威尔勒威这个美好的乌托邦就是建立在一个弥天大谎之上,显得摇摇欲坠。拉斯为小说留了这么一个尾巴,也许她也觉得灭绝男性的想法太极端,想借此稍稍淡化小说中浓烈的火药味。也许,对这个单一女性的乌托邦能否实现,拉斯自己也心存疑虑。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鲜明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和对未来乌托邦世界的生动描绘,这部小说表达了当时的女性主义者对父权制度下女性二等阶层的地位的强烈反抗与拒斥,也
饱含了她们对未来和谐社会的期待和向往。
四、“双性合体”的发展趋势
自伍尔芙以降,学术界对双性合体的批评主要以女性主义为视角,但各家褒贬不一。1973年,女性主义批评家卡罗琳·海尔布伦在 《对双性合体的认同》一书中赞美了伍尔芙的双性合体观念,认为双性合体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两性的特点和男性女性表现出来的人类冲动不再是固定的。”1977年,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认为,伍尔芙的双性合体“代表着一种逃避,不愿直接面对男性或者女性”。目前,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双性合体的意见已经从当年的强调“性差异”变为“求和谐”,这是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影响之下的产物,也是符合目前世界整体的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趋势的。而上文所分析的三部科幻小说中的双性合体思想也和女性主义发展趋势相吻合,呈现出清晰的演变脉络,经历了从传统到激进的发展历程。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体现了英美早期传统女性主义的写作特征,即以男性中心话语的补充为载体,以男性可以接受的方式言说,在文本的空白和缝隙处隐约透露出几许女性经验信息。玛丽意识到了男权的压制并力图加以抗拒,但主要还是以书写男性为中心,并单纯地希望男性能接受女性的某些性格特征,使他们自觉地达到双性合体的境界,这样的世界才是美好和谐的。厄休拉·勒魁恩的《黑暗的左手》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它第一次以女性作家的视角描写了一个没有性别差异和性别压迫的双性合体社会。勒魁恩借此给予我们一个重新审视人类文化的机会,更明确、大胆地表达了消除两性对立的意识,并用虚构的乌托邦社会来建构男女平等的对话渠道。同时,《黑暗的左手》中弥漫着浓郁的道家哲学思辨的味道,处处暗示着两性互补和文化互补是消除男女二元对立的理想方式。勒魁恩的这种远见卓识预示着后世女性主义从冲突到对话的转向,双性合体将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乔安娜·拉斯的《雌性男人》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的产物,其所宣扬的性别仇恨、消灭男权暴政、建立纯女性的乌托邦的口号很极端甚至很“危险”。这种否定男性的“逆向性歧视”重新设定了女性中心/男性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会导致社会象征秩序的裂缝,在现实世界中会让女性主义运动的成就功亏一篑。目前欧美国家出现的针对女性主义的“回潮”也从侧面反映出偏激女性主义的缺陷。针对这一情况,很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把双性合体的内涵进行了拓展,提出重“女人”的女权主义。这种新型的女性主义“不再强调男女对立和女性一元论,而是注重多元论,强调男女文化话语互补关系;注重女权、女性、女人的统一,使女人不再成为与男性对立的 ‘准男性',而是女人成为女人,男人成为男人;消弭冲突、对抗、暴力等男性统治话语,推进爱、温情、友谊等新的文化政治话语,使世界成为具有新生意义的后现代世界”。双性合体的这条传统—激进—对话的发展脉络标志了女性主义理论话语的成熟,也反映了今后女性主义的发展方向。
研究英美女性科幻作家的双性合体思想并厘清这个概念在西方女性科幻小说史中的发展和演变之后,可以发现双性合体是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的重要母题,反映出女性对两性平等和谐的理想状态的希冀。目前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已经从当年风起云涌的激荡状态恢复平静,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男性霸权和性阶级依然存在,较之以前更为隐蔽,女性在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依然遭受着各种性别歧视和压迫。在中国,情况可能还要更严重,毕竟,几千年男尊女卑的思想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十年内消除。但双性合体集中体现了女性群体对双性和谐理想境界的追求和渴望。众多女性科幻作家对双性合体的文本演绎,丰富了其内涵,也使其外延更具开放性,依然对当今的女性运动起着引导作用,激励着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利。这一目标对提高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改善她们的处境也不无益处。
注释:
(1)这段时期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关于普罗米修斯较著名的作品有:歌德的诗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1774)、拜伦的诗歌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1816)和诗剧《曼弗列德》(Manfred,1817)、雪莱的诗剧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18)。
(2)《弗兰肯斯坦》于1818年正式出版,但随后玛丽·雪莱对作品做了修改,于1831年又出过一个版本。目前国内外对 《弗兰肯斯坦》的研究主要以1831年版为基础。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所引译文亦是通行的1831年版,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3)玛丽·雪莱在1831年版《弗兰肯斯坦》的“作者导言”中说:“拜伦和雪莱多次进行长谈,在他们交谈时,我只是一个虔诚的倾听者,几乎一言不发。”
(4)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拙作《道家思想与女性主义的融合:“双性合体”的新境界——<黑暗的左手>评析》(《学术界》,2012年第7期)。
[1]Sigmund Freud,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C]//Art and Literature.Lon don:Penguin,1990:210-211.
[2]Carl Jung,Anima and Animus[C]//Aspects of the Feminine.London and New York:Ark,1989:77.
[3]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7.
[4]Anne.K.Mellor,Mary Shelley:Her Life,Her Fiction,Her Monsters[M].New York:Methuen,1988: 72-73.
[5]William Veeder,The Fate of Androgyn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23.
[6]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M].刘新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27.
[7]郭芳云.怪物魔镜中的自我——《弗兰肯斯坦》造物神话的女性主义解读 [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3,(4):81-85.
[8]陈本益,等.西方文论与哲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381.
[9]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M].陶雪蕾,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10]Brian Attebery,Decoding Gender in Science Fiction[M].New York:Routledge,2002.
[11]Craig Barrow and Diana Barrow.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Feminism for Man[C]//Mosaic.Winnipeg: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1987.
[12]Joanna Russ,The Female Man[M].Boston:Beacon Press,1986.
[13]Barbara C.Gelpi,The Politics of Androgyny[C]// Women's Studies.London: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Ltd,1974:151-152.
[14]Carolyn Heilbrun,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M].New York:Knopf,1973:Foreword:X.
[15]ElaineShowalter,A Literature of Their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289.
[16]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74.
(责任编辑 文 心)
I206.6
A
1001-862X(2013)02-0176-006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2SQRW085)
李倩(1977—),女,回族,安徽太和人,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陈兵(1968—),安徽庐江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