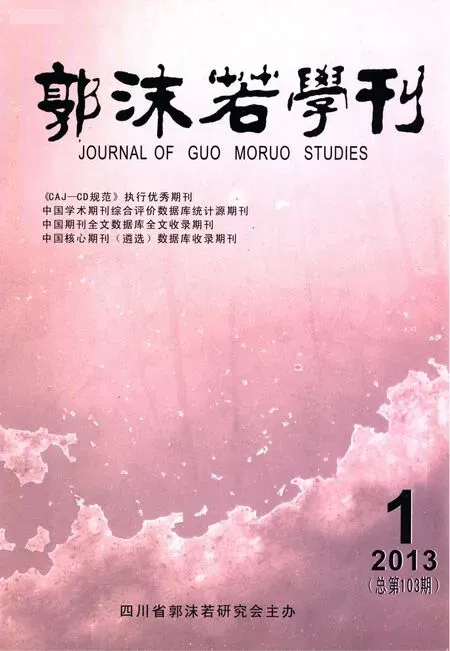关于《郭沫若全集》的考察
2013-11-16蔡震
蔡 震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一个浩大的出版工程。为此专门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全集》分为《历史编》《文学编》《考古编》,总计38卷,数十位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编辑注释工作,历经二十余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三家出版机构才全部出齐。这是关于郭沫若创作著述文献资料整理出版的一桩大事,为广大读者能全面阅读郭沫若著作,为郭沫若研究建设一个学术资料库,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然而,《郭沫若全集》的出版,似乎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反而非议不断。同时,现有的《郭沫若全集》毕竟只是一个“一期工程”,所以有必要对于《全集》编辑的得失做一些考察与辨析。
全与不全
《郭沫若全集》所遭非议,首先和主要来自对于《文学编》的批评,当然批评所指,都是用了全称的称谓(即《郭沫若全集》)。这一情况大概主要因为归入《文学编》编辑的文章作品的情况最复杂,而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学者,又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学者居多,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最为关注的当然是全集的《文学编》部分。
对于《文学编》的批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批评“全集不全”,一是批评部分作品因非文学和学术的原因被删去而未编入全集。
事实上,《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是有一些问题值得回过头来做一些反思,但不仅仅是从《文学编》的角度看问题,也不仅仅是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这需要对《全集》各编的情况有一个梳理,并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首先当然是关于《全集》的编辑原则。
所谓“全集不全”的批评,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关于《全集》编辑原则的评价,但这个批评恰恰罔顾了《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原则,因为这样评说的批评者们并没有注意到《郭沫若全集》有一个什么样的编辑原则。我们先来看看实际上是作为《郭沫若全集》基本编辑原则的《〈郭沫若全集〉出版说明》:
《郭沫若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编为《文学编》《历史编》和《考古编》,共三十八卷。各编卷序自为起讫,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全集》的著作,保留原有集名,适当地作了一些调整。
收入《全集》的著作在这次出版时,一般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进行校勘工作,个别地方在文字上作了修订;除保留作者自注之外,又增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
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将陆续收集整理、编辑出版。
编辑和出版《郭沫若全集》这是第一次。在编辑、校勘和注释工作中,可能有一些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这里说得很清楚,现在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只是郭沫若自己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其未曾编集和未曾发表过的作品等,俟以后收集整理出版。也就是说现在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三编三十八卷,是收集、整理、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部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可称为“一期工程”,真正作为“全集”的编辑出版物,还没有完成,还有待继续进行。所以,所谓“全集不全”,并非一个严谨的说法,只是无的放矢的泛泛而论。
事实上《郭沫若全集》的问题不在“全”与“不全”,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已经编定出版的这部《郭沫若全集》,其所依据的编辑原则是否合适,是否科学,应该作什么样的调整?这可以为后续的郭沫若著作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提供经验和思路。
需要一个编辑体例
郭沫若著作从有选集本出版,到文集本出版,再到全集本的编辑出版,已经历经几十年时间,然而一直还没有制订过一个作为辑选编辑工作遵循依据的“编辑体例”。《郭沫若全集》只有一个“出版说明”,这当然不能代替编辑原则。编辑原则的确定,应该体现在一个科学严谨的、规范一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编辑体例文本中。《郭沫若全集》没有制订这样一个编辑体例,应该说是其最大的失误。
尽管在“出版说明”中写有这样的内容:“收入《全集》的著作,保留原有集名,”“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进行校勘工作”、“保留作者自注”等等,这应该是构成《全集》编辑体例的规定条文的内容。但是,这些规定过于简单,完全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例。尤其不妥的是,“说明”中还加入了“适当地作了一些调整”、“一般采用”、“个别地方”等带有变通性的规定用语,这就使得原本应该成为体例规范而需要编者遵从的原则,成了并不确定,带有伸缩性,可以变通的东西。《全集》成书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为人质疑、诟病处,正是因为在编辑的过程中未能遵循一个统一的原则,而在各编各卷之间能够自行其是所造成。
编辑体例阙失所造成的问题,在《全集》编辑之初,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将三编各自所拟定的“说明”作一比对,就可以看到。
“历史编收入作者历史学论著和整理古籍著述,编为八卷,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第一卷),《十批判书》(第二卷),《奴隶制时代》《史学论集》(第三卷),《历史人物》、《李白与杜甫》(第四卷),《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第五、六、七、八卷)。
收入本编的著作,除《史学论集》是新编的集子,其它都保留作者原编定的集名。
收入本编的著作,凡是作者注释一律标明,以示与编者注释相区别。”
“《文学编》收入作者文学方面的著作,编为二十卷,包括:诗歌(第一、二、三、四、五卷),戏剧(第六、七、八卷),小说、散文(第九、十卷),自传(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卷),文艺论著(第十五、十六、十七卷),杂文(第十八、十九、二十卷)。
本编收入的著作,在上述六个部分中大体按时间编次。
本编收入的著作,都是作者生前出版过的,现保留原来的集名。有的著作,曾先后收入作者若干不同的集中,现只将其收在最初编成的集内。
收入本编的著作,主要根据作者修订过的最后版本,其与初版本有较大改动处,有的加注,有的作为附录。
收入本编的著作,除作者自注外,我们参考了其他版本的注文,增加了简注。”
“《考古编》收入作者考古方面的著作,分为十卷,包括:《甲骨文字研究》(第一卷),《卜辞通纂》(第二卷),《殷契粹编》(第三卷),《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商周古文字类纂》(第四卷),《金文丛考》(第五、六卷),《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七、八卷),《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第九卷),《考古论集》(第十卷)。
……
五十年代,作者将十一部旧著进行改编,分别对《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作了校改和补注,删除了一些篇章,增收了附录,并废除《古代铭刻汇考》及其《续编》、《金文余释之余》,而将其中有关甲骨文、金文的文章并入以上三书。其后,作者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其《考释》并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并作了增补;作者把解放后对大量出土的青铜铭文所作的考释以及他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同类文章,一并收入《金文丛考》作《补录》。一九七三年作者同意将他历年发表的甲骨、青铜器、石鼓以外的考古学方面的文章辑录《考古论集》。
收入本编的著作,我们调整了个别篇目,增补了校勘和注释,增补或更换了一些拓片、照片、摹本。除《考古论集》外,注释者录在眉端,新增补的注释用▲符号标明。”
在三编各自拟定的“说明”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存在有这样的问题:
其一,各编收录著作都有一个标准,但在三编之间,缺少一个统一适用,且可以操作的标准,并行诸规定性文字。
三编分别规定“收入作者历史学论著”,“收入作者文学方面的著作”,“收入作者考古方面的著作”,这固然不错,但是在编辑《全集》中实际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样认定某一篇著作为“历史学论著”、“文学方面的著作”,或是“考古方面的著作”?譬如:《论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直是收在《文艺论集》中,《全集》将该篇收入《历史编》;《题彝器图象拓本》《题延光砖五首》等旧体诗作,作者曾将它们辑入诗歌集《潮汐集》出版,《全集》则将这些诗作收入《考古编》。那么《全集》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判定它们是“历史学论著”、“考古方面的著作”,而不是“文学方面的著作”呢?
像这种情况,各编的编者在编选考虑中当然各自都会有一个因由,但是放在《全集》的范围内,就不免顾此失彼了。《全集》各编所收录著作的范围、标准,应该是在《全集》编辑的层面上设计规定性标准,这样自然可以在涉及到交叉于两编内容的著作如何作编选考虑的时候,有一个能够在编与编之间平衡一致的原则,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即便是作为一个个例去考虑的问题。就如上述情况,如在《全集》的层面有所规定,譬如,用收入某“编”而在另一“编”作存目处理,就能够既体现编选的具体考虑,又可以在《全集》内体现完整性。
其二,辑入《全集》著作文本的择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全集》的说明中规定“一般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但“最后的版本”是指作品集著作集,还是《沫若文集》,或单本著作,没有具体规定。《文学编》遵从了“主要根据作者修订过的最后版本”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以《沫若文集》作为择定文本的“最后的版本”(未收《文集》者除外)。《历史编》《考古编》都没有对于著作文本的择定做出规定,也没有将《沫若文集》视为一个版本。《考古编》仅对于部分在“五十年代”由作者进行过修订的著作,作了说明。
其三,各编对于收录著作的编排顺序,各自为阵,没有一致的标准。《文学编》在按照文体形式所分的各部分中“大体按时间编次”,但这个“大体按时间编次”又没有说明是按照著作集出版的时序编次,而单篇作品在原著作集的编次并没有按严格的时序这一实际情况。《历史编》没有对编排顺序作出体例的规定,全编在“历史学论著”和“整理古籍著述”两部分中主要按照著作写作出版的时间顺序分别编排卷次,即第1卷至第4卷为“历史学论著”,第5卷至第8卷为“整理古籍著述”。但是“历史学论著”部分的第4卷,又打乱了时间顺序。《考古编》亦没有对编排顺序作出体例的规定,主要是依据各卷收录著作的组合编排卷次。收入第6卷、第10卷文章的写作或发表时间的跨度能有二十余年。
其四,按照著作集辑录篇目并保留集名的编辑方式引出了一些矛盾,但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考虑和规范。
收入《全集》的著作,按照著作集辑录篇目并“保留原有集名”,是沿袭了《沫若文集》的编辑思路和方式,其优劣各有所在,从《沫若文集》的编辑中已经可以看到。但《全集》所面对的情况与编辑《沫若文集》时又有了不同。《沫若文集》的文本大多经过作者再次校订,包括有修改的文字,于是,《沫若文集》在《郭沫若全集》的编辑过程中,也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版本、文本因素,因为《全集》所收著作文本,是要落实于“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当然也包括《沫若文集》的。那么按照著作集辑录篇目并保留集名的编辑方式,我们在《全集》的编辑中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不同的因素混合在一起:
单篇文章的写作、发表有一个时间,作者辑录成作品或著作集出版也有一个时间,这两者是不同的,“保留原来的集名”,又要“按时间编次”,文学作品集还有同一作品先后编入过不同作品集的情况,选用初次入集的篇目,还要“采用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的文本等。同时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要求,如果没有综合起来的考虑设计,在逻辑上是无法使他们统一起来的。所以从整体上来看,《郭沫若全集》内在的编排顺序,实际上是含混不清的。
其五,注释体例不统一,各行其是。
《全集》对于注释没有做统一的、具有规范性的要求。《全集》的“出版说明”关于注释问题仅提到“除保留作者自注之外,又增加了一些简要的注释”。“简”要简到什么程度或范围,应该有一个可考量的规定。《文学编》谓:“收入本编的著作,除作者自注外,我们参考了其他版本的注文,增加了简注。”这与《全集》的“说明”相同。《历史编》则比较含混:“收入本编的著作,凡是作者注释一律标明,以示与编者注释相区别。”对于编者应作什么注释,是简,是繁,未置一词。《考古编》称:“收入本编的著作,我们……增补了校勘和注释。”也没有对于如何“增补”注释做出规定。
从三编实际的注释情况来看,《文学编》的注释(包括注释的条目和注释文字),总体上比较适度,但各卷之间不均衡,有的略繁,有的过简。《文学编》对于所收录的文章均作有篇注,说明该文最初发表的时间、报纸刊物的名称、刊期等。
《历史编》是最先完成编辑工作成书出版的,至1985年6月即已出齐全部8卷。其注释却过于简单,除作者原有注文外,编者注释主要就是文中一些引文资料的出处。《考古编》虽曰“增补了”注释,但情况与《历史编》大致相同。这两编的注释,都没有考虑作篇注,是疏于考虑的。
郭沫若的绝大多数文章著作,从写作、发表开始,到收入各著作集,或修订、再版等,都经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郭沫若全集》规定收入的文章著作是“作者亲自校阅订正的最后版本”,那么许多与该文章著作相关的、最基本的信息,如果不作注释,势必流失了。譬如:《历史编》第3卷所收的出自《史学论集》的那些文章,从该卷中甚至无法查找其原刊文在什么地方。《考古编》第6卷共收文31篇,其中《吴王寿梦之戈》辑录自《奴隶制时代》,《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等11篇文章辑录自《文史论集》,《正考父鼎铭辨伪》等11篇文章辑录自《光明日报》《文物》《考古》等报刊,《题越王勾践剑》等8篇文章未曾发表过(其中《永盂铭释文》等4篇写作时间亦不详)。所有关于这31篇文章最基本的信息,该卷没有任何注释的文字说明。那么,即使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也难以从这一卷的文本搞清楚31篇文章的来龙去脉。
所以,像篇注这样的注释,决非无足轻重。仅就这一点而言,它也关系着《全集》学术使用的价值。《全集》之“全”,在文章篇目、文本之外,也应有一个功能性的价值体现。当然,这是需要在体例设计中就考虑的问题。
“集外”文与“集内”文
尽管直至目前,《全集》的编辑出版只做成了前面的一步,后续的工作尚遥遥无期,但是在走前一步的时候,当然要想到后一步怎样落实,以便前后衔接。这应该是个“规矩”。然而,《全集》的三编都有“逾矩”之处:或是收录了著作集之外的文章作品,或是删去了著作集之内的文章作品。
在最先成书出版的《历史编》第3卷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明文字:“《史学论集》是新辑的集子,它主要收编作者在建国前后散见于报刊上未收入集子的,以及原收入文艺、杂文论集(包括原《文史论集》)中的史学论文。”《全集》明明规定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史学编》何以就自作主张“新辑”出一个集子呢?并且这两个“说明”文字都同时印在已经出版的《历史编》上,这是自相矛盾的。
第3卷在《史学论集》的名下辑录有“作者生前未编集”的文章二十余篇,这表明《全集》的编辑工作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完全规范、有序地进行。虽然被辑录入《历史编》的集外文章的数量不算多,但日后《全集》若开始下一步进程,即“收集整理、编辑”“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时,将如何与目前的《历史编》接续呢?同时,原收在《文史论集》中的4篇文章(见下文,还有其它文章)却未收入《全集》,也未予说明。
《考古编》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考古编》在《全集》中最晚结束编辑出版工作,历经24年,至2002年10月方全部完成10卷本的编辑出版。但《考古编》收录“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文章著作的情况更为突出,10卷中有3卷所辑录者,基本上都不在规定的“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之列。
第4卷所收《商周古文字类纂》,是郭沫若1944年即已完成的著作,但出版是在他去世后的1991年。
第6卷以《金文丛考·补录》的名义收文31篇。按照《考古卷》“说明”称:“作者把解放后对大量出土的青铜铭文所作的考释以及他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同类文章,一并收入《金文丛考》作《补录》。”事实上,只是作者生前同意做这样一个《补录》,“文革”之前已经由考古所安排人在整理,并请专人抄录(这一点应该特别予以说明,因为该卷亦为手迹影印,而郭沫若其他已经出版过的古文字研究著作,均为其自己的手稿影印)。这仍然是没有出版的著作。在该卷所收31篇文章中19篇为集外文章,其中还有8篇为未刊文。
第10卷所收文章全部为集外文,但编者在卷头“说明”中作了这样一个解释:“作者在考古学方面的著作,除本编前九卷所收的七部专著之外,尚有散见于书刊的文章。一九七三年科学出版社辑得三十余篇,经作者同意,编成《考古论集》书稿。在本卷编辑过程中,又将作者生前编入其它作品集的有关篇章补入书稿,并增收了郭沫若故居藏品中的有关题跋和近年发现的部分佚文。”然而所谓《考古论集》书稿的存在与否和它的辑成,不能仅凭一句文字说明,不然何以该卷未如第6卷那样署上集名呢?而且,即使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书稿,它也并非“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第10卷中还辑录有“郭沫若故居藏品中的有关题跋和近年发现的部分佚文”,这些都属于未刊作之佚文。
第10卷又将一些旧体诗《题彝器图象拓本》《题新莽权衡》《题天发神谶碑》《题王晖石棺画像》(三首)《题延光砖五首》《叠鞭字韵题汉墓墓砖》等,总计二十余首辑录入卷。这些诗作的内容尽管是与考古相关,毕竟属于文学创作(其中《题彝器图象拓本》《题新莽权衡》《题天发神谶碑》《题王晖石棺画像》(三首)《题延光砖五首》,原本就已收录于诗歌集《蜩螗集》和《潮汐集》中),这与学术论著是完全不同的写作。
以这样的方式辑录了39篇作品的第10卷,给人的感觉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卷其实成了凑齐《全集》计划中38卷著作之数的一卷。
《文学编》承《历史编》的做法,由“编者代拟”编订了一个《文学论集》,将《文史论集》拆分后所留下的文学部分的文章辑入其中。不过《文学编》没有在此名下任意增收篇目,即集外的文章。这算是遵循了《全集》规定收录已出版著作的基本原则。但是《文学编》删削了一些作品,从另一面违背了《全集》的编辑原则。这主要是在编辑处理《沫若诗词选》的过程中。
《沫若诗词选》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集子,它不是与其他收入《全集》的作品集同样意义上的作品集,而是一部包含有多部作品集作品的选集,在成书的性质上类似于20年代的《沫若诗集》。所以,将一个选集本的作品集《沫若诗词选》,以该选集本名义辑入《文学编》的编辑处理本身,就欠妥当。
《沫若诗词选》共收录诗词作品278篇(按目录所列篇题计)305首,编入《文学编》第5卷时,在《沫若诗词选》集名下辑录的作品仅有100篇118首。《沫若诗词选》实际上大半成了空壳。《沫若诗词选》原从《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等各诗集选录的作品,总计158篇166首,分别辑录于《文学编》第3卷、第4卷各诗集名下。此外,尚有20篇21首作品在编辑《文学编》时为编者删去。编者仅在卷头“说明”中记有“少数篇章未收录”一语,既未说明“少数”之数,也未解释各篇被删去的原因。
被删去的篇目(按照《沫若诗词选》的篇题)为:《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革》《国庆》《“长征红卫队”》《大民主》《新核爆》《科大大联合》《科技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向工人阶级致敬》《迎接一九六九年》《满江红·庆祝“九大”开幕》《满江红·歌颂“九大”路线》《满江红·庆祝“九大”闭幕》《西江月(二首)——献给地震预报战线上的同志们》《西江月》《粉碎“四人帮”》《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捧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些诗词所咏内容均为“文革”事,或者这就是编者删去的原因。
作为一个选集本的作品集,《沫若诗词选》之所以辑录入《文学编》,显然因为其成书时收录有相当数量的当时的集外作品。那么,与此性质(选集本)类似的还有郭沫若自订的开明版《郭沫若选集》,尽管该选集中仅有一首诗,即,《站在英雄城的彼岸》辑自集外,但毕竟也是在“生前出版过的”作品范围之内。《文学编》没有编入此篇(等于是删去了)也未予说明,肯定是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小问题。
《文学编》还有一个处理欠妥的问题:诗歌部分《集外》的编排。
《文学编》辑录的诗歌共5卷,第5卷末编排了《集外》,所辑录的篇目为《沫若文集》第1卷《集外(一)》的篇目和第2卷《集外(二)》的部分篇目。《沫若文集》的诗歌部分有两卷,《集外(一)》之所以编入第1卷,且排序在《前茅》《恢复》两诗集之前,就是因为其“集外”的含义,是指创作于1923年前,未曾收入《女神》《星空》两集之外的诗。同样,《集外(二)》也包含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是1945年至1957年1月所写而未编入集中的诗作。”《文学编》将两个《集外》均编排于全部诗歌作品之后,实际上改变了两个《集外》,特别是《集外(一)》与相关诗歌集的关联关系,也不符合《全集》编辑所遵循的基本的时间顺序。
《郭沫若全集》在编辑过程中“逾矩”收入的集外佚文,甚至是未刊佚文,将来若续编《全集》时,势必在衔接上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而曾辑录在各个作品集著作集中,却在编辑《全集》时被删掉,且并未记录在案的那些文章作品,很可能就会在两不管的状态下,完全被遗忘,成了新的集外佚文。
拆分与新编
《全集》按照著作集辑录篇目并保留集名的编辑思路,衍生出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拆分了由不同学科的著作混编成集的著作集,同时又由编者自行编订出几个著作集。
《郭沫若全集》与《沫若文集》在基本编辑原则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按照学科领域分作“文学”“历史”“考古”三编。这样一来,在沿袭《沫若文集》按照著作集辑录篇目并保留集名的编辑方式时,就必然会出现对于混编著作集如何编辑处理的问题。
郭沫若有一些著作集是将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文章著述混编辑录的,在编辑《沫若文集》的时候,因其初衷是编一个文学著作集,所以《沫若文集》并没有专门针对这些著作集做编辑处理上的特别考虑。尽管后来《沫若文集》陆续收录了历史、考古和古文字方面的著作,但在文集内各自成卷,也就没有显出不协调。《郭沫若全集》在卷次之上设置了一个二级的结构“编”,且以学科分编,混编而成的著作集的编辑处理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全集》这样处理了那些混编的著作集:
《文艺论集》,编入《文学编》第15卷,集中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王阳明礼赞》4篇辑入《历史编》第3卷;
《断断集》,编入《文学编》第18卷,集中的《社会发展阶段之再认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包括附录)《再谈官票宝钞》《答马伯乐教授》4篇编入《历史编》第3卷;
《羽书集》,编入《文学编》第18卷,集中的《驳〈实庵字说〉》《关于“戚继光斩子”的传说》《续谈“戚继光斩子”》3篇编入《历史编》第3卷,《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一篇辑入《考古编》第10卷(《文学编》“第十八卷说明”关于此篇去处所说有误);
《青铜时代》,编入《历史编》第1卷,集中原附录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序》《彝器形象学试探》2篇分别辑入《考古编》第8卷、第7卷,《周代彝铭进化观》一篇未辑入《全集》;
《历史人物》,编入《历史编》第4卷,集中的《鲁迅与王国维》《论郁达夫》《论闻一多做学问的态度》3篇辑入《文学编》第20卷;
《今昔蒲剑》,编入《文学编》第19卷,集中的《钓鱼城访古》《论古代社会》《论儒家的发生》3篇辑入《历史编》第3卷;
《天地玄黄》,编入《文学编》第20卷,集中的《“诅楚文”考释》《〈行气铭〉释文》《序〈美术考古一世纪〉》3篇分别辑入《考古编》第9卷、第10卷;
《奴隶制时代》,情况更复杂一些,被一分为三。该著作集编入《历史编》第3卷,该著作集上海新文艺版(初版本)中的《简单地谈谈诗经》《人民诗人屈原》《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6篇辑入《文学编》第17卷,《吴王寿梦之戈》一篇辑入《考古编》第6卷,该著作集人民出版社版中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篇辑入《考古编》第10卷;
《文史论集》,不复存在,同时衍生出两个新编集名《文学论集》《史学论集》,所收49篇文章一分为三,分别编入《文学编》第8卷、第17卷(共计18篇),《历史编》第 3卷、第 5卷、第 8卷(总计14篇,其中有5篇原出自《奴隶制时代》,复归于该集名下),《考古编》第6卷、第10卷(总计13篇)。尚有《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给北京大学学生的一封信》《坚持文物事业的正确方向》《给〈史学〉编辑部的一封信》4篇未编入《全集》。
另外还有《潮汐集》(分作《潮集》《汐集》)、《蜩螗集》,这两个集子并非混编而成的著作集,而是诗歌集,均编入《文学编》。但因为《考古编》的编辑考虑,《潮汐集》中的《题彝器图象拓本》《题新莽权衡》《题天发神谶碑》《题延光砖五首》《詠王晖石棺》《题王晖棺玄武像》5篇10首诗,《蜩螗集》中的《题王晖棺刻画》1首诗(《文学编》第2卷“说明”关于《题王晖棺刻画》所收集子的说法有误),辑入《考古编》第10卷。
从涉及到的9个著作集(不计《潮汐集》《蜩螗集》)编入《全集》的情况来看,《全集》采取了拆分与新编两种方式进行编辑处理,拆分后文章作品的归属,涉及三“编”总计14卷。被拆分的著作集,以其所收大部分文章的学科归属,保留集名,辑入相应“编”下的“卷”内,拆分出来的文章,依其各自的学科归属,以单篇辑入相应“编”下的“卷”中。《文史论集》不但被拆分,且未保留集名。拆分后归入《史学编》辑录的文章,由编者拟定了《史学论集》收入其中(除个别篇);拆分后归入《文学编》辑录的文章,亦由编者拟定了《文学论集》纳入其中(除个别篇)。这是新编的两个集子。拆分后归入《考古编》辑录的文章,则依单篇文章篇题编入卷内。《考古编》第10卷虽然没有在目次上署一个著作集名,但在卷头“说明”中用了所谓《考古论集》的名义,也在实际上新编了一个集子。
以上是仅就郭沫若著作集中文章涉及不同学科的内容,辑入《全集》情况所作的梳理,有些著作集辑入《全集》后可谓“七零八落”了。这还是以著作集的一个版本而论,同一著作集的不同版本之间亦有篇目增删易动的变化,若把这些变动也考虑进去,情况将更为复杂。
郭沫若的同一篇作品文章(尤其是文学类的),先后收入不同作品集著作集,或在不同版本的作品集著作集之间有所调整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它们在以作品集著作集的方式编入《全集》的时候,也有一个如何拆分再行辑录的过程。好在这一种情况的发生没有“跨界”,而是在同一“编”内的各卷之间,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与此相关还需要提及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在论及郭沫若作品集著作集的版本,与《郭沫若全集》关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全集本”的概念,把“全集本”视为一个版本。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固然沿袭了《沫若文集》按照著作集作品集辑录的方式,但《全集》因为分“编”之故,打乱了著作集作品集原收录的文章作品篇目,《全集》只是保留了著作集作品集的集名,它们许多已经不是以完整集子的形态存在,不应该有一个所谓“全集本”的某著作集或作品集,譬如:全集本的《文艺论集》、全集本的《沫若诗词选》等等。只有对于具体的一篇文章作品而言,存在一个“全集本”的文本。所以,所谓“全集本”,应该是作品文章的文本概念,而非作品集著作集的版本概念。
此外,关于郭沫若著作版本的概念,一直以来也都是针对郭沫若自己编订或者认定的著作集作品集,包括选集、文集等而言,所以讨论郭沫若著作的版本,并不涉及未经作者编订或首肯的出版物。从这一层意思上说,郭沫若著作集作品集也不应该有一个“全集本”的版本概念。
《郭沫若全集》在编辑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的原因,一是缺少一个科学严谨的设计,二是在编辑事务中缺少一个从“卷”到“编”再到《全集》,完整的工作机制,尤其是缺失了总览编审的工作环节。当然,现在来讨论编辑《全集》的得失,特别是阙失疏误之处,并不只为察其究竟,而是可以为总归要付诸实施的《全集》的下一步工程做准备。
壬辰腊月廿九,改定
注释:
①从《沫若自选集》到《沫若文集》均无编辑体例。
②根据王世民先生提供的信息。
③这一篇目数,是对应于《沫若诗词选》目录中所列篇题的数字。《文学编》第5卷中《沫若诗词选》下的篇题目录有所改动(将原列为若干篇题者改作一题),篇目数还要少于此数。
④见《沫若文集》第2卷卷头“说明”。
⑤见《沫若文集》第1卷“出版说明”:“这个文集收辑郭沫若到最近为止四十年创作生活中的文学著作,……他的考古研究著作和翻译的外国作品,都不收入在内。”
⑥《文学编》“第十八卷说明”关于“《羽书集》原收杂文七十四篇”的说明亦有误,香港孟夏书店1941年初版《羽书集》收文75篇,重庆群益书店1945年版删去17篇,其中《驳〈说儒〉》一篇后收入《青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