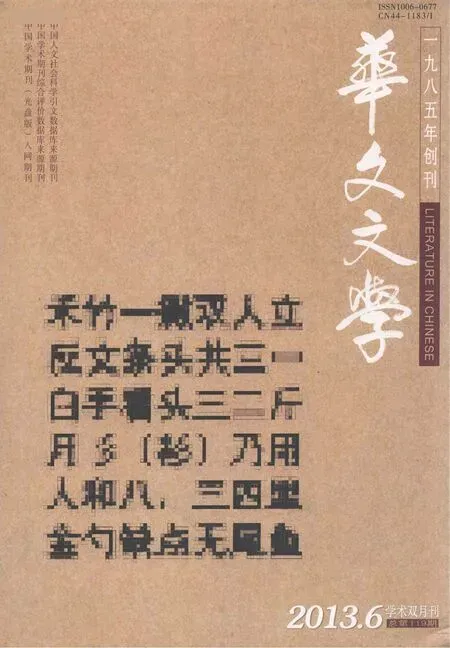陈河论
2013-11-16日本杨晓文
[日本]杨晓文
一、阿尔巴尼亚情结
“文革”时,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十分匮乏。于是乎,就有了外国电影的闪亮登场。
那时候所说的外国,实际上所指范围甚小: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越南等,它们里面经过筛选有幸被翻译介绍给广大中国观众的影片,所产生的影响巨大无比,因为它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这里,让我们来盘点那些译制片:北朝鲜的《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还有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
深入分析便会明晰那些译制片的接受度(或曰受欢迎度)还是有所不同的:近邻北朝鲜的影片与当时的国产片比起来,演员水灵,服装悦目(尤其是女演员的裙装令国人羡慕),但说教性强,大道理连篇,看多了便会产生似曾相识之感。但,来自遥远的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影片就迥然不同:异国风光,旖旎迷人;故事性强,人物具有个性魅力;艺术表现手法多样,比当时的国产片技高一筹(例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整体构思严谨,米哈依、安娜、托玛的三人戏演出了多重效果,就连那不长的开头序曲部分都充满了紧张感、人情味,引人入胜);而感情描写方面最具冲击力,表现男女性征等镜头给“文革”期正值青春的一代进行了生动的性启蒙教育。其中,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就是这么一部对当时的观众来说具有艺术与教育综合魅力的影片。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人们开始淡忘阿尔巴尼亚,《宁死不屈》似乎将要屈服于时代的风化。
但还是有人与实际的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有人念念不忘《宁死不屈》的精神,并将之文学化。
他,就是华文作家陈河。
曾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陈河,1994年出国前往阿尔巴尼亚,一住就是五年,靠经营药品生意为生,其间遭遇局势动乱,遭遇绑架,经历了生死考验,用文学再现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遭际之念重萌,孕育其日后作品主调与潜流的阿尔巴尼亚情结遂生。
陈河的阿尔巴尼亚情结最早是在发表于《收获》2007年秋冬卷长篇专号上的《致命的远行》(2012年以《红白黑》为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露面的。
《致命的远行》讲的是一个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的、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国际故事,有类似美国影片《教父》的情节;而在“第七章迷人的阿尔巴尼亚”,作者让男主人公谢青去了一趟他梦中的异国他乡,而且通过当地翻译、神通广大的亚历山大,竟然见到了《宁死不屈》里的女演员米拉(笔者注:米拉·格拉米是影片中的女主角,身份是女学生;而小说中写的“她脸颊上的那颗黑痣”的女配角名叫阿菲尔蒂达,身份是受伤的女游击队员。作者对阿尔巴尼亚影片及罗马尼亚影片中的人物、情节、歌词,有数处记忆错误),三人一起开怀畅饮,美酒佳肴,他乡遇故知,于是小说里一个感人的场面出现了:
米拉说:“你最爱看我在电影里的哪些镜头呢?”谢青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在枪伤换药的那个镜头,有人在边上为你弹吉他。”米拉转着眼睛想了半天,说:“那个镜头里我是脱下衣服露出了肩膀是不是?”谢青说是的。他说你当时不止露出了肩膀,还露出了一侧戴乳罩的胸脯。你这一美丽的枪伤给多少中国年轻人带来了幸福的梦想哦!他对米拉说,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直没忘记电影里的那首歌。说着他情不自禁唱了起来: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米拉听到这里已泪流满面了。餐厅里有弹吉他和吹风笛的乐手,亚历山大把一个吉他手喊过来,对他说了几句。那人点点头,一拨手指,一串音符泉水一般涌出: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米拉在唱,亚历山大在唱,乐手在唱,餐厅里的好多客人包括一个端着盘子的侍者都在轻声唱着,唱着喉咙里带抖音的和原版电影音乐一样的正宗的阿尔巴尼亚语。
米拉告诉谢青,电影里米拉的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说谢青应该去靠近希腊边境的吉罗卡斯特看一看。在那个全部用白色石头建造的山城城门口的圆形广场上,有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那树下有一个大理石雕像。雕像是个神色忧伤而严峻的少女,她在十八岁时就被德国人吊死在她头顶的这棵无花树上。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这个花样年华的中学生是个地下抵抗分子,为游击队做着机要联络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被德国人抓住。在她死后不久,无数的游击队员越过了山岗,进入这个黑暗的城市为她复仇。
看过《宁死不屈》的人一定会记住那抒情的吉他、动人的插曲吧,而“米拉在唱,亚历山大在唱,乐手在唱,餐厅里的好多客人包括一个端着盘子的侍者都在轻声唱着,唱着喉咙里带抖音的和原版电影音乐一样的正宗的阿尔巴尼亚语”是多么感人的场面,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泪流满面”。但笔者在这里意欲冷静地指出陈河阿尔巴尼亚情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性意识。
当女演员问谢青他喜欢自己的哪些镜头时,谢青(可以视为陈河的文学分身,而在下一部阿尔巴尼亚作品中,这种亲历性更明显)“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在枪伤换药的那个镜头,有人在边上为你弹吉他。’米拉转着眼睛想了半天,说:‘那个镜头里我是脱下衣服露出了肩膀是不是?’谢青说是的。他说你当时不止露出了肩膀,还露出了一侧戴乳罩的胸脯。你这一美丽的枪伤给多少中国年轻人带来了幸福的梦想哦!”
“毫不迟疑”说明对自己回答内容的记忆犹新和充满自信,而最后的语气词“哦!”与那个感叹号就更是意味深长了。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文化大革命时代文艺作品里的“性”,革命现代样板戏里出现的,不是鳏夫就是寡妇,阿庆嫂有个丈夫却在外面“跑单帮”始终没有露过一次面,江水英家的门上虽然钉着个军属牌暗示她名花有主但那位革命军人只是个影子般的存在;再来看看当时的电影:男女主人公一个个捂得严严实实,衣着单调,表情严肃,丝毫无半点“性”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镜头里我是脱下衣服露出了肩膀是不是?’谢青说是的。他说你当时不止露出了肩膀,还露出了一侧戴乳罩的胸脯。你这一美丽的枪伤给多少中国年轻人带来了幸福的梦想哦!”其实,青春期对性的觉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有了性觉醒就有对相关知识的渴求,所以在那似乎无“性”的文革时期,依然有一种叫做“手抄本”的地下文学在群众中流行,《少女之心》成了年轻人私下里的圣经、冲破“性”禁区的文字指南;不过仔细研究,它只不过是对性行为的一些简单的白描,只不过是给了青春期的中国少男少女们一些朦胧模糊的“性”想象而已。就在那个时候,阿尔巴尼亚电影来了,先是“露出了肩膀”,这对文革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就十分大胆了,然而事情不只如此,还“露出了一侧戴乳罩的胸脯”。当时的青年男女哪里听说过“乳罩”那样的洋文物品,何况与它同时映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国产影片里此路不通的活生生的洋溢青春美的“胸脯”,于是就有了“你这一美丽的枪伤给多少中国年轻人带来了幸福的梦想哦!”这样的性意识得到强烈反映的作者,也是那一代年轻人的心灵结果。
在翌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夜巡》(笔者认为:与纪实性显著的阿尔巴尼亚题材作品相比,《夜巡》和《布偶》是迄今为止的陈河作品里文学性最强的两篇)中,除了对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里“性”场面的热情回忆外,作者的阿尔巴尼亚情结在这里仍清晰可寻,“又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上演了。由于这个电影有女主角米拉换药时露出胸罩的镜头,电影院继续每天爆满,他得留在这里执勤,从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带队夜巡了”(《人民文学》2008年第11期,第86页)。原因交待得很清楚——“由于这个电影有女主角米拉换药时露出胸罩的镜头”,导致“电影院继续每天爆满”,甚至连负责夜间治安的三人小分队队长的“他得留在这里执勤,从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带队夜巡了”。陈河的阿尔巴尼亚情结之深,其情结中性意识之重,在此再次得到实证。
让我们继续《致命的远行》,“米拉告诉谢青,电影里米拉的故事是真实的,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说谢青应该去靠近希腊边境的吉罗卡斯特看一看。在那个全部用白色石头建造的山城城门口的圆形广场上,有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那树下有一个大理石雕像。雕像是个神色忧伤而严峻的少女,她在十八岁时就被德国人吊死在她头顶的这棵无花树上。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本以为作者只是说说而已,但在陈河的代表作《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里,他让主人公李松真的去了毗邻希腊的吉罗卡斯特(音译),见到了那棵高大的无花果树,目睹了那座少女的雕像。除了性意识(李松终于如愿以偿地跟一直想念的阿尔巴尼亚姑娘伊丽达进行了性结合)仍在外,笔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陈河阿尔巴尼亚情结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英雄气概。
李松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的吉普车被打开了,车上的药品被众人搬下来。马上有药剂师把普鲁卡因青霉素的箱子打开,把针剂分配到药房。这些上海第四制药厂生产的抗菌素很快被蒸馏水稀释,注入到阿尔巴尼亚肺炎病人的体内,在血液里循环,与病菌战斗。
在这中篇小说里,主人公生活在充满《宁死不屈》光影的遥想与现实里,不同的是《宁死不屈》里的英雄是跟德国侵略者作斗争的阿尔巴尼亚人,《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内的英雄则成了与阿尔巴尼亚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中国人,其中的含义可在各个层面上去理解。南方省份吉罗卡斯特出现流行性肺炎,需要抗生素针剂,而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缺少经费采购昂贵的欧美产品,中国制造的青霉素、庆大霉素、先锋霉素成了雨中送伞雪中送炭,所以开着自己的吉普车驰骋三百多公里把中国制造的抗菌素及时送到已经把药用完的医院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把中国人描写成斗病菌英雄的这一段明显来自于作者的阿尔巴尼亚情结内的英雄气概(从酷爱电影里的英雄形象升华出文学创作中的英雄气质)。
他看着监室黑黝黝的石头屋顶和墙壁,他知道这里是城堡的内部,屋顶上方和墙壁外边还是厚厚的石头。他很奇怪这个古老的城堡会造得这么精致结实,那个名叫斯坎德尔的市长曾经解说过,这个城堡在建成后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作监狱,这个说法要是真的,那么这些石室里也许监禁过古罗马时期的犯人。有一件事毫无疑问,那就是一九四四年的时候真正的米拉就是被德国人监禁在这里。而一九六九年一群演员和电影工作者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把一段历史凝固到了一盘盘黑白的胶片中。现在,他也被德国人关在了这里,说不定,这就是某种神秘的意志。
夜深了,凉气从一个看不见的通气孔里钻进来。他缩成一团,后来慢慢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被铁门打开的声音惊醒了。他赶紧坐了起来。两个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德国士兵走了进来,让李松站起来,给他上了手铐,示意他走出监室。李松想,现在带我去哪里呢?大概是去接受审讯吧?他得让他们通知伊丽达,只有她才会证明我的清白。
他走出了监室,在黑暗的通道里慢慢向前。他又看到了两边监室里的犯人,他们这会儿都一声不响地望着他,眼睛里闪着光芒。李松看见通道的尽头发着耀眼的亮光,那是外部的城市天空。李松再次想起了那部黑白电影最后的场面:米拉和女游击队员被德国鬼子押着从这条石头的通道里走出来。在那棵生长在城门口的无花果树上,绞索已准备在那里,她们正从容走向死亡。音乐在李松心里再次升起: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李松泪流满面,一阵对时间的悲喜交集的感动在心里汹涌成潮。
以上的小说结尾带来了高潮,它几乎动用了作者所能动用的各种文字激活读者的想象,这里有电影再现:“米拉和女游击队员被德国鬼子押着从这条石头的通道里走出来。在那棵生长在城门口的无花果树上,绞索已准备在那里,她们正从容走向死亡”;这里有音乐歌声响起:“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影像乐声相交织,使阿尔巴尼亚人眼里的中国英雄“泪流满面”,英雄气概充溢字里行间。
不过,《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里李松的“泪流满面”和《致命的远行》中米拉的“泪流满面”虽然遥相呼应,却已经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而是具有两种迥异的审美效应:《致命的远行》中米拉的“泪流满面”只是单纯的故乡遇他国知己的感激泪,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里李松的“泪流满面”业已是经过影像再现、音乐歌声烘托伴奏营造出的英雄氛围自然而然酝酿分娩的水到渠成的英雄泪。
这里的美学意义还不止于此,这里有时空穿越:“1944年的时候真正的米拉就是被德国人监禁在这里。而1969年一群演员和电影工作者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把一段历史凝固到了一盘盘黑白的胶片中。现在,他也被德国人关在了这里”;有过去和现今的混在:当时的米拉是“被德国鬼子押着”,而今天押着李松的也是“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德国士兵”(指为了稳定1990年代初期阿尔巴尼亚动荡政局而进入该国的北约多国联合维和部队里的德国兵),这些并不是“某种神秘的意志”使然,而完全是作者的良苦文学用心的结晶,从而让历史和现实在不同的时空里激荡回旋连接交叉,如此这般创造出来的厚重的历史感和生动的现实感,巧妙支撑并完美融汇“性意识”和“英雄气概”于作品之中,最终合力推出了最能体现陈河之阿尔巴尼亚情结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使他成功地成为引人注目的华文文学作家之一。
二、展示欧美不同经历的文学努力
在创作“自己熟悉的阿尔巴尼亚人竟然有了一种乡亲般的亲切感”(《去斯可比之路》)的阿尔巴尼亚系列作品之外,陈河也将笔锋延伸到欧美的其他部分,具体地讲,主要是指他1999年移民去北美的加拿大的人和事。
以“在移民加拿大的第二年,我和妻子决定买一座房子”开头的《西尼罗症》,并非像《蜗居》那样的寻房看房炒房贿房,而是借购房后发现邻居很奇妙、万圣节快乐又恐怖等把话锋引向主题“我要说说另外一件事”,那件事就是“我”不幸患上了西尼罗病:
西尼罗病首次于一九三七年从乌干达西尼罗河区域的一位妇女的血液中被分离出来并被确认为病原体是传播最广的黄病毒之一,它分布于整个非洲、中东和欧亚大陆南部的温带和热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估计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对此病毒血清反应呈阳性。在人群中,最大的一次流行于一九七四年发生在南非海角省,当时纪录感染此病毒的临床病例有近三千例。
西尼罗病毒主要由鸟类携带,经蚊子叮咬传染给人,引发西尼罗热,它的人际传染途径包括输血、器官移植和母乳喂养等。1997年,美国首次在纽约发现西尼罗病毒传染者,随后病毒向全美扩散,疫情愈演愈烈。有几种鸟,主要是候鸟,可能是病毒传播的主要媒介或扩散宿主。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人群中暴发疾病的巧合是大量鸟类死亡。三月中旬,美国纽约市及其周围,有好几千只乌鸦和其它鸟据推测死于该病毒。加拿大草原省份缅尼吐巴和沙斯卡楚瓦也发现大量的夜鹅和白眉雁死亡。鸟类和人群中的感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并存导致流行病学家们得出结论,即鸟类作为传入宿主可能感染嗜鸟蚊,嗜鸟蚊再感染病毒扩散宿主,最终感染人。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统计,2003年,美国四十五个州共有九千三百多人感染西尼罗病毒,死者达240人。去年又发现了2470个病例,其中88人死亡。加拿大目前感染病例已超过1000人,死亡47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合格的疫苗能预防西尼罗热。
我花了半个多小时研究这段文字,只觉得心里越来越沉。
仔细阅读上面“这段文字”,能看出陈河阿尔巴尼亚系列以外作品的特点:作品已经不像阿尔巴尼亚系列那样行云流水,而是需要上引的各国医疗机关部门公布或下发的新病毒介绍、疫情快讯般的知识积累资讯储备。这与陈河在阿尔巴尼亚和加拿大两地的人生经历、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把陈河视为“生活库存型”作家),同时也有为读者着想的一面吧:要讲的是西尼罗病,西尼罗病是这么样的一种病。
往下讲的内容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国外早有类似的突发怪病(毒)千钧一发令看者忐忑不安欲知后事(最后结局)如何的影片问世。首先“问题是我妻子摸到过一只死鸟会不会受感染呢?”(《西尼罗症》,以下引文同此)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敏感,胆子很小”的“妻子”身上,接着来了个政府部门雇用的专门负责调查北约克区飞鸟死亡事务的NORTH AMERICA BIRDSMAN(北美鸟人)优素福;“第二天是周一,我陪妻子一早去家庭医生的诊所去做检查”,由于“我有很长时间没检查过身体”就也“挽起袖子让许医生抽了好几瓶的血”,反应快的读者大概已经能够猜出结果来了吧:“许医生看见了我妻子,说:你的血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没有问题,一切正常,很健康。然后许医生转头对我说:你的血检报告西尼罗病毒呈阳性反应,说明已感染了西尼罗症,得立即接受专门的治疗”,“就这样,我糊里糊涂地成为了西尼罗病毒的感染者。卫生部对我的病例给以特别的关注,因为我是从亚洲来的移民中首例感染者”。出院后,“我”又被安排到一个康复中心做休养治疗,经常独自在湖里划独木舟自娱。
《西尼罗症》写的是“从亚洲来的移民”中成年人的不寻常经历,而发表在《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3期上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则应该定位为准成年人的平凡而又意外的经历写照。
之所以说三个主人公“平凡”,是因为马红堡和杨靖邦都是学习成绩连普普通通都很难达到的留学生,凭借其父亲们的力量来到加拿大,人地两生,精神苦闷,发泄在吃喝玩乐上,竟也都开上了所谓的名车;女孩子周琴倒是“读书成绩很好,已经在约克大学读书了”(《我是一只小小鸟》,引文下同),但她的家境不如那两个男学生,学费“得靠自己去挣。约克大学留学生的学费实在很贵”。这些,在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生里并没有特别之处。
说“意外”是作者(根据那些实际发生在加拿大的事件的中文媒体报道及个人博客)设置的结局都很悲惨:周琴在挣钱过程中不幸落入黑道之手,“被锋利剃刀割断喉管”身亡;喜欢周琴的马红堡悲恸欲绝协助警方破案,被黑道盯上,最后在深夜歌厅遭到暗算,“持枪者二话没说,对着杨靖邦的脸部开了一枪。杨靖邦的脸部组织炸了开来,应声倒下。年轻的枪手转过身,对准了马红堡的身体,一连开了九枪,把弹夹里的所有子弹打完。他换上弹夹,又朝马红堡胃部打了两枪”。这两个年轻的生命也像周琴那样,青春尚未完全绽放就凋零在异国他乡。
陈河在关于这个作品的《创作谈:成长的代价》里如是说:
这个小说就是个故事吧,可能没有很深的含义,属于福克纳所说的那种“轶事”。我用小说来表示一点对死去的学生的纪念吧,他们差不多已经被人忘记了。对于国内将要出国留学的孩子和家长们,也许会有点提醒的作用。
作者对发生在加拿大的留学生命案表示纪念,完全可以理解;出于为了忘却的纪念而动笔写文章也早有先例。只不过除了纪念外,可能是作者“对于国内将要出国留学的孩子和家长们,也许会有点提醒的作用”之写作动机太先行太直露的缘故吧,这篇作品几乎“就是个故事”,而且“没有很深的含义”,倒是其中对加拿大的衣食住行,尤其是那里的预科语言学校、大学的情况有不少描述。所以,它虽然名为小说,但就其内容写法而言,似乎更接近报告文学,甚或称其为加拿大留学之文学指南,也未尝不可。
三、“马共”题材作品得失谈
进入2010年之后,陈河开始进军马来西亚的抗日故事的写作。此种故事在马来西亚并不新鲜,因为经历过的人都会深深铭刻心间,而年轻一代也会通过历史课、历史书、家庭环境等程度不同地有所知晓。但,马来西亚之外、居住在遥远的加拿大的华文作家写出一两个那么长篇幅的东西来,就有些引人注目了。这是一得。
其实,关于这个题材早就有人写过,而且在历史并不短的马华文学中已经有了可观的业绩。不过,陈河此作另辟蹊径,是从家里看一位华裔老兵的参军经历中受到的启发,在互联网上进行查寻,又参考当年老兵的回忆录及历史资料,写成了以加拿大华裔军人远赴马来西亚作战的《沙捞越战事》,其中的加拿大与此有关的部分,可以说是填补了空白;而近日见铅字的《米罗山营地》中的那些故事对于熟悉“马共”题材的人来说也多是老生常谈了,不过西碧儿·卡迪卡素(Sybil Kathigasu)夫人及其所著的《悲悯阙如》(No Dram of Mercy)通过《米罗山营地》能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知的话,倒是非常有意义。以上这些都应当肯定。这是二得。
然而,“失”也不少。
从《沙捞越战事》谈起吧。
此书头绪纷繁,资料杂乱,主要是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因为有了互联网”(《沙捞越战事》,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作者把从网上收集到的杂学知识一股脑地拼凑到这本书里(相关知识的拼合粘结,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此后的同类题材成品《米罗山营地》的最大特色),这是其一。
作者移民加拿大,故英语资料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第二大来源,书中不时出现英语,如第61页、第128页、第199页等可为例证。
此书除了网络知识、英语资源外,还用相当多的篇幅涉猎日本人、日语、日本文化。这倒不失为一种创举,问题在于写得是否符合日本的真实。举一例:
“闭上你的嘴,把你的舌头打上结。”周天化说。把舌头打上结是日本的谚语。
既然作者十分肯定地指出“把舌头打上结是日本的谚语”,浅学的笔者先是翻遍各种日语词典,然后是询问日语为母语的众多朋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觅见“把舌头打上结是日本的谚语”的原文出处。既然作者胸有成竹,倘若能把“把舌头打上结是日本的谚语”的出典用平假名、片假名,或者用除了遣隋使、遣唐使带到日本的我国汉字外的日本人制造的所谓“国字”写出来,都会具有说服力。
以上来源以外,可能是缘于作者青少年时的知识积累、成长经历,特别是文革时代的人文储备吧(二律背反的是,它们却也成了作者的阿尔巴尼亚作品系列的底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成就了华文作家陈河的文学原动力),对活跃在丛林中的华人游击队及其领导人的描摹多有文革腔调,例如“我不知道你们在北美的生活怎么样?听说你们喝不到牛奶,因为那里的资本家们喜欢把牛奶倒进大海里去”(《沙捞越战事》第63页)等,透出浓郁的文革教育色彩。
陈河的《沙捞越战事》于2010年10月出版(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见该书封三),自然他写作这部与马来西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小说是在出版之前的事情;而陈河最新发表的《米罗山营地》的开头,读完全部文字便知那其中的“我”就是陈河的开头,是这样的:
二〇一〇年圣诞前夕,我买好新加坡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去拜访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老兵梁元明先生。起飞前我发邮件问他我得去马来西亚哪个城市找他,他回答说他根本不住在马来西亚,而是住在台湾台北市。
我这人做事粗心大意,老是会摆乌龙,可这回的差错还是有原因的。我和梁元明老先生在网上认识已有两年,几乎每次的话题都是有关抗战时期特工人员在马来亚的渗透潜伏和丛林游击战,以致我脑子里会根深蒂固地认为他是住在怡保或者吉隆坡。
作者“和梁元明老先生在网上认识已有两年”,实证了笔者在前面指出的陈河写作马来西亚题材的主要资料来源于网络;“几乎每次的话题都是有关抗战时期特工人员在马来亚的渗透潜伏和丛林游击战”,挑明了《沙捞越战事》也罢,《米罗山营地》也好,其话题(素材)有很大部分是台湾梁元明老先生提供的;而“以致我脑子里会根深蒂固地认为他是住在怡保或者吉隆坡”,才是笔者的学术关心所在,就是说:在“2010年圣诞前夕”(12月的圣诞的两个月前,《沙捞越战事》已经出版),作者还没有脚踏实地到过马来西亚,因而对马来西亚的地理、历史、文化缺乏实际全面深入系统的了解和理解。这,便引出了《沙捞越战事》的许许多多有关马来西亚描摹的不实、不妥。在这里,只就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展开探讨。
1930年的时候,李立三、瞿秋白批准组建了南洋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发展壮大。日军入侵马来亚前夕,英国当局和马来亚共产党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让共产党的活动合法化了。马来亚的华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义勇军参加战斗,可由于英军的大溃败义勇军的抵抗起不到什么作用。
以马共领导的游击队为主要素材的《沙捞越战事》里的这些文字,跳跃性甚大,含混不清之处颇多,“南洋共产党”和“马来亚共产党”是什么关系?马来西亚在地理上分为西马(马来半岛)与“东马”(婆罗洲北半边,具体指沙捞越和沙巴),东西马之间的各种不同造就两地的华人各有特色,“马来亚的华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义勇军参加战斗”岂不是有些太笼统太大而化之了?特别是“1930年的时候,李立三、瞿秋白批准组建了南洋共产党”,作者又是根据什么如此断言的呢?能像他三番五次地在《沙捞越战事》中明确写出英文资料的出处那样,为读者明示有关“南洋共产党”变成“马来亚共产党”的确凿证据吗?
回答上述的重大问题(因为马共题材本身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仍有种种禁忌)不是道听途说或网络搜寻就能仓促完成的,最可靠最翔实的证言应该是马来亚共产党自身的声音。下面就让我们倾听它的声音,资料来源自白纸黑字的马共言论集《南岛之春》:
马来亚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是在一九二五年就产生出来的,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更加紧的压迫剥削的时候,同时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的推动世界革命的浪潮,不仅是西方的无产阶级不断地爆发了英勇的斗争,而且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劳苦大众也都觉醒起来。于是在马来亚的先进的中国同志,便在这环境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在那时候的党部,事实只是中国党的海外支部,组织非常狭小,党的组织与工作都建立在中国民族的店员洋务树胶工人上面。
一九二六年党成立了南洋部委的组织,这时工作逐渐发展到南洋各地,在一九二七年便召开南洋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这时由于年青的南洋共产党员经验的不多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党的组织仍不能向前作应有的发展。
一九二九年南洋共产党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确定了马来亚的革命性质和总的奋斗的基本方针,同时由于各同志能够提高布尔塞维克的战斗精神,便使党的平凡软弱的组织,逐潮转变到坚强战斗的组织。
一九三〇年南洋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站在保障工人阶级劳苦群众的切身利益而英勇奋斗,这便进一步的唤醒了马来亚工人劳苦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反资反帝的斗争情绪,推进了马来亚的革命浪潮。
以上引自1946年1月15日由马来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马共言论集之一 南岛之春》。此书在前言之后,分出四大章:(一)共产主义浅释,(二)共产党,(三)马来亚共产党史略,(四)马共的主张与策略。上面的引文就是来自第三章“马来亚共产党史略”部分。对照上述马来亚共产党自己撰写的史略,我们不难发现《沙捞越战事》里的“1930年的时候,李立三、瞿秋白批准组建了南洋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发展壮大”,与历史事实是有许多出入的。
到了2012年8月发表在杂志《中国作家》上的《米罗山营地》的时候,陈河以其马来西亚之行打底子,言之有物多了,读起来也可以产生不少真实感,而除了把西碧儿·卡迪卡素(Sybil Kathigasu)夫人介绍给中国读者、把林谋盛的事迹展示出来、揭秘一三六部队的一些细节等外,《米罗山营地》最大的缺憾恐怕应该是其文学性的匮乏。虽然作者说它是“非虚构的作品”,但既然《中国作家》将其明显标示为“长篇小说”,小说所应具有的文学性、艺术特质、审美感召力该在这里存在。而实际上,那些文艺要素在印为“长篇小说”的《米罗山营地》里却稀薄渺远(换言之:其文学价值不高;欠缺艺术之美),因为它留下的总体印象读后感受是:用字讲马来西亚的抗日故事。
在中国,抗日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源源不断:正面战场,侧面游击,地道地雷,埋伏突袭,平原作战,敌后杀敌,军统中统,潜伏卧底……可以说“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可能是制作过快、情节雷同、人物似曾相识等缘故吧,抗日题材文艺创作如何创新成了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而在这一意义上,陈河取道国外(马来西亚),把发生在那里的、不大为国内读者所知悉的抗日故事写出来,其创新精神还是值得首肯的。
①陈河:《致命的远行》,《收获》2007年秋冬卷,第161页。
②③陈河:《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4期,第73页;第90页。
④陈河:《西尼罗症》,《人民文学》2008年第6期,第10-11页。
⑤陈河:《我是一只小小鸟》,《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3期,第31页。
⑥⑧陈河:《沙捞越战事》,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第60页。
⑦陈河:《米罗山营地》,《中国作家》2012年第8期,第139页。
⑨载2012年10月9日第11版《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