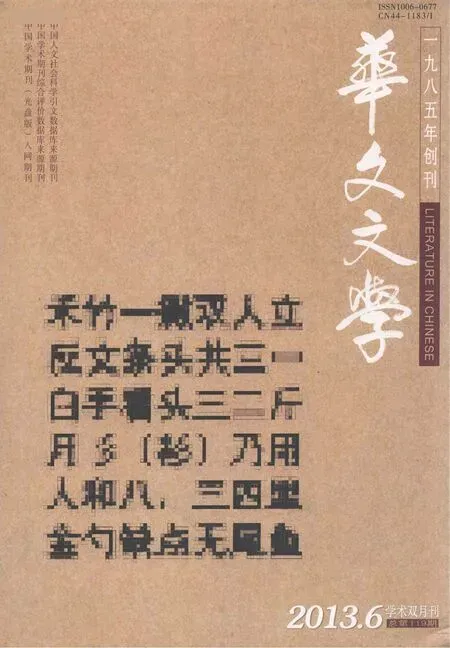从法语中国小说到华语法国电影——重塑戴思杰《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不同叙述模式的对话对象
2013-11-16陈荣强袁广涛宁译
[美]陈荣强/袁广涛 安 宁译
2000年,旅法导演戴思杰用法语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这是一部半自传性作品,以作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青经历为背景。小说一炮而红,在国际上引起关注,被译成25种语言,并获得5项文学奖。2002年,戴思杰自己把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作为法国电影在国际上发行,尽管电影对白是四川方言。在亚洲,电影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上映。虽然没能在中国大陆获得发行许可,但是那里的观众轻易就能买到影片的盗版DVD。本文试图考察面向法语读者的小说被改编成面向更广泛观众的电影,其重心的转变如何使文本的身份变得复杂,声音及视觉语言的使用如何改变了书写文本的意义。
作者戴思杰在文革期间是一个被遣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城市青年。在山区劳动了四年之后,他返乡完成高中学业。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戴思杰考上大学并获得艺术史专业学位。1984年戴思杰远赴法国,在法国电影学院学习西方艺术与电影。
戴思杰的小说处女作《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围绕两个被派到天凤山劳动的青年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这两个年轻人偶然发现了一箱当时被看作禁书的欧洲小说,并完全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为了分享阅读的快乐,他们轮流给中国小裁缝——他们同时爱上的一个姑娘——读书听。最后,中国小裁缝由一个天真少女蜕变为成熟的青年女性,她选择走出天凤山,到外面的世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作为文化使者的小说
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以小说叙述者和阿罗在文革期间来到天凤山开始。他们被遣送到那里接受再教育。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传统叙事模式。故事开始时,叙述者在讲述他和当地村民的初次碰面:
这个村的村长,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盘腿坐在房间的中央,靠近一个在地上挖出的火炉,火炉中燃烧着熊熊的炭火;他仔细打量着我的小提琴。照他们看来,在阿罗跟我两个“城里娃儿”带来的行李中,只有这一件家伙似乎在散发着一种陌生的味道,一种文明的气息,也正好唤醒了村里人的疑虑。
小说从一开始就暗示,叙述者不只是在讲述他接受再教育的故事,而是通过使用“陌生的味道”、“文明”这样的字眼来表明一种对村民的优越感,从而使读者随他一起对天凤山进行“精神征服”。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叙述者对故事的控制不断加强。即使小说的后半部分穿插着阿罗、中国小裁缝及老磨工的自白,但叙述者把这三种个人叙述融入他对往昔的回忆,依然掌控着故事的讲述。小说以线性方式展开,复述了叙述者和阿罗的改造经历。
小说叙述中困扰我们的是叙述者讲故事的语言,在结构层次上说,即作者的语言。小说以中国为背景,时间限于文化大革命,但是戴思杰的创作语言是法语,即使在结构上,法语与任何中国语言都相距甚远。戴思杰写这样一部半自传性作品,可以说是出自一种天真的愿望,希望保留一段重要的个人记忆。但《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最初是写给欧洲读者的,尤其是法国读者,这就必然让我们对它的文本完整性产生疑问。叙述语言不可避免地离间了小说主题(叙述者的过去)和法国读者,使小说无法完成作为文学作品的识别功能。然而在这个表现下乡经历的文本中,离间不一定是坏事,经历和接受在表现上分裂,对作者也会是一种动力,因为作者担负着类似译者的使命。瓦尔特·本雅明认为译者必须面向语言的整体,以便揭开源语的隐含意图,而这只能通过翻译完成。翻译行为使源语及其意图得以重现。通过区分译者和诗人的不同任务,本雅明认为翻译不应限于传递信息,而应帮助揭示语言间的相互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一个接触区域,为了超越语言,更好地相互理解,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协商。一旦读者意识到叙述者扮演了文化传播人的角色,小说中法语的支配地位立刻会有所变动。在创作《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过程中,戴思杰作为一个文化译者的使命是描述一次经历,同时避免在西方框架影响下把中国文化自我东方化。换句话说,通过避免真实地表现独特经验,戴思杰为本土叙述者和外国读者勾勒出一个接触和交换的空间。然而问题是像戴思杰这样的文化使者用第二语言写小说时会有什么风险?他如何能够避免诸如通过文学审美自我东方化之类的批评。
虽然多元文化主义本质上是伪善的,我们还是能从其话语中受益。因为创作语言是法语,《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勉强可以算作法国小说,这不仅说明了法国文学环境的开放性,也赋予文本一种自由,使其不必传达一种有自我东方化危险的独特而具体的中国经验。这种假定无疑暗示了法国文化总体来说政治性不强。如果《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中经验的独特表现是一种文学再现的话,作者必然要描写小说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这就无意中在法国小说里面体现出中国文化特异性。然而小说目的在于阐明文学经验的伟大,对于小说人物来说,他们通过阅读行为获得这种经验。
阿罗和叙述者都知道他们的再教育来自他们所读的禁书,虽然国家意识形态宣称这些书会毒害青年人的心灵。两人始终在阅读现代中国著名作家翻译的俄国、英国和法国小说。远离他们熟悉的城市生活,他们觉得和书中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毕竟小说主人公们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同样被迫背井离乡。偷偷地浏览完另外一个下乡青年——四眼的箱子后,叙述者这样形容自己的兴奋:
本次展览是继“丝路之光·2015中韩雕塑邀请展”“丝路之光·2016敦煌国际文博会雕塑展”后又一次盛典,旨在促进本土雕塑家相互认识、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增强凝聚力,强化创新精神。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讴歌党、讴歌祖国和人民、讴歌英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彰显时代特点,反映社会风貌,弘扬甘肃精神,不断提高甘肃雕塑创作水平,为推动甘肃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做出新的贡献。
伟大的外国作家们正伸开了臂膀在这里欢迎我们:在他们的最前头,是我们的老朋友巴尔扎克,有他的五六部小说,接下来就是维克多·雨果、司汤达、大仲马、福楼拜、波德莱尔、罗曼·罗兰、卢梭、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几位英国作家:狄更斯、吉卜林、爱米丽·勃朗特……
还有一次,叙述者提到了《堂吉诃德》,一部小时候他姑姑给他念过的西班牙小说(51)。小说在开头就提到《堂吉诃德》,预示了小说中人物的转变。堂吉诃德爱读骑士故事,沉湎于自己的幻想当中,并且像骑士一样出门远征冒险。尽管他的妄想让他吃尽苦头,在他返乡辞世之前,他完全接受自己的梦想,并享受其中的快乐。阿罗和叙述者都未曾料到他们的生活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比他们被要求接受的再教育更有益处。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生命演变,阿罗说他给中国小裁缝读巴尔扎克是想让她受些教育。书籍间接地改变了中国小裁缝。而且让阿罗和叙述者大为惊讶的是,在他们当中小裁缝的变化最大。从大仲马《基督山伯爵》的女主人公身上,小裁缝最终意识到作为一个性别个体,自己也有性欲与尊严。在小说的尾声,她能够第一次自己做主,决定离开天凤山,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通过讲述一个突出书写文本力量的故事,小说使我们借助阅读,参与可能发生的转变的过程。
从小说到电影
2002年,戴思杰把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改编成同名电影。这似乎是顺理成章,毕竟戴思杰是个导演。但是因为需要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协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往往让人觉得乏味。它会产生这些问题:书写文本变成视觉意象会损失什么?电影表达什么主题才能维持视觉创造性和文本原创性的平衡?是否必须把电影忠实地拍成小说的视觉再现?电影应该针对哪类观众?
电影的第一个场景就泾渭分明地区分了文本的电影形式与书写形式。电影一开始,叙述者和阿罗走在去天凤山的山路上。镜头扫过周围美景来制造一种电影审美,这种审美说明了电影的一个特征,用汤姆·冈宁的术语来说,就是“吸引力电影”。冈宁认为电影不仅建构线性的和传统的叙事,而且使用不同形式的视觉再现来表达电影主题或实现电影目的。这些形式,例如视觉奇观,除了以传统叙事模式讲述故事外,还带给现代观众新的时空观赏经验。这不仅拓展了透视法,而且促进了现代视觉文化的兴起。
这样来说,讲故事就不再是电影《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主要任务。电影的叙事性不是由传统而是通过现代技术和电影语言创造的视觉刺激建构的。我们作为观众以镜头为眼睛,变成了故事的旁观者,避免了单一叙事造成的具有限制性的单一视角。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好像能更好地掌控旁观者对故事的评价,从而摆脱了任何叙述者的操纵。在整个观影过程中,非限制性的叙事能够赋予观众一种自我主体性。即使知道还是有一个叙述者在讲故事,我们不再感觉必须要信从他的旁白。我们认同镜头,变成了窥淫癖,因为这样能满足我们对信息和知识的欲望。这种视角总是有问题的,因为在电影屏幕前我们永远不是自由主体;而且电影屏幕给予我们的是一个把我们带入大银幕虚幻世界的视角现实。在《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中,最能代表想象的偷窥姿态的场景是当村民们从四周赶来检查阿罗和叙述者所带物品的时候,镜头从屋内转向屋外风景。电影中始终穿插点缀着乡村美景。把乡村审美直观化不一定就是政治上不道德的,尽管有人会说这种手法有风险,会把中国描绘成落后的和有异国情调的,甚至是无意识地这样做。文学和文化评论家周蕾在她的《原初的激情》一书中认为把中国美学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积极意义。注意到这种美学化是“原初主义”,周蕾解释道:
……在政治化了的现代性(过程)中,“原初主义”不是对不再可能的过去和文化的渴求,而是指一种一厢情愿的思维,即由于某种原因,“中国”乃是第一的、首要的以及核心的。原初主义的两面手拉着手:将旧中国美学化成“古代”和“落后”必须与现代自强和社会建设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而后者继续以对中国第一和独特性的强调弥漫在民族主义的文化生产中。
尽管把中国视觉表现为“落后”和“原初”暗示了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永远的纠缠中东方主义的永久化,周蕾依然乐观地认为,“自我东方化”的姿态可能是一种恰当的策略,用来强化中国身份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对中国和外部世界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交往都是有用而且必要的。按照周蕾的逻辑,尽管从一开始就难以界定电影《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国籍——一部法国作品,使用了大量的中国乡村画面,并把这些画面与观众对旧“中国”的想象联系起来,电影所达到的效果却超出了导演的本意,即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体现了一种无法确定国籍的复杂身份;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可以帮助现代中国参与由离散人口推动的世界文化生产。就这样,一个特殊主义的中国通过普遍主义的话语被描绘了出来。
电影版《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重要价值在于把书写文本介绍给更多读者。让人意外的是,戴思杰对电影改编好像相当谨慎。就情节和故事来说,电影和小说相差不大。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戴思杰采用了电影史上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已为观众所熟知的视觉手法。中国小裁缝第一次出场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在这个场景中,周迅扮演的中国小裁缝在和阿罗(陈坤)、叙述者马剑铃(刘烨)调情。这就像约瑟夫·冯·斯坦伯格的电影《金发维纳斯》(1932年)中奈德·法拉第(赫伯特·马歇尔)和海伦(玛琳·黛德丽)初次相遇的场景,当时海伦和女伴们正在池塘中洗澡。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电影的尾声,场景是一间逐渐被洪水浸没的房子,里面有一台缝纫机和叙述者从法国买给中国小裁缝的香水。作为记忆意象的水慢慢注满了房子,而房子在空间上象征了叙述者的过去,包括缝纫机所代表的他的青涩的爱。对叙述者来说香水瓶封起了记忆,对观众来说则给电影画上了句号。观众几乎马上就能认出这借鉴了詹姆斯·卡梅隆的流行大片《泰坦尼克号》的主题。前一个场景通过讲述阿罗和中国小裁缝的相遇、调情预示了两人之间可能会有恋爱关系,而后一个场景象征着叙述者青春记忆的湮没与消褪。这样来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电影改编不仅使用了四川方言,而且使用了电影叙述的技术语言。
上文已经提到,电影《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身份比小说的复杂很多。既然小说因为创作语言是法语而被看成法国小说,那么电影的四川方言对白又能赋予电影什么身份呢?使用四川方言如何能重塑电影的目标人群呢?
电影《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作为法国电影发行,并代表法国角逐2002年的奥斯卡奖。电影的身份使一个涉及国家和文化问题的文本表现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借用托马斯·艾尔塞瑟对于德国新电影的分析,周蕾这样解释道:
……电影中至少有两种翻译。第一是作为编列入册的翻译:一代人、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被翻译或置换进电影媒体中;第二是作为传统转化和媒体之间转变的翻译:一种定位在书写文本方面的文化正处在转变过程中,并正被翻译成由意象支配的文化。
《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好像返回到了电影摄制的基本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在图像生产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国家或文化表现,这对艾尔塞瑟的民族电影概念形成了挑战。任何试图把小说转换成铭文电影的尝试都会受到含混性的视觉表现的困扰。无论如何,“视觉和主题中国”电影在文化和民族方面都不可能是“真正”中国的,因为作为视觉铭刻,法语片头字幕极大地瓦解了影片作为中国电影的“真实性”。电影使用远景,把环视天凤山景色作为叙事银幕空间的内容。这种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复制传达了一种文化和种族特性,使用中国民歌作背景音乐也强化了这一特性。然而,视觉再现和听觉再现的统一受到了非剧情的片头字幕的干扰,因为字幕语言只有法语。同样的,导演想把政治议题写入电影也干扰了电影框架内的传统转型。作为对过去一段时间的结构性记录,小说结束时有一种封闭感;换句话说,传统被书写语言改变,就这本书而言,受到了法语的改变。电影以叙述者看到因为三峡工程,天凤山即将被长江水淹没的新闻后回到中国而结束。三峡工程于1994年开始建设,竣工之后,这部电影的很多摄制地都会被淹没。电影表达了戴思杰的哀伤,也隐含着对中国政策的反对,这就破坏了小说的整体性。电影的民族主义立场转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电影的首要目的并非刻画成长历程。在个人层次上,它确实意义重大。对戴思杰来说,这一地区被淹没意味着他的青春记忆最终会随着时间和现代化而消逝。这样,电影作为法国作品的身份和电影表达的针对政府规划的中国民族主义主张在表征上的差异就产生了一种矛盾。乡愁只有在追忆往昔的精神空间中才是安全的。在戴思杰的电影改编中,回忆这一私人领域和公共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
如果当初戴思杰放弃书写“中国”,那他还会在电影版《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中重新灌输他的政治立场吗?文化生产层面上的政治议程是策略性的,它可能会满足观众想在银幕上看到“中国”的欲望。戴思杰加入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吸引观众参与他的保护中国原始美学免受现代化和工业化侵坏的计划。从这个角度上讲,带有政治意味的结局在观众和导演的愿望之间发挥了调解作用。这种姿态更直接地把女性作为国家建设意识形态的场所这一意象强加到中国小裁缝身上。小说没有表现这一层次,因为小说的重心主要在于探讨阅读改变个人的力量。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小说强调阅读经验,而电影版《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通过使用不同的叙述媒介抹杀了小说主题的意义。
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这一反讽因为电影依赖视觉效果而变得明晰。如果观众变了,那么这种转变是通过视觉刺激而不是小说所暗示的阅读来实现的。任何比较小说和电影可信度的尝试都没有意义。在讨论媒体特质这一主题的时候,诺埃尔·卡洛尔强调每种媒体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其他媒体相比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这样来看,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和小说的电影改编应被看作两个不同的方案。小说的作用是通过文学的影响,引导读者走向自我启蒙。电影作为技术媒体,使用视觉意象来增加观众的观赏快感,并通过展示优美风光营造乡愁气氛,这样既能表达导演缅怀往昔的哀伤,也能满足观众的窥探欲望。通过考察《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不同叙述模式间重心的转换,我们不仅能阐明两种不同文本表现的具体特征,还能通过比较小说和电影,明白为什么每种表现要采取独特风格来阐发故事的意义和达到作者或导演的目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①1966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政治工具,用来维护毛泽东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对抗反对党派。这个政治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和社会领域。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上山下乡”政策,大约一千七百万城市青年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这一政策开始于文革之初,到1976年文革正式结束后两年才结束。为了证明这一政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1968年宣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上述数据和毛泽东语录引自周雪光和侯立仁的《文革的孩子们——中国的国家和生命历程》一文。
②关于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把意义从一种语言传送到另外一种语言,本雅明这样解释道,对他来说“译者的工作是在译作的语言里创作出原作的回声,为此,译者必须找到作用于这种语言的意图效果,即意向性。翻译因为这一基本特征而和诗人的工作不同,因为诗人的努力方向从不是语言自身或语言的总体,而仅是直接地面向语言的具体语境。”这段引文来自[德]瓦尔特·本雅明的《启迪:本雅明文选》中的《译作者的任务》一文。(译者注:译文引自三联版《启迪:本雅明文选》中张旭东所译《译作者的任务》,略有改动。)
③[美]汤姆·冈宁把“吸引力电影”定义为展现作为视觉审美和刺激对象的图像的艺术。冈宁的具体定义是:“究竟什么是吸引力电影呢?首先,它本身具有莱热所赞赏的那种特性,即有能力呈现某些事物。与克里斯丁·麦茨分析过的窥淫癖层面相比,这是一种裸露癖电影……这种电影展露着它的视觉特性,它意欲撕破一个自闭的虚构世界,尽可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230)。上述引文来自冈宁的论文《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该文被收入《电影理论文选》一书。(译者注:译文出自范倍译《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该译文发表在《电影艺术》2009年第2期。)
④《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引文出自第一部分“视觉、现代性和原始的激情”,第36-37页。(译者注:译文引自孙绍谊所译《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美]周蕾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8-59页。)
⑤尽管在周蕾的文章中未被专门提及,这个概念呼应了后殖民主义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
⑥《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引文出自第三部分“作为民族志的电影;或,后殖民世界中的文化互译”,第182页。(译者注:译文引自孙绍谊所译《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美]周蕾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70页。)
⑦引自[美]诺埃尔·卡洛尔的《艺术媒介的特异性》,该文收入《电影理论文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