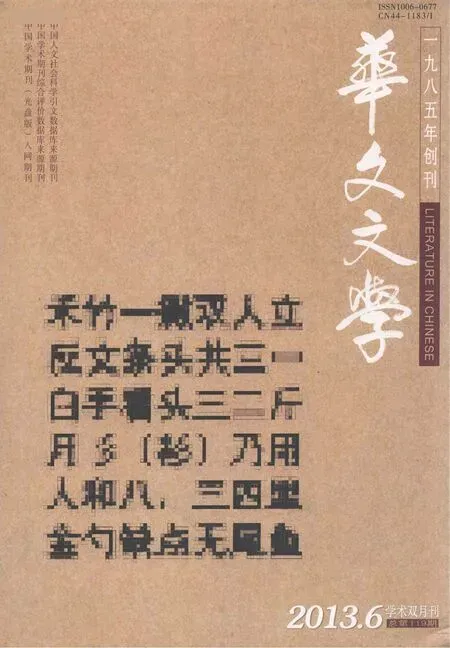英伸之眼与黑暗之心——19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运动与文学的互动
2013-11-16李娜
李 娜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北京 100732)
1986年1月,曹族(邹族)少年汤英伸在台北犯下命案。案发到死刑执行的一年多里,以摄影报道杂志《人间》(1985~1989)为中心,媒体、文化界、学术界和许多社会大众组织参与了“救援汤英伸”的运动。山地少年杀人案件的背后,是一个富裕社会的“黑暗之心”:少数民族在台湾社会中的困境;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价值沦落;威权社会的结构性压迫。有关“汤英伸”的报告文学、诗歌、小说,不但是运动的一种直接表现形式,召唤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自觉,也推动着运动从当下的揭示真相、抗议不公,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历史认知。
一、“拿开那只遮住阳光的手”
汤英伸杀人作为普通社会新闻在报纸、电视中出现,《人间》杂志以对台湾少数民族状况的了解,立刻知觉其中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跟踪报道。随着汤英伸背后的社会问题一点点呈现,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学生开始参与救援或讨论。
第10期《人间》的读者来信中,有人称汤英伸为“另一种形式的莫那·鲁道!”1930年带领泰雅·赛德克人发动日据时代最大、最决绝的抗日行动的莫那·鲁道,是原运提出的反抗精神的象征。与之相关的,“出草”、“番刀出鞘”成为原运的语言,展示的是原住民运动诉诸“抵抗”意识的策略。但“另一种形式的莫那·鲁道”的宣言,显然并非《人间》的立场。《人间》的汤英伸案报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原住民形象,是从阿里山迢迢赶到法院,为他们的“弟仔”的犯罪而“抽搐、落泪”却说不出话的曹族父老。这个形象,同英伸的忏悔、汤保富的献祭一样,以其柔弱真挚,以其身为弱者、被压迫者却成为罪人的荒谬现实,引人追究。汤英伸案无意中启动了原运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诉诸“共同处境”和“人间品格”的,不只获得知识、运动阶层的支持、而能唤起更普遍的大众关注的方式。
但这个“愤怒之声”仍有其必要性,因为被唤起关注的大众,对“民族歧视”的反省,基于“同情”,甚而不脱其文明优越意识。
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为山地人的苦难和希望歌哭的诗人,毋宁是本能地把汤英伸的悲剧,放置于民族压迫的视角。《人间》第20期《我把痛苦献给你们》的刊头,是他写的诗:
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是这样地黑暗
可是,太阳已经下山了
遮住正义的脸
使我看不见那双黑暗的手
在这孤寂的夜里
我的泪水淋淋
乃是因为我听到同胞的哭泣
亲爱的,告诉我
到底是谁带来这么多的苦难?
……
请你拿开那双遮住阳光的手
分给我们一丝温暖
用我们的血汗
换来明天
也换来挂在孩子脸上的春天
或应该说,即便汤英伸并未承受直接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也在其阴影之下。遮住阳光的手,遮住了山地孩子的希望。
遮住阳光的手,是什么呢?
《人间》第24期(1987年10月)的副刊上,刊载了布农族作家田雅各的短篇小说《忏悔之死》。玉山东埔的布农老人利巴,在醉酒中,抢劫了一个来东埔游玩的汉人家庭。夜晚,祖灵、鬼魂、上帝和汉人警察纷至沓来地入梦,利巴在梦中经历忏悔、逃亡的身心折磨,终于在黎明“蜷缩着死去”。小说俨然有着汤英伸案的影子。但犯罪的不是少年,而是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他犯下了在他清醒时,以他在狩猎生活中习得养成的道德品格,以他在部落里受人尊敬的年纪,绝不可能犯下的“抢劫”之罪。引发体内恶灵作祟的是酒精?而对酒精病态的耽溺和依赖是为什么?是为了这个在汉人中间商的盘剥和政府变相的土地劫掠之下的生存困境,是为了生活在汉人轻蔑的眼光中,无处可以发泄的愤懑。利巴一念之间犯罪的导火索是:利巴的族人,搬到新东埔去的巴路干,为女儿治病借钱回到东埔,却没有一个杂货商肯借给他;吊桥上,服色鲜亮的一家三口汉人游客,让利巴想起自己因无钱治病而耽误死去的孙女,想起眼前巴路干生病的女儿。
田雅各为利巴的“犯罪”,由远而近地进行了充分的辩护,其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台湾少数民族整体的困境。但“以暴抗暴”的抵抗本能,并非在法律和道德的层面,而是在荣誉、信仰和尊严的层面上,遭到了利巴内心的审判。
在现代之前的部落,一个拥有出色狩猎技能和经验的老猎人,是财富,而在被现代急遽冲击的年代,老人的意义随着凋零的传统生活消逝了。以勇敢、责任、分享、欲望的克制为本的狩猎文化所养成的猎人,竟然抢劫弱小!这一“堕落”带来的自责和耻辱,对利巴来说,毋宁是比汉人世界的律令严酷得多。
与此相伴的则是来自祖灵的谴责。在布农人的祖灵信仰中,善灵雷哈宁护佑人,恶灵哈尼杜则惩罚人的错误。在利巴的梦境中,桥上的女人化成哈尼杜,逼视利巴。如何从罪恶感中解脱?利巴召唤童年。犯错的利巴会受到母亲的惩罚,而这是“布农无形的道德及社会有形的法律”以及善灵雷哈宁,都无法替代的。但对母亲的怀想只能加剧利巴的痛悔,利巴辗转煎熬,转而求助于上帝。梦境中展现的利巴的信仰世界,毋宁是充满纠缠和歧义的。想起上帝是因为想起牧师讲的“出埃及记”。耶和华为帮助犹太人,将埃及士兵淹死在红海里。为了正义,为了民族的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上帝不也这样吗?这个故事,本是犹太人从其民族立场回望的生存史,与新约中耶稣的基督精神大不同。但犹太人的耶和华,与耶稣的上帝,并不为利巴区分。利巴在此期求上帝,恰恰投合了这个故事产生的民族历史背景。强烈的被侵害欺骗的悲情,让利巴选择了犹太人的耶和华,并且与自己的切身经验关联起来:利巴的父亲年轻时曾因交易山货受汉人的骗,愤怒地告诉他的儿子:为了生存,布农人可以使用令人作呕的手段,但只限于对付非常强大的外族……
利巴想向牧师忏悔,因为他想起来,上帝是唯一愿意赦免人的罪的神!自从上帝“被介绍来部落,从未像这一刻与上帝如此接近”。上帝站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点头不说话,像长者赐给幼年者的承诺,毫不犹豫”。利巴终于“舒畅”了。这个情节反讽而哀伤。在如利巴这样的老人身上,基督漂浮在“实用”的表面,嵌入灵魂的,仍是部落的祖灵信仰。
1980年代的原住民知识分子,多经历过在祖灵传统、基督信仰与现代化意识的夹缝中,精神重建的艰难。田雅各的本职是医师,并且以史怀哲的宗教奉献精神自励,投身于偏远地区如兰屿等地的医疗服务。作为以小说透彻地展示山地民族的处境和台湾社会结构不平等问题的原住民先驱作家,基督信仰和医生的身份,虽然使得田雅各的作品在处理原汉关系时更多求取和解、寄期望于进步的宁静色彩,没有许多年轻些的原住民作家常常抑制不住的悲愤。但田雅各的“宁静”亦是革命的宁静。正如在这篇小说中,利巴自认为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但“法律”不赦免他,利巴最终并非死于“忏悔”,而是死于抵抗梦中“执法者”的追逐,“宁死决不屈服于执法者”。所以,这暗含着汤英伸案影子的故事,翻转了现实中汤英伸作为接受现代教育并以现代价值为准则的、似乎不可避免的山地人汉化/现代化之路。
田雅各《忏悔之死》对汤英伸的回应,与莫那能“拿开那只遮住阳光的手”的吁求,有内在的一致性,但作为讲故事的小说,《忏悔之死》不但具化了山地人生存的困境,而且进一步探入信仰的领域。即便皈依“被介绍来的上帝”,山地人也不能免罪于“内心的道德律”,但也因此,不肯以泛泛的“宽赦与爱”作为原汉和解的根基——《人间》之前有关汤英伸的报道,以及发动包括媒体、原住民团体和基督教会共同为汤英伸和苦主家庭募捐的广告里,“宽赦与爱”是其口号吁求,是关注汤英伸案的人们所认同的“促使社会反省的力量”。那正是《人间》透过汤英伸案,将其“人间品格”和理想主义推入社会大众意识的有效途径。但这不意味着《人间》放弃激进地批判与变革理想。田雅各的《忏悔之死》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后者。他道出原住民所承受的来自官家和资本经济的双重压迫,因而利巴以“忏悔之死”拒绝了忏悔,拒绝了“宽赦”。固然在汤英伸的个案上,“宽赦”是一个社会反思的根基。但在更本质的原汉关系里,宽赦的主客体则要倒换。对此,与文学相应地,莫那能在现实中诉诸于运动,用诗歌召唤觉醒和抗争。田雅各诉诸个人行医救人的岗位工作。
或许,《忏悔之死》里对基督信仰与民族意识在山地人灵魂里的位置揭示,更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即便被认为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的汤保富一家,固然在整个事件里以基督徒的爱、忏悔、隐忍和责任,做出了最动人的选择,但支撑汤保富拒绝“为英伸请愿”,忍受失去爱儿苦痛的,何尝不是源自身为一个山地人,“英伸的罪是整个曹族人的隐痛”的“为我族承担”的意识!
二、与你同罪
在《人间》关于汤英伸的读者来信中,人们用着“罪”、“爱”、“宽赦”这样的词语,似乎是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种有宗教色彩的语言和思考。很难说这些读者本身便对基督教有一定的认识和信仰。如前所述,汤家父子的“人间品格”,与《人间》的品格,通过《人间》的图片和文字,合而为一种对读者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类宗教的磁场。
但读者也不是完全被动,而是以各自的世代、身份、经验,碰撞和转化着《人间》所传达的宗教感。这其中尤值得关注和分析的,是不同世代、身份的人们所表达的罪感。
更确切地说,是“同罪”的意识。一类是“与汤英伸同罪”。这多来自年轻人,出于自身也处于或曾经处于青春期困顿、迷茫、挫折,而格外敏感于社会不公正的经验,道出“汤英伸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或曰,“汤英伸是我们的兄弟,是你我”。激越的年轻人反省,他们只是较为幸运地平安度过那个愤怒和冲动的少年期,“汤英伸是代我们承受罪责的羔羊”。羔羊以自己的血为祭,将为人间赎回什么呢?这种“罪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青年体认到自己与社会中他人的关联,从而意识到对公义社会实现的责任。在此案之前和之后,都不乏高中学生因为读到《人间》某一报道,而毅然选择社会学专业,以求参与“社会变革”的例子。包藏着社会问题、体制之恶的悲剧性事件,往往能成为推进社会变革、意识重建的契机。
相关的,在汤英伸案中,另一类强烈的同罪意识便是“与社会同罪”。这一罪感不分年龄,建立于对社会问题的反省之上,经由诸多文艺界、知识界人士的阐述,构成了强有力的有关社会责任承担和社会意识建构的话语。作家黄春明说:教育和社会都应分担汤英伸的罪愆。詹宏志说:这是一桩大型的、复杂的、抽象意义的“体制罪行”……请把我们都绑起来,再枪毙他!
对此“体制罪行”,在知识和运动阶层的阐述中,最被瞩目的因素自然是台湾少数民族所受的文化歧视和经济、政治压迫。台大教授李鸿禧说:汉族应该反省对原住民的压迫。艺术评论家蒋勋则以其时打破“吴凤神话”的原运,提出:曹族没有杀吴凤,如果汤英伸判死刑,便是“吴凤杀人了”。
由此,汤英伸杀人,已经是在一个歧视少数民族的体制中生活的所有汉人的原罪,如果汤英伸被执行死刑,则无异于汉人再度亲手犯罪。这个观念的推进,是具有震撼作用的。其导向是唤醒普通人的社会责任连带感和“行动”的意识:“(汤英伸杀人)是我们还没有积极参与、改造社会的错误”。
有意味的是,对更多关注此案的普通人来说,“民族压迫”并不是重点。《中国时报》副刊的《赞成死刑的请举手——汤英伸案的感想》可能代表了更具普遍性的认识。作者认为汤英伸“并不必然背负了少数民族命运的包袱”,而从“一个纯朴的生命挣扎着在物质社会中定位,他的憧憬和挫折,是很多这一代台湾人共同的经验”,建构与汤英伸同罪的生命连带感:“汤英伸可能是你家的子弟,或是我家的兄弟,也可能就是我和你。”因此,除了援引丹诺的社会犯罪论来讨论死刑与正义,这篇文章的意义可能更在于:对“台湾是一个安和利乐的社会”这一因整体的经济增长而被构造的公共意识提出了质疑,因为那富裕背后“另一面的生活”在主流媒体和公众视野中是看不见的。
这也正是《人间》自创刊以来所致力的方向之一。《人间》创刊后做过在都市边缘聚居的阿美族讨海人、垃圾山上的拾荒人、被社会歧视的白化病者等弱小、边缘群体的报道,彰显这些弱小者生命中的尊严、光彩和力量,这自然刺激了读者(比例很大是学生、白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对于台湾社会“另一面”的认识,但同时,这些“另一面”终究是“另一面”,是可以关心、同情,甚而欣赏,却终究与自己不同的“他者”。而汤英伸案的报道,以血淋淋的暴力,将这一建立于一定距离之上的温情(从而是认识不彻底的)关系打破了。
不同于原本就有社会关怀和社运实践的人士,更多普通读者,并不是从“台湾内部的民族压迫”这个角度感受汤英伸的悲剧的。我们从报道中了解,汤英伸出身受人尊重的山地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皆为公务员,自己则是“资优生”——正是这样一个温良、积极向上的汤家人形象,得到了更多都市汉人的认同,对他们来说,这毋宁是一出将自身所认可的美好事物撕毁了的悲剧。在这样的悲剧意识里,他们的“生命连带”感是真实切己的,而不只是作为一种心向往之的更高道德。
这毋宁有些吊诡,由左翼底色的杂志为核心发起的救援运动中,是那种认同资本主义发展、带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意识,而非阶级、民族、反压迫的激进意识,更具有发动群众的力量,更能击中人心。
但这大约也是《人间》意中之事。1986年康来新采访陈映真,从宗教的背景切入对陈映真的创作和文化实践的理解,提及《人间》时,这样说:“剪报里透露他(陈映真)对这本中产阶级刊物的期许,这个阶级一方面不免流于庸俗,一方面也可以成为庸俗的反拨者,他当然希望自己是后者。”这段话或许是有误或含混的。所谓“中产阶级刊物”,是陈映真的自称,还是采访者的认知?在什么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就创办人(陈映真)而言?就读者而言?就刊物那“铜板印刷、文质彬彬”的外表而言?陈映真曾以严厉的内省意识,称自己为“小市镇知识分子”,以剖析这个阶层知识分子的某种苍白和柔弱性,但与“庸俗的中产阶级”也并非同义。事实上,这似乎更适合用来分析《人间》所面对的台湾社会现实环境:在一个“富裕社会”中,有读书阅报习惯、有“余裕”关心社会问题的人群,除了年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恐怕更多是所谓“中产阶级”市民人群。一个以“弱小者立场看生命”、呼吁“更丰富的‘人间品格’”、呼吁“信、望、爱”的杂志,其实是以更复杂、交缠的途径,通往陈映真所期待的“理想主义、人文空间”的。如同对“汤英伸案”,人们从不同的阶层、社会身份、思想立场出发,而有不同的接受和反应方式。但无论如何,将山地同胞看作一样的兄弟时,文化相对价值的观念,有了实在的情感基础。而对汤英伸之“犯罪”的连带感,生命相关、民族平等、乃至宗教性的宽恕意识,更是具公共性的人文意识的重要基底。
三、最后的少年
汤英伸死后一年,《人间时报·副刊》(1988年12月26日)刊登了陈克华的一首诗:《最后的少年——写给曹族的汤英伸》。出生于1961年的诗人,凝望曹族少年的生前身后。“救援汤英伸”唤起了广泛的普通人的社会参与,同时也是1980年代台湾原运的一个特殊组成,最终以“吴凤神话”的崩解迎来一个高潮。呼吁枪下留人时,尉天聪曾说:“让汤英伸活下去,用爱和哀伤,弥补社会和民族的伤痕。”汤英伸没有活下来,但他的死亡——如果可以这么残酷地说——反成就了山地人在道义上的纯粹,让汤英伸得到了最彻底的“宽恕”,从而吊诡地实现了莫那能所说的“被宽恕的汤英伸成为我们民族团结的一座桥梁”。
陈克华写于1988年的这首诗,几乎是同步地反映了这种人心人情的微变。诗人以汤英伸和他的部落所信奉的上帝的意象开头,三条被汤英伸杀死的生命,是“特富野的上帝”的三滴眼泪。这个伤痛不仅是死者和死者的亲人的,也是汤英伸和他的特富野族人、特富野的上帝的。1987年5月,汤英伸就刑,1987年10月,吴凤故事被公布将从教科书中删除。汤英伸以生命偿还了杀人之罪,吴凤也终于把历史的“真相”和公正还给了曹族人,曹族人从“杀死帮助自己的汉人”的集体原罪中解脱了:“他随着头颅已被抛入了历史/替所有负疚的眼睛/擦亮了历史/和胸膛”。然而社会对“大汉沙文主义”的知觉,并不意味原住民得到了平等发展的契机。现实是,“多元文化价值”对原住民的文化存在的肯定,更类于一种将其纳入“现代化体制”的恩赐。“文明和粗制的律法”在诗人眼里,仍是加诸曹族少年和他的族人头上的权柄之剑。“那么诚实或者欺罔/文明和那些粗制的律法你们也都可以不信……”“曹族少年啊我深深知道/在平等得一无所有的子宫/你曾在血流中央的殿堂里,祭拜过/我们共通的原始,少年啊”。
于是,在诗人笔下,伏法死去的汤英伸,并没有如现实中《人间》报道中那穿着心爱的运动服在鲜花中静静躺着,或是在骨灰盒中安静地被兄妹们怀抱着,而是从天堂出走,带着猎弓弯刀,回到了他最初为“索要身份证”而杀人的那种愤怒……
猎弓握在举起的意志里
山刀依旧配挂在细骁的腰间,舔血,而且经常
愤怒地勃起
少年啊少年
何苦便将日出刺死在颈项
野草一路带领晨曦
为你
在鬼魂记忆里的荒蛮中回溯
月满时你便出窍为寻觅的兽
守护的禽
在城市
月光侵蚀的混凝土衰老地形中
伴你度过最后一次的狩猎——
这是一个与现实中忏悔、苍白的英伸相悖的少年,是诗人想象中仍未驯服的少年,少数民族的公义并未因汤英伸的死亡得到实现,而因为汤英伸而唤起的人们对原住民问题的关注,如果仅仅谈论“文化差异”、“文化适应”,而不触及背后的根本的政治经济平等问题,也就是说,导致少年杀人的社会机制,并未改变,那么下一个英伸,如何不会出现?
秋决当日一家豆腐店里
有人拎着一周积下待洗的发酵衣物
有人和平地接过
又送走手中熨好的早报
这城市听不见关于你的审判:
相对于《人间》大量读者来信所表达的感动,以及“爱与宽赦的实现”所带来的某种微妙的满足感,诗人毋宁是严苛的,这也使得他的社会反省意识从普遍的“黑暗面揭示”推进到对社会运转基础的质疑。
首先,是对“文明和律法”的质疑。此前多数的讨论,都是自然而然地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承认律法的正当性,讨论“法外容情”,而诗人的想象和立场,通向了与文明相抗衡的“共通的原始”。
其次,对由悲剧召唤的社会反省的可能性和程度,显然有所保留,“这城市听不见关于你的审判”。来自山林的少年猎人陷落于都市混凝土的漩涡,是多数山地人在都市平淡无奇的命运。汤英伸因这陷落的暴烈血腥,而成了召唤关注、揭开真相的引子。某种意义上,汤英伸确实是山地人的献祭。只是这样的献祭,果然能带来山地民族的复兴吗?
在《最后的少年》中,我们还看到诗人对于“少年”意象的特别吟味。不同于泛泛指称的被压迫者,这是一个“少年之死”,“少年”意象中的命运感,与《忏悔之死》中利巴那样的猎人不同,猎人无罪,本于尚待讨还的历史正义,而“少年”仅只因为“少年”,便是“无罪的”:
一如青苗超过朽草
特富野初春的那种妩媚那种清真
那种
生机。
因为,少年的冲动源于他关于世界的美好的想象还在展开,却遽然破碎——一切反应都是直接的,不是经验。少年的冲动象征着人对公平正义的本能渴望。
这样的少年将成为“最后的少年”,意味着什么呢?田雅各写于1985年的短篇小说《最后的猎人》,已是原住民文学的一个经典:它以山林子民的狩猎生活的消逝,透彻揭示了原住民当代生存的困境和社会不公。政府对山林的管制,使得原来为山林主人的猎人如今成了违法的“盗猎者”,而山林狩猎资源也在资本主义开发逻辑下,遭到严重破坏,动物们的消失,终将使得猎人成为最后的猎人。立法的狂妄,掠夺的贪婪,这来自现代文明的汉人社会的国家暴力,使得原住民成为自己土地上的流亡者,“最后的猎人”是命运的缩影,也是定格的预言。而“最后的少年”呢?汤英伸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少年,他的理想是“到美国看音乐会”,以及,学会先进的汉人的知识、做一个山地教师,像他的父亲一样,为山地小孩走向“外面的世界”,而以己身作为桥梁,“桥梁”的实现,便是他人生的成就。然而这条路破败了。汤英伸倒在他所追求的都市现代文明脚下。这个失败绝非一种“个人主义奋斗者”的失败,而是对原住民在汉人引领的现代化世界中的命运的隐喻。假如田雅各的《最后的猎人》以拒绝现代文明而成为“最后”的猎人,汤英伸则以拥抱现代文明而成为“最后”的少年。退不得,进不得,这样一个姿态至今在困扰着台湾原住民。
1980年代末期的此时此刻,陈克华由汤英伸案透露的对现代性的反省,还是较为孤立的。而到了1990年代,一些原住民知识青年自身开始意识到,争取政治权益,跻身汉人的现代性链条,并不应该是原住民运动唯一的诉求和方向。原住民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也不应该是只被统治者、知识界和商业集团供奉在庙堂、课堂和“九族文化村”那些地方。那么他们在哪里呢?
四、航向历史的黑河
被汤英伸攥在手中,伴他越过生死之界的那枚美丽的、小小的圣体十字架,是特富野的本堂神父高英辉送他的。高英辉凝眉看着汤英伸被关押的台北土城看守所,说:我的父亲就死在这里。当《人间》的记者官鸿志为汤英伸案几上阿里山,从汤英伸背后,从那些在法庭上无言抽搐哭泣的曹族父老背后,隐约浮现出一个山地民族曲折沉痛的近代史——从另一个被抑制、掩埋的视野,为台湾的近代史作注。
高英辉的父亲高一生、汤保富的叔叔汤守仁、英伸的母亲汪枝美的父亲汪青山,都死于195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清洗中。他们在日据时代受教育,可称为第一代山地知识分子。在官鸿志采访的1980年代解严前后,这些记忆,无论对于受难者遗族还是整个社会来说,正处于将醒未醒之间。对于年轻如《人间》记者官鸿志,那切近的历史如同阿里山密林的“黑暗之心”。他得到的契机是呼应着1985年开始由原住民知识青年发起、得到大学生和知识界众多支持的“破解吴凤神话”运动,深入阿里山乡,致力于“从民众史的立场”,还原吴凤成为汉人舍生取义的神、原住民的原罪的历史过程。官鸿志以之为一场艰难的“航向历史的黑河”之旅,见证了历史禁锢之幽深,也见证了1980年代年轻人摸索历史,并从中得到理解现实、推动变革的资源和动力的过程。陈映真在回顾《人间》的工作时,曾经说“生活现场是最好的课堂”,来赞叹《人间》的年轻人如何在采访中自我锻炼成长,官鸿志有关汤英伸的报道和有关吴凤的《一座神像的崩解》,或是此言的生动注解。
《一座神像的崩解》一方面借鉴台湾少数学者的持续揭发——自1950年代起便有学者指出吴凤背后的民族中心话语——初步梳理了自清代到光复后吴凤传说的演变,一方面,力图通过实地对阿里山曹族人的采访,建立从曹族民众的立场出发的历史。这篇报道是对山地纵深历史的初步探访,密切关联着山地人的当代生存。以今天所能掌握的更多资料回望当年的报道,可以看到,吴凤与汤英伸,实则在1980年代的社会转折点上,联结起了曹族人的历史与现实,撞破了横亘于原住民社会之前的,由傲慢的体制、轻忽的人心所构筑的高墙。
有清一代,吴凤的传说内含着汉人移民与原住民接触过程中的恩怨情仇,也寄托着清代文人以儒家精神感化“番人”,以求台湾边疆之安稳的愿望。日据时代,殖民者采集吴凤的传说,并发动了一场近代意义上的媒体造神运动,目的在于从思想意识上完全驾驭山地,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这一殖民策略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官鸿志采访时,即便部落里的老人,即便他们有着发自民族本能的怀疑,也仍然无法跳脱自小被殖民者灌输的故事构架。于是,吴凤被杀的真相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一再被统治者利用,特别是,在光复后,吴凤庙大张旗鼓地重建,是紧接着高一生、汤守仁等山地精英人以“通共、叛逆”之罪被清洗之后的1953年。
1990年代之后,有蓝博洲的民众史调查,日本学者如下村作次郎等成立的“高一生研究会”,台湾山地精英在日据到光复初期的面目逐渐得到揭示。在国民政府档案中,记载着高一生等人参与了中共在台湾发展的地下组织,以“蓬莱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里山从事“叛乱”行为。“国防部”内部文件对汤守仁案的判定是:本案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展山地工作,最具体、最有成效之一案。而我们亦可以从高一生这个出色的音乐天才所创作的融合着东洋与曹族民族风格的歌曲中,窥见作为最先被强制的现代文明“唤醒”的山地人,如何在文明与暴力的夹缝中,寻求着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路。日据时代高一生致力于从医疗、农业上改善族人的生存环境;光复后成为阿里山乡的乡长,则有了与台湾左翼运动的秘密接触。可以揣想的是,与左翼力量的结合,仍建立于对本民族生存道路的选择:先有民族的解放,方有民族的发展。
国民党肃清了这样的山地精英之后,吴凤庙的重新供奉,实则是复制日本殖民者的统治逻辑,以文明之姿进行思想控制,在“保护”的名义下是对山地资源的掠夺;在同化的温情中掩盖着歧视和压迫。
而在这样的战后环境中,怀抱着父辈受难阴影长大的一代,是汤保富、高英辉。汤保富是受汉语教育、进入体制编制的公务员,他召集族人自力修山路,沟通政府修特富野桥,为族人开拓通往外在世界之路,以求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而高英辉在战后基督教、天主教深入山地部落的历史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山地神父。教堂对山地社会的影响,对山地民族的信仰世界和传统文化的改变,在不同的地区、民族和部落中,各有状况,是复杂的。虽然在《我把痛苦献给你们》的报道中,作者曾感动地说出:光复四十年,只有基督教真正照顾了山地民族的心灵……并不能回避基督教在山地传道过程中的“实用功利”(所谓奶粉教)所导致的另一层面的传统信仰与价值的溃散。但无论如何,在汤保富和高英辉身上,我们仍然看到与对民族命运的责任感结合之后,基督信仰的光亮。
但汤保富一定不会想到,他和族人所开的路和桥,带来经济活络的同时,也预示着山地与都市愈密切愈悲剧的关系。汤英伸在都市的漩涡中一念失足,看似偶然,却又是必然;而他的曹族父老,成了在他者的社会中失语的同罪之人。出身于小康、模范的山地基督教家庭,汤英伸也在汉族中心的“惩罚式”教育体系和消费社会的价值观中成长,“最大的愿望到美国看音乐会”,“我不会耽误自己的前途的”这样的少年誓言,注定要成为自我压迫的梦魇。
从高一生、汤守仁,到高英辉、汤保富,再到汤英伸,阿里山曹族三代人的身影中,背负着“杀死吴凤的野蛮人”的原罪,叠合着“被强制的现代性”的苦痛。《人间》在其时并未明确剖示三代人悲剧命运的同构性,却以诚恳的报道,为之留下文字与影像的实时见证。“历史”的进入,也才能给在汤英伸案中以“爱和宽赦”召唤出的属于整个社会的“人文空间”,注入更持久的能量。
①后题名《亲爱的,告诉我——给汤英伸》,收入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台中:晨星出版社1989年版。
②③黄怡:《赞成死刑的请举手——汤英伸案的感想》,《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6年7月18日。
④康来新:《在山路看云——陈映真的仰望与关怀》,第22页。收于康来新、彭海莹编:《曲扭的镜子——关于台湾基督教会的若干随想》,台北:雅歌出版社1987年版。
⑤官鸿志:《一座神像的崩解》,《人间》总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