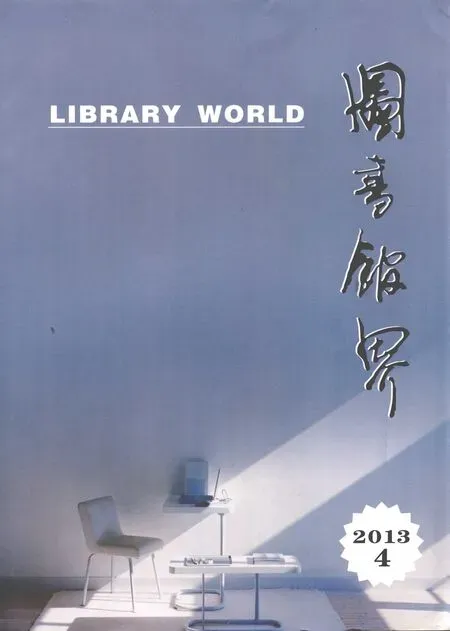愚斋书目的两个问题及引发的思考
2013-11-15郑晓霞
郑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愚斋藏书指的是清末盛宣怀的藏书。盛宣怀一生致力于洋务运动,不以藏书显名,然其藏书数量过十万卷,书籍类型涵盖古今中外,且能摒弃传统藏书家敝帚自珍的习气,创建愚斋图书馆,将收藏向公众开放,嘉惠士林,传播文化,开一个时代藏书家收藏理念转变之先河,从这些方面而言,完全可以跻身近代著名藏书家之列。令人惋惜的是,愚斋藏书在盛宣怀过世之后,逐渐流散,今天人们对于其当年状况的认识主要基于藏书书目。目前存世的愚斋藏书书目共有四部:《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18卷附《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务局铅印本,以下简称“18卷本”;《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词曲类·戏曲类》,“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务局铅印本,是18卷本书目集部第五卷的补辑,以下归入18卷本讨论;《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不分卷,附未分类书目、《愚斋图书馆丛部书目》,“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务局铅印本,以下简称“不分卷本”;《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抄本,以下简称“善本书目”。在通过这些书目对愚斋藏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愚斋图书馆的普通本藏书为什么会有两部书目,即18卷本书目和不分卷本书目,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是《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善本数量及品质相对于盛宣怀的经济实力和当时的善本流通量而言,似乎太过薄弱,是否真实反映了愚斋所藏善本的全貌?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又直接关联着愚斋藏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本文拟将书目之间的比对分析、相关文献的搜集爬梳与盛宣怀所具备的收藏条件的分析相结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目前愚斋藏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有所启示。
1 “18卷本”与“不分卷本”书目之间的关系
善本书目之外,愚斋藏书还有两部书目——18卷本书目和不分卷本书目,著录愚斋所藏普通书籍。二者从题名到编纂体例几乎完全相同,然将它们详加比对,著录重出者仅50种50部3375本(未分类者除外),在卷帙和内容方面,又几乎完全相异,显然著录的是不同部分的愚斋藏书。18卷本书目卷前《叙》有言:“适敦聘缪筱山、罗榘臣诸公主持编辑,未及竣事,愚斋公作古。该馆基地原属义庄,迩以变产输将,馆址亦预其列。仓卒迁让,错乱不可言状。爰由同人商请四五老友,担任清厘,搜蠹拂尘,经五阅月之工作,始获整理上架、粗具规模。计纂成经、史、子、集目录十册。至种类、卷数、悉系于各部子目之下,不复赘列云。”可知缪荃孙等人在盛宣怀去世之后,仍然坚持编纂并完成了盛氏所建愚斋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即18卷本书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另外一部相类书目的出现?这部书目著录的图书又从哪里来?由于相关文献的缺失,要通过直接论据得出确切结论显然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我们转换视角,顺着愚斋藏书本身的方向追溯,却能使这些问题得到相对合理明确的解释。
众所周知,愚斋藏书在盛宣怀去世之后,除了善本秘籍被盛氏后人分割变卖外,普通书籍中的主要部分分别捐赠给了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关于圣约翰大学得到的这部分藏书,1933年12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有一则题为“约翰大学将建盛氏图书馆”的报道,文曰:
久为全国知识界景仰的盛氏(盛宣怀)藏书楼,搜储国学新旧善本图书达数十万册之巨,平素封秘珍藏,外人莫窥其奥。闻今已由盛氏后裔全部捐赠梵王渡圣约翰大学,士林赞美,以较浙江天一藏书之终不免于散失为善多矣。特盛氏不捐于其先人所手创之交通大学,而转赠与外人统制之约翰大学,似犹令人寻味。个中人言,此事系约翰大学旧同学,国府前财长宋子文先生介绍之力。该校已准备另建三层大厦之新图书馆以藏之,且命名为“盛宫保图书馆”,日下第一箱书已到校云。
这里所说的“盛氏(盛宣怀)藏书楼”,应指盛宣怀一力创办的愚斋图书馆。据此报道,可知愚斋图书馆的普通藏书在1933年应该已经全数捐赠了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的这批藏书新中国成立后又归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子美和吴平两位学者通过对该校所藏愚斋藏书的调查,亦肯定了这批藏书就是18卷本《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不包括未分类书目)著录的图书,即愚斋图书馆的藏书。
既然愚斋图书馆的藏书基本都捐给了圣约翰大学,那么,上海交通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得到的愚斋藏书又来自哪里?关于上海交通大学得到的藏书,查阅《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善本目录》,可以发现,交通大学得到的这部分书籍与不分卷本《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的著录基本一致(不包括未分类部分)。联系吴平、周子美二先生的研究都指出愚斋藏书“有一部分捐给了交通大学图书馆,这批藏书共557种,16702册,在《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18 卷本)中没有著录”的事实,应该可以认为,除了愚斋图书馆的藏书外,愚斋藏书还有家藏的部分,而交通大学得到的这部分就应该来自家藏。也许是出于共同的编纂者之手,也许出于捐赠公藏的共同原因,在编目时采用了与18卷本一致的题名和体例。
至于山西铭贤学校得到的藏书,由于战乱与时代变迁,辗转流徙,今已不知身归何处,加之又未发现相关书目,要明确其面貌,目前确实不太可能。笔者还是偶然在近年的图书拍卖会资料中发现了这批藏书的两条线索:一是中国书店海王村拍卖公司2006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图录中的一部图书,著录如下:
《筹济篇》三十二卷首一卷
作者:(清)杨景仁辑
年代:清光绪四年(1878)诒砚斋刊进呈本
函册:1函6册
纸张:白纸
装帧:线装
尺寸:半框:20.4×13.2
钤印:铭贤学校亭兰图书馆之章、愚斋图书馆藏
二是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2008年夏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中的一部书,著录如下:
淮鹾备要(残)
历史年代:清道光间写刻本
函册:4
纸本线装
是书存卷1 -3、9、10
钤印:愚斋图书馆藏、铭贤学校亭兰图书馆之印
这两套书显然属于山西铭贤学校得到的那批盛氏藏书。对照愚斋藏书目录,前者与18卷本所附《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史部第340号著录吻合,后者与第373号著录吻合。由于愚斋的未分类书目编纂过于简单,当然不能就此完全确定铭贤学校得到的就是18卷本所附《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中的藏书,但是比照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所得部分,这个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山西铭贤学校得到的愚斋藏书应该有1714种,1948部,15248本。
通过追溯愚斋藏书的方向,笔者认为,18卷本书目为盛氏所建愚斋图书馆的普通本藏书目录,不分卷本书目为部分盛氏家藏普通本书籍目录,也就是说,愚斋藏书并不像之前一些学者认为的就等于愚斋图书馆藏书,应由图书馆藏和家藏两部分组成。
2 善本书目是否反映了愚斋善本的全貌
《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是迄今所见唯一的愚斋善本书目。该书目共著录图书245种251部,其中宋元本17部(含三朝板史籍1部,宋刻明补本2部),明刻本80部,稿抄本109部。这样的收藏数量和品质,在盛宣怀这样的收藏家而言,似乎不合常理。善本收藏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收藏的意愿、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相对丰富的善本流通量。盛宣怀正好具备了这三个条件。首先,追寻善本,拥有更多的善本,历来是藏书家们的理想,盛宣怀也不例外。虽然他将普通本的收藏与利用摆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也重视珍本、古本。比如他曾咨询缪荃孙:“有人送来《晋书》,是否宋版,索价三百元值否?”只要是听闻有名家、旧族的收藏流出,总是想方设法收购过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写给亲家吕海寰的信中说:“宅有隙地,拟造图书馆,近颇收买旧书,如部中有罕见典籍价不甚贵者,乞代留意。孙济宁收藏甚富,能否设法收购,两有裨益。”
其次,在经济实力方面,盛宣怀办洋务40年,其巨额家产难以计算,足以支持他收藏到更多珍稀图籍。所撰《愚斋东游日记》对其在日本的购书活动有这样的描写:“中国书籍不少,而精本标价极昂。内有钞本《钦定西清砚谱》一部,计二十五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凡陶之属六卷、石之属十五卷,共砚二百,为图四百六十有四,附录三卷。则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傍制澄泥诸品,共砚四十有一,为图百有八。每砚正背二图,亦间及侧面。凡御题及诸家铭识,一一钩摹,精好绝伦。称系内府藏本,问其价二千元。”虽然日本汉籍并不便宜,盛宣怀却可以“随阅随购,总计新旧不下千余种”,可知其完全有能力购入那些价格不菲的珍藏秘本。
第三,盛宣怀生活的时代,社会上善本的流通量远远多于今天。尤其是正处时代变迁、社会动荡之时,贵族没落,世家轮替,名家大族的收藏时有流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善本收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与盛宣怀同时期、收藏条件相当的另一藏书家李盛铎,其木樨轩就收藏有宋元古本三百部,明刊本二千余部,抄本与稿本两千余部,从中可见当时古籍珍本的流通量还是相当可观。盛宣怀也充分注意并试图抓住这种机遇。他在1912年致信赵凤昌曰:“近日常赴公园(日本)各图书馆博览群籍,华洋今世无所不有。闻罗叔蕴、董绶金辈各携所藏而来,深有慨于吾华数十年明哲精英沦落于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共襟怀夐远,若到此一览,当无不喟然长叹也。弟前因上海为各国散处,可以持久不变,特建图书馆一所,以便士林。闻南中旧家藏书迫于乱离,倾箧而出,若能趁此时广为搜罗,未始不可为东南保全国粹。公谅有同心。兹先措上日金二万元,交妥便带上,到日即请查收,代为留意收买。俟奉复翰再当续筹,大约义四万元为度,专买未见之书。”在他的这类购书活动中,最著名的就是购入了清末著名藏书家江标和方功惠的藏书(18卷本《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叙》)。江标(1860—1899),字建霞,一作蒹葭,号师郧,一号苫誃、萱圃、师许,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工诗文,好藏书。收藏重宋元刻本、旧校旧抄,所藏皆精品。藏书在其身后流散,今已无法了解全貌,然观复旦大学所藏抄本《江氏灵鹣阁藏书残目》,著录图书仅32种,而宋元本就有13种,可以想见其收藏品质之高。
方功惠(1829—1897),字庆龄,号柳桥,湖南巴陵(今岳阳)人。以父荫任广东监道知事,官至潮州知府。方功惠自幼嗜书,其碧琳琅馆藏书十万卷,富甲粤东,收藏之富,当时几乎可与陆氏皕宋楼和丁氏八千卷楼相匹。《碧琳琅馆珍藏书目》四卷,著录各种类珍本约680种,其中宋版有《周易本义》等34种,元版有《乐典》等400种,精抄本有《佳趣堂书目》等200多种。所著《碧琳琅馆藏书记》,收录方氏孤本藏书题识75篇。由江、方二家的收藏,加上盛宣怀得天独厚的收藏条件,反观其善本书目,实在是有违常理。唯一的解释就是盛氏所藏善本大多并未归入愚斋图书馆。这一点,存世文献和藏书中也能找到一些印证。《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收录了盛宣怀致缪荃孙的一封信,其中写道:“昨奉手示,书目已完,深为感慰。秋后拟即开馆,大约阅书室求备不求精。弟勿虑宋元本之少,甚虑种类之不齐耳。都中携回善本亦属无多,且恐缺短,已命五儿即日检送书馆,即乞补入书目为幸。”可知盛宣怀认为图书馆藏书的宗旨是“求备不求精”,开始并未给予图书馆宋元本这样的珍稀善本,似乎是由于缪荃孙认为如果缺少珍稀善本,显得图书馆图书种类不全,才从家藏中捡了一部分纳入图书馆馆藏。从中透露了愚斋藏书的善本大部分属于家藏的线索。今天存世的一些盛氏善本书籍亦能说明这点。如在2008年上海嘉泰秋拍中露面的《黄石斋先生遗书》,为明黄道周编,稿本,内封有盛氏藏书专用贴签,上书“黄石斋遗集原稿”“善本”“原稿本”“不分卷四本”等,另附有盛宣怀亲笔所书一纸,上云“一百二十两文珍斋”,是为当年盛氏购此书之价。该书就不见著于《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另外,日本天理大学和小汀文库所藏的部分盛氏书籍,也未见诸存世书目。这些亦印证了盛氏大多数善本家藏不宣的事实。
结论:盛宣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善本收藏条件,结合存世文献、藏书的线索,都揭示了《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反映的仅仅是愚斋图书馆善本的状况,并不是愚斋所藏善本的全貌。
3 思考
一直以来,藏书书目都是相关学者认识、研究盛宣怀藏书活动及藏书的重要依据。由于目录不止一部,没有明确的编纂体例,亦未表明著录对象的具体归属,一些研究者往往依据题名中“愚斋(盛氏)图书馆”的字样,将这些书目均视作盛氏所建愚斋图书馆馆藏之目录,并据此展开相关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注意到了部分藏书未见诸于书目的情况,但往往也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进行深入探讨,这就使得愚斋家藏部分藏书成了一块未经开发的处女地,造成了愚斋藏书研究的缺陷。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愚斋藏书而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书目之上,而应该从书目出发,充分注意到其特殊的藏书状态,才能获得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1]本报编辑.约翰大学将建盛氏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12).
[2]佚 名.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善本目录[K].上海,1933:1—34.
[3]吴 平.盛宣怀与愚斋藏书[J].图书馆杂志,2001,20(3):56—57.
[4]周子美.愚斋藏书简介[J].图书馆杂志,1983,2(3):62.
[5]盛宣怀.盛宣怀十五、十六[G]//缪荃孙等.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盛宣怀.寄吕尚书函[G]//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盛宣怀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210.
[7]盛宣怀.愚斋东游日记[O].盛氏思补楼,1916:35—36.
[8]盛宣怀.壬子亲笔函稿[M]//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