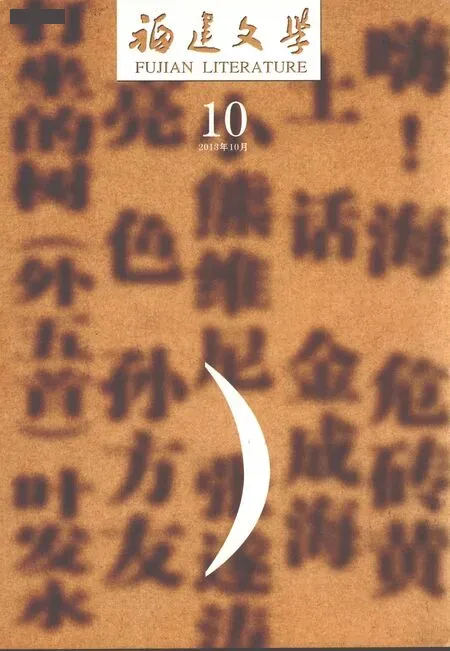土 话
2013-11-15金成海
□金成海
一
德爹爹的儿子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腊月头,突然打电话回来说,今年回家过年。一贯简单的德爹爹老两口把自己的小世界弄得复杂起来。打20斤米的糍粑,糊10斤绿豆的豆饼,推10斤米的汤圆,杀年猪、灌香肠、吊腊肉,反正一个腊月就没有消停过。德婆婆不仅自己自个儿忙这忙那,还把个德爹爹指使得像个转轴儿。
腊月二十八早上,德爹爹怀里抱着长竹扫帚将几片绿黄的桑树叶归到一堆垃圾里后停将下来,一抬头,红红的冬日已经像一个大南瓜挂在了他家屋后的竹梢上。
德婆婆即时送上早点,一碗煮酥饼。在小江湖,人们爱用面粉、食用油和黑糖做成酥饼,那东西银圆样大小,是德爹爹大半辈子的美食。他喜欢干吃,也喜欢煮了吃。如若用油煎一遍后再煮一会,他最爱吃。在“唏唏溜溜”吃酥饼的同时,他想,今天即将回家过年的儿子也喜欢吃。这是德爹爹最得意的。德爹爹私下里管这个叫“踏代”,即“遗传”。德婆婆看着老头吃得香,心里美滋滋的,比起年轻时候的倔强和懒散,她觉得这老头子越活越清白,这不,儿子要回来过年了,让做啥就做啥,没有了平日里的得过且过。想到这儿,德婆婆又吩咐说:“吃完了到小卖部看看,把团年的鞭买回来。”
德爹爹嘴里“唔”地应了一声。
德爹爹唯一的儿子小名叫水清,学名叫王水清。不仅德爹爹盼他,德婆婆也盼他。之所以说德婆婆“也”盼他,是因为德婆婆是水清的后妈。尽管是后妈,可德婆婆自进了王家门,当他亲生儿一样对待,娘俩关系胜似亲生,隔壁三家谁不夸?德婆婆一辈子没有生养,老两口子越老越把儿子当成了依靠。古往今来江汉平原的农村老人都这样,养儿防老,倒也不奇怪。
水清的亲妈在水清3岁的时候便“卖桃子”去了。小江湖人把女人私奔不叫“跟人跑了”,而是称为“卖桃子”,大约是取逃之夭夭之意吧。是给人留情面的说法。民风真是淳朴。那时节,小江湖这地交通不发达,但外来做生意的特别多。裁缝啊,卖麻糖的啊,做绷子床的啊,都往这地跑。水清3岁那年,隔壁小妈家里请了个天门的裁缝做衣服。那裁缝脸皮白白的,说话软软的。一会儿浓浓的天门腔,把小江湖人的过日子,说成“过入子”,把小江湖人说的苕称之为“憨巴”。但一会儿又能说很标准的北京话。小江湖人把猪子身上那些粉红的肉称“精肉”,这种称谓如果放在现在是很准确且很俏皮的,但在那个时候,裁缝师傅却将精肉用北京话说成了“瘦肉”,彻底颠覆了小江湖人对肉的认知。说北京话舌头弹得很厉害,这就是裁缝师傅的过人之处。无论是天门话还是北京话,都把个年轻漂亮的水清妈笑得前俯后仰。那时,水清妈是村里公认的大美人,两条油亮的长辫子,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皮肤白里透红,走到哪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如此,当年的小德才防范甚严。他本对裁缝师傅不屑一顾,认为一大老爷们净耍嘴皮子,终归不是正道。有一回收工回来见自己老婆笑成那样,醋意顿生,把眼睛瞪成了两个牛卵子,女人吓得直哆嗦,晚上少不得被小德劈头盖脸收拾一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家的“贱女人”却被那裁缝师傅的天门话北京话迷了心窍,在那个人离开三天后,就追寻去了。那时节不像现在有手机,可以微信,也可以Q Q,天知道他们是怎么约定的,足以证明他们的智商高过防范严密的小德。小德遭遇了一个男人的奇耻大辱,躺在床上半个月起不了床。先怄气,再痛定思痛,不断检讨自己过日子的过失。自己的脾气是不是太大了些呢?特别是不应该打老婆的呀。自己是不是有些懒散呢?有些家务活比方挑水、劈柴做得不够。再就是自己对过日子的要求太过简单,没有个计划,啥事都得过且过,女人不大瞧得起这样的男人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婆的跑,倒促成了他的成熟,改变了他的人生,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他还是固执地把这一切归罪于那个裁缝,归罪于该死的外地口音。
后来,小德有了现在的德婆婆。德婆婆家的男人在公社企业当采购员,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染花了心,跟一个城里女人好上后,一脚把德婆婆踹了。女的有被踹之怨,男的有夺妻之恨,两个命运相似的人走到一起后,同病相怜,把倒塌的日子捡起来,过得牢牢实实。左邻右舍夸赞他们,猪圈里“哼哼哼”,狗窝里“汪汪汪”,鸡舍里“各打各”;菜园子四季青,后园里桑柳竹。德婆婆没有生养,将那水清当宝贝一样地供着,从小到大,丁点的委屈都没受过,让水清不知道自己还有个亲妈。小德和德婆婆就这样让儿子在甜罐子里长大,水清又特别争气,学校里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村里头人人都夸水清听话。小德也成长为“德爹爹”,德爹爹心想,儿子不听老子的听谁的?他花那么多钱把儿子培养成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就是他的骄傲,他的脸面,同时也是他老来的依靠。就算是他的亲侄儿水满,在他眼里,也是个没有读多少书的文盲,没有他家水清有出息。这些话自然都闷在德爹爹的心里。毕竟,水满是他亲侄儿,打着骨头还连着筋呢。
二
德爹爹今天心情好,吃罢早饭,背了双手出了门。
他要去买一挂大一点鞭,里边还要夹带着炮的那种,一炸一个脆响,喜庆啊。
他竟然不知不觉地踱到村头老孙家的小卖部。本来他是瞧不起老孙这个人的,原因是他是天门人。老孙在小江湖做了上门女婿,脑瓜子反应快,嘴也甜。但德爹爹一听那口音就本能地生出厌恶。常常对人说:“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三个汉川佬,抵不过一个天门嫂。”这话是湖北人总结湖北人的。有褒义也有贬义。高兴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个比一个聪明”;沮丧的时候那就是指他们“一个比一个狡猾”喽。是褒是贬完全看说话人的心情和态度。那个时候的德爹爹说出来肯定就是贬义。不过他今天高兴,如果他有心情调侃的话,说不定用一句“你个天门佬”来表扬一下老孙的精明能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到老孙的店里来,有和解的潜意识。所以,一进门就将钱往柜台上一拍,用陈述句说:“买一挂一万响的鞭。”
老孙是啥人啊,见了德爹爹惊喜万分,讨好地问:“德爹爹,是不是你家水清要回来呀?”老孙个子小,脸也小,一惊讶人就像刺猬一样缩成了团。
德爹爹目不斜视地“唔”了一声。那些在店子里抹麻将和看麻将的一干人一听,都“啧啧”地说:“难怪德婆婆又是新絮又是新被套的吆喝呢,原来儿子、媳妇、孙子都要回来。红中,杠!”“德爹爹家今年可热闹哦!还杀了年猪哦,发财,碰!”
德爹爹听到这些话语,心里麻酥酥的,很受用,沟沟壑壑的脸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
老孙说:“哎呀,德爹爹,真不巧,这种货卖缺了。明天上午才能来货。要不,来两挂五千响的?”
德爹爹迟疑了一会,摇摇头说:“算了,我到老吴那里去看看。”
老孙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在他眼里,这是一个与生意无关的机会,说长一点的话,还是德爹爹那事闹的。自打德爹爹前妻跟人跑了后,德爹爹总不拿正眼看他,原因就是他也是天门人,和那裁缝是老乡。德爹爹姓王,是村里的大姓,辈分又高。虽说年轻时脾气大得有点不着调儿,可身边也不缺追随者。年纪大了,人就变老成了,村里人都开始正儿八经地尊重他。这些年,他在村里明里暗里总不说老孙一句好话,并且还单独警告老孙:不许向水清透露半点前妻的信息。以至于水清成人后多次找他打听,他都没敢告诉,只是让水清找自己舅舅问。无疑把小的也得罪了。有了这些因素,村里人都跟着小看他,甚至欺负他。有人在耕田的时候公然把他家的田带一犁过去,让老孙受了多年冤枉气。老孙一个外地人上门,全家都靠他这个男人撑着门户,那个委屈呀,真是一言难尽。
老孙陪着夸张的笑脸,小心翼翼地和德爹爹商量着说:“这样,德爹爹,您也不用急,明天中午前我给您老送过去。”那声音完全变成了颤音,让老孙很自卑。
德爹爹知道和解的目的达到了,本不想多留,但人把话说到这份上,还有许多乡亲在这儿,就这么一走,让人觉得没气度,索性就问:“不误事?”
老孙哈哈哈地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用不容质疑的口气说:“保管不会误您团年!”
三
太阳刚要下山的时候,三个被日头拉得长短不齐的人影像三个箭头朝德爹爹家门口移过来。紧接着,王水清和他城里的老婆和他4岁的儿子出现在家门口。
“哎呀呀,田田,我的小孙孙回来哒……”德婆婆张开双臂朝她朝思暮想的孙子迎上去。
那眉清目秀的小子双手抓住他妈妈的衣襟,身子紧紧地贴在他妈妈肥硕的屁股上。
德爹爹也站在了门槛跟前,微笑地看自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心里顿时升腾起一股融融的暖意。
“爸,妈。”儿子、儿媳齐声叫了二老。
德婆婆脸上聚成了一朵菊花,连连答应着,过去牵过孙子的小手。德爹爹的脸上的微笑则有些僵硬了,眼里有一片云飘过。他听惯了儿子叫“爸爸”“翁妈”时脆生生的声音,他觉得那是最真实的叫法。多少年都是这么叫的,几年不回,连叫法也省略了一半。那声音也仿佛来自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德爹爹耳朵边蓦地掠过一丝天门口音。不过儿子几年不回,此时还脸露倦容,德爹爹心生疼痛,心想,他太累了。也就不计较。他德爹爹也不是不懂道理的人。
水清牵了儿子田田,教儿子认人:“田田,快叫爷爷、奶奶,叫啊!”
尽管一路上水清一再教自己的儿子回到老家了要按照老家的叫法管“爷爷奶奶”叫“爹爹婆婆”,但在城里时间长了习惯使然,加之一路转车又辛苦,自己倒是把这称呼的事给忘记了。更加要命的是,田田大声问爸爸:“爸爸,我们今天早上不是刚从爷爷奶奶家出来吗?你不是说,这是爹爹和婆婆吗?”
这一说,水清心里炸了毛,他知道父亲一辈子都不肯原谅母亲。哪里敢让他知道自己找到了亲生母亲的事。一拍脑子,说:“哎呀,你看看爸爸这记性,是叫爹爹婆婆,快叫快叫。”
于是,田田懂事地一一叫了“爹爹、婆婆!”
德爹爹只道孙子所说的爷爷奶奶是外公外婆,他没有在意。他知道,时下,有了独二代了,许多外公外婆都喜欢外孙管自己叫爷爷奶奶。这有什么呢?叫什么也不能改变“外”这个身份。德爹爹笑容可掬地抱起了孙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塞给孙子。孙子说:“老师说,不能要别人的东西。”德爹爹更加高兴了,说:“哎,别人的东西不能要,爹爹的东西可以要啊。”
看到爹孙俩那亲热劲,水清内心释然。
四
水清回来的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九。这一年的腊月小,没有三十,各家各户二十九就团年。按照小江湖的风俗,德爹爹将兄弟一家人喊过来,这样才算一家人团圆了。德爹爹这辈就俩弟兄。兄弟两口子养了个儿子叫水满,比水清大,这几年小两口一直在外面打工,留下孙女让爹爹婆婆带着,不过年年都大包小包地回来过年。德婆婆没少羡慕,德爹爹则说:“那有什么?我们家水清是大学毕业,当的是干部,比他一打工的高好多档次,哪里会年年回家?”德婆婆则横他一眼,说:“亲侄儿你也糟践?”德爹爹嘿嘿一笑:“这不是我们俩说说吗。”其实,德婆婆心里最清楚,德爹爹那里娃还是自己的亲。
一家人几年不见自然是亲切,兄弟找兄弟说话儿,媳妇和媳妇拉家常。两个小家伙则怯生生地牵了手,在一边一问一答。小江湖把自己老婆不称老婆,叫做“我屋里”,外面人称呼的时候就说是“谁屋里”。别看这称呼土,但直白,还多了层亲切。水清的屋里是南方人,自然要说普通话。按说,水满的屋里在外打工也有见识,应该用普通话交流,可是她就是不肯讲一句普通话。她知道,大爸——德爹爹最不喜欢本地人说外地话。村里老孙家的幺姑娘嫁到汉口没有一年,回来的时候一口一个“么事唦”,让德爹爹指着背狠狠地骂了一通:“山西的驴子学马叫,叫得人一身鸡皮疙瘩。”骂人家姑娘,这在小江湖是极严重的事件。但是老孙家没人敢出来顶真。一来,自己姑娘蹩脚的汉腔他们自己都听不习惯,二来那时水清在上大学,放假回来都是一口纯正的小江湖土话。水清一个本家兄弟在沙市打工,时间一长,说话难免带点沙市的尾音。水满女儿做满月的时候,这小子回家赶人情。这样场合是要等到娘家人来了才会开席的。那天娘家人来得迟,这兄弟有点急,便自言自语说:“翁嘛半天不来。”恰好让坐在上席的德爹爹听见了,他也知道“翁嘛”就是“这么”的意思,但还是把眼睛一瞪,训斥道:“你把‘翁嘛’这两个字再说一遍试试!”那兄弟吓得不敢再言语,借口到另外的桌子坐了。水清和他的屋里哪里知道个中缘由?这样水清的屋里就不太听得懂妯娌说话,每听一句就要问水清,水清便用普通话给她翻译一遍。
一家人说着话儿,那老孙气喘吁吁拎一挂大鞭跑来,讨好地说:“哟,一大家子好热闹!德爹爹,您的一万响的鞭来喽!”
德爹爹接鞭的当口,田田突然叫道:“爸爸,我要上洗手间。”
水清的屋里连忙问水清:“王水清,洗手间在哪?”
那水清一边土话一边普通话说了半天还搅在里边,随口就问德婆婆:“妈,洗手间在啥地方?”一出口却是普通话。
德爹爹听得真真切切,还没回过神,水满就“扑哧”笑出声来,他的屋里连忙用腿碰他。老孙听了一愣,随即明白怎么回事了,也不说话,斜视了德爹爹一眼,转身就走。
德爹爹脸色顿时铁青,把筷子拍在桌子上。水清知道自己犯了父亲的忌讳,连忙又用小江湖话问了一遍:“妈,厕所在哪?”
德婆婆也是不知道什么叫“洗手间”的,但还听得懂所谓厕所就是他们这儿的“茅房”,赶紧拽了孙子朝屋后跑。谁知,没过一会,田田从屋后跑到水清身边,边哭边嚷嚷:“那不是洗手间,那不是洗手间,我不上嘛,脏死了,脏死了……”
德爹爹一见孙子这样,脸红一阵白一阵,像唱戏的化妆一样,羞愧难当。在他想来,自己的儿子光去适应了城里的老婆。陪她们讲外地话,在丈母娘家过了好几个年,就连结婚也是在城里操办,搞得像个上门女婿。但却没有教他们适应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的风土人情,连对老辈子人的称呼都没有教一教孙子,连入个茅房都没有教一教孙子。这绝对是忘本的表现,比那老孙家的幺姑娘讲蹩脚的武汉话还要丢脸。特别是刚才老孙那一瞥,让他最愤怒,姓孙的算个么东西?这么些年自己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敢放个屁?昨天刚给了他一点好脸色,今天就忘长八尺了。他想起自己曾经骂过人家的幺姑娘“山西的驴子学马叫”,显然别人那一瞥意味深长,那是反唇相讥,是恶毒诅咒,是让他从地上钻到地下。还有水满,虽然是他亲侄儿,只是个初中生,哪里能和水清相比,可初中生就是笑了大学生,你咋了?简直就是两只手一边一下在打他的老脸,先是打疼了,然后又打麻木了。
席间出现了短暂的安静。
最终还是水满灵光。原来,他在城里打工,很羡慕城里人讲卫生的习惯,去年就在自己的房子里做了洗澡间。不仅在里边安装有浴霸,冬天可以洗澡,还安装了大便器。当然,他父母使惯了茅房,是不用屋里的厕所的,他们也觉得在屋里拉屎别扭。这时,他就抱起田田,哄着说:“走,到大爸家去上洗手间。”其实,当初水满也劝过德爹爹:“大爸,您也做一个吧。水清兄弟现在是城里人,特讲究卫生,怕到时回来不习惯咧。”德爹爹却把他呛了一顿:“你小子用心想想,城里人为啥在屋里拉屎,那是他们没地方盖茅房!你看我们这宽敞大世界的,哪里用得上那个?依我说,你是瞎折腾!”这不,儿子没嫌孙子嫌。德爹爹感觉这世道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简单了,连水满都不可小看了。
上洗手间的事很简单就解决了,但这一闹,就缺少了原有的欢乐气氛。原先准备好的鞭炮本是在吃饭之前放的,到了中途才由水满想起,拿出去放了。
五
大年初一,水清领了他屋里和田田给两位老人拜年,水清叫“爸爸、翁妈”,他屋里叫“爸、妈”,田田则叫的是“爹爹”、“婆婆”,德婆婆哈哈笑着,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两百块钱给田田开压岁钱。水清的屋里显得生疏地说:“田田,不要、不要。”田田一回头,说:“爹爹说,爹爹的钱可以要。”推了半天,德爹爹不满地咳嗽了一声。水清连忙制止了他屋里。田田双手接过压岁钱,小脸上写满快乐。
小江湖有俗话说:“爹亲有叔,娘亲有舅。”意思是爸爸和翁妈的兄弟姐妹是最亲的。叔的意思,昨天团年已经表达了。今儿格,水清拿了礼物,分别到舅舅和姨妈家拜年。他让他屋里跟他一起去,他屋里说腿软,明知是托辞,就不强求。田田却闹着要去,水清便笑了,觉得儿子跟自己的亲人有感情。当即表态:“行!”田田一蹦老高。
德爹爹却不容质疑地说:“田田就在屋里。”
水清感到意外,说:“两个人去显得热闹和亲热些吧?”
德爹爹却比他想得周到:“大年初一呢,带个娃去,别人是给压岁钱呢,还是不给压岁钱呢?你舅舅和你姨妈年纪大了,不当家,没个来源,手头紧巴巴的。”
水清没想到会这样,他知道父亲说得也在理,同时他知道,如果自己带了儿子去的话,老辈子的人会更高兴,毕竟又是一代人啊。
水清不甘心,道:“要不,我多给他们点钱?”
德爹爹手一摆,说:“水清啊,不是这个礼儿。”
水清只好作罢。昨天的洗手间的事就够让父亲难堪的了,他不想在大年初一这天与父亲起争执。父亲这辈人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老来还是把自己禁锢在所谓的“礼”上,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变,那固执比扁担倒下来不知是个一字的爷爷有过之无不及。害得田田哭闹了好一阵,要不是他屋里几巴掌扇在那小屁股上,只怕还不会停。德爹爹见状,不满地说:“哪有初一打人的?”示意德婆婆将孙子牵走,儿媳妇却不肯放人,俩老只得由她。
水清记忆里到舅舅家大约有五六里路,可是村头那条河早就干涸,河底的裂缝塞得进一块砖头,中间已经被踩出一条路来。这样就节省了大把的时间,半天时间就拜完年。突然,他想到了邻村,那里有他的亲舅舅、亲姨妈。成年后,他只偷偷去过一次,打听亲生母亲的住址,也被父亲发现了,挨了顿臭骂,还警告他“再去就打断你的腿”。今天,他们都还好吗?他是腊月26去的天门妈妈家。妈妈已经是胃癌晚期,人已经瘦得不像人样了。同母异父的弟弟告诉他:“妈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了。”听到这话,他的鼻子就酸酸的,母亲给了自己生命,却没有与自己的儿子真正相处几天。他知道,有许多个日日夜夜,母亲对着家乡的方向流泪,那是牵挂她的儿啊!回到娘家后只能躲在远处看望一下他,在她的心里打一个结,暂时有一个安慰。见自己流泪了,母亲还是低低地、用他们小江湖的声音说:“娃子,不哭,我这不好好的吗?你回去,回去过年。几年没有回去,你爸爸不知多想你们呢!”说着,她自己倒哽咽起来。唉,母亲啊,您一时的选择,让儿子格外背负了多少感情的债务啊!水清拜年回来的路上,又过小河,使他想起小时候在里边嬉戏的情景,一个猛子扎好深,小伙伴追逐好远都不到边。渴了就掬起一捧水喝个饱。那时,爸爸常常拿一根细小的树枝,来河边恭候他,只要抓住保管一抽一个“扑楞”。小伙伴就常常掩护他逃跑。回家后,现在的妈妈还帮他瞒着,把他藏在身后,不让父亲刮他的腿肚子——那是小江湖人的发明,凡是下过水的,手指在腿肚子上一刮,就有一条清晰的白印,反之则是黑的,黑的是身上的汗泥,没有让水浸润的。那时节啊,多来劲哦!现在,爸爸还是原来的爸爸,但老了。小伙伴们不是原来的小伙伴了,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更让人沮丧的是河也没了,河到哪去了?也许随着远处镇上招商引资来的那些个林立的烟囱流到天上去了吧。
六
德爹爹瞌睡浅,对屋子周围的动静洞察得很清楚。他知道,这天晚上,夫妻两个人嘀嘀咕咕了大半夜,不知道说了些啥,有时声音还很大。后来还接个电话,听水清轻轻叫了声“翁妈”,然后,声音就压得低低的,似哭似诉。德爹爹就得意,把丈母娘叫“翁妈”,这小子还是地地道道的小江湖人。鸡子叫头遍的时候才静下来。
次日早上却起得早。水清屋里把田田穿起后,收拾行李。德婆婆在灶门口添柴烧早饭,一缕青色的炊烟在寒风中摇摇摆摆地不断分着好多岔来。水清到德爹爹房间,德爹爹披了衣服坐在床上养神,一副悠然的神色。
水清叫了声:“爸爸。”
德爹爹一惊,赶紧“唔、唔”两声,眉头舒展开来。
水清的眼睛红红的。支支吾吾地说:“我突然有要紧事,让赶回去。”
德爹爹不相信,问道:“啥事?”
水清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营造了一个腊月的团圆气氛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德爹爹显然不愿意,也显然有点生气了。“叫化子也有3天年呢?你说你放假了还有么事?”
水清犹豫了一下,突然双膝一折“咚”跪在父亲面前,泣不成声地说:“爸爸,我翁妈,她、她过世了。”
德爹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忽地从床上爬起来,惊讶地问:“你说什么?”
水清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德爹爹像被人抽了筋一样,一下跌倒在床上。水清本想挨父亲一顿好骂的,没想成了这样,慌忙过去将父亲扶起来,见他的眼角竟然渗出两滴混浊的泪珠儿。
半晌,德爹爹才艰难地问:“啥时候的事?”
水清哽咽着回答:“昨天晚上。”
德爹爹长叹一声:“唉……那你去吧,你们都去吧……”
水清内心立时升腾起一股热热的东西,那热好重,好厚,像是要冲出他的腹腔一样。他歉意地说:“爸爸,对不起。”
德爹爹一摆手,说:“苕娃子,没有这么说的。”
德婆婆从灶房里过来是准备叫他们吃早饭的,不想却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人一下子也惊呆了好一会,一股子眼泪就漫了出来,走过去抱了儿子的头,放在怀里,哭将起来:“水清,我的儿啊,我苦命的儿啊……”
水清赶快扶了德婆婆,抽泣地安慰道:“翁妈,别这样,大年初二,不兴哭的。”
“唉——”德爹爹长叹一声,走出自己的小屋的时候还催促道,“水清,赶紧收拾了去啊!”那声音好重、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