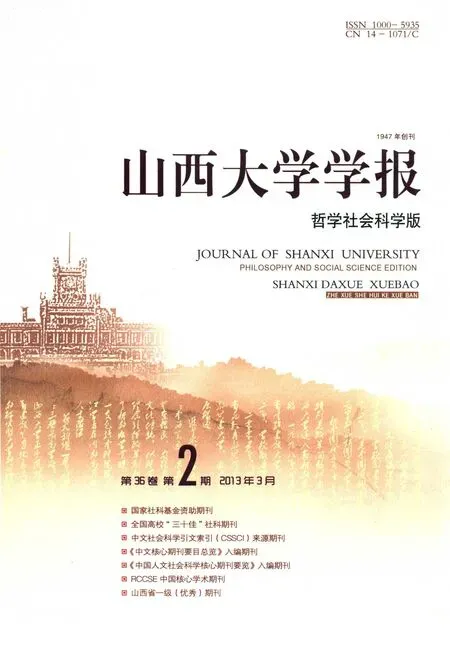德音孔昭于犹邦——以色列汉学家柯阿米拉《论语》希伯来文译本初探
2013-11-07唐均
唐 均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中国文化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自近代以降首先是随着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运动而急遽增加的。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载体之儒家经典,特别是以《论语》为基础的“四书五经”往往成为英、法、德、俄等欧洲大国语言首选的迻译作品。时至今日,由于欧洲主要国家之间语言关系的相似性和文化背景的趋同性,更多儒家经典的译本在更多欧洲语言中间诞生出来。
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语言文化上迥异于欧洲诸国的犹太人直到20世纪中叶才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独立的以色列国,而又因阿拉伯世界的强力排斥而成为欧洲政治版图的一个边缘国家(注意:地理版图上的以色列属于亚洲国家)。尽管犹太人曾经为世界贡献了包括《圣经》在内的多种文化成就,但是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实质性的交流,还是在以色列国逐渐和中国展开交往后才发展起来的(注意:早期来华犹太人在中国境内的文献传播仅有片段信息存世,对中国主流社会几乎没有影响,故暂不计)。
由于现代希伯来语接受欧洲语言影响的系统性以及以色列国居民强大的英语背景,较早时期的希伯来文翻译中文作品大多经历了英语的转译。近年来随着更多直接阅读中文的犹太学者的出现,开始改变中国和犹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途径,其中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直接译自中文原文的希伯来文译著逐渐增多。下面我们集中考察儒家经典之首的《论语》最近的一个希伯来文全译本,从中体会这种直截了当的译事之于民族文化交融的深远意义。这个译本是由当代以色列汉学中坚力量之一的柯阿米拉教授完成的。
一 译者及译本
柯阿米拉(Amira Katz-Goehr,希伯来文拼作),现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传统中国思想文化,其全文译出的儒家基本经典《论语》即是我们在下文予以重点介绍的对象。她还用希伯来文翻译出不少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多数已用于以色列高校中国历史文化课程方面的补充读物[1]——例如,其《骆驼祥子》希伯来文译本于1985年刊于耶路撒冷,她也因为在犹太世界推介老舍文学作品的功绩而成为中国北京老舍纪念馆的荣誉馆员。目前她正和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Plaks)合作,将荟萃中国古典文化的集大成《红楼梦》全文译成希伯来文,现已有了前三回译文的进展[2]3-22。
“论语”一词的本义就是“接闻于夫子之语”的“论纂”,亦即“孔子讲话的汇集”。柯阿米拉的这个《论语》希伯来文译本,题名即作“孔子的语录”()——这里的遣词用语值得注意——首先,希伯来文中关于“孔子”的这一表达()明显是源自拉丁语、而后通行于欧洲语言中Confucius一词的希伯来文音译;其次,所谓“语录”(),则是希伯来语动词词根“说”()派生的名词“文章、言语”()的复数形式,这个意蕴同样切合于欧洲语言中的固定译法——比如英语的analects“语录”,尽管后者可以追溯到希腊语中性名词“选择、抉择”(analektos)的复数形式(analekta)。由此可见,仅从题名的翻译处理,我们已可管窥这部译自中文原文的希伯来文译作所受欧洲语言影响的深刻性了。
在书衣的封面部分,就以此希伯来文和繁体汉字并列题名;此外还分三行用希伯来文题署“Amira Katz翻译、介绍和注释”——

正文部分包括繁体中文原文和希伯来文译文的对开对照[3]1-195以及详尽的注释[3]197-505和丰富的参考文献[3]507-519。这里所用的中文原文有两个突出的特色:一、所有的“悌”均写作“弟”;二、作为篇章题名的“泰伯”和作为正文的“太伯”用字不同。希伯来文译文的特色是:将中文习用的标题略去,改以希伯来字母次第表明篇目——因而在随后的注释中,注释标号搭配标识章节的希伯来字母便于读者快速定位至译文的相应章节。或许由于上述处理,这个双语对照译本更多的是考虑犹太读者的需要;而对于译文和原文之间的对等问题,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撰述详加讨论。不过从下面一个细节可以看出本书译者遵循中文原文的准确性来:希伯来译文处理汉人复名或复姓的规则是:对单姓或单名的音译单独成词而音译复名或复姓的两个希伯来音节之间用连接号缀上,例如“蘧伯玉”()[3]143、 “ 公 山 弗 扰 ”()[3]165、 “ 公 孙 朝 ”()[3]189;但在音译“柳下惠”这个人名时,由于“柳下”是食邑之名而相当于复姓,故用连接号缀上音译这个部分的两个音节,作为单名的“惠”则单独成词,从而得出这样的音译形式:[3]179。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参考文献”征引中文部分有个笔误:即在胪列历代儒经注疏者时误将南北朝时人“皇侃”记为今人“黄侃”了[3]518。
之后还有三个附录:其中“附录二”[3]561是“中国历史朝代简表”()、“附 录 三”[3]562是“主 要 儒 教 经 典 译 名 对 照”(),而“附录一”[3]521-560也是一篇煌煌之作,但亦非出自该译者之手。附录之后是一个指引详尽的“索引”()[3]563-589,依照希伯来文字母排序,便于迅速定位各种中文概念和指称的希伯来文迻译处理形式。
二 序言和附录
由此可见,这个序言的核心内容是介绍儒家经典,先历数范围更广的“十三经”,这有助于对儒教产生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和对直接反映儒家始祖——孔子言行载体《论语》一书的认识,再缩小范围集中论述“四书”这一后世经典化并直接作用于中国古典政治科举仕途的文献载体,从而凸显该序言引出的本书主体——《论语》的内容译介。
而“附录一”是一篇篇幅颇长的专题论文,由以色列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尤里·皮涅斯(Yuri Pines,希伯来文拼作)撰述。此人1964年生于乌克兰基辅,1979年移居以色列,1998年博士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现为该院系教授。其主要学术兴趣在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中国历史文献学以及早期中国社会政治史。附带说一句,宋立宏将这位汉学家的名字处理为“尤锐”,如果不是本人的自取汉名,就明显是英译这个斯拉夫人名作为中文指代的结果了,对照其希伯来文读法即知其不妥。
这篇附录题名作“失败之后的成功:作为汉人路线导师的孔子”(:)。全文除引言部分,另外分成七个小节,各节小标题以希伯来字母为序号加以标识:
仅由此标题即可窥知,擅长先秦思想史的这位汉学家,将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置于华夏民族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中进行历时考察,系统梳理了儒教理论的起承转合,使得这篇长文当不失为阅读完这一译本之后深入了解孔子、深化儒教认识的优良读物。
三 几个核心概念的迻译
孔子本人所提倡的核心概念有“仁”、“礼”和“中庸”,这些在《论语》一书中都有突出的反映。与之相关的希伯来文翻译情形可以参见下表的数据展示——出现次数引自一部《论语》英译研究专著[4]236,237,266,虽然所据版本未必一致,但是可以部分反映这些概念的相对重要性:

表1 《论语》三大核心概念希伯来文翻译统计
作为儒家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仁”在《论语》里出现的极高频率从某个角度可以印证这一点。在其希伯来文翻译中,表现形式却也并非唯一,主要有两种形式:多带定冠词、表特指的单词“人性”()和名词短语“仁慈之人”()——有关的内涵问题在译文所附的注释中有着较为细致的讨论[3]203-205,282。无论如何,这里借用希伯来语言中指称“人”的固有词根(√和√)来对译中文原文中同样渊源自“人”的儒家核心概念“仁”,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可以借助其间重合的某些因素来达到译文和原文严丝合缝的扣合境界,从而摈弃了欧洲语言中习见的以“道德良善”(moral、good、benevolent等)来模拟“仁”[4]236-237的偏差。
对于崇古守制的孔子而言,“礼”是其推崇备至的一个方面,因而《论语》中这个语词出现较高频次也在情理之中。这个希伯来文译本中该概念一般都译作多带定冠词的复数名词“仪礼”()——有关的内涵阐释在译文所附的注释中也有着较为细致的讨论[3]213-214。这个复数处理模式似乎参考了以英语为代表的欧洲语言的相应对译情形——rules of propriety、rites、education and good manners等[4]237-238。
上述两个儒家基本核心概念在这个希伯来文译本中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克服了以往借助英语译本中转翻译成希伯来文时所带来的概念迻译之偏差[5]307-308。
而“中庸”一词虽然在《论语》里只出现了一次,但由其后来统领《四书》之一篇即可窥见这一概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枢纽性。这个儒家核心概念的希伯来文翻译处理成为“中间之道”()而且用引号加以凸显[3]15,从而使其作为专门概念的地位得以体现,这种模式在希伯来字母这样缺乏大小写区分的文字系统中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处理方式。
下面再行考察另外几个具有鲜明儒家思想特征的重要概念的希伯来文翻译,亦如下页表2数据所示——其中的出现频次同样引自同一部《论语》英译研究专著。[4]235-272
其中,作为关涉人性的抽象概念“德”“信”“义”,这里的希伯来文翻译利用语义相关的抽象名词来对译,再加上表示特指的定冠词之后可以接受。“忠”“恕”的希伯来文对译则可能是源出动词的名词化形式。而非具有汉文化特征的“孝”“悌”观念,在希伯来文的对译中直接用短语加以意译,很有可能是参考了欧洲语言——比如英语中的相应处理:filial piety/responsibility“孝”和 fraternal submission/responsibility“悌”[4]249-251。而原文中涉及的三种类型的人——“君子”“小人”“圣人”译成希伯来文的基本模式都是带修饰语的名词短语,但构成“君子”的两个希伯来语词之间有连接号,显示其是一个并置的整体,从而区别于“小人”和“圣人”的译法;另外,作为对译“君子”和“圣人”的中心名词用的是充满神性的“人(亚当——来自神用泥土所造的)”()且不用定冠词,表明其高贵特性,而对译“小人”的中心名词则使用相对鄙俗的措辞“人(丈夫)”()且带上定冠词,就在语法形态表现上体现出其对应的贬义色彩来了。而最为特殊的处理,是对“士”翻译:不仅有单引号括起的音译形式(),而且接踵括出其语义注释“学者”(),这就显示出译者已经明确意识到原文的“士”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学者”虽然存在着语义交叉但绝不能等同。

表2 《论语》部分儒家重要概念希伯来文翻译统计
以上针对部分中文概念希伯来文翻译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希伯来文译本的处理,是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中文原文语境加以进行的,译者也匠心独运地调动希伯来语言的多种表现手段,以便区分出原文某些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这样处理的前景,正是中国文化深入影响像希伯来犹太文化这样的异域文化、从而有可能与之水乳交融的结果。
四 结语
中国文化之于犹太世界而言,不论从语言关系上看还是自文化背景而言,都是具有相当陌生度,而两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又是缺乏厚重历史积淀的。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和中国文化的主动出击,使得包括犹太世界在内富于文化积淀的民族都可能积极吸收中国文化要素,用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
然后这种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直截了当的文化接触。从原文译出某些经典作品,就是上述接触和交流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根据上文对这样一个《论语》希伯来文全译本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关系疏远的两种语言——汉语和希伯来语,以及文化背景迥异的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逐渐可以摆脱第三者的间接影响,真正走向两种语言、两个民族之间的自我互动。而在这种自我互动的直接实现过程中,我们或可发掘出两者之间隐藏的一些共性,从而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刻体认和了解。
参考文献:
[1][以色列]伊爱莲.以色列的中国研究[N].宋立宏,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2-10(162)第13版.
[2]Katz- Goehr,Amira.A Dream of Translating the Dream into Hebrew[J].Journal of Sino - Western Communications,Volume 3,Issue 2(December,2011).
[4]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5]Eber,Irene.A Critical Surve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 Hebrew[M]//One into Many: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edited by Leo Tak - hung Chan,Amsterdam - New York:Rodopi,2003:30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