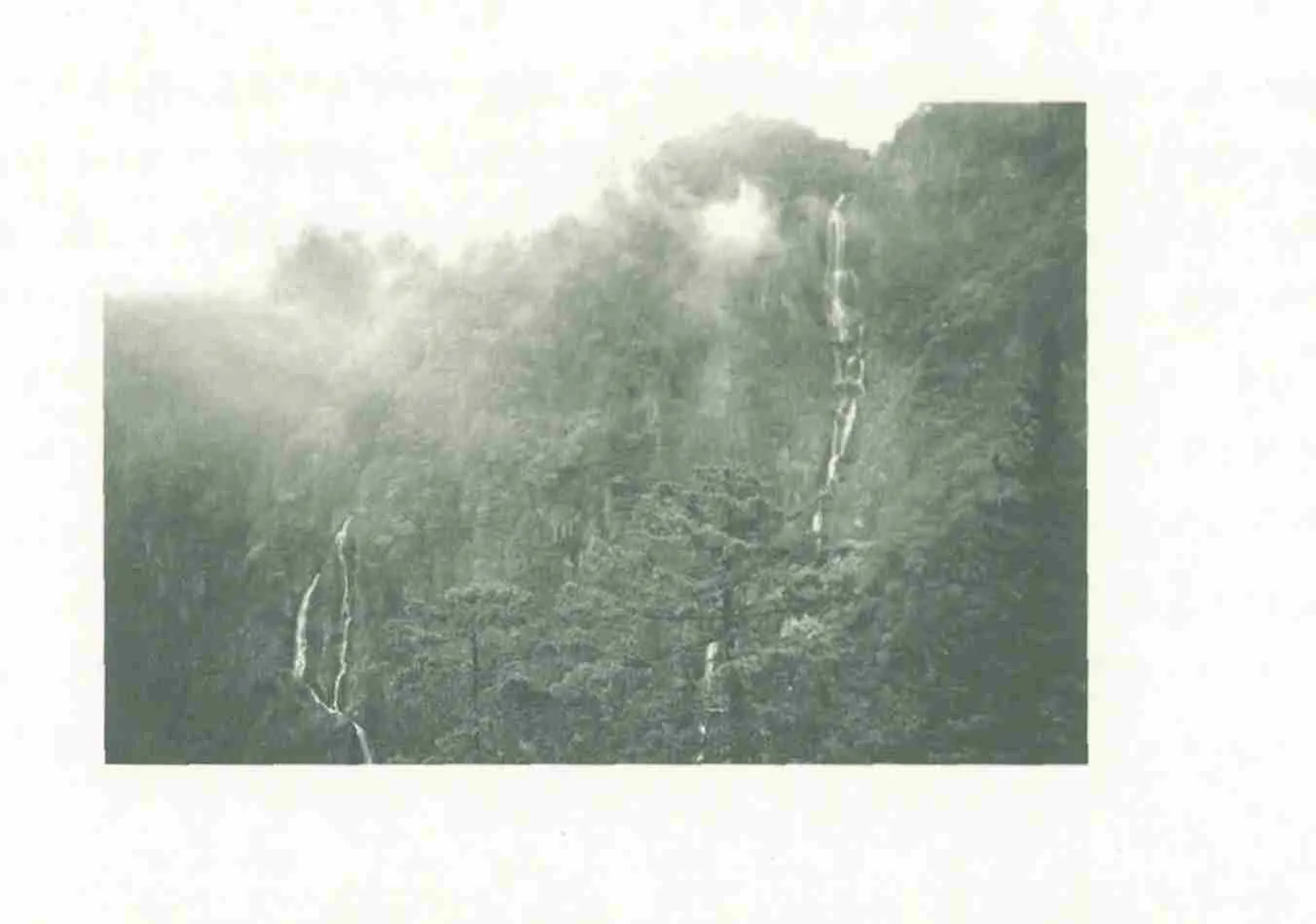崛起、困境与出路:青年批评家论坛·文学批评与文学生态研讨会综述
2013-11-05方岩
方 岩
2013年8月9—10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扬子江》评论杂志社共同举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文学批评与文学生态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批、第二批共十七位客座研究员、青年文学批评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范小青,党组副书记、《扬子江评论》主编张王飞,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著名学者、批评家丁帆、汪政、王彬彬、黄发有等人全程主持、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近年来一批被称之为“70后”、“80后”的批评家的迅速崛起是当代文学研究界中一个比较引人瞩目的现象,因此,与会的青年批评家代表们围绕着“如何建构当代青年文学批评的品格”、“青年批评家与文学现场”、“《扬子江》评论与当代文学批评”这三个会议主题展开了更为具体的讨论。
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史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来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再次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丽军由此引申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批评”这个话题,涉及批评家的代际形成、命名以及青年批评家如何与同时代的作家共同成长。他认为,青年批评家要将研究与批评贯通,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进行批评实践,如此方能在文学现场树立批评家的形象,并打破创作沉寂带来的批评的相对沉寂。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志荣以钱钟书关于学术研究的一段话将话题继续推进。钱钟书曾在《谈艺录》中说:“发大判断外,尚须有小结裹”。所谓“大判断”,即今天通常所说的宏观研究,而“小结裹”则指微观研究。刘志荣认为钱钟书的观点同样适用于青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他认为“小结裹”与“大判断”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方式,但是作为具体而微的作家作品分析的“小结裹”,其中应该有时代精神、历史视野、理论深度等“大判断”作为支撑或背景。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莉更关心青年批评家如何在时代的文学大潮中披沙拣金,以自身的批评实践为文学史挑选经典。她以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对同时代作家如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发现与推荐为例,强调广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深厚的历史修养方能让批评家在历史现场及时地做出判断,并为此后的历史叙述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青年批评家的代际形成、划分、命名及其面临的问题是此次会议的又一个焦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平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回避“80后批评家”这样的命名对批评家群体和批评生态所造成的遮蔽,但在批判之外,他更愿意平和地审视类似的批评现象命名的由来、更迭与影响,并对“80后”这个批评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式的溯源。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金理在发言中提及黄平近期对电影《小时代》的持续的追踪批评,将话题推向深入,即在这个资本急剧扩张、媒介宰制日益强大的时代里,青年批评家如何面对、选择批评对象?在金理看来,黄平在历史现场对批评热点不知疲倦的追踪固然体现了一种可贵的职业精神,但是批评家如何既能敏锐地捕捉现象、做出判断,又不会被拖入资本、媒介的自身逻辑而在受控于它们的文学、文化现象中疲于奔命?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庆祥对此保持了必要的警醒,他认为,这是一个批评过剩的时代,青年批评家过分沉溺于热点的追踪与制造,事实上是在强行构筑历史。他觉得,优秀的批评家应该适当地保持缄默,冷静地等待、选择有价值的批评对象,就像猎手一样,耐心地隐没于丛林深处,等待猎物出现,并给予精确、致命的一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刘大先则补充道,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只关注于重要现象,他与平庸的批评家的区别就像猎手与猎狗的区别那样,猎狗被目标牵制着东奔西突从而丧失了主动权,而猎手则能屏息静观从而捕捉自己感兴趣的猎物。
正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房伟所指出的那样,在目前理论来源、阅读兴趣、价值判断愈发趋同的批评生态中,批评实践到底是在披沙拣金还是在捡垃圾,成为青年批评家必须面对的一个困境。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立群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面对一个理论过剩、批评从业人员亦过剩的批评现状,适当的沉默不语方能使得批评走出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涛从历史根源分析了原因,他认为,一批被冠之于“70后”、“80后”的青年批评家被批评界关注,从根本上讲是从晚清延续至今的青年崇拜这种肤浅的历史进化论心理所致。因此,这一代的批评家若要为历史留下有分量的批评,还需进一步的沉淀与积累,不要轻易草率地发言。《解放军报》文化部编辑、记者傅逸尘指出,青年批评家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困境在于,因为感受力、经验、阅历的局限,他们的批评实践大多是纸上的人生,这些批评远离现实的人生,缺乏穿透力。所以,青年批评家如果能接受更多的现实历练,批评实践才能坚实而从容地穿梭于思想、人生、历史与批评对象之间。
上海市作协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对批评家的代际命名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70后”、“80后”这样的命名、代际划分同许多常见批评概念一样,对批评生态、文学生态的多样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遮蔽。与这种命名类似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年选、年鉴,这些批评行为、实践,制造了昙花一现的热点现象、话题,不仅遮蔽了历史现场的复杂性,而且强行切割了历史的连续性。在他看来,关于青年批评家如何进行批评这样的技术性话题的讨论已经太多了,但是批评终归是一种实践,是通过文字书写来传达价值判断和意义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批评是自律性、创造性的个体选择。因此,他觉得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应该是伟大的作家。其实,这印证了杰弗里·哈克曼在《荒野中的批评》一书中提出的“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这个观点。
事实上周立民的发言已经涉及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文风、文体和思想资源等问题。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岳雯将侧重于审美感受的印象式批评与侧重于理论实践的学院式批评,分别形容为在历史现场裸奔和穿戴盔甲在战场上鏖战。在她看来,两者不同的文体、风格的批评实践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价值等级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两者可以更好地融合,实现批评生态的多样性。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丹梦引用了《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段话来强调,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方法、文体、风格、资源的自由选择与应用才是实现批评的自由与繁荣的前提。学院批评目前的困境有目共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如是说,国内现有的学术培养机制和学术评价制度决定了当下学院批评的基本品格、形态。她认为,学院批评固然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但是趋同的理论、文体、文风和价值推导判断方式亦反映出学院批评在重重的盔甲之下的僵化。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批评家只有不断反思、自律并积极推动学院批评的生存状况的改变,学院批评方能焕发新的活力。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曾一果则强调因为理论的多元和研究兴趣的多样,学院批评的内部还是呈现了一定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他在自己的批评与研究中就非常注重批评实践和批评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思路能够在具体的批评行为与思想/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等层面的宏观视野之间建立起可靠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大先关于青年批评家如何构建自己的精神品格、学术风格的谈论,很能代表与会青年批评家的共识。他认为,青年批评家应该具备“不屈不挠的博学”这种素质,青年学者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乃至跨学科跨专业地汲取理论、占有材料,才能更好地判断、定位自己的研究对象;身处媒体与资本急剧扩张的时代,青年批评家既要密切关注历史现场,又要审慎地判断,以免沦为媒介与资本的宣传工具,因此,青年批评家在批评立场上应该处理好守护现场与走入公共之间的关系;青年批评家还应该关注中国文学生态的复杂性,不仅关注热点与主流,而且要给予边缘现象如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以足够的重视,换而言之,批评实践只有重返大地才能更好地张扬诗性正义。
在此次研讨会中,作为青年批评家的文学引路人的一些著名作家、批评家也参加了会议,并与青年批评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著名作家范小青认为,目前的青年批评家与前辈相比,有着更为系统、扎实的学院专业训练和较新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视野,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表现出一种锐气和深度兼具的学术风格。江苏省的文学界有着创作与批评良好互动的传统,范小青希望青年批评家能够继续关注江苏文学的发展,积极参与到江苏文学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历史进程中。著名作家李洱非常欣赏青年批评家们的扎实的才学和广泛的阅读量,他希望青年批评家继续保持锐气、站在文学风尚的前沿,为作家和读者挑选有价值的作品。《扬子江评论》主编张王飞希望青年批评家能够继续与杂志合作,将杂志办成一本既有敏锐的现场感又有厚重的历史感,即不回避争议也不制造噱头、伪命题的批评刊物。
丁帆认为,无视审美感受、理论先行的技术化批评是一种非常病态的现象。现有的学院体制化背景下,缺乏历史意识和哲学高度的工匠式的批评实践将无法进行有效的价值判断并参与到历史进程中。他希望青年批评家能够克制这些弊端。王彬彬也提醒青年批评家,不能忘记批评的起点在于审美判断,他希望青年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能够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与审美判断融会贯通。汪政希望青年批评家要像前辈那样积极沟通、交流,实现个体的感受、知识的及时共享,共同推进批评生态的繁荣。吴义勤认为青年批评家应该超越时代环境的限制,在现场和历史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实现批评形态的多元化。黄发有认为青年批评家是打破目前批评僵化状态的新生力量,他希望青年批评家不仅能够迅捷、及时、深刻地捕捉文坛新生现象,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批评变成美文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