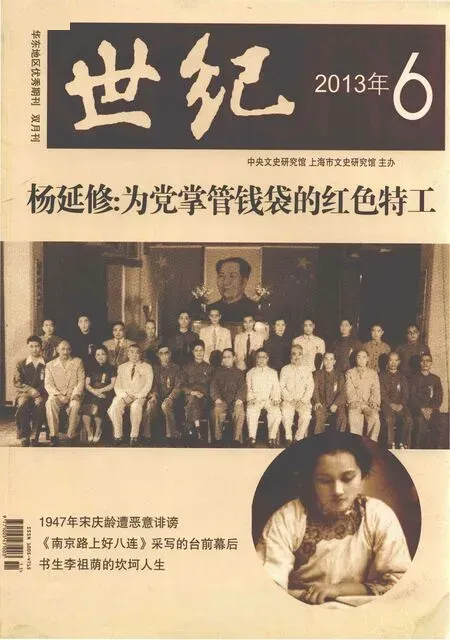复旦首届女生严幼韵
2013-10-31周桂发
周桂发
严幼韵十八岁时曾遇到一个看手相的人,说她会度过精彩的一生,足迹遍布四方,身边的人非富即贵。百岁之后她回想起这段话,“每一句都应验了”。
她是上海滩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也是子孙们爱戴的Grandma(奶奶)。她是整个近现代史的见证人。严幼韵的一生,跨越了一个多世纪,并没有被岁月的沧桑淹没,而是沉淀得越发美丽。
名门之秀惊艳复旦
故事要从1905年讲起。这一年,复旦大学初建;而沪上的严家,也新得了一个女孩儿,取名严幼韵。
严幼韵的祖父严信厚(字筱舫)早年在上海的一家银楼学生意,后经人介绍,入李鸿章幕府,获其赏识,得到署长芦盐务帮办的官职,开始其以盐务起家,积累资金投资工商业的历程。在晚清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严信厚是一个在商海的浪潮中长袖善舞的弄潮儿。

1932年风姿绰约的严幼韵
严信厚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产,使得严幼韵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富家生活。在天津的中西女校毕业后,严幼韵随全家南下,回到祖父的发家之地上海。1925年,严幼韵进沪江大学读书。192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尚在艰难的起步之中。1925年这一年,全国包括专科学校在内的高等院校才刚过一百所,在校学生的总数是三万二千五百多人,大致与今日复旦大学一所学校的在校全日制学生数相近。因此,当年能进大学的女生实属凤毛麟角,大都来自富裕的家庭。沪江是一所教会学校,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但有严格的校纪校规,学生被要求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生性活泼好动的严幼韵呆得并不舒服。
适逢1927年,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严幼韵就和女性好友萧子雄一同转校,来到校园氛围宽松得多的复旦大学念商科。
女生初进校园,使复旦的男生如沐春风。笔者翻阅了当时在复旦就读的几位校友的回忆录,其中,校友齐云回忆道:“平常一般顽皮而天真的男同学们,骤然之间见了哪位典型的女同学,好似人力车夫见了交通警察一样,深恐触犯规章,不敢乱动一步,人人均谨言慎行,衣履清洁,内务整洁。在功课方面,亦较往昔加倍用功,不但白昼专心苦读,晚上还要开夜车,深恐成绩落在裙钗之后。”
严幼韵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严家在南京路上开有“老九章绸布庄”,各色衣料随大小姐挑选,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因此,严幼韵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
她的同班同学章宗钰说,无法形容严幼韵美在何处,只是“好有一比,萧子雄同学和她寸步不离,一高一矮,一美一丑,例如邱正伦教授的公司理财课,她俩每次必迟到,门声响处,皮鞋答答,大家一定‘向右看’,弄得邱教授讲‘Issue Bond Issue Bond’接着说不下去,足证其魔力之一般”。
她于功课上并不大用心,但也自有应付的办法。遇到要交习题或报告,她会电话某位男同学,说借他的习作一看。闻者无不欣然听命,一位周同学整本报告被她拿去交卷后,甚至认为“受宠若惊”。在归还的习作上,她会洒上一些香水致意。
严幼韵转入复旦时,后来被称之为“东宫”的女生宿舍尚未建好,正合她不愿住校的心意。她坐自备轿车从静安寺的家中来校上课。轿车配有司机,车牌号是84号。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沪语的“爱的花”。年轻的严幼韵喜爱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自己驾着车一路开过来。很多男生守在校门口,就为了一睹“爱的花”芳容。
这一外号不胫而走,名声更传出复旦校园,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红遍了上海滩。严幼韵的女儿杨雪兰于2012年末接受笔者采访时还提到,1980年她从美国回上海的时候,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朋友,老先生听到严幼韵的名字,脸一下子亮了起来:“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呢!”
郎才女貌“爱的花”
严幼韵和第一任丈夫杨光泩的相识,也和“爱的花”有关。
杨光泩出生在一个丝商家庭,其祖父也是在十九世纪末来到上海开丝行的。1920年,杨光泩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庚款资助赴美留学。四年后,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法博士学位。1927年,杨光泩谢绝了华盛顿美利坚大学远东史讲师的聘书回国,受聘于母校清华,担任政治学和国际法教授,并兼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年初,北京政府大势已去,杨光泩受邀南下,进入了南京政府外交部。
杨光泩第一眼见到严幼韵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路跟着她。很巧,他们是去同一个聚会的。他立刻请朋友介绍认识,随即对严幼韵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不断地送花,请她看电影、跳舞……两人情投意合。
1929年9月6日,严幼韵与杨光泩举行婚礼。婚礼就在他们经常去跳舞的大华饭店举行,这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有千余人出席,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婚礼的照片在报纸刊登后,成为上海滩众多青年男女向往的风尚。一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照片仍然被引为旧上海时髦婚礼的佐证。
1930年,新婚不久的杨光泩出使海外,严幼韵也随夫出洋,开始了外交官夫人的生活。1938年,杨光泩奉命赴菲律宾,以公使衔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当时菲律宾尚未独立,中菲间没有互设使馆,驻马尼拉总领事就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最高外交代表。1939年初,严幼韵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也来到了马尼拉。

1929年,严幼韵和杨光泩在大华饭店举行婚礼
作为总领事的夫人,严幼韵亲手设计并操办了总领事官邸的装潢,陪同杨光泩出席各种外交礼仪活动,还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了菲律宾和美国的官员及华侨领袖。由她出任名誉主席的华侨妇女协会,发起了捐赠金饰、折复活节纸花的爱国募款活动,华侨妇女们走上菲律宾的大街小巷,向街坊、商店、工厂募款募药。此外,她们还为前线战士赶制了一百万个急救医疗包。虽然辛苦,但能帮丈夫做一些事,能为祖国尽一点力,严幼韵形容这段日子“非常美好”。
然而,幸福是短暂的。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两天后,3个日本宪兵踢着正步来到马尼拉饭店,对正在用早餐的杨光泩说:“你被捕了。”杨光泩十分平静地回到房间,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包衣服,告别了妻女。
被日军拘禁期间,杨光泩严词拒绝了日军要其向华侨募款的要求。4月17日,杨光泩和七名外交官惨遭杀害。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严幼韵才知道丈夫已经遇害。
杨光泩被捕后不久,严幼韵就带着孩子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作为总领事的夫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七位外交官的妻儿,况且那些外交官太太都比她年轻,孩子也小。于是,这栋有三个卧室的屋子,就成了这些外交官家属共同的家园。严幼韵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解决食物供给、平息争端,后来还带着一大家人几次搬家。她自小养尊处优,从来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的经验,但生活压迫下她便只能适应,从未有人听闻她抱怨。

几十年后,年逾百岁的严幼韵在自传《My Story》中回顾这段日子,自豪地说:“现在回头想想,我们当时的确非常勇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又很担忧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命运也完全茫然不可知。但我们做到了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与顾维钧相伴的幸福晚年
1959年9月,严幼韵与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这一年,严幼韵54岁,顾维钧71岁。
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严幼韵与他早就相识。1945年5月,严幼韵初到美国时,轮船停靠在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她的二女儿急性阑尾炎需动手术。正在旧金山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顾维钧立即伸出援手。严幼韵在旧金山住了三个月,直到女儿身体恢复才赴纽约。
1946年7月,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严幼韵护照到期后,顾维钧还以大使身份亲自为她向外交部申请。退休后,顾维钧又赴海牙出任国际法院法官,两人两地分离。顾维钧有首诗写在此时,由严幼韵收录在《My Story》中:“夜夜深情思爱人,朝朝无缄独自闷。千种缘由莫能解,万里聊航一日程。”
和严幼韵结婚的时候,顾维钧已经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了两年,一直住在旅馆里。杨雪兰记得:“当时的顾先生非常瘦,也非常严肃,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仆人专门站在他身后服侍,随时递上一块餐布。”
和活泼的严家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严肃的顾先生”也被“改造”过来。有一年全家一起去滑雪,两位老人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结果有一天孩子们回来时,发现顾维钧正喜滋滋地试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和孩子们一起滑雪去。《时代》周刊还为此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顾维钧谈养生心得,只三样:“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他习惯晚睡晚起,严幼韵担心他从晚餐到早餐间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不利,所以每天凌晨3点起床,为他热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就是在家安排牌局。去世那天(1985年11月14日)晚上22点左右,他还问严幼韵:“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
他们一起生活了26年。严幼韵(Juliana)的桌子上,至今摆着一对玻璃小猪,上面的纸条是顾维钧(Wellington)亲手写了贴上的 :“W admiring J”。
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未加入美国籍,直到离开。顾维钧去世后,严幼韵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2007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落成于上海福寿园,如愿魂归故里。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王生洪教授参加了揭牌仪式并讲话。严幼韵的一尊坐像,目前也在计划中,打算落座于顾维钧的铜像旁。

顾维钧致严幼韵手迹
百岁亦从容
现在的严幼韵,居住在美国纽约,四世同堂,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她看书读报,旅游,去超市购物、烤蛋糕,甚至还有眼力织补羊毛衫。她一直热衷的麻将聚会,如今每个星期举行两到三次,她能从下午三点半打到晚上十一点半,整整八个小时兴致盎然。
但最让老人高兴的,莫过于看子子孙孙欢聚一堂了。她自己也很惊讶,说:“我原来只是一个带着三个小女孩的单身寡妇。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家庭?我有三个女儿,七个孙子孙女,和十八个曾孙!”
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女儿都很出色。长女杨蕾孟是资深编辑,经手出版了《爱情故事》、《基辛格回忆录》等250多本书,是美国出版界为数不多的华裔成功女性。次女杨雪兰是一个有成就的企业家,上世纪末她出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为通用汽车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牵线搭桥。近年来,又担任美国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致力于推进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幼女杨茜恩早年致力于房产开发,卓有成绩;后来相夫教子,也治家有方,可惜因病较早去世。
据杨雪兰回忆,严幼韵从不干预子女的终身大事,三个女儿的婚事都是她们自己定的。女儿带男朋友或是未婚夫回家时,严幼韵总说:“要是你自己确信(是这个人)了,那我也满意。”杨茜恩的丈夫唐先生从事金融业,被严幼韵称为家庭的“key member”(极重要成员)。她和顾维钧晚年的积蓄,都是交给这位三女婿打理的。
与顾维钧结婚后,顾先生的子女也成了这一大家子的组成部分。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谈起继母来也不禁感慨她的不容易:“我们顾家这些人,跟她们原来不认识的,她能够把我们全部召集起来作为家庭,这不是简单的事情。”顾家的子女并不叫严幼韵母亲,而是直呼其名“Juliana”,她也不在意。顾维钧早年离家,和子女难得亲近,而严幼韵和他结合而成的这个大家庭,却能让顾菊珍感到“回来真是回家一样”。
称呼严幼韵“Grandma”的,不仅是她自己的孙辈,还有得她关爱的佣人子女。严家的保姆和管家换过几次,严幼韵对他们的孩子都视如己出,从来不骂,非常宝贝。严家第一任保姆的孩子,便是在顾维钧和严幼韵的亲自照看下长大的。孩子们在严幼韵的床上跳来跳去,老太太很开心。有的孩子刚来时不会也不敢说英语,严幼韵便让她和自己同桌吃饭,和她用英文对话。这些家庭成员往往都是第一次出国,难以支付子女在美国就读的学费,严幼韵便一一提供学费赞助,鼓励孩子申请合适的学校,不要有顾虑。孩子们也都感念于心。毕业、结婚的重大时刻,他们都不会忘了和守在家中的“Grandma”分享快乐,称她为“我的偶像”——正是从她身上,他们学会了要去爱别人。
早年出国后,严幼韵常要应付各种外交场合。各种酒宴聚会,正是绅士淑女们争奇斗艳的时候,严幼韵却一直只穿中国的旗袍。她的旗袍,从布料、设计到剪裁,处处考究,件件都是精品。在严幼韵看来,这不仅是形象问题,更关系到生活品质,马虎不得。央视记者给她拍纪录片时,她仔细地挑香水、闻味道,恍惚间叫人觉得,几十年时光过去并没有伤到她分毫,她依然是那个惊艳了上海滩的爱美女郎。这一辈子,她从没穿过平底鞋:“叫我光着脚就不会走路,觉得好像要仰过去。我的拖鞋都要有点跟。”面对镜头,她笑得开心灿烂——严幼韵一向爱拍照片,家里的保姆平时就常常给她拍,老人每次都很高兴地配合。
用女儿杨雪兰的话说:“她就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严幼韵从不像一般老人一样束手束脚,“我不觉得老嘛,可以吃,可以睡,可以打麻将!”也从不忌口:“我已经活了那么长,我才不在乎吃什么。”她觉得,自己的长寿要感谢家人和朋友的爱。杨雪兰则把母亲的长寿归结于她终生保持的乐观精神:“母亲一生常说一句话,‘事情本来有可能更糟呢’。”严幼韵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戴假牙,结果有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出了事故,把老人家的牙撞掉了。女儿们听了消息都很沮丧,严幼韵却反过来安慰她们:“我可幸运啦,要知道出租车本来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大概只有每年的三次生日,会提醒人们严幼韵是个年逾百岁的老人。笔者从严幼韵的侄女徐景灿那里得知,退休以后,老太太每年要做三次生日:一次大家庭聚会的 dance party;一次麻将party ;还有一次由保姆当主人的party。小孩子们变着花样逗老人家开心:把她的头像顶在头上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排队给她献玫瑰花;为她订制电风扇,一按按钮就可以看到“庆祝严幼韵107岁生日快乐”和“happy birthday ,Juliana”的字样……
每个生日都是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其乐融融。2012年9月24日,在纽约上东区Pierre酒店隆重举行严幼韵107周岁生日party,全家五代人和140多位宾客出席祝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夫妇也特地到场祝贺。《纽约时报》还以《顾严幼韵107岁生日 大家族祝寿》为题,做了专题报道。

说起来,笔者与严幼韵学长颇有缘分。2005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也正逢严幼韵百岁华诞,笔者主编了一本名曰《巍巍上庠百岁星辰》的书,收录杨国亮、李仲南、蔡尚思、夏征农、钱悳、雷洁琼、严幼韵、周有光、李兆萱等九位健在的复旦百岁以上校友的人生历程,委托当时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历史系金光耀教授送予严幼韵,她甚为兴奋。2007年9月2日,严幼韵女儿杨雪兰在参加上海福寿园顾维钧铜像落成后,应邀在复旦演讲,笔者将特制的反映严幼韵精彩人生的牌匾赠送给杨雪兰,如今这块匾还挂在杨雪兰在上海老锦江宾馆办公室的醒目位置。笔者和严幼韵一家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年老太太过生日时,杨雪兰都会把家庭聚会的照片寄一份送给笔者留念。2012年9月,笔者根据学校留存的档案资料,特地制作了一本画册——《“复旦履痕”——致严幼韵》,并在扉页上书写一副嵌名联:“期颐添筹情心幼,盛世常品爱花韵。”让杨雪兰带给严幼韵,作为她107周岁的生日礼物。老人家收到之后,非常高兴,并应笔者要求,在9枚复旦百年校庆纪念信封上亲自一一签名,送给复旦。2012年12月16日,杨雪兰带回由严幼韵在照片上亲笔签名赠送杨玉良校长的镜框和严幼韵的英文自传《My Story》一书,以及9枚纪念封。笔者代表复旦大学档案馆提出,希望能把老人家的照片、实物、档案资料,包括她的一些旗袍都捐赠给复旦,杨雪兰当场答应:“能有一个地方专门保存老人家的资料,我们也觉得很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