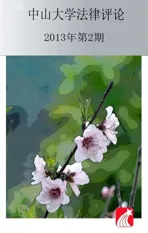法和政治的存在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现象学阐释
2013-09-27周维明
一、绪论
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体系崩溃后,现代性(modernity)伴随着马基雅维利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降临到了人类世界。[2]See Leo Strauss&Joseph Cropsey,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p. 296ff.现代性的发展经过了三次浪潮:[3]See Leo Strauss,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Ten Essays,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81ff.第一次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它斩断了政治与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联系,以进步与落后取代善与恶作为政治的评价标准,从而确立了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进步这一相对主义观念;第二次浪潮的代表性人物是卢梭、康德、黑格尔,它坚信人类世界的历史将由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最终走向历史的终结,因此确立了所谓的历史主义、历史终结的观念;第三次浪潮则是现代性的危机大爆发的阶段,现代性通过历史主义、相对主义所体现出的虚无主义引发了西方文明最深刻的精神危机,尼采和海德格尔不得不严肃地面对现代性的问题。因此,海德格尔既是现代性的三次思想浪潮中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也是第一位对现代性和虚无主义进行形而上学式的严肃思考的政治哲学家。
人们似乎很难将海德格尔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挂上钩。这不仅是因为海德格尔既在其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很少论及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又在其晚期断言了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不可能性;[1]See Leo Strauss&Joseph Cropsey,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 888.还因为海德格尔直接论及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专著几近于无。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海德格尔看来,法并不具备“本真”(eigentlich)的存在形式,相反,其指明的是“非本真”(uneigentlich)的存在形式,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无助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2]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不过,在《海德格尔全集》(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第 86卷《研讨班:黑格尔—谢林》(Seminare:Hegel-Schelling)于2011年2月出版后,这种观点可能会得到改观:该卷包含了海德格尔于 1934—1935年冬季学期开办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的研讨班的授课纲要。其基本上是海德格尔根据自己的存在哲学对黑格尔的法和国家学说的提要钩玄和借机发挥,因此,通过这些文本来窥探一下海德格尔对于法和国家到底抱持何种态度,既可以有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哲人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又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性的品格及其政治本质。
二、以现象学存在论作为阐释的基本立场
黑格尔哲学是启蒙理性的产物。[1]See Frederick Beiser,Hegel,Routledge,2005,pp.21ff.启蒙理性发端于笛卡尔的哲学。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意味着人本身充当了一切真理的尺度和标准,人类借助理性,摆脱了基于先天存在秩序的古典自然法,人类社会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政治哲学)都将在人类理性这个法庭面前接受裁决,[2]参见[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第2—3页。以主观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由此而生。黑格尔哲学是启蒙哲学的集大成者,因此也可以被看作现代性思潮的最完美体现。黑格尔的庞大哲学体系,可以看作绝对知识即理性的一场历险,借助辩证法(Dialektik)这个“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3][德]黑格尔:《小逻辑》(第2版),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7页。,理性最终返回了其自身,达到自在自为的完满境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作为对客观精神发展历程的描绘,同样遵循了辩证法的原则。
海德格尔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研讨班上,他不仅简要地回溯了辩证法自苏格拉底一直到柏拉图的发展历史,[4]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51.还专门从《法哲学原理》中挑出体现黑格尔辩证法哲学体系基本原则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Was vernünftig ist,das ist wirklich;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1页。这句名言来加以称颂。[6]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54.但是,海德格尔同时又严肃地指出,黑格尔同他的先辈们一样,都“遗忘了存在”(Seinsvergessenheit),存在具有先于辩证法的意义结构,只有存在,才是真正规制万事万物的λγος(逻各斯)。[7]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57.对存在的追寻正是海德格尔用来克服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的利器。[8]参见[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3页。对柏拉图与黑格尔而言,本质(辩证法)先于存在,而对海德格尔而言,存在先于本质。“事物的本质”并不先于存在,反倒只有在存在的视域上方能得到领会。[9]参见[德]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赵卫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5页。因此,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阐释立场是基于存在论而不是辩证法的。而海德格尔又在其代表性著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指出,循着存在论的历史(实际就是指辩证法)来澄清存在论这一条方法根本走不通,对存在的意义的探索应基于现象学的方法,即面向具有“自明性”(Evidenz)的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1]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版),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2—33页。所以,海德格尔在此使用的是现象学的阐释方法,整个研讨班的授课纲要都可以看作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阐释。
三、法权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法哲学的阐释始于法权。什么是法权?黑格尔有一个简明但晦涩的定义:法权是“自由意志的定在”[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6页。。很多哲学家将这句话解读为,法权意味着,法律应当敬畏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的理性主体的人,尊重其人格,保护其自由,使其能自主地构建自己的社会生活。自由意志的人格应该成为抽象法的基本原则。[3]Vgl.Michael Quante,“Die Persönlichkeit des Willens”als Prinzip des abstrakten Rechts.Eine Analyse der begriffslogischen Struktur der§§34—40 von Hegels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in: Ludwig Siep(Hrsg),G.W.F Hegel-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Akademie Verlag,1997,S. 73ff.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观点恐怕是过于自由主义化的解读。海德格尔并不反对自由,也不反对法权有自由的因素。但是他认为,如果单纯地将法权简约化为自由的话,那不过是对法权的一种粗糙的、不全面的把握罢了。举例来说,鲁滨逊孤身一人漂流于荒岛之上,他的法权的虚无性与否是不劳任何事物来加以证成的;只有在星期五到来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才会促成法权由虚无转化为实存。因此,法权不是理性人格主体自身反思中的同一性,而是其他物反思中的差异性。借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只有在理性人格主体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中,才会产生法权。这就意味着,理性人格主体之间的互相承认才是法权得以诞生的基础。
海德格尔在其研讨班授课纲要中专辟一章《为什么存在法权》来研究法权的谱系学。
海德格尔首先考察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中关于主奴辩证法的论述。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主人是自为存在的意识,即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而奴隶则是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主人之所以成为主人,仅仅是因为在之前的殊死斗争中,后来成为奴隶的一方失败了,而不得不承认他是主人,而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也仅仅是因为胜利了的主人承认他是奴隶。但是主人与奴隶的地位并没有固定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奴隶通过劳动的培养或陶冶,培育了自我意识,并迫切地需要自我意识的承认,而主人又拒绝对此加以承认时,主人和奴隶之间围绕承认与被承认的斗争就开始了。[1]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第2版),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7页以下。
法国的黑格尔主义者科耶夫继承和发扬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他将整个世界历史看作主人和奴隶之间围绕着承认与被承认不断斗争的历史。在其《法权现象学纲要》(Esquisse d’une phénoménologie du droit)中,法权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就是作为正义理念之源泉的、关乎人类起源的、对于承认的欲望。[2]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5页以下。法权的诞生和发展史,遵循着辩证法的结构,就是从作为正题的主人正义转变为作为反题的奴隶正义,最后转变为作为合题的公民正义的过程。在那个阶段,人类社会达到了世界大同。按照科耶夫的设想,那会是一个普遍的、均质的、无差别的社会。[3]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46节。在那里,人类的历史终结了。
海德格尔与科耶夫一样,将法权理解为人类围绕承认与被承认的斗争的结果,他所提出的法权的存在论起源是:人类的历史性此在—斗争(πÓλεμος)—为了自立性(Selbstständigkeit),为了自由,为了存在而斗争。[1]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35.总而言之,就是为了承认而斗争。[2]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73.这样,海德格尔就比科耶夫更早地认识到了只有承认才是法权的真正发源地。科耶夫的基于人类相互承认的欲望的法权理论几乎成了海德格尔的法权理论的注脚。[3]Voir Florence de Lussy,Hommage à Alexandre Kojève:Actes de la《Journée A.Kojève》du 28 janvier 2003,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2007,p.46 ff.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法权之诞生的历史性进路在于:自由—自由存在的方式—某种意志的各种意愿方式—人如是自己意愿着自己—在此方式中—返回—自身存在—承认的存在—朝向存在的承认的本质(即法权)。[4]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49.因此,法权的本质就是自由的此在返回其自身的存在,更确切地说,就是作为此在的人类围绕承认而开展的斗争。法权所朝向的事情本身(即本质)就是对存在的承认。
究竟什么是“对存在的承认”呢?海德格尔的法哲学对此秘而不宣,含糊其辞。这个秘密只有在研究了他的国家哲学后才能解开。
四、国家
黑格尔宣称:“自由的理念只有作为国家才是真实的。”[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65页。海德格尔据此认为,法权作为自由意志的最高实现,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致完满的状态。哪里有国家,哪里才会有法权和法律。[6]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36.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呢?海德格尔对国家之形而上学式定义从对以下几种国家观的严厉批判开始:
1.有机体式的国家观(Organismus)
有机体式的国家观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国家在宪法中才达致自身的本质。[7]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64.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此理论的始作俑者,但是很清楚,海德格尔在这里指的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凯尔森的法和国家理论。凯尔森的整个纯粹法体系以基础规范(Grundnorm),即宪法作为根本出发点,再由宪法这一基础规范演绎出下位规范,从而形成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封闭式的法律秩序。凯尔森对此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等级体系的结构大体如下:由于预定了基础规范,宪法是国内法中的最高一级。”[1][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27—128页。国家在这里被等同于金字塔式的法律体系结构,国家本身也在这种结构中被消融了。
2.自由主义的国家观(Liberalismus)
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将国家视为保障个人自由的社会架构。通过权力分立达致权力平衡。这充分表现了对国家的不信任和警惕。因此,国家的整体性陷入了空洞之中,国家仅仅被视为原子式的市民的集合体。[2]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72.黑格尔就斥责这种国家观“假定着不存在任何国家制度,而只存在着集合一起的原子式的群氓。群氓怎能通过自身或别人,通过善、思想或权力而达到一种国家制度,那只得听其自便了”。[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90页。此等国家观的根本性缺陷就在于:它完全摒弃了国家自在自为的本质,对于超个人的政治正当性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海德格尔认为,以上的国家观都把国家看作人造之物(Kunstwerk),都犯了将现象当作实存的错误。国家不是被决定者,而是决定者。[4]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61.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8页。,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9页。,“在谈到国家的理念时,不应注意特殊国家或特殊制度,而应该考察理念,这种现实的神本身”[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9页。。
那么,海德格尔眼中的“现实的神本身”是什么呢?那就是存在。海德格尔对国家的形而上学式定义就是:国家是作为此在的人民的存在。[1]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15.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的考察,提出了以下的意向性结构:
操劳(Sorge)—此在(Dasein)—国家(Staat)—存在(Sein)。
海德格尔自己注明,这就是国家、人民和操劳之间的关系。[2]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61.
何谓操劳?一言以蔽之,这是作为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的此在——人民,对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国家的承认。因此,之前提出的“对存在的承认”之谜在这里才被解开了,就是对国家的承认!
法权的基础在于承认,而承认乃是对国家的承认,这就意味着,法权只有在国家中才能真正获得实现,法权的精神——自由,也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黑格尔声称:“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4页。通过对国家的定义,海德格尔用现象学存在论也得出了同黑格尔一致的结论。国家(存在)是人民(此在,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国家是有限性中的无限性,是特殊性中的普遍性,是个体性中的统一性。个人任何权利主张,都必须在国家中才能实现。个人从一出生,就“被抛”(Geworfen)到国家之中。在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中,人不是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而是在国家中存在(In-dem-Staat-Sein)。这就意味着,与之前的通说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法和国家才是人作为此在的“本真”的存在方式。
海德格尔的国家学说隐含着令人不安的结论。如果人民都是此在,那么就意味着,人民只属于其所承认的政治共同体,只有在此政治共同体中,人民之间才可能具有主体间性。政治共同体之间,不同政治共同体所属的人民之间的商谈将成为不可能,反倒是区分敌我才是可能的。人类之间不存在什么共通性的普遍价值,只存在共同体之间的殊死斗争。这就说明了,人类的生存,从终极上来说是无根据的,充满了令人恐惧的偶然性。[4]参见[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周宪、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4—65页。人类作为被抛入某个政治共同体的此在,将不得不如其所是和所能是的那样存在——承认自己所处的政治共同体的同质性,进行反对作为异质性的其他政治共同体的斗争。当人类认识到这是其根本的生活意义时,此在之畏(Angst)将常伴人类左右。[1]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为什么海德格尔对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所言甚少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似乎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而是反对那种普遍化的、普世性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生存的无根据性和偶然性都证明了这些全是虚妄。世界历史似乎就是一个大竞技场,各个国家乃至人类本身都在上面明争暗斗、争权夺利。这一切似乎正如赫拉克利特那反映人类总是处于相互仇恨和自相残杀之中的箴言所说的那样:
战争既是万物之父,又是万物之王,它让一些人变成神,让一些人变成人;让一些人变成奴隶,让一些人变成自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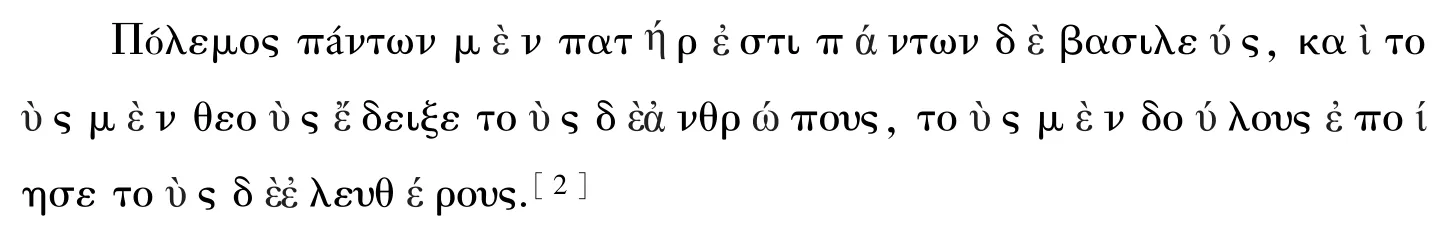
[2]Heraclitus,fragment 53.
五、政治
在考察了黑格尔的法和国家学说之后,海德格尔试图进一步通达政治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政治与城邦(π8130CC32λις)有关,城邦反过来又是具有政治性的。政治就是作为存在和本质的城邦的基础,国家(城邦)则是政治的国家本质起源。[3]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72—173.政治存在哪里?就在国家的本质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国家的存在方式之中。[4]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73.什么是国家的存在方式?根据海德格尔,就是原初的统一—无限的精神(运动、具体的自由)—返回—达致—包含自身的自我主张。[1]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73.
海德格尔借助荷马的《奥德赛》考察了城邦的政治本质:城邦是完全自由的(vollfrei),城邦的成员(πολης)具有思想的统一性(μÓνοια),那就是爱(φλια)。[2]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72.虽然海德格尔没有明言,但是我们很容易通过反向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非城邦的成员,就是恨(хθρα)。 这就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同质性(Homogenität)的基础之上。既然如此,那么,划分敌友就是政治的基本特性,海德格尔的政治哲学由此转向政治决断论(political decisionism)。
通说认为,在政治上划分敌友的学说源自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其出版于1921年的专著《论专政:从现代主权思想的肇兴至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中首次提出了敌我划分的主张。其出版于1927年的《政治的概念》则提出了比较系统完善的划分敌友的学说。
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提出了这样一个挑衅性的问题:在道德领域可以划分善与恶,在审美领域可以划分美与丑,在经济领域可以划分利与害,那在政治领域为什么不能划分敌与友呢?[3]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施米特借此进一步指出,政治具有以某种自身特定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划分敌与友。所谓敌人,不是指抽象的哲学或道德、宗教观念,而是历史中具体的政治阵营。敌人不是个人的私敌(inimicus),而是国家的公敌(hostis)。敌与友的概念必须从具体的生存意义出发来加以理解。它最终依赖于主权者的政治决断。施米特的政治哲学,由此最终走向了政治决断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施米特的政治学说与海德格尔的国家理论有相契合之处。在施米特的眼中,国家是由某个具有同质性的共同体所构成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状态的本质在于它具有政治性——从政治上划分敌友。这恰恰跟前述的海德格尔的国家理论如出一辙。所以海德格尔在其研讨班上对施米特的划分敌友的政治理论大加赞赏,但同样批评施米特仍是从自由主义的视域来思考政治与敌友关系,[4]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74.因为:(1)施米特把政治也看作一个领域;(2)施米特的观点是从个人及其态度出发的。施米特没有看到,斗争也有其对于国家的先验性,而这正是其对于国家的根本意义。国家应当是人民的存在、人民的所是,但不能说国家本身同时又“是”什么。[1]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74.
海德格尔进一步发挥说,政治的存在就是人民的操劳,以及由此显现出的可能性。如果将操劳解释为围绕承认与被承认的斗争,那么敌友关系仅是政治的本质结果,而非政治本身。施米特的政治学说颠倒了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没有把握到政治的实质。
施米特的关于敌友划分的政治哲学免不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敌友划分意味着战争状态,谁来解释这种战争状态?(Quis interpretabitur?)又有谁来裁判这种战争状态的存在?(Quis iudicabit?)施米特最喜欢引用霍布斯《利维坦》中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是权威,而不是真理创造法律。(Auctoritas,non veritas,legem facit!)[2]See Carl Schmitt:The Leviathan in the State Theory of Thomas Hobbes:Meaning and Failure of a Political Symbol,Translated by George Schwab and Ema Hilfstei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eorge Schwab,with a new foreword by Tracy B.Stron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44.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回答仅是一种无根基的政治决断论而已。海德格尔试图从其基础存在论入手来为决断敌友提供一个稳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存在与时间》中,他就曾论述到:
“决心依其存在论本质而言就是当下实际的此在的决心。这一存在者的本质即是其生存。决心只有作为领会着筹划自身的决定来生存。但此在在下决心之际是向什么方向作决定?此在应为何而作决定,只有决断本身能提供回答……决断恰恰才是对当下实际的可能性的所有开展的筹划与确定。此在的一切实际被抛的能在都具有不确定的性质,而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属于决心。决心只有作为决断才吃得准它自己。但决心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生存上的每次只有在决断中才得到确定的不确定性,却正具有其生存论上的确定性。”[3][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版),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40—341页。
海德格尔用政治存在论为决断论奠基。那究竟由谁来做出政治上的决断呢?海德格尔隐晦地指出,政治上的元首(Führer)才是引领作为此在的人民进入作为整体性的国家的领路人。元首知国家之所想,济人民之所需。元首不是个体性的权力(Macht),而是权力的聚集。元首之所以成为元首,不是基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体性,而是基于形而上学的先验基础,是作为此在的人民在存在中的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决断,将最终由元首作出。[1]Vgl.Heidegger,GA86,Klostermann,Auflage 2011,S.169.联系这个研讨班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段有关元首的论述很容易引起他人不愉快的联想。但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在海德格尔所处的1933年,像元首(Führer)、人民(Volk)、决断(entschlossen)这些词语并没有后来所特指的那种贬义,它们在那个时代的涵义就跟今天的英语中的对应词一样清白无辜。[2]See Michael Inwood,Heidegger: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130.所以,正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君主制的演绎不是为了论证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而只是为了论证一个个人作为国家首脑(该首脑本身并没有专制暴君的权力)的必然性而已一样,[3]参见[英]W.T.斯退士《黑格尔哲学》,鲍训吾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2页。海德格尔在这里对元首制的演绎也并不是为了鼓吹希特勒和纳粹的僭政的合理性,而只是演绎出,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有必要设立一个主权者(元首),需要他来对有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性政治问题作出最后的仲裁和决断而已。这很明显是受到了施米特的政治哲学和宪法学说的影响。[4]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六、结语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法哲学有两条发展进路:一条是受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的影响,借助“事物的本质”、“物本逻辑结构”等主张实然和应然统一的理论来为法律打下先验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实体存在论法哲学;另一条则是坚持康德的实然和应然截然区分的二元论命题,摒弃一切法的形而上学式先验基础,单从法律规范的形式或内容来演绎具体的法律命令的规范论法哲学。[1]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第124页。海德格尔可谓是第一种进路的集大成者。但是,海德格尔用现象学来阐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不停地为法权、国家、政治理论打下先验的形而上学基础,论证法和国家是人类作为此在的“本真”的生存方式,究竟是出于何等目的?这只有结合德国当时纳粹当政的时代背景才能得到解释。
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德国掌权之后,黑格尔哲学曾经一度有“复兴”的倾向,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黑格尔法哲学流派。[2]参见[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8页。在法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新黑格尔主义曾经喧嚣一时。海德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研讨班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笼的。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在早期赞赏过纳粹主义,认为纳粹运动赋予人类新的存在含义,并为克服欧洲的虚无主义,重新建构一种新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3]See Leo Strauss&Joseph Cropsey,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 896.他还认为那些有智慧的人理应负担起教导纳粹当政者的义务。海德格尔在其于1933年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讲《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就宣称过:“教师和学生的战斗共同体才能把德国大学改造为精神立法的场所,并在这个场所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核心,为民族国家提供最高的服务。”[4][德]海德格尔:《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吴增定、林国荣译,登载于中国现象学网,网址: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168,2013年5月29日。联系其就职演讲来看,海德格尔似乎想象色诺芬的《论僭政》[5]参见[美]古热维奇、罗兹编《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施特劳斯、科耶夫著,何地译,观溟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页以下。中的哲人西蒙尼德那样扮演僭主的教育者的角色。其黑格尔研讨班似乎在证明,法权、国家、政治乃至元首本身均有其先验的政治存在论结构,均服从先验的存在秩序。僭政本身从理性上也不得不服从此存在秩序。因此,海德格尔似乎在此表现出了一种规训的欲望,他似乎期望当时的纳粹党乃至德国能遵照他所探询出的政治秩序进路,遵循他的“精神立法”。这从他在授课纲要中反复鼓吹“有人说黑格尔在1933年死亡了,不,恰恰相反,他只有在那时才真正开始生存”中可见一斑。
然而,以上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纳粹政权中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罗森堡就曾严厉指出,纳粹官方只承认瓦格纳、尼采、拉加得和张伯伦为自己的精神先驱,并彻底地拒绝了黑格尔。[1]参见[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9页以下。纳粹的官方哲学认真地执行了否定黑格尔的方针。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海德格尔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研讨班结束后就匆匆地抛弃了黑格尔转向尼采了。海德格尔的教导,所谓的“精神立法”都彻底地归于失败。这一失败的结果,不仅导致其改造大学进而改造纳粹运动的理想破灭,也导致了他最终没有完成《存在与时间》。[2]See Leo Strauss&Joseph Cropsey,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 896.
不难探究出海德格尔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纳粹这种极端非理性的政治现象以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正是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的必然结果。[3]参见[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8页以下。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述,海德格尔是现代性的三次思想浪潮中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出现的时刻是如此之晚,以至于他根本无力去扭转现代性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和伦理真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本身,从总体上来说,非但不是对现代性和虚无主义的克服,反而是其最完美的体现:一切历史均只是某个“特别时刻”的“绽出”(Ekstasis)或“缘构发生”(Ereignis),一切所谓的历史、世界和人都仅仅是断裂的、破碎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预料、无法确定因果性、最终依赖于“天命”的。[4]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引言第14页以下。在海德格尔的此种时间和历史观念下,一切基于正义的探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煞费心机的阐释以及借此所企图实现的“精神立法”,从他自己的哲学观点来看也是矛盾百出的。因此,尽管海德格尔嘲笑黑格尔遗忘了存在,但是黑格尔很可能会嘲笑海德格尔在阐释《法哲学原理》时居然遗忘了他在序言中就说过的那段著名的论述:
“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也必须略为谈一谈。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呈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序言第14页。
(初审:刘诚)
法和政治的存在论
——海德格尔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现象学阐释
周维明[1]
海德格尔向来很少提及法哲学和政治哲学,而从海德格尔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研讨班的授课纲要入手,则可以系统地讨论其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存在论的阐释方法的指引下,考察了法权、国家、政治等主题并阐明了其本质。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政治哲学以政治存在论为奠基,最终表现为政治决断论。
现象学存在论;法哲学;政治哲学
[1]作者周维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E-mail:8zwm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