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生灵(四题)
2013-08-16杨泽文
■杨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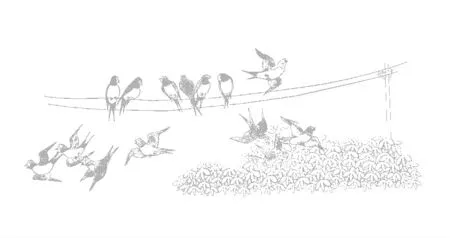
喜鹊
乌鸦、野鸽和喜鹊是最常见的乡下鸟。它们虽然生活环境相近,形体相当,但羽色和鸣叫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乌鸦是通体墨黑,野鸽则为一身浅灰。而喜鹊呢,黑白灰三色羽毛依次和谐于一体的形象显得庄重而不轻浮,活泼而不呆板,加上它的悠然飞翔之姿和清脆的鸣叫,最终使其在乡下赢得了“吉祥鸟”的美誉。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老家有先辈栽下那么多核桃树,除了保证食用核桃油之外,其实还有" 引鹊鸣枝"的良好愿望。事实是,在我曾经生活过十多年的那座村庄,谁家门前有棵高大的核桃树,就少不了要被人羡慕乃至刮目相看。就说我家吧,由于门前有一棵常引喜鹊前来栖息与做巢的老核桃树,爱喝酒的父亲就常带着醉意对我说:“好好看看吧,祖上栽下的这棵百年老核桃树长得多高啊,连喜鹊都常恋着不走,今后会有好日子过的……”有一次我禁不住问父亲:喜鹊真的能给人带来喜事吗?父亲听后不假思索地回答:怎么不能?你仔细听听喜鹊是怎么叫的?我回答:不是“唧唧喳喳”么?父亲带着有些责备的口吻说:你没听仔细啊,不是“唧唧喳喳”,而是“喜事常常”。从此之后,只要我认真聆听喜鹊的叫声,就觉得是“喜事常常”而非“唧唧喳喳”了。
于是我想,乡亲们之所以喜欢听喜鹊的叫声,很有可能是面对眼前不如意的生活时,总希望内心能涌起一些吉祥的好兆头,从而对未来的日子充满向往和期待。而乌鸦和野鸽为何不大受人喜欢,可以说十之八九与它们的鸣叫声有关。乌鸦那“乌啊乌啊”的叫声,仿佛是“哭啊哭啊”之音;野鸽那“咕呼咕呼”的鸣啭,则好像是“苦乎苦乎”之意。尽管这样的“闻声生义”显得有些荒唐,但在困苦年代里却是情有可原啊!如果乡亲们都能生活得丰衣足食的话,也许会逐渐改变对乌鸦与野鸽业已形成的偏见。好在乡亲们虽然并不大喜欢乌鸦与野鸽,但不至于发展到不让它们生存的地步,故而在我所生长的乡村,乌鸦与野鸽一年四季照样自由地飞翔和随意地鸣叫。不过,有一年春天,一对乌鸦在我家门前的大核桃树上准备做巢时,父亲还是忍不住愤怒了。他以毫无商量的语气命令我:赶快想办法把树上的乌鸦巢给撤了!我仰头一望高入蓝天的乌鸦巢,立刻就没了上树的勇气。于是转而建议父亲不必上树去撤,用弹弓射石将乌鸦赶走不就行了。后来的几天里,我先后向空中的乌鸦巢弹射了不计其数的小石子,终于把乌鸦巢打得个稀巴烂,迫使一对乌鸦在高空盘旋忧伤了数日后无奈地离去。随后一对喜鹊在毁坏了的乌鸦巢上构筑了新巢,父亲见后脸上才流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喜鹊在乡间备受人们爱戴与尊崇,使其获得了不受惊扰的自然繁衍生息,它们也因此永远守护着我所熟悉的一座蓝色村庄。记得《禽经》上说喜鹊是“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而在乡间老人常给孩子们讲的神话故事中,喜鹊则变成了让人为之动容的神鸟,它们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都纷纷飞离人间到广袤的银河之上搭成一座彩虹般的桥梁,让牛郎和织女顺利完成一年一次的“鹊桥相会”。可以说,正是乡间喜鹊的普通与神奇,让孩子们适时张开了想象的翅膀,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有了热爱万物与尊重生灵的意识。
转眼之间,我已离开乡村来到都市闯荡了多年,成了独自漂泊异乡的游子,自然也少不了在睡梦中经常被乡间喜鹊的鸣叫声所惊醒。而在乡村电话的那头,父亲更是少不了一次次地摧我:“再忙也该回来看看呀!如今家门前的老核桃树上除了鹊巢之外,还有了乌鸦巢和野鸽巢。不论是喜鹊还是乌鸦与野鸽,它们都在核桃树上和谐相处、随意鸣叫和相安无事……”
在异乡,我一次次沉重地放下来自乡村的电话之后,才开始日渐明白:哪怕自己奔跑得再远,终究还是少不了要踏上归乡之路的。毕竟唯有鹊鸣乡间的诗意图景,才可望最终彻底澄明我混沌的身心。
斑鸠
在我熟悉的乡下鸟中,除了麻雀、燕子、喜鹊和乌鸦之外,就要算斑鸠了。这种身体呈灰褐色、颈后有白色或黄褐色斑点、嘴短、脚为淡红色的鸟,常成群结队地在村庄上空飞翔。一旦在飞翔之中选定某一片田野之后就迅速落入其中,然后尽可能地放开嗉囊,把谷粒麦粒豆丸什么的通统放进去,然后再飞到村边的树林里慢慢地消化。
与麻雀和喜鹊一样,斑鸠终年生活于同一个地域,没有迁徙的习性。因而在乡村,几乎可以一年四季见得到它们的身影,算得上是典型的留鸟了。不过斑鸠并不像麻雀、喜鹊和乌鸦一样四时都可以毫无节制地鸣叫,它有自己的鸣叫期,除此之外,你只能永远看见一群或是数只沉默飞翔和静栖的斑鸠。斑鸠的鸣叫期一般在春末初夏,这个时节也是斑鸠交配产卵育雏的季节。斑鸠的声音并不高昂,属于中低音部,音节更是单调,但节奏感却很鲜明,如果用汉字拟音表达就是:“咕咕——咕——,咕咕——咕——”。从斑鸠的叫声类型来看,在鸟类学家那儿它应该被视为“鸣啭”而非“叙鸣”。“叙鸣”是一种言说,是鸟儿之间日常信息的沟通;而“鸣啭”是一种歌唱,主要为雄鸟对爱情的赞美。可见,斑鸠还是一种灵犀之鸟,在其爱情生活中它们敢于打破沉默的生活。斑鸠的巢一向在树上做得很隐蔽,一般很难让人发现。巢也做得并不复杂,用料也仅限于枯枝与杂草。枯枝做底起支撑作用,杂草铺垫起柔软之效。斑鸠的蛋上有杂色的斑点,因而在巢中并不显眼,让人感觉到从一枚小小的蛋上开始,斑鸠就不喜欢张扬。我在乡下生活了近二十年,但总共也只见过两个斑鸠巢。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巢中有蛋,第二次见到的那个巢中有幼雏。两次见巢我都爬了树,惊吓得一对斑鸠夫妻充满敌意地反复绕树急飞,虽然没有发出仇恨的声音,但那无声的情景其实更可怕,毕竟我担心自己的双眼一不小心就会被斑鸠啄坏。因为在乡间,大人们常对那些上树掏鸟蛋和捣鸟巢的顽皮孩子发出的警告就是:“不要这么作孽哟,小心眼睛被鸟啄瞎。”自然,我从不敢去干掏鸟蛋和捣鸟巢之类的坏事,但出于好奇,我还是常常少不了对自己意外发现的鸟巢进行一番仔细观察或探究。
尽管斑鸠的肉味很鲜美,但在我生长的乡间,却很少发生公然射击斑鸠的事。当然,斑鸠成群地到农田偷食粮食而遭到打击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但斑鸠凭着固有的机警与灵巧,总有机会化险为夷,因而要想成群地击伤它们是做不到的。毕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人都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出猎枪对着斑鸠群开火。如此一来,乡间的斑鸠群也就有机会和有胆量常常在乡村的上空飞翔复飞翔,构成了乡村最具有诗意的祥和美景。记得在县城上高三那年,有个喜欢写诗的同学随我到乡村的家中度周末,当他远远地看见一群斑鸠在村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时,便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赞叹:“多美呀,宁静的蓝色村庄,幸福的乡村鸽群……”我立即纠正说,那不是鸽群,那是一群斑鸠。这个同学听后愈加赞叹不已,说真是绝了,斑鸠变鸽群,村庄更神奇。两年之后,我的这位同学在省城的一所大学里成了有名的校园诗人。他的许多乡土诗中经常出现了“鸠鸽”这个新鲜名词。我明白其所指的就是斑鸠,只不过诗人觉得用“鸠鸽”更有诗意罢了。
在乡间的一些年月,我也曾怀疑过城镇里成群放养的家鸽就是由斑鸠驯养而成的。因此有一次我在田野里看见一只翅膀受伤而不能再飞翔的斑鸠时,便信心十足地将其带回家治伤和驯养。结果呢?斑鸠的伤倒是治好了,但其性情并没有丝毫变得温顺起来。即便你喂得再好,它还是依然在笼子里站立不安而扑腾不止,自然不时又添新伤,继而接受新的治疗。最后我断定,斑鸠性情刚烈,注定无法驯养,只能选择放飞。
其实,就单个斑鸠来说,缺少观赏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就一群斑鸠而言,一旦与一座村庄构成不远不近或者说不依不离的景象时,无论其观赏性还是诗意感也就充分地彰显出来了,以致再单调的村庄也因此而变得日渐生动起来。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依然在异乡常常为自己身后有一座被斑鸠守望的蓝色村庄而欣喜。
野鸡
在我的印象中,野鸡是集群性强而又胆怯机警的野禽。它们时常三五成群地游走于山野草木之中,喜食昆虫、草籽和嫩叶。虽然奔跑速度快,但高飞能力差,只能短距离低飞。一旦受到侵扰时,则群起而飞,并发出一连串尖锐的“咯咯”声,寂静的山野便立即被打破。
野鸡警觉性高,而且很机敏,往往是人还未发现其身影,它却已不是躲藏隐匿就是震翅而飞,因此突然受到惊吓的往往是人而非野鸡。记得年少时在老家的山野中放牧,就时常被眼前突然腾飞而起的野鸡群所惊吓。由于野鸡的羽毛多以褐色为主,因此在草木间让人难以提早发现。即便是羽毛较为鲜艳的雄野鸡,也有在草木间善于隐藏自身的能力。
尽管野鸡很聪明,但却缺少像小鸟一样在草木间做精美之巢的本事,这似乎表明野鸡的“筑巢”能力并不强。不过让人称道的是,野鸡对于下蛋孵育之巢的环境选择却又显示出其特别精明之处。在山野之中,每到春夏之际,就不难发现各种各样的鸟巢,但却不容易发现一个野鸡巢。原因在于野鸡能很高明地将“筑巢”之地选择在地势凸起而又草木茂盛之处,周遭还要有带刺的浓密植物,这样既可防水防潮又能防范动物的侵扰。
在山乡生活过的十余年时间里,我只发现过一个野鸡巢。记得有一天我奋力追逐一只小野兔,结果被小野兔最终带进了一个茂密的荆棘丛中,然后小野兔却不见了踪影,而眼前却呈现出几枚野鸡蛋。白色的野鸡蛋静卧在枯枝干草随意编织的简易巢中,孵蛋的雌野鸡可能听到动静而提早躲开了。抚摸着还有些温热的七八枚野鸡蛋,我一时不知如何处理。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只带走一枚野鸡蛋,而且一回到家就将其放进正在孵蛋的母鸡腹下。我的想法是看能否孵出个小野鸡来,结果还真让人欣喜不已:最先出壳的竟然是小野鸡。可后来在一群可爱的小鸡仔中,小野鸡显得很不合群,细米粒也吃得越来越少,直至有一天,在母鸡的带领下,它随一群小鸡仔外出觅食之后就不见其回来。也许是小野鸡的天性促使它选择离开小鸡群,然后躲进屋后的那片菜园,继而穿过绿色的刺篱笆,再经过一片绿草地,最后隐入我时常放牧的那片山野。出于好奇,我立即动身前往山野中探查那个好久未见了的野鸡巢,结果只是见到一个空巢,于是只好失望而归。可哪里想到,在返途中竟然碰上了一只雌野鸡正带着一群小野鸡在林中觅食。大概是小野鸡还没学会群起而飞的本领,于是只能在草丛中尖叫着到处乱窜。而雌野鸡则在我前面不远处时而佯装跛行时而拍打着翅膀,我明白它是在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让它的一群小野鸡能够赶快逃走或躲藏。而我却无意于伤害它们,我只是黯然地想:我丢失的那只小野鸡,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它的“妈妈”和“兄弟姊妹”,会不会成为现在这群四散而逃的小野鸡中的某一只……
我在山乡生活的年代,可以说每一座山峰和每一片林地,都是野鸡最惬意的乐园和最美好的家园。它们出没于林丰草茂的山野,时不时地发出“柯——哆——啰”或“咯——克——咯”的悦耳叫声。而受到惊吓时,则发出“嘎咋——嘎咋——嘎咋”的急促高音,并随之从一片林地或草滩,飞到另一片密林或草海。乡亲们早已见怪了野鸡们的生存场景和生活方式,故而不会惊奇也不会好奇,更不会四处猎杀野鸡。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些年月里,山乡人和野鸡就这样在一方水土上和谐共处,相安无事。后来我到外面读书和工作之后,曾一度听到因为城里人爱吃野禽美味,因而有人到山乡高价收购野鸡,于是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在山野中繁衍生息的野鸡很快就被人猎捕殆尽了,山野也因此变成了死寂的山野。至此,乡亲们才觉得好像失却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记得亨利·梭罗曾在其《瓦尔登湖》一书中这样写道:“要是没有兔子和鹧鸪,一个田野还成什么田野呢?因为它们是最简单的土生土长的动物,与大自然同色彩、同性质,和树叶、和土地是最亲密的联盟。”由此,我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没有野鸡出没与守护的山野,还能叫真正的山野吗?
世间万物,其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永远寂静的山野终究是会让人心里发慌的,就像现代环保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森笔下所描绘的“寂静的春天”其实是一个可怕的春天一样。为了让死寂的山野恢复应有的生机,让我们从宽容一只小小的野鸡开始吧。但愿我所熟悉的乡亲们也能够早早地醒悟过来。
马蜂
在我的乡下老家,马蜂是最常见的一种野蜂。马蜂的外体大多呈棕黄色,并带有黑色斑纹或斑点,静止时透明的膜质翅覆盖于身体背面,飞舞时双翅能煽动出嗡嗡的声响。而人们之所以惧怕马蜂,是因为马蜂的尾部有一根蜇人的螫针,其注射的毒液能致人产生过敏性反应和过敏性休克,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马蜂是杂食性昆虫,无论是树汁花蜜,还是果蝇蜻蜓,都能成为其美食。马蜂能在树上建造出让人惊叹的球形巢,即人们常说的马蜂窝。悬挂在树枝上的土黄色马蜂巢,日晒不黑,风吹不落,雨淋不透,让人不得不佩服马蜂的高超建筑本领。
马蜂是因为在树上建巢并设立了一定范围的“军事禁区”,才让人感觉到了某种真正的威胁所在。本来在村边的某一棵树上,马蜂选择建巢早有些时日了,只是巢小还未让人发现,因此人与马蜂相安无事。然而这样的良好局面,每每随着马蜂巢的变大直至赫然暴露于众人眼前而结束。接下来的问题是,越来越大的马蜂巢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碍眼,数量越来越多的马蜂也视人为潜在威胁,进而不时向行人或目击者急速绕飞发出轰鸣警告。终于有一天,有人被马蜂蜇伤了,树上的马蜂巢随即成为众矢之敌。人们开始或以石击巢,或以箭射巢,以期将马蜂巢毁掉,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往往是,蜂巢即便有了破损也依旧牢牢地悬挂在树上,而袭巢者则早已被成群结队的马蜂追(蜇)得鬼哭狼嚎。于是在月黑风静的夜晚,曾被马蜂追(蜇)得狼狈不堪而开始复仇了。他们悄然地潜伏到树下,将松明子(松油木片)紧扎在一根长竹竿顶端,勇敢的上树者很快将长竹竿顶端点燃的松明火举送到马蜂巢上,木浆质地的蜂巢便立即燃烧起来,巢中的马蜂不是烧死就是被熏死,待巢皮燃尽之后,就可以上去摘下宝塔似的蜂房。要是烧到大型蜂巢,其圆盘蜂房层数可多达七八层,各层之间留有空隙和连接的“柱子”,每片蜂房上,成百上千个六棱形的“育婴室”里,布满了成形或未成形的白色蜂蛹。取出蜂蛹用文火油煎至金黄,即成外酥里嫩的难得乡村美食。当然,烧杀马蜂者也并非每次都能轻易得手,原因在于机警的马蜂嗅到树下的人烟气味后便纷纷沿着树干往下爬,碰上人就或咬或蜇,让夜袭者只好逃之夭夭。
在我所熟悉的乡村,顽皮捣蛋的孩子大都被马蜂蜇伤过。原因不外乎他们都喜欢去捅马蜂巢。对乡村男孩子来说,对火烧马蜂巢并不一定感兴趣,但对袭击马蜂巢的危险事却可以做到乐此不疲。常常是,用手或弹弓将石子投射到马蜂巢上,那些作为“哨兵”的愤怒马蜂就沿着石子飞来的轨迹疾速扑来,一群乡村孩子便四散而逃。那种慌不择路和风呼耳畔的奔突体验,真是太刺激了。而跑得慢的孩子一旦被马蜂蜇伤之后,第二天自然是手脸肿胀,模样大变,弄得家长一顿责骂,小伙伴们则是一阵窃笑。记得有一次去袭击村边核桃树上的一个马蜂巢,结果遭到一群马蜂的凶猛追击,最终导致一个小伙伴差一点被马蜂蜇死。这个叫“余生”的小男孩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人却从此变成了傻子,在学校也读不了书,要是见到核桃树,就流着口水指着说“马……马……马蜂……”,并伴随着全身抖动不止。
在我的乡下老家,虽然人们为取食蜂蛹而时常采取野蛮的方式去火烧马蜂巢,但一般都会选择在秋末时节来进行。因为在乡下一些老人的尊生意识中,春夏时节火烧马蜂是不可原谅的,是违反自然伦理的,只有秋末火烧马蜂才会得到默许。原因在于即便秋末不烧马蜂巢,马蜂也会很快在寒冬里自然死亡。因此,每到秋末时节,村里就会出现一些“找蜂人”。这些找蜂人,眼力好,听觉灵敏,腿脚也麻利。他们寻找马蜂巢主要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到林中透过树枝缝隙直接寻找蜂巢;二是在树林中倾听马蜂的声音来寻找蜂巢;三是用小蚂蚱或小蜻蜓作诱饵逮住在野外觅食的马蜂,然后用一根头发丝,一端拴住马蜂的细腰,另一端系上轻巧的白色小羽毛,再让马蜂将小蚂蚱或小蜻蜓咬住后放飞,以此观察马蜂回巢的方向和路线,通过几个人的分段跟踪,直至最后寻找到马蜂巢。
印象中,乡下老家的一些大树上总是悬挂着几个硕大的球形马蜂巢。人们之所以容忍它们,是担心一旦火烧不成功时,惹急了的马蜂会袭击村里的人畜,造成不必要的大面积伤亡;故而村里村外的大树上,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一些新旧的马蜂巢,仿佛是乡村最有意味的高悬徽章。
在人面前,再凶恶的马蜂实际上也是绝对的弱者。事实证明,只要人能给予马蜂一点不被侵扰的空间,人与马蜂就有机会化敌为友,和谐相处。而对于马蜂的死亡处置,其实人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只有大自然才有最恰当和最正当的处置方式。而人一旦超越了自身的权限,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也就会接踵而来。这是一个曾经敌视马蜂的乡村少年,多年之后写下这篇《马蜂记》时最想要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