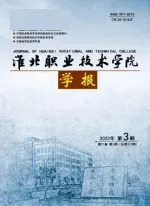试析19世纪西方绘画艺术的意象——以莫奈作品为例
2013-08-15张文纨
张文纨
(淮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意象”一词,在汉语里可以解读为“意境”,即寓“意”之“象”。西方的“意象”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表象,它是修辞化的形象性语言,属于哲学文论的范畴。由此可见,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意象是大大不同的,意象在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上,追求的是主客观交融的情境空间;而西方传统绘画上则体现的是物象的真实性,表现相对静止性的特点。自然美与艺术美一样,都是意象世界,都是人的创造,都真实地显现人的生活世界,就这一点说,自然美和艺术美并没有谁高谁低之分。[1]7
西方艺术美的意象在不同时代,其具体所指是有区别的:原始美术时期主要泛指洞穴壁画、岩画、浮雕、建筑;文艺复兴之前是指与西方宗教有关的圣像、影像、壁画等;文艺复兴的时期是指以人为本,崇尚人性和自然,主要是指人文意象;17~18世纪被赋予感觉,强调综合性,与浪漫、象征、隐喻等手法的综合运用;19世纪时是指绘画语言上的形象,但是艺术手法开始独立,强调幻想、印象、浪漫等;到了20世纪,美学家们开始对意象进行分类性的研究,比如象征意象、地理意象、人文意象、自然意象,等等。在不同文本、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中,意象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在19世纪表现的意象,诗歌意象往往通过感性的思维物象作隐喻或者暗喻,绘画意象是一种被使用的艺术语言。因此,作为这种艺术语言,必须要通过一种表象来传达视觉的意象,来传达富有感情的意象以及让观赏者与艺术家思维互换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共鸣。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是通过构成故事的各个谱系打乱而交织成几条中心线,组成统一性,最终形成故事的意象。
无论是19世纪的诗歌意象,还是绘画意象,最终都引向文字的意象,其影响是一致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诗歌里有这样一首小诗,“人群中的这些面孔幽灵般,一根阴湿黑枝上的片片花瓣。”这简单的两句话,“面孔”“幽灵”“黑枝”“花瓣”这些物象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系列的景观。这些景象产生了“阴”“黑”“茫”的字境,字境结合语境,通过“幽灵般”“黑枝”“阴湿”等表象的修饰作为隐喻或者暗喻,用来表现当时的环境是多么得恶劣,得到起承转合的朦胧效果。这让人不禁想起了莫奈的那幅《乌云密布下的紫丁花》,莫奈主要通过人与自然的环境关系来进行形象塑造。片片的紫丁花开得那么灿烂,人群面孔却是如同幽灵般。艺术家通过画面上形象语言,表达了隐藏面孔的真实意义,恐惧与怜悯往往就是艺术家们内心深刻的东西。莫奈喜欢用自然和人物作为形象刻画的对象,使之充满对自然生命的热爱,这是一种被视作理性的灌注生气的情感力量。
本文拟以印象派艺术大师莫奈的绘画作品为切入点,探讨19世纪西方的绘画意象,以进一步深化艺术作品的意象研究。
一、莫奈绘画意象图式的思想表现
莫奈是19世纪印象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在绘画领域里进行了一场大胆的变革。他反对官方学院派和传统的艺术理念,追求个性绘画特点,传达出一种浪漫诗意的意象,从而使其在绘画作品中的光之韵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时光的意象
莫奈认为,所有事物都能显现真正的光,它与特定事物相关;光处在变化之中,事物的每一个变动都可能引起光的变化;真正光的特征,更多地接近于笼罩物体的映衬意象;光又分为光线、时光、灵光等,运用光线的独到之处给莫奈的绘画增添了不少色彩。莫奈是一个艺术家,他极力表现他的绘画作品。无论是日出还是粮堆,都离不开光的作用,无论是白桦林还是鲁昂大教堂,不同的色彩来表现不同的自然,让人体会到时光的匆匆。在这虚无的飘渺之间,画家的心灵也玲珑般浮沉。在这里,画家表现的不单是物象,而是在这静穆的时间里。阅画家眼里的世界千年,依然如一日,在这理性的世界里,时光灼灼自有天意。
图像时代之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艺术需要建设,艺术需要创新。当代艺术创作,归根到底,是对社会变革的记录。随着城市步伐的加快,某些自然的景观正在被建构成城市的一部分,比如说广场、草地等。城市不断地改变它的布局,规模不断扩大,马路不断扩宽。因此,当人们希望从自然景观中寻找美感时,这常常令人失望。然而,莫奈喜欢对自然场景进行描绘,他对自然场景的描绘都是在现场作画,一气呵成。当更多人去追求艺术市场化时,莫奈提倡回归自然,通过自然中的静物进行对大自然的刻画,抓住瞬间时光的变化,必然有其中的韵味。当然,莫奈通过它们去寻找思想的乐趣,但却不会回到一种原始,而是一个真理的时代。
(二)诗意的意象
毫无疑问,在莫奈的绘画作品里都大胆地运用了光。莫奈说过:“如果年轻时不大胆,以后你将干什么?”这句话表现莫奈将勇敢去寻求自己独特的艺术创作。在莫奈的《日出·印象》中,莫奈试图对在大自然中突出日出的自然意象和一叶扁舟,还原这原始的生态,这是意生象。通过光和画面上的朦胧气氛,比如说烟雾、小舟的倒影,让人不禁联想到白居易的山水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触景生情,这是象生意。日出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现不同的景色,使画面极其富有诗意,这是色象。符号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提到艺术符号,是这样解释的:“艺术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暗喻,一种包含着公开的或隐藏的真实意义形象。”[2]134艺术唤起自然中各种色彩,也就是这种色彩与人文情感思维关联。通过日出特定的艺术符号来突出情感特质,表现人文情感的意义。如此,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情感共鸣。
(三)空气的意象
莫奈在描绘晴空下的雾气时,超越了当时的绘画模式。他扩展了欧洲绘画中的“疏散法”,结合了东方艺术的美学原则,这种巧妙的结合预示了一种新的变革绘画手法的开始。由于莫奈长期探索光和空气的表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光影下去表现物象,对统一的物象多次描绘,从自然中寻找艺术韵味。在1891年创作的《粮堆》中,从早上到傍晚,从夏天到冬天,莫奈不停地表现粮堆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用不同的光和空气表现出来的。莫奈曾经说过:“作品描写在我不能承认它自己……我隐约意识到的对象是从这张丢失的是什么……然而,很充分明白,在调色板中难以想象的电源,电源我从未怀疑。”[3]160有了电源就有了光线,而这个电源就是自然,就是光和空气。莫奈所表现阴沉天气的粮堆,与晴天的粮堆产生强烈的对比,在不同天气的光和空气质感是不同的,因而粮堆所表现的色彩也是不同的。莫奈是“色彩的发现者”,是用眼睛表现光的大师。通过大面积的色彩来实现光在空间里的表现,从而刻画形象的朦胧。当阳光照射了万物,反射万物通过视觉形成不同的颜色,产生不同的色调。任何的色彩理论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正如赫伯特·里德所说技法理论,“我们并不总认为15世纪发展起来的透视法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程式;它不过是描绘空间的一种方法,并不是绝对有效地。”[4]181
二、莫奈绘画中的东方图式意象
西方美学对于意象的生成与审美的主体精神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物观物、以物观人等。物是指物象,就是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这种形象始终离不开生活的具体感受,带着想象力,饱含感情而进行的一种思维。因此,它作为一种意象变异,来自于形象的直观性。比如在19世纪70年代,莫奈开始对东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种浓厚的兴趣仅仅只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里。
(一)日本桥形象
任何的艺术品都能展现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关于这一点的肯定,西方的美学家海德格尔的方法是:“我们应该会转到存在者,从存在者的存在的角度去思考存在本身。”[5]390所以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这些艺术作品的存在者,却常常忽略了本身艺术品的存在。莫奈明显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作品是《日本桥》。日本桥作为一件艺术品,本身就少不了物性,主要特征在于它的有用性。但是这种有用性又被植根于可靠性之间,也就是说,桥的有用性在于本身具有跨过河流,方便人们交通。当人过完桥的时候,这个状态是一个完整活动的一部分,人们过完桥时就觉察不到桥的可靠性。如果说桥断了,桥烂了,那么人们就会用另一种的眼光来看待它了。在莫奈的笔下多次呈现出不同色调的日本桥,日本桥在睡莲的映衬下,根据或明或暗的固有的颜色进行对比,形成不同颜色的桥。这是诗意的栖居,是心中的家园。这画面上桥不是绿色的,树叶不是褐色的,叶子的绿色和树干的褐色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化,把不同颜色的笔触分布在画面上,通过笔触之间的色彩对比,在不同时间、空间的程度上体现光的跃动。为了研究和表现景观的氛围,画是在交谈,它是一种召唤。
(二)睡莲形象
如果说科学是一种理智的活动,艺术就是一种与之相反的感情活动。艺术是一种具体化的过程。卡西尔在艺术的具体化的过程中指出:“在艺术中,我们不是将世界观念化,而是将它感受化。……艺术不是印象的复制,而是形式的创造。这些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诉诸感觉的。一旦我们摈弃了感觉经验的世界,它们便会立刻丧失根基,便会立刻蒸发。”[6]166因此,莫奈的睡莲形象不是印象的复制,而是诉诸直觉感受的意象,它是一种充满了感情、旺盛的生命和艺术家生命里的意象。
一幅画就是一个世界,一朵睡莲也能表现心灵的意象。莫奈的莲花是用色彩来描述的。在睡莲的形象里,莫奈混合采用了蓝、红、绿等色彩,在薄雾的笼罩下显露五光十色的光芒。莫奈把画面的颜色处理得越来越厚,表现得越单纯。睡莲在春天的季节里显得生机勃勃,在变化莫测的绿色水面上,映照着天空下的玫瑰色的睡莲,它洋溢着内在美,形神兼备,是一曲歌唱春天的小调。
远远观来,湖面犹如一面镜子,照的莲花春色三分。仔细看来不是花,这是他心中的自然。人们逐渐认识到,莫奈的睡莲是自由的。迷离恍惚,莲花朵朵,像音乐里的音符,富有韵律节奏,这是一种独特的美感。雾里看花,小桥流水,创造了一个回荡的空间,展示了一个丰富的艺术。这样的朦胧假如出现在中国画里,是作画妙在含糊,是作画模糊到底,是作画山水要迷离有序。模糊迷茫比清晰写实更能露出美妙的美感,中国画所描写的睡莲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物象,而是需要各种景物来进行巧妙的化境,将自身的主观感情与自然融为一体,共同的表达整幅画所体现的意境。
(三)人物画形象
成功借鉴了东方艺术图式的元素,使得莫奈艺术作品中出现了新的气象,出现了超凡脱俗的气韵,增加了创新性。19世纪中叶,有专卖中国和日本的物品的商店在法国的各个角落里开业了,市场里一出现东方的艺术品就立刻引起热烈的追捧。于是,印象主义画家首先在这种东方艺术的融合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灵感。莫奈的《穿和服的女人》中,从画面上看,是结合了东方艺术的图式,实际上是绘画技法的改变,在画面上更加注重写实。通过想象力和全新的构图方式,色彩、构图、题材的运用颇为讲究。莫奈是想通过表现日本和服和手持的折扇展示一种全新的审美理念,是这种被植入的东方绘画图式所表现的语言。折扇上的东方图式成为了画面上的背景,依然清晰的感受到扇中的图式造型,线条力度和柔和画面表现的效果。莫奈夫人手持折扇,穿着大红色的和服,和服上的图案可以显露出灵活优美的装饰性。这种强烈的装饰效果不仅带来感官刺激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后期印象派的画风,促进了印象派的发展。
三、总结
艺术形象作为一种艺术中使用的符号,它所构成的形式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摹仿,而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带着艺术家的感情世界去探索未知的一切。莫奈的意象基于以形象之图画为前提,进而认定艺术作品造就了的意象。这意象如同漩涡一样奔腾着的信息,在艺术作品的表现面前带给我们一系列的未知信息,从而形成以动见静,以动写静的艺术意象。在莫奈的艺术中,给予我们很多丰富生动的形象,我们认知了许多。莫奈的日本桥、睡莲等,种种形象的信息运动,能深刻地认识到美的终极意象,这种美就在于图可尽意或者图意同在,用这种叠加的形式将其意象叠在另一个概念上,同时这也是莫奈绘画最强审美艺术的魅力之一。
[1]叶朗.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藤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Karin Sanger-Düchting.Claude Monet[M].Hohenzollering:Benedikt Taschen Verlag Gmbh,1998.
[4]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5]李普曼.当代美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6]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