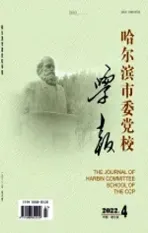试析德里达解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2013-08-15吾1
陈 辉 吾1,2
(1.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10073;2.国防大学,北京 100091)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后,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苏俄的发展形成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西方社会思潮的结合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形态都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之内的巨大生命力。当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一股批判与继承西方近现代哲学,批判与反思西方社会、哲学、科技和理性的文化思潮,即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旋即与之结合,从而诞生了一种新的流派: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其中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基于解构主义的角度去诠释马克思主义,更是从某种意义上丰富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幽灵”的存在
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在此书中,德里达用其在60年代就已经确立的解构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进行了热烈的拥抱,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并没有消亡,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种“幽灵”深深地介入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21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写作有着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动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历史已经消失,马克思主义已经消亡,未来的世界将是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国际新秩序。
正当西方布尔乔亚阶级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的胜利,准备埋葬马克思的幽灵的时候,德里达却毅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构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进行重新确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并不是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他本人也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目的是为了抗议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话语霸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祛除媒体社会的新国际的同一性魔咒,为了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向所有霸权式的政治言说打入离心化的楔子”[1]4。
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幽灵。众所周知,“幽灵”这个词语来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在《马克思的幽灵》第一章的开头,德里达就采用了他所惯用的互文式的写作方式,引用了作家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的一段文字,从而引出“幽灵”的出场。正如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召唤哈姆雷特负起拯救颠倒的乾坤的责任一样,马克思的幽灵也在召唤着后人继承他的遗产,发扬他的遗志,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抵抗霸权主义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建立一种国际正义的新秩序。所以在德里达看来,已经逝去的马克思和哈姆雷特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幽灵,而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幽灵,这种幽灵从产生开始就缠绕在西方资本主义身上,它与整个资本主义同在。在上个世纪中叶,它刚出现的时候没有被西方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神圣同盟”驱逐,今天,这个幽灵依然挥之不去。德里达用“幽灵”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可谓非常的生动,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即巨大的影响力、广泛的适应力以及与时俱进的开创力。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幽灵,那么其必定具有缥缈的不确定性,即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某种定型的东西,无法用某个确定的东西去界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这种幽灵有着“自身在场的丰富性”[1]141,任何一种个别的在场和显现都无法涵盖它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幽灵中的一种显现,它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苏东剧变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而且事实上,它是无法被消灭的。西方思想家如弗朗西斯·福山等人将苏东剧变视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死亡,就是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自身在场的丰富性”。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幽灵是不定型的,它的在场形式完全可能是多样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共产党宣言》将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等版本。鬼魂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就像货币一样,货币有着本土的和政治的特性,它‘讲不同的国家语言,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1]147。德里达指出,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幽灵的这种多样性日显突出,而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表现。所以,在德里达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的“幽灵”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它并不是某个单数,“马克思的幽灵们,这里为什么是复数呢?它们有很多个吗?这意味着可能有一撮,尽管不是一伙、一帮或一个社会,要不然就是一群与人或者不与人共处的鬼魂,或某个有或没有头领的社团——而且是完完全全散居各处的一小撮”[1]8。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见的可见性”的特征,它是不确定的,可是又是存在的;这种存在在本质上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却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它,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具有某种哲学和科学形式的谋划或者说允诺的绝对独特性的继承人。……并且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不论我们对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我们都不能不是它的继承人。”[1]127-12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诞生开始就遭到各种反动力量围剿的幽灵,正是由于它“自身在场的丰富性”,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复活和显现,从而无法被否定。“资本主义所能做的只能是否认一个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者复活的鬼魂。”[1]141
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它的异质性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幽灵的存在,异质性是其根本特征。所谓异质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表现形态,任何一种个别的表现形态都不能真正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正如幽灵的飘忽不定,不确定。在德里达的解构逻辑中,这叫“在是与不是之间”,用通俗点的话语来说,即对文本的多元化的诠释。德里达很赞同布朗肖特在《马克思的三种声音》中从哲学、政治学、科学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离之物本身的‘结合为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不是要坚持让分离之物合在一起,而是要我们自己进到分离之物本身‘结合为一’的地方,不要损害裂隙、分散或差异,不要抹除他者的异质性”[1]42。德里达认为异质是一种在某个方面内在的不可翻译性,是不可简约的,异质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缺点,“相反。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它任由自己被那展开、到来或即将到来——特别是来自他者——的东西的碎片打开。若是没有这断裂,便不会有指令,也不会有承诺”[1]48。“而提供同质性和系统的连贯性,这确实就是给出指令、遗产和将来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不可能的东西。必须有断裂、中断、异质性,如果说至少必须有,或者如果说必须有一个机会给予任何‘必须有’,那它必定是职责之外的。”[1]49-50但是,缺少异质性的理解,即“提供同质性和系统的连贯性”的理解方式,只会导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解读,这正是传统的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当面对这些教条主义的解读时,马克思自己也无奈地发出过“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感叹,以撇清自己与他们的区别。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态度呢?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应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说:“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3]。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理论创立开始就为自己的理论规定了向未来敞开的无限性,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异质性。所以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说,德里达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正确方法。
那么,德里达为什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呢?这必须要谈到德里达所自创的一个词:differance:异延(也翻译成“分延”)。differance这个词是德里达模仿法语词difference(差异)创造出来的新词,既有“差异”也有“延宕”之意。这两个词的发音是一致的,可是在意义上却有着不同,所以从语音上是无法区别二者的。德里达借此向语言中心主义发难,认为语言中有无声的内容,语言无法表达特定的意义,用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话来说,就是“所指”与“能指”的脱节。对于德里达来说,这个例子充分表明了意义的内在的不稳定性,意义总是不会如期出现,它总是要受到一种语义滑动或者延宕的影响。德里达用“异延”的例子重申了解构的基本策略: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终极不变的意义,正如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结构一样,任何符号不过是“异延”的永无止境的游戏。马克思主义同样也不例外,它的意义必定是异延的,即既是差异的,又是延搁的。所以德里达说“没有异延是不具相异性的,没有相异性是不具独特性的,没有独特性是不具此时此地的”[1]45。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幽灵”的最终化身将是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马克思本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可是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逻辑体系中,不仅马克思主义是异质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也将是多样的。当今社会,政党的存在正变得岌岌可危,“在那正在成形的政治世界中,也许还有在民主政治的新时代中可能会趋于消失的东西,正是这种被称为政党,称为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的组织形式的统治……在当今世界的每个角落,政党的结构似乎不仅变得越来越令人可疑(而且其理由不再必然总是‘反动的’,不再都是古典的个人主义的极端反动),而且变得从根本上无法适应新的—电视—技术—传媒—公共空间、政治生活、民主政治以及它们所要求的代表制(既有议会的,也有非议会的)的新模式的形势”[1]145。既然现代社会政党正趋于消失,那么它自然无法承担显现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包括共产党组织,马克思主义这种幽灵的真正显现和在场的途径是侵入整个空间,通过各种形式在现自身。马克思主义将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显现出来,在德里达看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表现。
在我们看来,德里达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异质的思想是正确的,正是因为这种异质性,马克思主义才可能在不同国家得以传播发展,生根发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在中国的生动体现。毋庸置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体系是他们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反思,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意义并非固定不变,更不是我们可以随手拿来就用的宝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有力注脚。同时,德里达关于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是多样的思想也是深刻的,可是德里达从现代社会“政党的岌岌可危”出发来断定现代一切政党已经丧失了重现马克思主义的重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代共产党组织的理论来源,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加以警惕和批判。同时,按照德里达关于现代政党不能承担重现马克思主义责任的逻辑,这就必然导致否定了从政治学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而这与德里达本人所提倡的“异质性”和“继承者的多样性”观点是矛盾的。
三、马克思留给人类的遗产是批判精神
德里达认为,我们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那么,我们所继承的马克思的遗产到底是什么呢?在他看来,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说:“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的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1]124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多的精神,“我们应当把这种精神和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的整个历史中”[1]125。德里达排斥作为其他各种精神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即本体论和体系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将它们叫作“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转化成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只有批判精神是“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所应该继承的遗产。在当今这个充满“独断主义”和“世界性的霸权”的时代,要打破那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我们就必须求助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结出硕果”[1]122。所以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剥去了如本体论、方法论等诸多意义的仅剩下批判精神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切基本原则、理论知识早已被德里达抛到了历史的尘埃中。德里达认为,坚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能够仅仅在理论层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必须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紧密结合。“如果说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我永远也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决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它甚至更主要的是某种解放的和弥赛亚式的声明,是某种允诺,即人们能够摆脱任何的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经验。允诺必须保证兑现,也就是说不要停留在‘精神的’或‘抽象的’态度,而是要导致所允诺的事变,或者说行动、实践、组织等等的新的有效形式。与‘政党形式’或某种国家或国际形势决裂,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实际的或有效的组织形式。”[1]126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能停留在“精神的”、“抽象”的层面,而是要付诸实践,德里达认为“只要对马克思的指令保持沉默,不要去译解,而是去行动,使那译解(阐释)变成一场‘改变世界’的变革,人民就会乐意接受马克思的返回或返回到马克思”[1]46。
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肯定是深刻的。批判性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别的理论,同时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2]680马克思主义总是坚持“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批判的精神。而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精神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正好有着内在的相通性。其次,德里达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观点是正确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二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理论只有与实践结合,才会显示出巨大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德里达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深刻见解,是值得我们弘扬的。这种可贵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中所牢牢坚持的根本原则,是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将我们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中解放出来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理论得以不断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化的历程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更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当今时代正确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德里达在消解马克思学说的具体内容时却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肯定批判精神却否定了其他精神,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成为一种孤零零无所依靠的东西,最终只会走向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坐标,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以辩证和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