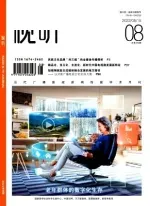目光与防线:虚拟群体反腐心理探究
2013-08-15邓晓慧刘政洲
■邓晓慧 刘政洲
(作者系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 级研究生)
近年来,网络反腐事件不断走入公众视野。互联网动员力壮大的背后,无不反映出网络虚拟群体的强大力量。
2012年8月26日,在视察“8·26”陕西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的现场,官员杨达才因在现场微笑的一张照片被网友挖掘并微博转发,其信息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短短27 天内便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职落马,这一事件被称为“表哥事件”。类似事件并非只此一例。在网络这一平台上的虚拟群体,是基于何种心理热衷于揭露官员贪污?新媒体在当中起到了何种作用?相关部门如何拿捏好网络群体的特殊心理,并掌控、疏通好媒体传播这一管道,从而促进民众参与政治、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呢?本文通过分析“表哥事件”,对虚拟群体反腐现象进行探究,从舆论环境、舆论个人、临时集群等方面着手分析集群反腐心理的缘由,提出相关部门可供应对的策略。
一、碎片化的舆论环境
(一)平台的开放
生活在日渐开放的社会中的个体,对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事物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并有机会把自己对某些公共话题的观点、态度、意见公开地传播给他人,与他人分享。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跟新媒体一道形成了多维度的媒介汇流“立交桥”,打破了传统媒体垄断的舆论格局,使得人们分享、诉求表达的管道多元化起来。新媒体这一平台,更是以便捷、及时的先天优势成为不少民众分享信息的优选资源。
(二)意识分野与冲突加剧
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今天,因自身阶级、阶层、社会身份的迥异以及利益变动的不均衡,不同利益主体对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焦点问题,存在着一定的态度分野。这种态度分野在新媒体平台上呈现出的,则是碎片化的意识分野,甚至是冲突的舆论分流。
网络媒介上出现的群体反腐行为,正是在这一碎片化的意识分野中形成的一种突出现象。政府官员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是属于改革中在各种社会资源方面获得明显利益的群体,其个人信息暴露在网络上时,本身就有一定的围观率。当这部分群体因为有贪污渎职等嫌疑时,便容易激起社会中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与社会底层群体的反感,导致群体化围攻。
二、碎片化个体的反腐起因
(一)狂欢心理的延续
“狂欢”这一术语原用于描述欧洲民间的狂欢节上,全体社会成员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年龄的区分与界限,通过庆贺、仪礼等群体聚会和传统的表演场面,尽情狂欢,进而得到情感宣泄,达到普天同庆的盛大场面[1]。将“狂欢”这一术语借用到网络平台上来,并不为过。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诸如通货膨胀、就业难、房价飙升等多方面的压力。而网络上的不少内容恰好能为这些人们提供以戏谑方式将现实问题仪式化解决的途径。很多展示个性、解构经典、嘲弄权威的恶搞文字段落、反讽假大空作品的视频、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求虐”微博(如新浪微博@留几手)等往往能受到诸多网友青睐,通过论坛、贴吧、QQ、微博、MSN 等平台的转发和分享,便形成了像节日那样的全民“狂欢”状态。
网络个体围观反腐事件,也是“狂欢式”心理的一种延续。当新媒体将杨达才个人的“名表信息”提上媒体议题时,最初起作用的是网民普遍的“猎奇”与“看客”心理,目睹杨达才落马过程,就有如古时在广场上看到罪臣被汹涌的人潮争相推拉、嘲讽、打击,最终被送上断头台一般解恨。基于舆论客体的切身性、重要性及争议性,网民自发挖掘出杨达才其他个人信息,将他推上舆论浪尖。网友在反腐事件上推波助澜的举动,就有如转发“杜甫很忙”“陈欧体”等热门微博一般无意识、自主和随意。网络生态中个体的这种集群行为,是对现实宣泄不满、获得情感释放的一种“狂欢”举动,也是将现实问题获得幻想式解决的一种路径。
(二)学习与强化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他人的行为表现,以形成态度和行为方式;加上强化作用的激励,就能够较好地进行模仿学习。在“表哥事件”中涌现出的年轻建言者——刘艳峰,因为给陕西政府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情况而被众人熟知。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正是由于此前受到浙大学生雷闯的事迹鼓舞,才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动力,因而乐意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做出此举。除了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刘艳峰个人外,在网络中出现的部分匿名个体,也是因为以其他参照群体的行为——以个人力量参与反腐为榜样,才继续做出“人肉搜索”官员信息、转发杨达才“微笑门事件”信息等行为的。“表哥”落马后,参与揭露、分享和转发、质疑、问责等行为的网络个体,因为“切身参与”而收获一种近似“奖励”或满足的情感。当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时,这类群体的行为便会再度强化,在关注事态发展、分享案件进展状况等方面更为主动和积极,这些显著性举动会将案情发展成舆论热点,经由媒介“立交桥”的融合传播,相关政府部门引起注意后采取举措,让案件最终浮出水面,真相大白。
三、舆论临时集群的推波助澜
回顾“表哥事件”的整个过程,大致如下:
个人→群体→媒体播报→大群体共鸣→政府参与→反腐热潮
即:首先经由网友个人挖掘名表照片,引起网民火速围观,新媒体随即将其事件提上网络议事日程,继而引发大面积群体注意并引发反腐共鸣,强大的舆论功效促使政府部门涉入调查,最终掀起一场反腐热潮。此间可以看出,网络这一平台使关注“表哥”的个体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临时集群,在推动案件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无意识人格与相对剥夺感
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群体心理。他认为个体一旦进入到群体中,无意识的品质便占了上风。群体中的个人表现出的特点是:个人的感情和思想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倾向于同一个方向;这种由暗示所获得的观念又立刻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成为一个受群体意识支配的玩偶[2]。
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网络时代的民众,人人都是一个传播者。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寻求自我表现、经济保障、政治权利,抑或归属感时,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未得偿所愿、自己的目标没有得到完全实现的时候,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3]。当“官员”、“名表”、“别墅”、“房产”、“二奶”等名词在某事件中曝光时,直接刺激到部分个体的视觉神经,这种相对剥夺感再度遭到动摇和强化。“曝光”由此成为网络个体形成临时集群的导火索和牵引力。各行各业的、散落在不同城市的网民,因为某官员腐败这一事实触动了共同的社会准则,强烈的利益不均衡感使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网络平台上参与交流、追踪或分享这一事件,企图获得情感上的合拍与共鸣。个体与其他个体间的情绪分力相继传染、碰撞,并受认知上的不均衡感和无意识的磁场牵引,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体意识合力。由于媒体赋予反腐事件的显著性,大众的议题认知得到加深,形成一种政治放大效应,使群体意识合力的效应更为显著,网络舆情更为汹涌。
(二)沉默的螺旋:社会心理与舆论
根据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个体天生就有害怕孤立的心理,因而在表达观点和想法时,倾向于加入与自己观点一致的群体,并会越发大胆地将其发表和扩散;如果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便倾向于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人们便会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4]。
诺依曼的这一理论,可以用来理解大众反腐社会心理的形成过程。杨达才名表曝光的后几天曾做客新浪微访谈,坦诚自己5 块表的不同来历,试图回应网友质疑,但此举并未引起太多网友的赞成和同情。可见在事件广泛扩散的情形下,基于网民对“周围意见环境”的感知,大部分网民俨然已经形成“杨达才贪污毋庸置疑”的心理思维定势。而少部分认可杨达才个人财产为正当收入的网民,有些因为证据的不明确而倾向于沉默,对该事件置若罔闻;有些表示支持的言论被埋没在谴责杨达才的呼声中,力量微乎其微;有些在感受到反腐言辞的强大威慑力后,改变了原有的个人立场,加入到问责杨达才的阵营中。由此,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问责之声,不断累积,支持之声则日渐削弱。社会舆论一边倒的意见气候,使杨达才企图力挽狂澜的公关举措,宣布无效。
(三)保护伞下的本能释放
勒庞认为,野蛮与破坏是人的本能,孤立的个人在生活中很难表现出这种本能,但当他处在一个不负责任的群体中时,他会因为无须受罚而放纵这种本能[5]。知情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贪污事件时,未必有质问或揭发的勇气与举动。而当个体撑着匿名的保护伞混迹于网络集群中时,便感受到了群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使得他有胆量去发泄天性中的欲望——宣泄不满、揭露事实、诋毁个人或问责真相,做出种种宣泄原始本能的冲动行为。
群体心理出现偏激与冲动,也与群体的推理能力有关。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群体缺乏推理能力,并很难辨别出真伪,接受的仅仅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非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后得到采纳的判断。我们也可以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这点,个体在面对官员腐败这类跟自身命运、生死牵连关系较少的信息时,往往会采取周边性信息处理模式——对信息细查处理的可能性降低,对问题深思熟虑的程度随即减弱。群体中的个体这种普遍欠缺思考的方式,导致推理能力的降低,在无形中便容易接受外界带来的强制性观点与立场。新浪视频、腾讯微博、QQ 等播报表哥事件的网页中,常能看到一些表达对杨达才作为的不满、对政党当前反腐力度不够的谴责、对社会现行利益分配的失望等内容,大都是一时的牢骚和抱怨,并及其缺乏理性思考。在网络上,共时迅捷的交流方式使得这些籍籍无名者偏激的言论得到扩散,迅速产生蝴蝶效应,通过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使偏激的观点更加逻辑化、系统化,出现舆情产生的“法不责众”心理[6]。
四、面对反腐集群心理的针对性规制
(一)因集群心理的特殊性而滋生的网络反腐缺陷
诚然,网络为网民反腐提供了极为低廉、快捷通畅的民意表达渠道,但由于个体和参与反腐形成的临时集群两者心理的特殊性,这种自由宽松的表达渠道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该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容易侵犯被举报者的权利。举报者及知情者容易因为携带个人情绪而难以把握个人权利信息和腐败信息的尺度,从而侵犯被举报者的权利。
2.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由上文可知,网络舆论容易形成一边倒的趋势,而网络群体基于对腐败的仇视,通常缺乏理性的态度和推断能力,极易产生舆论围攻。当网络舆论成为普通民意时,容易给腐败案件的当事人及司法机关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二)权利所有者的针对性规制
面对浩浩荡荡的网络反腐,政府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正确引导并进行规制,充分发挥作用,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
1.疏堵结合。官员腐败信息曝光后,相关部门必须具备高效的工作态度,第一时间查清事情真相,并将准确的反腐进展情况告知公众,主动地发布权威信息,避免网络虚假信息的夸大和蔓延。相关部门必须对碎片化的舆论分流进行疏导,才能使民众行使监督权、知情权的表达通道变得更为有序和通畅。
2.法律制度对接。为网络监督、曝光及举报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确保网络反腐成为公民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的合法有效的行使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网民因“法不责众”心理而做出诽谤、诬陷、打击报复等非理性举动,混淆反腐临时集群形成立场的判断力,最终影响民意舆论场风向标的确立。
五、结语
综前所述,处于网络开放平台中的反腐个体,对政治公共事务往往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分野与冲突,常用一种“全民狂欢”心理围观反腐事件,并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而做出进一步的举动。而由于参与反腐事件形成的临时集群,通常都由无意识的品质所引领,对优势意见往往采取趋同行动,也因缺乏一定的群体判断力,容易产生偏激与冲动的心理,做出难以抑制本能的种种非理性行为。
公众的目光是反腐第一道防线。当前政府要想利用好网络反腐这把双刃剑,就必须学会洞悉网络反腐个体与临时集群的心理,拿捏好表达与引导民意的合理尺度,学会疏堵结合,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机制,使自己处于网络舆论场的主动地位。只有网络反腐走上和谐健康的发展之路,才能成为我党进行反腐倡廉之战的良驹勇将。
注释
[1]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7),P151。
[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P18。
[3]周晓虹:《社会心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P189。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P221。
[5]《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39。
[6]闫硕:《新媒体时期网络心理群体浅析——基于〈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的认识》[J],《卷宗》2012(1),P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