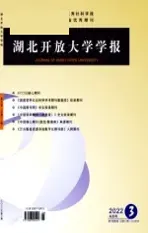浅论翻译者即叛逆者
2013-08-15李胜玉
李胜玉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 南京 210037)
一、忠实与叛逆
有译者说,原文的意思在翻译中不应进行处理,任何的添加都是不允许的。也有译者说,翻译就如一面镜子,文中总会有译者的思想和感情,这就要求译者藏起自己的思想,抑制自己的感情,将原作的思想内容全部译出,不做任何变动,否则就是叛逆者。正所谓“翻译者即叛逆者”。
其实不然。译文的种种调整,都是为了更好的忠实于原文。忠实并不是死搬硬套,其间也需要创造。那何为忠实?创造是否意味着叛逆?
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杨绛说过:反正一切翻译理论的指导思想,无非是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的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也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1]136这可说是忠实的定义。他同时认为在翻译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无规律可循[1]。这实际就谈到了创造性的问题。
庞德也曾用“忠实”指代原文意义上的以及对原文氛围上的忠实。也就是说翻译要考虑上下文,在具体的语境中判断其意思,不能将其独立出来。即所谓的“决定并翻译”。
由此可见,翻译需要创造。失去了创造,一味的“忠实”,有可能使译文晦涩难懂,反而无法将原文的精华译出。西方早期《圣经》就因为过度的忠实而无法表达出原文的真实意思。
二、符号学理论
符号学研究的是形式(即符号)与内容(即意义)的三大关系。第一,符号与符号所指实物间的关系,即所指意义;第二,符号与使用该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即语用意义;第三,同一符号系统内符号与符号间的关系,即内部意义。
正因为符号所具有的这三种不同关系,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极力保留和传达符号所具有的这三种不同关系。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内容或者意义的不变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而言,意义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善于牺牲才能善于保留,必须有意地牺牲些东西,以便将原文中更加重要的东西传达出来[2]160。
在翻译过程中,内部意义传达的最少,也是多数时候损失最多的,但有的时候却是原文的精华。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所指意义来传达内部意义,例如:
1.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So many deeds cry out to be done.
And always urgently,
The world rolls on,
With pressing time gone.
Ten thousand years are too long,
Seize the day, seize the hour.
2.On Sunday they pray for you and on Monday they prey on you.
星期天他们祈祷你的幸福,星期一他们欺盗你的财产。
这两个例子优先考虑了节奏、押韵、谐音、双关词形和语法结构等,以求完全准确的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同时与原文的修辞保持一致。
1.You are a lad, you are, but you are as smart as paint.I see that when you first came in.
你还是个小孩子,可是非常机灵,你刚进来时,我就看出来了。(《综合英语成语词典》,1985:931)。
在这个例子中,原文的形象没有保留。因为原文形象的保留不仅无法清楚
的表达原文的含义,反而会使读者摸不着头脑。这就需要上面提到的“牺牲”,因为“翻译不是简单机械的复制原文内单独要素,而是有意识的选择表达原文各要素的各种手法的复杂过程。”[2]160。再如:
2.When you said that what he chiefly lacks is selfdiscipline, you hit the nail right on the head.
你说他主要是缺乏自己约束自己的能力,真是一针见血。(陈文伯,1982:137)
由上可见,原文的形象在习语翻译中一般都不太容易保留,因为这些形象好比不同的符号,属于两种符号系统,要通过某种转换才能有意义。于是就出现了翻译中原文形象的转换或者遗失,这实际是翻译的进步和创新。
三、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认为接受者即读者是翻译的服务对象,因此要评判译文的质量好坏,不仅要比较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是否一致,最主要的是必须要看译文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是否和原文的接受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基本一致[3]202。如果不一致,就要对译文加以适当变化以取得同样的反应。例如:
1.It was an old and ragged moon.
原译:那是一个又老又破的月亮。
改译:这是一弯下弦残月。[4]88
原译若直接采用原文的“old”和“ragged”,在译文读者中就无法产生和原文读者同样或相似的共鸣,不如改译的形象传神。
2.A 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译文读者是无法接受原文形象,产生和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的,必须进行转换。因为“翻译的对应不是建立在原语词汇的对应的基础上,而是从双方的语用功能和意义相当的角度出发来替换的”[2]246。
3.如今,作个大丈夫也有他的难处。譬如吵嘴,你就是有理,却也只能装着无理,拱手告降。
One of the embarrassments of being a good husband today is tha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defend yourself in a quarrel and have to go down on your knees pretending that you are not on the right side.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拱手做辑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特色。原文的“拱手”表示退让。如果译文不做变动,译文读者就会由于不了解中国文化而无法将这里动作与告饶和让步相联系,因此译文改译为“go down on your knees”,以便最大程度的传达出原文的意思。
4.春怨 金昌绪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A Lover’s Dream Jin Chanxu
Oh, drive the golden orioles.
Farm off our garden tree.
Their warbling broke the dream wherein.
My lover smiled to me.(translated by W.J.B.Fletcher)
由于不同语言诗歌的形式不同,诗歌的翻译只能放弃形式的对等而采用功能对等。该诗的译者采用了省略,添加等方法通过功能的对等传译了原文的意思,而不是着重形式上的对等。如,译文用“smiled to me”取代了“到辽西”,同时省略了意义重复的“莫教枝上啼”。这是因为译文读者对“辽西”的寓意不一定了解,用这种灵活的表达比直译更能传神。此外,译文也很押韵,如“tree”和“me”,表达了原文的意义和神韵。
四、结论
从上面的实例分析很容易看出,真正好的翻译不是对原文亦步亦趋,死抠字眼,貌似忠实,实为背叛,这样的翻译会使译文晦涩难懂,有时甚至让人不知所云。好的译者应该紧跟作者的意思,在原文基础上根据目标语言的特点和文化背景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变动,从而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特点和文化。这种创造是翻译中不可少的,它使得译文能具有原文的神韵。当然,这里所说的创造是以原文为基础,不是无原则的。否则就如德梅西里阿克所说:“偏离原作意思的翻译不是翻译而是背叛。”[5]114-115。
[1]彭卓吾.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E A Nida, Taber Charles R [M].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Leiden: E.J.Brill.1969.
[4]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