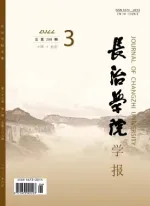王充《论衡》的文学接受论及其成因探析
2013-08-15杨火枚崔林芳张智毅
杨火枚,崔林芳,张智毅
(1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2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接受美学从西方传到中国,许多学者将之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接轨,以接受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学进行探究。许多人认为这是开端,其实不然,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关于接受心理的片段探讨。
当时百家争鸣,诸子各家为了向君王推销自己的学说,纷纷揣测君王心理从而投其所好,希望君主能采纳自己的主张。如韩非子在《五蠹》中分析了五种人在不同的情况下提出了不一样的学说和主张。“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韩非子指出,“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因为君王喜欢听花言巧语,所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合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人盈廷,”世人为了迎合皇上的爱好,总是讲一些不切实际的花言巧语,以至于朝廷里到处都是称颂先王和高谈仁义的人。在其《外储说左上》的“郢书燕说”的寓言中也有说到接受论的问题,“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本意是烛光太暗希望举高烛台,却被燕相国理解为治国应该举荐贤人辅佐君主,并认为只有如此国家才能昌明。燕王大悦,开始广泛搜罗人才,国家出现大治的局面。这种误读已经从文学的角度认识到读者会意创造的奥妙之处。其实从接受美学角度看,读者的创造可以使作品的意义价值更加丰富和更易彰显。王充继承前人的思想,在《论衡》中也对接受论予以一定关注。
在关于士人际遇的的论述中,王充指出士人能否被任用,不在于言论水平、德才的高低,关键在于是否迎合了当权者的好恶心理。“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逢遇篇》)就是说,只有自己的才能符合了君王的爱好才能被赏识,这也就是王充强调的“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文学也一样,作品价值的彰显离不开接受者的参与。
一、《论衡》文学接受思想的体现
在创作缘起上,王充对接受者以“奇”为衡量作品的标准进行了分析。“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艺增篇》,作家为了迎合世人的这种求“奇”的趣味爱好而创作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作品,因为只有“奇”的言语世人才会采纳,不“奇”的话没人听。“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艺增篇》。但是这种仅仅是为了迎合某一时期接受者不健康的心理而不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去创作的做法是王充所否定的。关于接受论王充主要是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文章的形式要求
汉代的汉字增多,书面语开始追求繁复艰深,赋体主张“骋其言辞”,使得书面语和口语相脱离。当时社会上也流行艰深的行文风格,“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王充极力反对当时“文语与俗不通”的言文分离的情况,他认为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分离会造成人们著作上的语言文字不理解,限制了语言文字的实际表达效果,同时也限制了读者的接受。他对深覆典雅的辞赋进行了批评,认为像辞赋一类的文章读者难于理解,因为其语言“深覆典雅,指意难睹”。他认为文章如同说话一样,浅显易懂的文风胜于“深迂优雅”的文风,因为文章也是表达一定的目的志向的,“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所以不应该“隐闭指意”,明确指出应该“笔辩以荴露为通”。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语言应该通俗易懂,这样才能为读者接受。他的《论衡》“行露易观”,不仅仅是如此,其它著作亦然,“《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行露其指,为分别之文”。只有文章主旨显露且读者易于理解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即使有才之士很优美的文章也是应该做到“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的,能让读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同耳”,受益匪浅,从而达到行文的目的。王充指出当时造成言文不一致的原因,有时代和地域的因素,“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前人著作中的语言与汉时的语言不通导致时人不理解的,而不是为了故弄玄虚、玩弄文字故意为之。他随即举了秦始皇的例子,“独不得此人同时,”秦始皇对韩非子的著作大加赞赏是因为韩非子的书“其文可晓”的缘故。
(二)文章的内容要求
王充认为主体需要有感情冲动才能进行创作,也就是内心要蕴含着一定的情感才能将之“著之布帛”。所谓“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超奇》),“心”是主体内在思想感情的体现,文章在内心酝酿构建,发而成文,文是创作主体心灵的展示,“心思为谋,集扎为文”即是此体现。因此“文”是作者“托文以自见”的载体,创作者凭借文章可以超越生命有限性,让后世的人还能阅读自己的文章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佚文》)。即是指通过接受者的角度来体现文章内在的价值。刘勰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1]就是对王充这一文学理论的继承。不过王充的“情”不是个体生命生存的情感而是指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情感,刘勰的是从纯文学上提出来的人对生命存在等个体情感,指的是人的审美之情。王充还从文学性情愉悦功能上指出读者和创作者通过文学作品的沟通达到心灵的交汇才是真正好的作品。在《论衡》中王充对陆贾的《新语》赞不绝口,他在《佚文》中指出陆贾每向汉高祖上奏一篇,左右的臣子都高呼“万岁”,这是由于“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的缘故,阅读《新语》的接受者看到了著作中的精彩之处,愉快之气发自内心,所以欢呼。王充从读者接受角度意识到文学对于读者的审美愉悦功能,这说明只有引起读者共鸣的作品才是值得称道的作品。
二、王充接受论思想的成因
(一)王充的平民思想
王充提出文章语言浅显易懂和提倡真情实感等主张,是与他的平民思想是分不开的。
首先,从王充的身世看,他出身于“细族孤门”,其祖先以农桑为主,世辈都“勇任气”。由于常受当地豪族的欺负,所以地豪族的欺负,所以以暴抗暴,最后只能不停地迁徙。其祖辈家庭状况一般,到王充的时候家里已经到了“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的地步。因为他出身于“细族孤门”,导致他在仕途上屡屡不得意。他在《讲瑞》中就代表下层身份低微的知识分子对门阀制度表示不满。当时世人认为“龟故生龟,龙故生龙。……见之父,察其子孙”,因为王充的祖父一辈没有什么出息,所以王充本人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当时世人的这种观念导致王充很难从平民阶层进入统治阶层。王充针对这种血统论,据理力争道:“马有千里,不必骐驎之驹;鸟有仁圣,不必凤凰之雏。”当时汉代流行举察制度,而地方长吏举用人的标准是依据“阀阅”(即经历和“政绩”),“儒生无阀阅,所以不能任剧,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程材》)所以被举荐者往往是通晓公文的“文吏”,而像王充这种满腹才学的有德之儒生很难得到推举。因此他的平民出身和一生不得意是他平民文论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
其次,王充对士人的评价也可以窥见其平民意识。在对士人的评价中,王充不论其地位之高低贵贱,他认为“才有高下,言有是非”,应该以才能论士人,他举例说明自己从才能的角度评价士人的正确性:“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在《案书》中王充对当时很多名不见经传却很有才能的士人大加称赞,如“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他们“位虽不至公卿”,但是“诚能知之囊橐”,称赞他们是“文雅之英雄”,并且将“广陵陈子迥、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这些人的赋、奏与屈原、贾谊和唐林、谷永相提并论,对他们的才能大加称赞,认为他们虽然暂时不出名,但是在百年之后他们必定是刘子政、扬子云一类的人物。同时他的平民思想意识还促使他敢于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当时被当做神一样的儒家圣贤。“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书解》)王充把周公和孔子看作和“世儒”相对的“文儒”,从创作才能的角度对他们大家称赞。这种打破出身和阶级限制来肯定士人才能的评价标准也是他的平民意识使然。
最后,王充的平民意识还体现在他为文颂汉的动机上。王充的《论衡》宗旨是“疾虚妄”,但是同时他又写了一组为汉代歌功颂德的文章,如《齐世》、《宣汉》、《恢国》等。王充的颂汉篇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东汉时期迫于汉明帝和汉章帝的政治压力,文坛上当时笼罩着一股歌功颂德之风,王充为了自保,只得在其《论衡》中写下些歌颂汉代的篇章。不过除了自保这一消极因素以外,王充代表的当时满腹才学的在野知识分子也对进身朝廷还存有幻想,希望能通过为汉代大唱赞歌受到当朝者的重视。当时班固等人因为歌功颂德而谋得高官,王充也想跻身他们行列。“《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由于自己地处偏远,所以就算自己为汉代歌功颂德,当朝者也未必知道。正所谓“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但是如果自己能像班固一样“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一旦能做作文学侍从之臣,那么自己的歌功颂德也能达到显著的效果。他的颂汉目的也是他平民意识的体现。
(二)王充功利主义的文章观
王充浅显的语言观和情感真实论的主张也与其文章观是分不开的。在王充看来,写文章的目的不应该是夸耀创作者的才华,而是让时人和后人通过阅读理解接受文章,只有如此才能发挥作品的影响和教益作用,实现文学的劝善惩恶功能。“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他认为只有根据实际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达到劝善惩恶的效果,“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免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历史上著名圣贤的文章也是为达到教化的目的而创作出来的,如孔子因为周朝有弊端从而创作《春秋》,周朝没有弊端的话就没有《春秋》这部伟作,“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为世用”的正确性,他创作《论衡》不是因为“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的审美目的,而是为了除虚妄之语,辩证是非而作,“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这种创作动机充满功利性[2]。王充是希望通过文章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作用,引导时人和后来者向善,其实这也是文学接受理论的一个方面。王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能起教化作用的文章才能为读者接受,才能为当权者接受,从而达到治国和使文章永垂不朽的目的。
王充的文学接受论虽然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对接受论的成因探析也不系统不全面,甚至王充的文章观因为一味追求功利化而导致了忽略艺术形式的偏颇,但是这是王充代表的汉代对文学接受的有益尝试,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链条,不应该被忽略。
[1](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