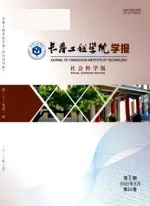从《他们眼望上苍》看非裔女性形象的文化身份阐释
2013-08-15黄真真
黄真真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常熟215500)
一、引言
文学形象的文化身份阐释对于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1]“在身份的建构上,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解说那些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1]文化身份,即Cultural Identity。无疑在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这部作品中就反映了非裔女性形象文化身份的困惑和重构等问题。
佐拉·尼尔·赫斯顿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杰出的黑人女作家,但她却一直默默无闻,直至艾丽丝·沃克在一篇题为《寻找佐拉》的文章中重新发现了她,认为她受此冷落是不公平的,并赞誉她为“南方的天才”。赫斯顿于1901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黑人小镇,她很早就离开故乡去往当时黑人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纽约,在那里她结识了著名的黑人桂冠诗人兰斯顿·休斯,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1925年,她有幸被巴纳德学院录取,成为该校第一名黑人女学生,在著名人类学学者佛莱兹·波斯(Franz Boas)的指引下,她开始学习人类学,这一决定对她日后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波斯的鼓励下,她对黑人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收集黑人口头民间故事。在此期间,她逐渐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下定决心要将此文化从白人主流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她将这些民间故事收集于题为《骡子和人》(Mules and Men)(1935)及《告诉我的马》(Tell My Horse)(1938)的故事集里。这些素材成为了她日后创作的灵感源泉,并对后来许多其他黑人女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眼望上苍》是一部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小说以女主人公珍妮的三次婚姻为主线,探索了黑人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幸福的向往。同时这部小说也掺杂了作者本人的经历,赫斯顿用黑人口语艺术化的表达,展示了她对于保存黑人传统习俗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如何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氛围中阐释非裔形象的文化身份,尤其是非裔女性的文化身份,是作者始终萦绕在心头的创作根基。
二、女主人公文化身份的困惑
《他们眼望上苍》中的女主人公珍妮是一个黑白混血儿,混血儿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罕见,作为当时文学作品中主要黑人女性形象的一种,(黑人保姆形象、荒淫无耻的荡妇形象及可怜的混血女形象)[2]英文单词是 mulatto,来源于 mule(骡子),是驴和马的交配物,却比它们更低劣,没有繁殖能力,这就暗指了混血儿的非法地位。珍妮的外婆年轻时被白人强奸生下了珍妮的母亲,而珍妮的母亲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生下了珍妮,所以珍妮其实就是奴隶制和强暴的产物。珍妮从小和外婆相依为命,生活在一户白人主人家中,她一直以为自己和别的白种孩子没有什么区别,直到六岁的一天,她和其他白人小孩一起拍照,她竟然认不出照片中的黑孩就是自己,还问道,“我在哪儿? 我看不见自己”[3]。(以下小说原文均引自此译本)。当被指出来后,她惊讶地说,“啊! 啊! 我是黑人!”[3]作为一名生活在白人社会中的黑人女性,她可能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大家都叫她字母表,因为人们给她起了太多不同的名字。
在珍妮的成长过程中,无疑外婆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外婆作为黑人传统女性的代表,历经了生活的磨难和沧桑,她不愿意珍妮重蹈前两辈的覆辙,所以为珍妮挑选了在她眼中可保珍妮衣食无忧的人家。虽然这并非珍妮自己的意愿,但她却顺从外婆家给了有六十英亩地产的老鳏夫洛根。这桩婚姻完全是笔交易,洛根只把她当可以干活的骡子和供他发泄的玩物。所以这第一次的婚姻象征了非裔美国人历史中所经历的一个时期,即美国内战刚结束这一阶段。黑人女性刚从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她们仅仅寻求一段合法的婚姻作为庇护。可对于珍妮来说,她只能问自己:“婚姻能结束无配偶者那无边的寂寞吗?婚姻能像太阳造成白昼那样造成爱情吗?”[3]没有人告诉她答案,在等过“一个开花的季节,一个茂绿的季节和一个橙红的季节”后,她突然明白了,“婚姻不能造成爱情”,于是“她的第一个梦消亡了,她成了一个妇人”[3]。这是珍妮在极端孤独的心境下产生的顿悟,于是她开始尝试寻求一种新的生活,但在这一时期她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她想摆脱眼前的生活,可对于自己确切要什么并不清楚,于是在第二次婚姻中,她草率嫁给了乔,一个“吹着口哨,打扮入时”的男人[3],并随着他私奔到一座建设中的黑人小城开始生活。没过多久,随着乔的不断发迹,珍妮成了他豢养的宠物一般失去了自由,并被剥夺了话语权,“我的妻子不会演讲,我不是因为这个要她的”[3]。乔把她当成装饰华丽的痰盂——仅仅是一种自我炫耀,体现身份的文化符号。这第二次的婚姻象征了20世纪初大批黑人农民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时期,乔就是这一批中新兴黑人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极力否定黑人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将白人价值观念作为模板,全面追求白人的生活方式。随着乔的过世,珍妮“扯下头上的包头巾,让浓密的头发垂了下来,她仔细审视了自己,然后梳好头,重又把头发扎了起来”[3]。她在凝视自己,思考自己的生活,她意识到在这一阶段的生活中并没有找到自我,作为一名生活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美国社会中的非裔女性,她仍然在追寻。
三、女主人公文化身份的重构
珍妮的第三次婚姻和前两次有本质上的区别,甜点心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个体,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在和甜点心的交往中,珍妮感觉到真正的愉悦和和谐。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便是赫斯顿笔下最为关注的爱情的力量,其实不然,珍妮所感觉到的美好仅仅是甜点心给她所带来的快乐吗?玛丽·海伦·华盛顿说过:“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部小说,除了它的优美的语言和女主人公外,还有它在黑人民间习俗方面的描写。终于我们发现了一位妇女开始了寻找自我的过程,不同于黑人文学中的其他人物,她的探索过程不是使她远离,而是越来越深入她的黑人角色,深入到爱佛格莱兹(the Everglades,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地),那儿有着肥沃的黑土,野生的甘蔗及社区生活。这一切都意味着与黑人传统的结合。”[4]所以赫斯顿笔下的女主人公正因为发现了自己独特的“黑人性”,才最终回归了自己本真的状态。“‘黑人性’主要有以下三个表征:首先,‘黑人性’表现在美国小说中的黑人形象中,通过塑造独特的黑人人物形象,表现美国黑人的双重身份和双重眼光;其次,‘黑人性’还体现在美国小说中的黑人文化的因素,包括黑人戏剧,黑人生动的口语、民间传说和以爵士乐为代表的黑人音乐等;第三,‘黑人性’是美国黑人小说区别于其他种族小说的重要标志,‘黑人性’在文学作品中主要表现为黑人文学中的‘表意性’和‘音乐性’。”[5]
甜点心的本名是佛基布尔·伍兹(Vergible Woods),“Woods”在英文单词中是“树林”的意思,并且在小说中甜点心经常与阳光、植物、种子等自然界的物体相联系,他教会了珍妮一种新的语言,珍妮可以在大自然中尽情地欢笑、耍闹、劳作,在白人眼中不负责任的嬉戏实则是黑人群体乐观向上的民族精神的体现。珍妮被带到了沼泽地,一个充满原始野性的地方,她不再被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内,而是使自己的个体空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沼泽地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广场,打破了一切等级和界限。”[6]珍妮在沼泽地学会了打猎、赌钱以及更重要的一种自给自足的观念,她不再是任何男人的附庸,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不仅如此,沼泽地的环境也给了她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之感,沼泽地的小舞厅每晚都会热闹无比。“一架钢琴起着三架的作用,当场即兴创作与演奏黑人伤感民歌,跳舞、打架、唱歌,哭的、笑的,每个小时都有人得到爱、失去爱。白天为赚钱整天干活,晚上为爱情整夜打架。肥沃的黑土附着在身体上,像蚂蚁般咬噬这皮肤。”[3]珍妮这种生活的自在就在于她在这里感受到了黑人传统文化的根。“黑人伤感民歌”实质上是由美国非裔即兴创作出来的一种民间音乐,被称为“布鲁斯”,它没有固定的旋律和曲调,是美国黑人对于内心情感的一种自然的流露,作为一种黑人文化传统,由祖祖辈辈一代代流传下来,在黑人群体中传唱延续。它较爵士乐相比,更加具有一种乡土气息,往往包含一种忧伤郁结的情绪,这恰好表达了非裔美国人所经历的不公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歌唱方式对于缓解并治疗珍妮内心的创伤有极大的作用。另外,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珍妮和她的女性好友费奥比以现在时作为时态的对话,赫斯顿这样的安排是暗指女性的话语权,通过言说和歌唱,以珍妮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不仅能够重新找回自我,还能通过口头叙述这一黑人文化传统方式将之传承下去。
此外,赫斯顿将小说命名为“他们眼望上苍“实则别有深意。“上苍”译自于单词“God”,本意为“上帝”,这是在美国白人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一个无所不能、掌控世间万物的造物主形象。而在这部小说中,上帝遭到了嘲弄和戏仿。小说中主要共有四处提到“他们眼望上苍”的情景。第一处是当外婆为珍妮的第一次婚姻祈祷祝福的时候,她请求耶稣基督怜悯她们并使珍妮不要重蹈覆辙,可结果却是珍妮破碎的婚姻及外婆悲伤的过世。第二、三处是戏仿场景。第二处是当小镇的路灯点亮是乔居高临下对着所有居民发表演讲,一个自我膨胀无限虚荣的黑人此时仿佛化身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荒诞可笑。第三处是在描述仇视黑人的黑白混血儿特纳太太时,她虔诚地崇拜一切白人性的事物,憎恨一切与黑人沾边的东西,她希望“通过膜拜将能到达自己的乐园——一个直头发、薄嘴唇、高鼻梁的白色六翼天使的天堂”[3]。第四处是当暴风雨来临时,他们询问着上帝,而上帝尽管使他们暂时逃过一劫,却使甜点心被疯狗咬了一口,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所以尽管“他们眼望上苍(上帝)”,上帝却是冷眼旁观的,“一切接受顶礼膜拜的神都是无情的,一切的神都毫无道理地布下痛苦,否则就不会有人朝拜他们了”[3]。至此,赫斯顿大胆地向美国社会白人传统文化发出质疑和挑战,作为美国非裔女性,只有当她认清并重新构建本民族的根文化时,才能在社会中真正找到自我,赫斯顿的这一选择是坚定而决绝的。
四、结语
文化身份的探讨对于了解具有某一民族文化背景的族群在另一种文化土壤中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S·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认为,确立文化身份一要把它看做一群人在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代码基础上产生的连续的、稳定的意义架构;二要在承认群体共性的基础上重视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差异性,把文化身份看作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的意义建构[7]。赫斯顿笔下的人物形象第一次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非裔人物文化身份特征,尤其突显了非裔女性形象的文化身份,从正反两方面展现了女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困惑和重构,揭示了各个族裔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压迫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她已经开始当代建构非裔女性文化身份,对于后来的作者如艾丽丝·沃克及托尼·莫里森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Culler,Jonathan.Literary Theo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50,112.
[2]翁德修,都岚岚.美国黑人女性文学[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50-51.
[3]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眼望上苍[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11-156.
[4]Mary Helen Washington.“Forward”to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M].New York:Harper& Row,1990:8-9.
[5]朱振武.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22-123.
[6]陈广兴.《他们眼望上苍》的民间狂欢节因素探讨[J].外国文学研究,2005(4):33-34.
[7]Hall,Stuart.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ves[J].Framework,198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