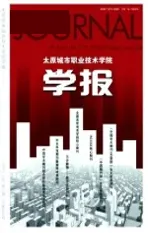禅宗空观论的美学蕴涵
2013-08-15杨毅华
杨毅华,张 伟
(昭通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一、心性本空——超越主客关系的本体结构
李泽厚在《庄玄禅宗漫述》一文中认为:“禅宗同整个中国哲学一样,其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但从根本上说,佛教的终极目标是超脱生死、解除烦恼,无意于探讨什么美学问题。相反,它还告诫人们应远离对尘俗的追求,确立以自心对外物环境的主动性。例如佛教的“八关斋戒”就明确规定:“不着香花蔓,不香油涂身;不歌舞娼妓,不故往观听;不坐卧高广大床。”这种戒律的宗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佛教弟子们建立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态度,把对外物的追逐返归到对自心的关照,从而达到对心灵的解脱和自由。
禅宗在历史上被称为“心宗”。南宗禅就曾提出了“道由心悟”“即心即佛”的命题,而“禅”的本意即是“心”的觉悟。元代禅门高僧中峰明本说:“禅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禅之体也……然禅非学问而能也,非偶然而会也,乃于自心悟处,凡语默动静不期禅而禅矣。其不期禅而禅,正当禅时,则知自心不待显而显矣。是知禅不离心,心不离禅,惟禅与心,异名同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禅宗从把握本源——“心”这一点出发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禅宗之“心”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唐朝画家张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心源”一词出自佛学,使用最多的是禅宗(主要是南宗禅)。从美学上讲,心源和造化不能作分别解,所谓造化,不离心源;心源也不离造化。造化只是外在的色相,以心源融造化,造化则是心源的实相。造化即心源,也即实相。这样“心”即是“物”,“物”也即是“心”中之“物”。所以,它的内涵本身就有突破主客二分、发现世界意义的重要思想。在文学艺术中,这就是纯粹客观地让景物呈现自身心源,主体以心源去映照世界,表现出的是物与我冥然不分的境界。所以皮朝纲在《禅宗美学论纲》中才认为:“禅宗的审美活动乃是一种富有具足一切的圆满性、自在任运的自由性、绝妄显真的纯真性的生命活动,一种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而因此把禅宗哲学、美学的本体定位为“心性本体论”。
禅宗以“心性为空”,而“空”应是“无心”的最好注解。但前面所述,禅宗始终都是把“心”作为修行对象,也即承认了“有心”。故二者似乎产生了矛盾,而实际上在禅宗看来,佛法就是这不二之法、无二之性,就是佛性。外部世界与人内在心灵的关系,是以空对空、以净对净的关系,就是无相,就是空,不执著于有和无,是对相的超越。因此,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禅宗美学,显示出了一中不同于传统哲学“以空为美”的新思路,并对中国的美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以空为美——超越现象之美
“空”为何物?所谓“空”,梵文原文是sunya,意思是“空虚”,若以“空”为空虚,空空如也……作解释,那么,世上的一切的一切都成了虚无,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现象(“自然”)就都不存在了,还谈什么“空”?还谈什么“般若玄鉴之妙趣”呢?这显然不是大乘空宗的意思。“空”作为“有物之终极者”,必与物相关涉,它是物的“空”或物上之“空”,即与“有”相联系的“空”。“空观”仅仅把万物万象视作纯粹现象罢了。但这种“现象之有”并不是诸法的本性之有,诸法的“有”是由因缘所生的,所以它在本性上、自性上乃是“无”;诸法在本性上虽是“无”,但这种“无”又不是不存在或零,它是有之为“有”的本性,所以它又是“空”。《坛经》中是这样来叙述“空”的:
“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无嗔无喜,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恶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这里所说的“空”,根本上乃是讲“性空”,可纳万物,可生万法,故以“空”为本,万物、万法为末;此空又与人之性空为同一体,是人本然不变之性体,也即是说,作为人之本体的自然之性也为空。
由此可见,禅宗的思想基础是大乘空宗。许多大乘的重要经典如《法华经》《华严经》等等,其主要思想都是建立在“般若性空”的基础之上的。所谓“般若”,梵文为Prajna,意译“智慧”,佛教用来指如实了解和透彻参悟万物之实质、本性或真谛的智慧。慧能有自己的解释说:
“何谓般若,般若是智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心中常愚,自言我修般若,般若无形相,智慧性即是”。
般若是人的智慧的心性,也就是佛所具有的觉性,即自性,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在慧能看来,不仅是心能生万物,自性(空)也生万物,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在《坛经》中记载着著名的“风吹幡动”的公案。说慧能在广州法性寺看到两个小和尚争论,一个说风动,一个说幡动,慧能却说“仁者心动”。这本来是一个物理问题,只是一个视觉上的直观,然而在禅宗这里则是境随心转,禅者从这个直观上来了知人的精神上的变动,最终产生了“悟”。同样的这一类的直观变化被赋予了宗教“领悟”的意义。但是我们所应重视的是,宗教的意义是在借助感性的直观的方法而来的,它所牵涉到的“心”与“物”即是美学上的“心”与“境”的关系。“心”即是纯粹的直观,“境”是纯粹的现象。此一直观的心相,保留了传统经验所有的感性细节,却又不是自然的简单模写,它是心对物象的“观”,是两者刹那的统一。这样一种直观的发明,虽然后起于传统经验,但本质上却是真正的原初经验,具有美学上的重要意义。而这也正是禅宗的特殊性,它一改庄子和孔孟那自然而然的亲和关系,自然被心境化了。诸法境界只是心性的表现,那再看上述的公案无论是“风动”还是“幡动”,都仅仅是表象而已,从本质上看,是仁心在动。从仁者心动的意义来看,人心是基于它的因缘和合观,它是变动不居,是没有自性的,根本上来说就是“本来无一物”的心性空无观。禅宗强调不仅万事万物本体为空,而且一切名实概念为“空性”,因为假名是因缘生法,所以说“我说即是空”。空和假名是同一缘起法的两个方面,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的。因为是空,才有假设;因为假设,所以才空。都是当体即空,自然现象被空观孤立以后,它在时空中的具体规定性已被打破,因此主观的心可以将自然现象任意组合,形成境。那么,境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境有三种含义:一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相状,即人们当下所见的万物现象,它存在于具体时空中;二是“诸法实相”之性,是真如,为最高实在,是超越时空而存在;三是“诸法空相”之境,是诸法所具有的空性,即诸法无自之性。
《坛经》指出:“无相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
所谓相或境,是人们的知觉与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对象,是现象的世界。人在这一现象世界中存在,却往往把现象看得过于重要,而为其纠缠不休,生起许多计较与执著。所谓无相或离相,却并非要求人们离开现象界,而是于现象界中又不为其所迷,把自然一切之色仅仅看作纯粹的表相,也即佛教经常讲的把自然和人生看空。因为“色”是基于因缘的和合观,所以“无相为体”是专为破相和境而设。例如,某一片雪花的飘落没有其必然性,是偶然的,因此,它没有本质或自性。不过,若是某一位禅者对这一片偶然飘落的雪花作直观,雪花成为了顿悟的一个契机,刹那间获得了对空的觉解,那么,在此一刹那之后转换成为一个绝对之物。于是,这一片雪花在禅者的精神生命历程中占据了一个固定的位置,它不但标志着禅者的觉悟,而且还在觉悟的刹那与禅者的精神生命化而为一,成为一个“境”。并以此为基础向着宇宙万物真如本性的超越,也即是通过对现象无明的无尽烦恼的超越,而体证“于相而离相”、“无相为体”的不为物累的自由忘缘之境,最终使得习禅者主体获得更大的自由。
因此,“从境悟空”之“境”应该理解为直观中瞬间生成的现象,正因为它刹那发生、不可重复,所以它才“一切现成”、一切圆满。
由此可以看出,在禅宗这里,所谓的“本性自空”的思想不仅回复了心灵的智慧特性,而且恢复了现象世界的本来样子。它既否定了单纯肯定中对外境的执著,又否定了单纯否定中对心灵的执著,最终达到了对外境和内心的双重肯定。这种双重肯定的境界中见到的事物本身,就是事物在心灵上刹那掀起的样子,也称之为刹那真实。目的在于破除一切与普遍联系(“缘起论”)原则相违背的思想。说明事物的自性存在的一种特殊情况,人与物、事与理、无限的时间与无穷的空间,一切都在对刹那永恒这一本真之美的体验中高度融合统一,而禅悟所领悟到的也不仅是大自然的物态天趣,而是一种宇宙的哲理、“以空为美”的生命哲理。
三、结语
在美学上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禅宗思维的“空观”持的是否定主义观点,否定美存在于永恒不变的本质,即在终极意义上,禅宗之美不去竭力寻找能够使美的事物之所以美的终极根源。因为这个绝对自性的共相,也是“空”,因此直接把“空”“无”作为美的最高本质,作为美的最高意境,作为人生、人格的最高境界。禅宗美学也孕育而生,它思想的高妙之处在于用“心”提升了传统佛教意义上的“空”。既否定了单纯肯定中对外境的执著,又否定了单纯否定中对心灵的执著,最终达到了对外境和内心的双重肯定。这种在双重肯定的境界中见到的事物本身,就是放下分别执著,使万物保持原初的“如如”状态,就是人无限趋近于最为根本的原初存在,事物在心灵上刹那回归到本质与现象未分之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也就是所谓“梵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所以,禅宗空观论就使得禅宗超越一般的宗教而成为一种人生美学、生命美学。这种以纯粹现象而悟空的色,实际上就是对审美体验活动的自由性、纯真性与圆满性的高度概括,它既是一种渗透着禅学哲思的审美感性,也为后世意境理论的萌生开辟了道路。
[1]李泽厚.庄玄禅宗漫述[A].中国古代思想史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皮朝纲.禅宗美学思想的嬗变轨迹[M].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4]钟明.金刚经·坛经[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5]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张节末.禅宗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