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任侠与《中国舞蹈史话》
2013-08-04沈平子
○沈平子
1939年9月15日清晨,从重庆北温泉驶往嘉陵江北岸的民生轮停靠在牛角沱码头。从轮船走下的乘客们纷纷改乘摆渡小船,甫离岸边,忽然风浪大作,将船掀翻。乘客纷纷落水,所带物品随波四散漂流,幸亏近岸水浅,未遭灭顶之灾。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奋力将落入水中的皮包捞起,顾不得浑身尽湿,踉跄返回上清寺寓所,赶快将包中的物什掏出摊在桌子上,看着那册封面上题有《汉唐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的朱栏宣纸稿本已被江水浸淫漫漶,好在纸上工整墨书笔迹依旧,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昏然倒床。
当晚闻讯赶来探视的有两位先生:一位是著名音乐家兼篆刻家杨仲子,另一位是文字学家兼书法家胡小石。伴着一周的阴霾天气,主人公终于从惊吓余悸和受凉伤风的病症中渐渐恢复过来,将受损的文稿重新清录。三天之后,一册厚达220页的书稿经过重新装订,又复重现,插图一百余页未能列入,仅附目录而已。
事发一个月前,作者曾致函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讲述从事此项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
弟乐舞论文写成三卷二十二章,计音乐一卷,舞蹈一卷,百戏一卷,版图百余幅,大率唐以前图像及实物照片。弟重在纪元前二世纪至八世纪期间之研究。王静安氏著宋元戏曲史,重在唐以后,日友青木正儿著中国戏曲史,重在明清,弟思补写上代卷,故先撰中国原始音乐与舞蹈一稿,继成此编。惟力有未逮,且参考图籍亦缺耳。
一年之后,作者接到中英庚款董事会函告,上半年所送《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史稿》成绩评列甲等,将继续协助一年。这之后,与此相关的专题论文不断发表在学术杂志及报纸的学术专栏上,直到1945年春,一本署名常任侠著、马衡题签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略》书稿,由重庆说文社排印。在书稿清样首页上有这样一段题词:
此稿草创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时,曾受盐谷(Shihoya)教授之推荐,于上野(Uheno)帝国学士院汉学会年会中报告。二十八年后获蒙中英庚款之协助,更加改写。并承故宫博物院长马衡教授题签,说文社代为刊印。
谨献于七十七岁的慈母座前。
三十四年著者
是书稿凡上中下三编:汉唐间西域音乐之东渐;汉唐间西域舞蹈之东渐;汉唐间西域百戏之东渐。中编四节为:一、汉唐间之舞蹈;二、西北与西南诸国输入之舞蹈;三、唐代之健舞与软舞;四、唐代传入日本之乐舞。可惜的是,由于战时缺乏纸张,战后百废待兴,此类学术著作无人问津,加之作者应邀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讲学,没能如期出版,凝结着作者十年心血的研究成果就这样被尘封起来。
常任侠(1904-1996),原名家选,字季青,安徽省颍上县人。自幼喜好戏曲艺术,1922年入南京美专时,正值中国早期话剧在南京衰而未亡、现代话剧新而未兴之际,在洪深、侯曜等倡导者的影响下,开始尝试校园戏剧演出活动。192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师从戏曲大师吴梅,开始从事戏曲创作,并担任学校戏剧社团负责人,投身话剧演出活动,结识了谢寿康、余上沅、阳翰笙、马彦祥、曹禺等一批为推动中国现代话剧运动而努力的同志。他不仅参与唐槐秋、田汉等人编剧或执导的《未完成之杰作》《复活》《卢沟桥》等戏剧演出,亦为1935年在南京成立之“中国舞台协会”发起人之一。1931年,常自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毕业,受到教育系孟宪成的垂青和推荐,留任该校实验学校高中部主任。1935年春,又受导师胡光炜(小石)鼓励,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进修,先后得到原田淑人、岸边成雄、田边尚雄、盐谷节山等诸学者的协助,进一步厘清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西域交流的关系,以及中日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后研究领域逐步拓展,专力研究东方古代音乐、舞蹈及演剧史,立意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戏曲史》之后,填补原始至汉唐间中国乐舞百戏发展史。
恒念西人著述,独详欧洲,对于东方演剧舞蹈,多不具悉,此则非吾人从事努力不可。中国官私册籍,侠曩曾加研讨。自渡东瀛,对于唐代乐舞,更获观其遗舞遗曲,并集中亚印度有关方面材料,综合观察,互相推证,东方系统,渐得条贯,著为论文,送呈帝大大学院。十月卅一日,并应上野帝国学士院学术演讲会之招,公开演讲唐代乐舞之西来与东渐一题。当时大使馆及留学监督处均派代表到会,认为国人在此演讲者尚系创举也。近两月来专事参观各博物院、美术陈列馆、戏剧博物馆等,并各私家及专门家藏书藏品。上月游西京奈良,观其雕塑建筑,皆准唐制,吾盛唐文化传之东瀛不啻留一缩影也。
这是常归国前夕写给谢寿康的信。作者如是自道治学心得,从中可以体会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鲜明的民族意识。从常任侠后来的研究领域和成果来考察,这种自觉承担社会改革意识,具有学科开拓性的意义。
抗战爆发后,常任侠暂别教职,毅然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六处,与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人从事抗敌宣传活动。1939年1月,经胡光炜介绍任中英庚款董事会协助艺术考古研究员,继续从事他未竟的汉唐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的研究课题。这样的选择,是影响作者一生至关重要的时刻,在日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他的主要研究课题即在西域文化东渐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上,撰写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论著,最终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者。著名画家、美术史论家傅抱石对此评价,将“一二千年来茫无由绪之百戏问题,挈其纲领,成立相当明晰之鄞郭,在我国学术史上其可珍视”。
新中国成立前夕,常任侠应召从印度辗转香港、天津踏入北京,参加新政权的建设。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赞美新的时代,撰写发表有关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典艺术的研究著述,其中也包括运用新的观点和史料对中国舞蹈史论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曾应中国舞蹈家协会邀请作《原始社会的舞蹈》之报告。1962年9月,应几家出版机构的邀约,常任侠将有关中国舞蹈史的研究文章加以整理编辑,准备出版。一年之后,完成《中国舞蹈史话》初稿。在每一时代,又选择较有代表性的舞蹈,专文叙述,着重在民间的舞艺发展。书稿成而时局变,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袭扰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版复又搁浅。
“文革”中,常任侠随中央美术学院下放河北农村接受锻炼,荷锄陇亩,未忘著述,尤为对旧著《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略》不能释怀,考虑到当初是用文言撰写,不适于当今读者,且有关丝路的出土文物新材料陆续发现,修订着不少几十年前国际上所公布的材料和论点,因此改易旧稿,重新撰写。于是,在“日行五十里,夜写一千言”的境况下,昏灯草舍,走笔夜书,凭借着对学术追求的信念和顽强毅力,终于完成《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一书,并于1981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较之初稿,书中充分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融入多年来所获得的从事中外艺术交流史研究所必需的实地(田野)考察知识,领悟文献材料所呈现出的特殊价值,以历史学家特有的严谨态度和敏锐的思辨力,借助流畅典雅之文笔,为学术界贡献出一份珍贵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化交流史的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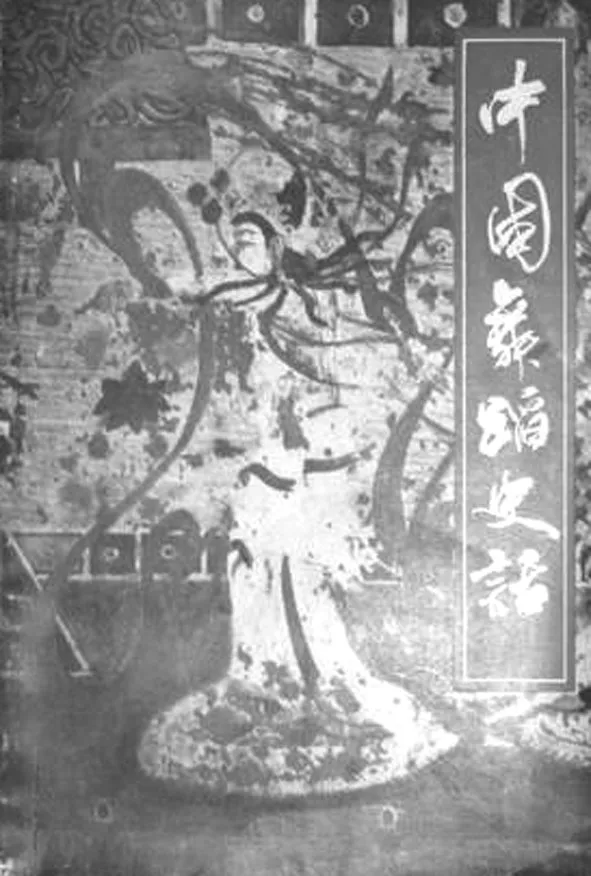
《中国舞蹈史话》,常任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与此同时,有关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的新篇章也伴之而生:《舞蹈》1978年第3期发表《从彩陶盆上的原始乐舞谈起》,《南亚研究》1979年1辑发表《北朝的拨头舞探源》。1983年10月,常任侠编著《中国舞蹈史话》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4篇文章相对独立又成系统,从原始古代到近代,每一时代专文重点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着重民间的舞蹈艺术的发展,究源竟委,据实求证。作者在《前言》指明写作动机在于:“中国舞蹈的历史颇为悠久,但过去尚无专书,加以系统的叙述。承研究此艺的同志督促,勉励写此短册,筚路蓝缕,未免荒疏。希望抛砖引玉,能有更好的此类著作出现,以补我的缺失。”其中也谈到了该书与《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略》之间的关系。至于这本书着重论述在民间的舞艺发展,而忽略宫廷创作的郊祀宴飨诸乐舞,认为“以其徒备封建统治者的歌功颂德,耀武扬威,多略而不录”。显然有着作者一贯主张的“乡土的也是最有世界价值的”以及“人民创造历史”的主观认知,也是成书时代的真实写照。
常任侠终身以“待人宜宽,律己宜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为座右铭,性格正直耿介,温和朴质,淡泊名利,笔耕不辍,其成果出版有《民俗艺术考古论集》《中国古典艺术》《中印艺术姻缘》《东方艺术丛谈》《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常任侠文集》等。从最初研究戏曲艺术到《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一书的出版,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从《中国舞蹈史话》最初成稿的1963年到最后出版的1983年来算,其间整整经过了20年;这样的呕心沥血之结晶,足以堪称是作者乃至学术界的拓荒之作、扛鼎之作。这本书最初的写作动机,作者曾在1962年8月26日的日记中有所披露:“近日需要知识性小文,为青年补充常识。但凡有益,便非浪费笔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常任侠《秦汉时代的舞蹈》一文。如此看来,早在50年前,作者就有意自觉承担着文化普及性的社会责任,八十忘其老,在《生日述怀》七律有言:“著述岂为升斗计,育才翻忘鬓毛苍。无功报国空伏枥,欲藉鲁戈挥夕阳。”真可谓忘身报国,志在千里。直到1984年间,《百科知识》还在连载他的《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研究散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称得上是部名符其实的“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了。
